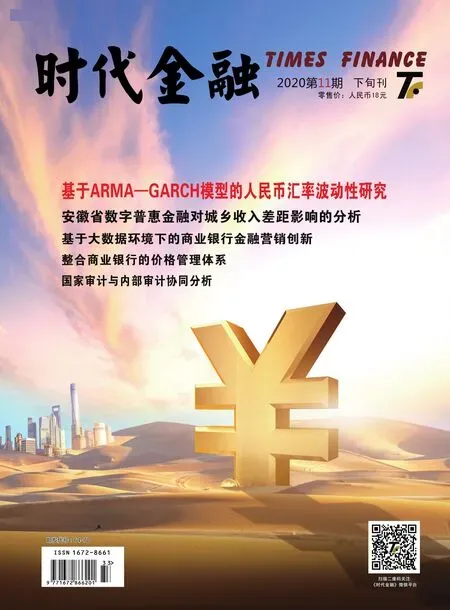對整合連片貧困區扶貧資金使用效益的思考
羅本彪
昭通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截至2016年末,還有貧困鄉鎮90個、貧困村825個、貧困人口111.95萬,居全省第1位;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態環境脆弱、基礎設施落后、產業發展滯后、教育資源匱乏的地區,資源型貧困特征明顯,素質型貧困較為普遍,災害型貧困比較突出,呈現綜合性貧困特點。在全市扶貧攻堅的大會戰中,資金來源方面存在國家財政投入、金融撬動、企業幫扶等渠道,但是在整合資金,提高使用效益方面仍然面臨很多困難。
一、昭通市財政金融協同推進區域扶貧攻堅的主要做法
十二五期間,全市投入專項扶貧資金達23.52億元,比“十一五”增加14.09億元;全市深入推進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實施,累計完成投資862.7億元。全市共解決和鞏固了61.13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貧困發生率從37.5%下降到25.71%。
(一)財政多方爭取籌集資金,確保扶貧資金投入
一是爭取上級加大財政扶貧資金轉移支付力度和專項補助力度,2015年以來,累計向上級財政申請下達財政專項扶貧資金34.95億元。二是在安排新增政府債券資金時,全力保障脫貧攻堅和民生工程,2015年以來累計安排脫貧攻堅政府債券28.2億元。三是做好優惠金融產品財政貼息工作。按照中央承擔70%、省級承擔23%、縣級承擔7%的比例承擔,對貧困地區符合條件的個人創業擔保貸款,財政部門給予全額貼息,2015年至2017年8月創業擔保貸款貼息資金共計3.07億元,其中中央2.42億元、省級0.58億元、縣級0.07億元。四是加大政策性農業保險補助力度,保障農民增收。將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補助納入財政預算安排,2015年至2017年8月累計補助政策性農業保險資金6996.38萬元,其中中央3969.54萬元、省級1961.76萬元、市級746.18萬元、縣級318.9萬元。
(二)做大扶貧投資主體。撬動放大扶貧資金
扶貧部門積極創新融資模式,依托市級相關平臺公司和各縣區平臺公司、扶貧投資公司等融資主體,通過基金融資等途徑進行籌資,最大效應撬動放大扶貧資金來源。截止2017年6月末,全市扶貧投融資主體共41家扶貧投融資債務總余額233.11億元,融資來源主要是國開行、農發行貸款、專項建設基金和浦發銀行扶貧投資發展基金,用途主要是易地扶貧搬遷、貧困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其中用于精準扶貧債務余額82.54億元,占總余額的35.4%;用于其他扶貧項目債務余額149.98億元,占總余額的64.3%。
(三)金融部門細化精準支持措施,促進金融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
一是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圍繞實施《昭通市精準扶貧規劃(2011~2020)》,推動建立了由人民銀行牽頭的昭通市金融扶貧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構建了政府主導、財政扶持、金融精準支持扶貧工作的總體框架,促進了金融機構與貧困地區特色產業、扶貧項目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需求的精準對接。二是細化政策支持措施,加大精準支持力度。綜合運用定向降準、宏觀審慎政策、扶貧再貸款、支農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引導低成本資金投入扶貧開發,調動金融機構參與扶貧的積極性,扶貧再貸款實現貧困縣(區)全覆蓋。截止9月末,扶貧再貸款余額10.52億元,支農再貸款余額8100萬元,貧困縣(區)各項貸款余額645.49億元,比年初增加56.82億元,增長9.65%,高于全市各項貸款增速1.5個百分點。三是創新金融產品,豐富群眾選擇。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發放專項貸款,資金實行專戶、轉賬、專人管理和封閉運行,在全市創建60個“扶貧再貸款扶貧小額信用貸款”示范基地,在魯甸縣創建8個“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示范基地。推動銀行業金融機構創新推出“企業+農戶”、“專業合作社+農戶”、“企業+基地+農戶”等特色鮮明、貼近“三農”信貸產品。9月末,全市納入監測的24種創新型農村金融信貸產品余額為142.82億元,支持企業574家,涉及農戶數為27.5萬戶。全市貧困縣(區)精準扶貧貸款余額105.47億元,1至9月累計發放25.67億元。其中,項目精準扶貧貸款余額79.06億元(含易地扶貧搬遷貸款余額30.07億元),個人精準扶貧貸款余額13.26億元,實現有貸款需求的貧困戶貸款滿足率達70%以上,產業精準扶貧貸款余額13.14億元。
二、存在問題
(一)風險補償機制與項目需求不匹配,精準扶貧項目落地難
一是地方整體經濟體量限制,導致部分扶貧項目貸前條件難以有效落實。轄內只有市本級和昭陽區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達到10億元,財力相對較好外,其他各縣區財力均較弱,加之大部分申報項目貸款金額均較大,導致部分縣區在項目保證擔保措施落實方面難以落實,如:每年組織召開的項目推進會上都有150億元以上的項目投放需求,但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項目真正實現有效投放的只占項目信貸需求的20%左右,需求與投放嚴重不匹配。二是儲備項目的成熟度參差不齊,影響了項目申報進度。項目的最終實現無縫對接與承貸主體、政府規劃和相關部門報批等綜合因素息息相關,許多儲備項目僅有融資意向,承貸主體無法按銀行機構貸款要求提供項目所需完整的報批資料,導致項目調查評估難以跟進。
(二)扶貧讓利與資金來源不匹配,地方性財政資源配套支持力度不足
扶貧信貸資金貸款利率都是執行基準利率和優惠利率,對易地扶貧搬遷貸款更是在基準利率基礎上優惠10-20%,經營管理成本擠壓利潤空間。如:農發行資金來源主要是向總行借款,經營資金籌措手段相對單一,籌資成本相對較高,各項存款總額較低,近十年來存貸比一直都在200%以上,扶貧貸款在執行優惠利率后基本沒有獲利空間。又如:村鎮銀行被定位為區域商業性金融機構,按照財政部關于預算單位開戶的管理規定,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無承接財政預算單位開戶的資格。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地方法人金融機構面臨吸儲成本較高,降低了金融機構承擔扶貧社會責任的動力。
(三)資金整合效率低,信貸資金杠桿作用發揮不充分
扶貧資金來源渠道較多,對部分上級統貸到位的資金,由于各承貸主體和有關部門未按照相關資金使用要求及時落實和完善相關手續,導致撥付使用率較低。甚至出現上級統貸下劃各縣區的中央財政貼息專項貸款和前期下劃的各類資金的支持對象與前期信貸資金已支付的對象存在重疊的情況。如總額為200億元的昭通浦發扶貧基金,全部投向列入昭通市扶貧項目清單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改善農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就業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社會事業發展與公共服務、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投放項目107個,部分項目爭取到上級專項資金后,由于基金不允許提前償還,同時上級項目專項資金又不得用于其他項目支出,造成資金積壓。2016年,全市財政涉農資金統籌整合率僅為71.2%。
(四)財力薄弱與需求巨大的矛盾突出
昭通貧困人口占全省貧困人口近四分之一,而得到省級以上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不到全省的十分之一,需求與供給差距很大,2011年以來,總計獲得省級以上財政扶貧專項資金23.52億元,年均僅4.7億元,貧困人口年人均投入僅300余元,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全市財政對上級的依賴程度高,財政收支矛盾尖銳。2017年,僅水利項目建設需市級配套資金1.4億元,實施農村危房改造項目市、縣兩級財政就需安排資金8.4億元,地方高速公路建設需配套資金21.6億元。
(五)償債負擔重。財政風險加大
截止2017年4月30日,全市政府性債務外融資371.1億元,其中扶貧融資233.11億元。加上全市政府性債務余額308.7億元,未來10年每年需償還投融資及政府債務本息超過80億元,其中:每年扶貧投融資還本付息約25億元。由于這些融資地方政府大多投向沒有任何收益來源的公益性項目,政府具有實質支出責任,同時又不能納入政府債務系統進行管理,在當前的融資形勢和背景下,一旦融資不能繼續,資金鏈斷裂,不僅項目建設將受影響,潛在的財政風險不容忽視。
三、建議
(一)強化跨部門的扶貧政策聯動,凝聚扶貧合力
扶貧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需要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產業政策、扶貧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有機協調配合,深度互動,才能真正受惠于貧困戶。一是建立風險補償、財政補貼、貸款貼息、稅費減免及扶貧激勵政策機制。二是整合分散的財政涉農資金建立扶貧開發專項基金,引導金融扶貧對接項目,深入挖掘不同層次的“三農”金融需求,三是以產業開發為主導,著力培育農業農頭企業、專業化合作組織,遵循市場規律,積極參與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精準扶貧聯動工作。
(二)完善扶貧信貸風險補償與分擔多元化平衡機制
一是健全與完善擔保制度,推動農村信貸抵押源多元化。建議政府出臺專門針對“三權”抵押貸款(農村住房、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抵押的價值評估和流轉的管理辦法,引入相對獨立的第三方對“三權”抵押價值進行評估,明確“三權”流轉及抵押處量的有關規定,建立“三權”產生爭議的仲裁機制,消除金融機構的法律風險顧慮。二是建立金融精準扶貧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建議由省、市、縣財政按比例出資建立扶貧貸款風險補償金,專項用于建檔立卡貧困戶種、養殖貸款損失補償。對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扶貧貸款發生損失時,由風險補償金代為清償,基金不足清償的,由財政審核后彌補對因其他因素造成的經追償無法歸還的建擋立卡貧困戶貸款損失,由風險補償金與合作金融機構按8:2共同承擔。
(三)建立與精準扶貧相適應的政績考評機制
政府要對精準扶貧立項的項目建立終生責任追究機制,對扶貧項目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審計考核評價,防止資金“趴窩沉睡”和項目效益不及預期等情況,真正發揮金融精準扶貧的“造血”功能。
(四)積極探索新的融資模式
為扶貧項目提供多渠道融資方案加快扶貧項目在全市PPP項目論證包裝入庫進度,采取PPP模式開展融資,解決好在建項目后續融資的問題。
(五)加大貧困地區轉移支付補助力度
為確保貧困地區與全國一道如期脫貧,建議在測算均衡性、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民族地區、革命老命區等財力性轉移支付及扶貧專項轉移支付補助資金時,將貧困人口作為資金分配的主要因素,進一步給予貧困地區大力傾斜和支持。同時,對國家、省級在貧困地區安排的公益性建設項目,不再要求市、縣級配套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