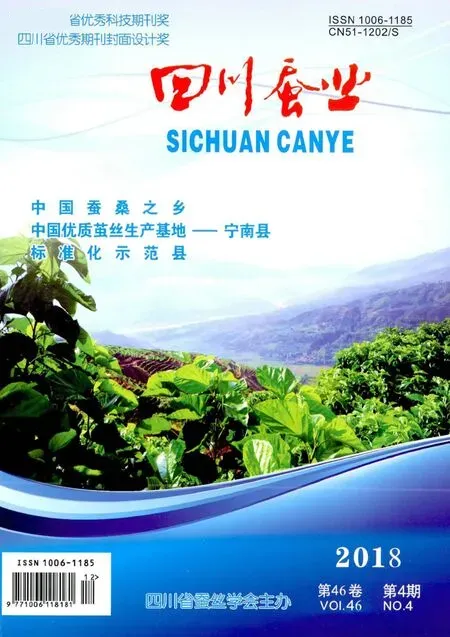淺析漢簡中的廣漢郡織品
肖佳憶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 北碚 400700)
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在大夏見到據說“得蜀賈人市”的“蜀布邛竹杖”,獲知巴蜀有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上世紀初以來,歷史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黑城附近和甘肅省金塔縣的金關附近,即漢代的張掖郡居延縣地發現和發掘出土了漢代本簡共三萬余枚,這批漢簡被稱為居延漢簡。后來,又陸續在甘肅西部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關塞遺址中發掘出九批漢簡共兩萬余枚,稱為敦煌漢簡。其中關于“廣漢八稯布”的記錄,為我們研究漢代蜀地紡織手工業的發展狀況提供了重要史料。
1 漢代簡牘中的廣漢麻布
《居延漢簡釋文》[1]卷三第二頁記:
出廣漢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給吏秩 百(石)一人元鳳三年正月盡六月積六月□ (居 90.56, 303.30)
元鳳是漢昭帝的第二個年號,元鳳三年指公元前78年。
稯,是布的粗細計量單位。《說文解字》卷七上云:“布之八十縷為稯。”《史記》卷十一《孝景本紀》、《正義》和《漢書》卷九九《王莽傳》中注皆引孟康曰:“稯,八十縷也。”故布有七稯、八稯、九稯、十稯之別,八稯布即布之一種。漢代布帛一匹當四丈或四十尺,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內以八十根經為幅的稱八稯布。從價格上來看八稯布應該是漢代最便宜的布料之一了。
據漢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為“徒隸”等勞作者提供的服裝,“布皆八稯、七稯”。漢景帝時制度,“令徒隸衣七緵布”。漢代邊防士卒的軍裝也以“七稯布”、“八稯布”制作。居延漢簡資料可見,“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數量甚大。
居延簡牘中所提到的“廣漢”,是秦滅巴蜀設巴郡和蜀郡之后,西漢王朝在四川新增的第三個郡。《水經注·江水》云:漢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于乘鄉[2]”。《漢書地理志》注:治繩鄉。領縣十三,即梓潼、什邡、涪(今綿陽)、雒(今廣漢)、綿竹(今羅江黃許鎮)、葭萌(今廣元昭化鎮)、郪(今三臺郪江鎮)、新都、剛氐道(今平武)、白水(今青川白水鎮)、甸氐道(今九寨溝縣)、陰平道(今甘肅文縣)。
《漢書》卷七二《貢禹傳》載:元帝時,“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漢書·地理志》第八之十三載:“廣漢郡”,“莽曰就都,屬益州,有工官。”工官乃掌管國家重要經濟企業之官,西漢全國僅有9郡配有此官。廣漢郡工官在滿足上層社會高端奢侈“金銀器”“漆器物”用器的需求的同時,生產的“廣漢八繌布”已經形成中低端大眾消費品牌。
2 廣漢郡蜀布物美價廉
漢代沒有棉花及棉織品,麻和絲織品有廣泛的用途[14]。《鹽鐵論·本議》提到,“齊陶之縑,蜀漢之布。”左思《蜀都賦》兩次提到“黃潤(一種細麻布的名稱)比筒”、“布有橦華。”經濟學家李劍農說:“中國固有之服裝原料,以絲麻為主。普通絲織物為絹帛、麻織物為布。蜀在西漢似惟以麻織之布著稱[3]。”麻是草本植物,種類很多,有“大麻”、“苧麻”、“苘麻”、“亞麻”等,莖皮纖維通稱“麻”,可制繩索、織布。
一九八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原漢代廣漢郡涪縣邊堆山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陶器紡輪11件,可分三型,A型似鼓,兩頭小中間大。B型束腰,中間小兩頭大。C型似圓柱形[4]。”經鑒定,邊堆山遺址距今年代約為4500——5000年。廣漢三星堆考古發現了“數量種類為最多”的石紡輪和陶紡輪,揭開了古蜀文化神秘的面紗。考古工作者發現有些紡輪之類的生活工具就是從石璧中間取下來的石芯加工而成的,可謂物盡其用。陳立基介紹:三星堆出土的陶紡輪,有圓餅形和梯形兩種。圓餅形的直徑一般在3-6厘米之間,厚約1.5厘米,中間有一小孔,古人在那孔中垂直插上一根木棍,擰轉木棍,利用紡輪的重量和轉動的慣性,紡出一根根絲線來。梯形陶紡輪下大上小,以優質的黑陶為主,體型較小,直徑一般在2-3厘米,中間穿孔,制作較為精細一些。古蜀人用這陶紡輪將絲、麻和動物的毛紡成線,然后再編織成絲綢和細麻布[5]。考古專家鑒定說,這種石紡輪、陶紡輪距今至少4500年以上。由此可以推斷,當時廣漢郡是植麻、紡織的集中產區,不僅適宜種植桑麻,而且紡織也是一種普遍的行為。
漢代絲織業生產機構有蠶室、織室、服官三種類型。漢代絲織業的生產有官營和私營兩種形式,官營絲織業大多采用手工藝作坊進行生產,規模比較大。《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李雄說,蜀地的“女工之業,覆衣天下”。私營絲織業主要由私人進行作坊式或家庭式管理,廣漢郡生產比較普遍。《后漢書·列女傳》記,廣漢姜詩妻者,“晝夜紡績”,“常作冬夏衣”。《漢書·食貨志》記載:“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兩漢時期廣漢郡的婦女是勤勞的,也是辛苦的。不僅冬天的農閑時節,她們不得休閑,因為此時是她們紡織的最佳時節。而且夜晚她們也不得休閑,因為這樣可以延長勞動時間,將一月變成一個半月使用。
據《九章算術》所記:一個學習紡織的女工,第一日織寸余,第二日織三寸余,第三日織六寸余,第四日織一尺二寸,第五日織二尺五寸余。以最后一日的生產水平計算,約十六日方成一匹。然從理麻、紡紗到成布需要時間,又婦女平時需要承擔炊事、縫補、洗漿等家務勞動。今就低額估計,假若按一個熟練婦女每日織布二尺,年織二百日,則可成布四百尺。當時一匹布帛的規格是長四丈,寬二尺二寸。四百尺布是為十匹。當時的布價,因質量不同而高低不一。據《居延漢簡》:粗布價格,有二百、三百或四百錢一匹者,也有五百、七百錢一匹者,然一般多在三百至四百錢之間[6],若以四百錢一匹布計算,則十匹布,折錢四千錢.這可以說是終歲家庭紡織的收入。
漢簡中所見布帛價格,涉及布、帛、縑、素、練等幾種。布為麻織品,是漢人衣著原料之貧賤人所服,價格相對較低。
(1)《居延漢簡甲編》[7]第547簡:
出廣漢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六(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居》90·56,303·30)
漢代布帛一匹當四丈或四十尺,折合匹價為二百二十六錢余。
(2)《居延漢簡釋文》卷三第76頁說:
八稯布八匹,直二百卅。
這里應是指的匹價二百卅。或者“匹”下有重文,由于磨損脫去,由于未見原簡,不敢臆測。
(3)《居延漢簡甲編》第1656簡:
戌卒魏郡貝丘功里楊通,貲買八稯布八匹,匹直二百卅,并直千八百冊。
(4)《居延漢簡甲編》第2426簡[1](《居》285·5):
驚虜隧卒東郡臨邑高平里召勝字游翁,貰賣九稯曲布三匹,匹千三百卅三,凡直千。匹布應為三百三十三錢余。
(5)以皂布八尺直百廿八錢尺十六錢[8]。(《敦》2324A)
(6)人布一匹直四百。(《居》308·7)
(7)《胡中文布計》載:“尹圣卿二匹直六百,孫贛二匹直六百 孫贛二匹直六百 張游卿二匹直六百(《居新》E·P·T56:72A)
(8)《新簡》EPT56:10云:“戍卒東郡聊成昌國里 何齊貰賣七稯布三匹,直千五十
西北邊疆部隊士兵的衣著供給標準,現在尚不明確。從居延漢簡的有關記載衣著的最低價格計算,西漢時一個士兵一年的衣著費用約為一千七百錢。
(9)單衣價:七月十日鄣卒張中功貰買皁布章單衣一領,直三百五十。(《居》262·29)
(10)袍價:第卅四燧卒呂護買布復袍一領直四百。(《居》49·10)
(11)绔價:绔即褲子。□□隧長董福□□绔直五百。(《居》257·17)
第卅卒鄧耐賣皁復绔一兩,直七百(《新簡》EPT57:56)
(12)枲履價:枲履是用麻織成的鞋子。《流沙墜簡》卷二《屯戍叢殘考釋·器物類》簡五十四:
兵曹書佐蓬卿用枲一斤,直十。
戍所將戍田卒還有出售官袍衣服的詳細登記在案的記載,在漢簡中極為常見:
卒居署貰賣官物薄(《居》271:15A)
甘露三年二月卒貰賣名籍(《居新》E·P·T56:263)
第十七部甘露四年卒行道貰賣名籍(《居新》E·P·T3:2)
□□年戍卒貰賣衣財物名籍(《居新》E·P·T3:2)
毋得貰賣衣財物太守不遣都吏循行□嚴教受卒官長吏各封藏□(《居》213.15)
二月戊寅張掖太守福庫丞承熹行丞事敢告張掖農都尉護田校尉府卒人謂縣律曰藏他物非錢者以十月平賈計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貪利貴賈貰予貧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時驗問(《居》4.1)
通過上述列舉可以看出,官政府雖然屢令禁止戍田卒出售“廣漢八稯布”等官袍衣服,實際上是有令難行[9]。這也說明了邊疆的軍餉主要以實物方式發放,但官兵對現金的需求仍大,所以在當地市場交易。這也是漢代“錢帛并用”現象的一個旁證。
3 廣漢郡是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廣漢郡位于石牛道(金牛道)上,是關中、漢中通往巴蜀地區的重要蜀道,官私商旅來往頻繁。根據簡牘記載,廣漢郡布和車、藥材等都是在河西廣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據以上簡牘中有關蜀地物品的內容,可以肯定這些物品有蜀地生產的。由廣漢郡往河西作為重要軍需物資的“廣漢八稯布”等紡織品的運輸路線,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別支。敦煌馬圈灣漢簡記:
官屬數十人持校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 (敦981)
五十名驅驢士從蜀地驅趕五百頭驢到敦煌,說明了西北邊疆部隊需要定期從廣漢郡等蜀地采購大量物資。簡文“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所透露的軍運形式可能具有保密性質的特點,或許與這條交通線路附近“羌”、“虜”、“夷”分布的復雜形勢有關[10]。
敦煌懸泉漢簡中有一條簡牘明確記載具體走向,廣漢郡到漢中,再溯西漢水而上到天水。漢代已開辟河西經天水到河西長安的驛道: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東南。東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Ⅴ1611③:39 65 61)[11]
廣漢郡蜀布不僅遠銷邊郡,如敦煌、居延等地,而且還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2]。
張騫“鑿空”西域,開通北方絲綢之路。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記,“西北國始通于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后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明代蜀人學者楊慎《丹鉛總錄》卷一四《訂訛類》“空有四音”認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空”的讀音都應當是“孔”。蜀布經北方絲綢之路,過秦嶺轉西安遠銷西域和中亞西亞至地中海沿岸歐洲各國。
開拓便捷的南方絲綢之路(即滇緬道)。班固《漢書·張騫傳》記,“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就是古印度,這段材料說明早在西漢時期,蜀布就銷往了南亞地區。這也說明,在西漢建元三年(前138)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南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打通。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何志國認為,從漢武帝經營西南夷開始,到東漢初哀牢夷內附漢朝止,這一時期,是滇緬道開拓、開通的漫長過程,其間經歷了兩百年。東漢中期,以撣王遣使進貢漢廷為標志,表明了滇緬官道的正式開通[13]。
結語 通過對漢簡的初步考釋和考古、文獻的印證,我們發現漢代廣漢郡的麻紡織業已經相當發達,“廣漢八稯布”等滿足社會中下層大眾消費需求的低等級織品,價廉物美暢銷海內外,形成了蜀地優勢紡織產品品牌。“廣漢八稯布”的簡文,絲綢之路史研究者應當予以重要關注,對于南方絲路交通開拓相關考察也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