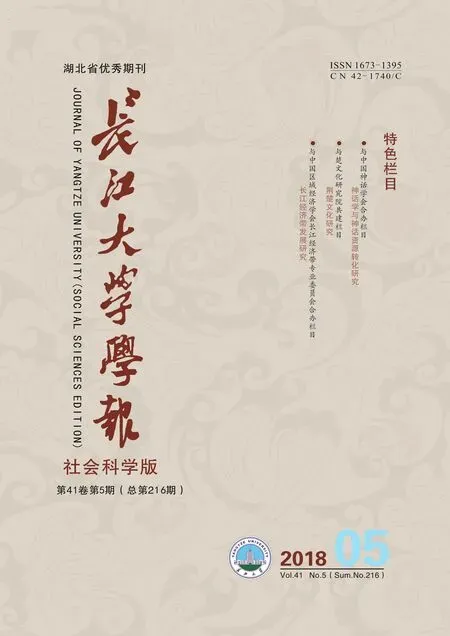王柏心與湘籍名臣往來書札考略
謝葵
(荊州市社科聯 學術部,湖北 荊州 434000)
王柏心(1799-1873)字子壽,又字冬壽、堅木、筠亭,號螺洲、薖叟,湖北監利螺山(今屬洪湖市)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進士,授候補刑部主事,旋辭官歸里,專事講學著述,著有《百柱堂全集》51卷(以下簡稱《全集》)。其成就不限于詩文,更兼軍事、水利、方志、書畫等。“柏心自負有經世之略,而當時群以詩人目之,所為詩亦獨富。”[1](P469)“蓋柏心之學以致用為歸,所著書如《樞言》上下卷,尤究極古今治體,非拘墟之士所能為。”[1](P469)《全集》及多部地方志便成了他留給后世的寶貴精神財富,“尤其可以說是填補了鴉片戰爭前后湖北思想界的空白”[2](P203)。
王柏心與當時的名流賢達、同僚好友多有信函往來,其中不乏很高史料價值和書法價值的珍品。因他僻處湖鄉,時乖命蹇,歷經劫難,這些往來信函散失甚巨,《百柱堂全集》搜輯不全。筆者多年來從大量清人別集、《昭代名人尺牘》《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清代名人翰墨》等書中鉤沉輯遺,搜集、整理王柏心佚文數篇及朋僚書札共140余通,其中《防海輯要·序》《與姚椿論章草》等文及半數手札《百柱堂全集》均失收。迄今已知與王柏心函札往來者計四十余人,以籍貫而言,南及兩廣,北至直隸,東達江浙,西至川黔。以身份而論,大多為名臣碩儒,也不乏草野平民、畸人逸士。書札涉及內容極其廣泛,舉凡軍國大事、社會經濟、學術文化、治水賑災、民情風俗幾乎無所不有,許多資料可補正史之不足,特別是咸同時期安內攘外的資料,對于研究晚清社會歷史,很有參考價值。
湖南湖北一衣帶水,與王柏心交游密切者首推湘籍名人,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燾、李星沅、吳大廷、周壽昌、楊彝珍、吳敏樹、孫鼎臣等與王柏心都有書信往來。王柏心書札中尤以與湘籍名臣的數量居多,很多尚未公開披露。這些書札涉及面廣,信息量大,內容豐富,與太平天國的戰事也是主要內容之一,“每諮軍事,知無不言,多見采用”[3](P1444),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因此,筆者擇其與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燾、郭崑燾、李星沅、李桓等部分湘籍友人往來書札略加考釋,以便為研究王柏心思想和晚清政局、社會等提供第一手資料。
一、與曾國藩往來書札
王柏心與比他小三歲的曾國藩是在北京會試時認識的。1845年,王柏心辭官歸里,曾國藩作《送王子壽歸荊州五首》。曾氏答王柏心書存二通,王氏上曾國藩書存三通。《全集》中有《上曾滌生侍郎書》,作于咸豐五年乙卯(1855)四月,略云:
我據長江,已扼其吭。賊不敢遠掠糧食,又寡舟楫,將陰有遁志。若群帥用命,水陸速攻,克復如反掌耳!然營壘相望,無所統率,未聞有決策深入者也。麾下能少割兵力,擇一有勇略之將,由陸路取鄂,或從潭州上游浮舟而下,會楚北諸將,廓清江漢,必易于拉朽。長江中流,關系餫道腹心根本,分援似不可緩,麾下明于算略,計當有以處此。[3](P1092)
此信附上《兵勢臆議》五則,曾氏當有答書,惜已佚。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復王柏心一書,如老友談心,直抒胸臆,且提及天津教案,足資考證。
三月間增發疝氣,起居不便,入夏甫就全愈。目光昏蒙如故,近又兩腳浮腫,衰態畢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曷勝兢兢。
中秋以前尚擬出省一行,補行大閱。先赴淮、徐,次至蘇、滬,大約十月內方可竣事。雖無搜乘補卒之實,亦聊循行舊典,稍壯觀瞻耳。
客歲津門之事諸多棘手,以致辦理過柔,為清議所不韙。神明內疚,至今耿耿。乃來示無鹽,曲加原諒,或者愛而忘其丑,為此過情之譽耶?昔歲謬竊虛聲,自省羌無故實,瓦缶雷鳴,終當隕越。今僅一事見譏于時,猶為至幸。然自此彌悚懼知勉矣。[4](P602)
《全集》收錄王柏心上曾國藩第二書,但受信人誤為胡林翼。此信亦載《曾國藩未刊信稿》,且照錄了曾氏在原信上的批語,結尾署“咸豐庚申(1860)新正四日”,[4](P313)足證受信人為曾國藩。但《曾國藩未刊信稿》刪除了“季高被鑠金之毀”一段近三百字,今迻錄于下:
季高被鑠金之毀,大抵功高為人所忌,又其負性剛偏,疾惡太甚,故罹此多口也,揣季高意,游聲雜沓,所不樂聞,必浩然有還山之志。則湘東軍事,誰與主持?且此才其可以山中老者,麾下盍請之于朝,延至軍中,專任兵謀,他人不能用季高,季高亦不樂為他人用。若為麾下贊畫軍事,必欣欣然展盡智能,相與戮力戡除,以遂其滅賊之本懷。俟大功克濟,然后長揖歸田,不受爵賞,與少伯、留侯同其高蹈,豈非載美談乎?為季高代籌出處,莫如此策為當,且無令泉石中淹此奇才也。麾下夙重季高者,當有以處之。[1](P1133)
“季高被鑠金之毀”,指湖廣總督官文、永州鎮總兵樊燮同湖南布政使文格聯合彈劾左宗棠之事。1864年6月南京城破之后曾左交惡。曾氏刊印信稿時刪除此段,大概因為其中“季高亦不樂為他人用”礙眼,而“若為麾下贊畫軍事,必欣欣然展盡智能,相與戮力戡除,以遂其滅賊之本懷”也是王柏心一廂情愿的揣測。
王柏心上曾國藩第三書為同治五年(1866)元宵節后所作,通報“今年燈節后曾為宮保左公邀赴漢皋行營,從容話舊,留半月即歸。”[5](P313)
曾國藩病逝后,王柏心作《侯相湘鄉公挽詞》六首。曾氏安葬后,其弟國荃致函王柏心,詳告安葬經過,并說“閣下夙與先兄為道義文字之交,關愛倍逾尋常”。[5](P514)《全集》卷二十六有《奉送沅甫宮保謝病還湘鄉》,可見王柏心與曾國荃交往亦多。
二、與胡林翼往來書札
王柏心與胡林翼往來書札今存16通。胡林翼在湖北巡撫任上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政治、人事方面的措施,對湖北財政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頓,使湖北成為湘軍最穩定、最可靠的戰略后方,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王柏心為胡林翼出謀劃策,對湖北丁、漕、鹽、厘等稅項進行整頓,使地方財政扭虧為盈,在胡林翼及湘軍成功鎮壓太平天國的進程里起到重要作用。
咸豐五年(1855),胡林翼書招王柏心入幕府,稱他“忠藎有加,隃度兵事,如壯侯指類羌情,又如馬忠成聚米言形勢”“欲引與共商籌策”。[5](P515)王柏心復函稱:
頃奉手瀚,詳示近事,并垂獎借,且以楚事孔棘,不遣鄙陋,欲引與共商籌策,開寫款誠,抑損貴勢,至有北面請師之語。嗟乎!麾下勛略如此,位望如此,而折節若是,使豪杰之士,進當為墨翟、魯連,重繭飛書,展其智計,共濟艱危;退當為田光、侯贏,感激刎頸,以報高義。惜乎柏心非其人也,受性孱懦,未習軍旅,老謀壯事,兩無一長。承命裹足,非敢盤桓。自度無運籌決勝之才,仰慚盛意,莫副渴懷。且小人有母,年屆八旬,此時未能以身許麾下,度蒙垂亮,不之強也。謹納辟書,幸邀寬宥。惟是伏處江皋,使于軍事稍有臆說,皆兵家常言無奇異者。麾下智略絕人,又在兵間久,書生遙度,豈能有助高深哉!特感麾下延跂之誠,身不能赴,無以仰酬,懷此區區,愿獻愚悰,謹錄出奉呈,惟賜財擇。此后江上續有所見,凡愚慮能及者,必削牘奉聞。倘有裨萬一,亦不啻藉手以報也。柏心相識中,知兵無過季高者,又膽決可仗,盍手書招之乎?其才勝柏心十倍也。[3](P1094)
此札婉辭聘請,但將他撰寫的剿匪方略“錄出奉呈”,并力薦左宗棠。
是年秋,胡林翼遭遇奓山之敗,九月十五日,王柏心寫信去安慰他說“兵家勝負何足為名將累哉”,以古代名將也有失利為例,勉勵他“減兵省將,明罰思過,布所失于境內,校變通之計于將來。”[3](P1103)
咸豐六年(1856),太平天國西征軍在江西連破八府五十余州縣,曾國藩坐困南昌。曾國華赴武昌湖北巡撫胡林翼處求援,欲調李續賓部馳援。但湖北形勢也不妙,王柏心又力陳李續賓“留楚為兩得,去楚為兩失”,胡林翼最后還是分兵5000人援之。[3](P1105)
四月八日,他致函分析敵我形勢,指出清軍處處被動的原因在于“兩城之賊,首尾環應,如率然之勢,而我畫江分地,不能引北軍以濟南軍,譬如左右手足,無故自為拘攣”,建議胡林翼“緘商制府,反復開譬,勸以分師助圍鄂城”“縱有明旨責令分剿,然兵家機宜,貴權道以濟事,不貴拘牽以遺誤也”。[3](P1106)
六月三日,上書胡林翼提出夜襲草埠門計策:
賊之窮困,外形昭然,然不降不走,豈城內尚有積糧耶?偽眾多寡,此間無真耗,難以懸揣。竊聞賊起草埠門,出入自如。以我軍悉屯南路,故不防北面,此可乘之隙也。凡臨江各門,地勢迫狹非戰地,攻之不便。鄙意謂可盛兵鼓噪,見形于南路,以分賊勢,而潛師銜枚于草埠門左右。彼處稍東有鳳凰山,城趾跨其麓,可梯而上,約于五鼓時,或日晡后,偵其無備,一面攀堞,一面奪門。但一處得手,賊即驚潰,不暇拒我矣。以老成之見論之,賊窮不待攻,攻之徒損士卒。但相持太久,恐江右敗賊,倏忽闌入,令彼頓增氣勢,而我又有腹背受敵之患。且賊固乏糧,我亦乏餉,殆略相當。所恃者,賊衰而我銳耳。此所以不得不急與賊競者也。若鄂城先拔,彼江右敗賊,即犯吾境,我力有余,折棰驅之,譬以湯沃雪也。[3](P1107)
十一月,太平軍出為背城之戰,清軍奪門入,大勝。胡林翼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并實授湖北巡撫。王柏心立即致函祝賀:“喧傳露布,喜動江天”。[3](P1108)
咸豐七年秋(1857),胡林翼“慨然下減漕之令”,致函王柏心:“乞先生坐鎮新堤,以正氣主持一應事宜。”[5](P518)這一年王柏心致胡的信尚存五通,雖非全璧,亦可見本年商榷之多,過從之密。
是年除夕,王又賦詩《除夕夜憶及齊安行營,時宮保胡公駐節軍中,因賦是詩,遙致憫勞之意》。胡去世后,王柏心有長篇挽詩《挽宮保胡大中丞排律八十韻》紀念胡林翼。
三、與左宗棠往來書札
王柏心與左宗棠書信現存25通,數量最多。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1853年1月12日)太平軍攻克武昌。清廷調張亮基署湖廣總督,張偕左宗棠于次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達武昌。八月,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左宗棠遂于九月初四日由鄂返湘。王、左二人在張亮基幕府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離開武昌時便結伴同船回鄉。途經螺洲,王柏心曾邀左宗棠順訪薖園。在王家,左宗棠看了王柏心撰寫的《樞言》,認為此書對“歷代興亡成敗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3](P23)
現存左宗棠致王柏心信第一通收入《全集》附錄,無上下款,函中稱“向提軍聞已卒于軍”,而欽差大臣向榮1856年8月9日死于丹陽軍營。則此信當作于8月末或稍后。信中對向榮頗有微詞,略云:
此公自廣西盜起之時,即身與其事,前后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廟堂至于草野無不同聲推服。而此賊由溪峒而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終冰室數年,不但祿位無損,即譽望仍復赫然,不但村野之人推為健將,即明略最優,熟習古今事理者亦復云云,何不察之甚也
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日,清廷任命陜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陜甘軍務。十一月十日,左宗棠離開福州赴陜。廿一日,王柏心致函左宗棠,為其出謀劃策:
明公上奏,宜先與朝廷約,勿責速效,勿遽促戰。必食足兵精,乃可進討。請以三年為度;不效,甘受其責。廷議既從,則展盡碩畫,以奏膚公。[3](P1161)
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抵達武昌,二十八日于漢口后湖扎營。此前他于“臘月廿日”函邀王柏心:“即日刺舟前來,一敘闊悰,兼領籌略。”[5](P555)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九日再次致函稱:“延頸江干,日盼客槎之至。”[5](P556)此信發出之后恰好接到王柏心來信,于是左宗棠在同日又作一書:
前書去后,未奉復示。今晨又以一書奉迓,甫欲發遞,忽枉惠緘。所言西事,無一不與鄙衷符合,業經陳奏施行者什居六七,自詫所見略同。急盼文從來營逐一商榷。座中無雜沓之賓,不嫌耳屬也。
此迓賁臨,不勝盼待之至。[5](P561)
左宗棠三次敦請,甚至一日兩札,期盼之殷,情見乎辭。“所見略同”正是他們交往的基礎和友誼的源頭。
王柏心應邀從監利赴漢口,與左宗棠縱談關隴形勢和用兵步驟,其第十通手札建議:
為麾下計,請分軍為二,盛兵向潼關虛張攻勢,而潛引師由山右絳州之龍門,渡河入朝邑韓城,渡渭而南,直出潼關之背。關上有賊,則表里夾擊,無賊則分路入長安,益大張軍勢。度捻賊在秦不能久留,食盡必走鳳漢,或窺楚蜀,或結連群回。麾下入關,相機剿滅,賊走必出武關,先檄豫師伏兵于前,夾而擊之可殲也。若已去秦境,麾下宜駐師鳳翔,防逆回之進犯。然后大興鳳、漢二郡,屯田三年之后,兵食并足,鼓行下隴,埽群回如拉朽耳。[3](P1152)
王柏心在左宗棠營中盤桓數日,有《漢皋營次感賦》《將歸留呈宮保左公》《臨發再呈左公》《宮保左公以師西定秦中賦此壯行》《歌詩送左公總師入秦》等詩作。
光緒四年(1878),左宗棠收復新疆,奉旨回朝,封爵二等候,聞王柏心病歿,上奏《已故軍務人員志節可傳請宣付史館》摺稱:
(王柏心)籌筆從容,算無遺策……親故聞臣將有萬里之行,來鄂渚省視,言及入關度隴艱險情狀,多為臣危者,王柏心獨不謂然,臣為氣壯。后此三道進兵,堅持緩進急戰之議,亦王柏心有以啟之。堅持緩進急戰之議,亦王柏心有以啟之。其學問深邃,識略超群,足達其忠愛之意,非時賢何易及也。[3](P23)
四、與彭玉麟往來書札
咸豐七年(1857)九月,彭玉麟收復太平軍固守五年之久的湖口,在石鐘山上修建水師昭忠祠,并筑梅塢,植梅花60株。《全集》有《彭雪琴觀察石梅歌》記載此事:
人中之杰彭雪公,戈船破浪乘長風。奪江奪湖數十戰,戰勝直泊吳城東。吳城舊日周郎鎮,彭郎再見威名峻。凱歌張宴望湖亭,水國千年兩雄俊。[3](P422)
王柏心將此詩及函托羅某轉呈彭玉麟,故彭氏復函:
一昨羅公子書來,道先生繾綣下問之意,并示佳章。三薰捧讀,不禁心花怒茁,狂喜上天。
麟耳大名久矣,顧未獲蹇修,無由通款。不意正法眼藏,見石梅愛之,且為諛飾詞翰,實鄙人所念不到者。但拈粉調丹,弱而好弄,酒酣耳熱,時有悲歌。年來蒿目時艱,覺壯志千尋,漸成弩末。先生謬加宏獎,雄詞健筆,颯颯生風,傳之千載,后人好讀先生詩而兼重麟之畫與人,豈非附驥以行?其榮幸何有比數?昔昌黎于長吉,一經品題,名噪長安,麟雖非昌黎如其人,而君則今之退之也。仰借余光,得增身價,感甚且慚甚耳。
前代工墨梅者,以吳中圭為絕,今罕有其匹,知精此技者鮮矣。麟以醉后,信紙涂抹,輒邀鑒賞,嗜痂之癖,何古今人不甚相遠哉?然善梅巨幀,麟多醉后作。非借酒以助興,實因酒而發狂,信手縱橫,無鹽忘丑,亦以時際艱難,杞憂恒抱,郁郁不平之氣,特假作梅老干以舒之。可謂無聊復無奈矣。
入春以來,肝疾作楚,久不訪紅友,亦久不夢到羅浮。昨以軍次,清明寒食漉酒,悵觸遙深。不覺玉山欲倒,走筆染紙。曾記前人有句云:“囊中剩墨無多少,聊為逋仙寫一枝。”蓋此意也。
驛使將來,寄塵雅盼,未審鐵干橫斜中,尚有疏影寒香,仿佛一一否?
并附拓本八幀,先生試嗅之,楮墨間當拂有酒氣,借博胡盧一笑。[4](P850)
信中稱“羅公子書來,道先生繾綣下問之意,并示佳章”,由此可知,王柏心事先看見彭所作《石梅圖》拓本,作詩頌之,將彭比作東吳周瑜,對其文韜武略贊譽有加。為表示感謝,彭“走筆染紙”,畫梅贈送給王柏心。
王柏心收到彭氏梅花圖,喜出望外,又賦《雪琴方伯自軍中枉書,兼寄墨梅,裁詩報謝》詩三首,《全集》系于戊午,即咸豐八年(1858)。詩云“春來鷗夢閑江渚,天外鴻書下陣云。”則王是在春天收到彭的來信,彭書云“昨以軍次清明,寒食漉酒”,即可推斷此札作于咸豐八年三月初四,因為這一年三月初三為清明節。
彭玉麟一畫一札,王柏心三詩,見證了二人之間的友情,相得益彰,堪稱雙璧。
五、與郭嵩燾、郭崑燾往來書札
王柏心與郭嵩燾書存二通,其一作于咸豐元年(1851),對平息少數民族地區動亂提出對策,指出:
當賊初起,利在卷甲疾馳,出其不意,直搗其巢,渠魁殄滅,余黨不煩兵下矣。及賊勢既張,蔓延四出,則散地可棄可不救。惟當扼吾要害,斷彼饋餫,簡練壯勇,偵探徑路,檄滇、黔、川、楚、粵東之師,迭分奇正,數道并進,使賊力分勢寡,不知所備。我乃決策摧鋒,躪其窟穴,自可擒馘無遺。若懾于虛聲,連營縮朒,或不權利鈍,所至與戰,是不能致人而致于人,皆取敗之道也。[3](P1081)
他強調“以土兵治土寇”“蕩平之后,擇其險岨不毛者割而裂之,仍復前明土司之制”堪稱真知灼見。[3](P1083)
其二作于咸豐五年(1855),略云:
九江死賊與湖口為指臂,悉其精銳,以一面當我,守御甚固。我師萃于鄱湖之內,水陸并攻,蹀血而戰,日夜不息。雖搤其吭未拊其背,彼方外據長江,調取皖境諸賊,往來抽換,番休迭戰,饋餫不絕。彼主我客,彼逸我勞,久頓兵堅城之下,守者有余,攻者不足,古之智將,似稍異此。今誠得羅廉訪一軍,道通城而入,假途鄂渚,合楚北戰艦新勝之師,水陸并下,出其不意,直指湓浦,賊必震潰。或明示形勢,旌旗蔽江,鼙鼓震天,順流東騖,以武臨之。或約鄱湖之師,悉力搏戰,牽掣其前。度彼將疲,潛引江外之師,夾擊其后,合而蹙之,一戰可拔此。與但用鄱湖諸軍,專斗實力,僅乃勝之,其遲速巧拙,相去不啻倍蓰也。兵法:“相持既久,在于用奇。”羅廉訪一軍,名為援鄂而來,實則乘機合取九江,此即田忌救趙直走大梁之計。竊謂批亢搗虛,勢有必出于是者,請為少司馬詳言之。而力加贊成,則拔九江若反掌。然后整眾東下,兵不留行矣。[3](P1101)
時郭氏在曾國藩幕中,故王請郭“為少司馬詳言之而力加贊成”。何以不直接上書,大概當時地位懸殊,自覺人微言輕。郭氏復王函僅存乙丑(1865年)四月二十五日一通,主要談福建、廣東一帶剿匪事。[5](P531)
1873年,王柏心病逝荊南書院,“易簀之頃,骨肉無一人在側”。郭嵩燾作《王公墓志銘》云:“江漢間言道德文章,裒然屬之先生者五十余年。”[3](P1441)對他推崇備至。
郭嵩燾之弟郭崑燾致王柏心函現存三通。其一是咸豐六年(1856)年四月托人帶去江忠源遺稿刻本十部、李杭詩集兩部。第二通作于九月六日:
石逆率屢勝之,當悉銳援鄂。潤之中丞、迪安觀察會合馬隊,八戰皆捷,力挫兇鋒,遂使劇賊膽寒,潛師宵遁,軍威大振,殊快人意。惟城中饑鼠又復得食,以為負固之計,未能迅速克復,為可慮耳。北岸諸軍,以二萬之眾,數月未聞一戰,沙口水營尚須南岸派陸勇防護。專閫何人,付之一嘆而已!江省所在糜爛,自曾、劉、吳數君抵瑞后,道路稍通,事機漸轉。而豐城敗賊復糾合會匪,擾及貴溪、弋陽一帶。河口厘金為章門軍餉大宗,頃又被賊殘破,彼中局勢,未卜何如?東望茫然,惟增感喟。[5](P542)
信中提及胡林翼在武昌周邊地區擊敗太平軍,又對江西局勢感到憂慮。
第三通云:
聞蘄州之賊,并力以圖黃梅。竊謂宜撤黃梅之師,繞赴上游,轉戰而下,庶上可保武漢,而下無腹背受敵之虞。若久此相持,萬一餉道中斷,則患乃大矣。江右事勢,尚無轉機,吉安又有六月十七日之挫,滌帥三疏請終制,不肯即行。
邇來江流大漲,敝處水田多遭淹沒,旱田晚稻又苦蟲荒,人事天時,徒觀增慨,家兄擬于杪秋北上,非希仕進,亦思作朝市之隱耳。知念附聞。季翁近忙甚,計常有書達左右。[5](P539)
信中提及“滌帥三疏請終制”,當作于1857年曾國藩喪父之后。書中通報了“家兄(郭嵩燾)擬于杪秋北上”的消息。
六、與李星沅、李桓往來書札
李星沅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兩江總督任內告病回原籍湘陰。道光三十年(1850)早春,聞皇帝旻寧逝世,他請求去北京行禮。四月初五北上,途經岳州時致函王柏心:
前因蔡世兄附上片緘,旋見惠寄桓兒書,拳拳摯愛,三復滋感。當令肅箋申謝,并陳疏止折漕顛末,度邀青電。
辰惟皋比講學,望重荊州,文藻江山,暉映千古,可勝仰羨。弟家居卻掃,借遂烏私。愴聞軒馭升遐,何敢因疾不臨。頃遵旨由漢口北上,能于叩謁之余,蒙恩即予歸養,幸何如之。
杭兒詩刻奉政,其顯言時事者,留俟續出,非得已也。[5](P491)
王柏心與李星沅長子李杭、三子李桓亦有交情。他曾為李杭作墓志銘,為其遺集《小芋香山館集》作序。現存李杭致王一函:
執事銳意述作,毅然以復古自任,所為古詩歌文辭,咸溯源于周秦,導軌于漢唐,睎先生之盛媺,矯末流之放失,摛藻下筆,體質彪文,頡頏古人,誠無愧色。既遺棄軒冕,徜徉于江湖之間,俶儻恢奇,蕩滌情志,其所論說,亦將洸洋自恣,不可端倪。譬之神龍游于重淵,元豹隱于溪谷,其蜿蜒變化、爛漫陸離之狀,殆非寡聞渺見者所窺也。[5](P740)
此函無系年,但由文中“魏默翁甫(魏源)權東臺”,可推斷作于1846年。
李桓與王柏心是同年進士,李桓與王柏心書今存五通,而王柏心與李桓書已無一幸存。李桓致王柏心第一函如下:
昨由李少尉交到手札,反復莊誦,憂國之意與愛士之誠,悃悃款款,忠藎悱惻。桓雖不敏,亦得窺大君子用心之厚。近日士大夫多務為隱怪之論,下筆累數千言,非不驚炫耳目。細按之,則矜奇立異之意多,博厚慈祥,民胞物與,于孔門忠恕、詩人忠厚,夐乎其闊絕也。
讀來示論歲收、論關中形勝、論新交奇士,藹然有道之言,蔚然大儒氣象,自桓有知識以來,默數所聞見巨公長德,求如閣下植品勵學、中正和平、足為人倫之表,實無其匹。斯言也,亦非桓一人之稱善,凡如桓之用心者,莫不如是言之。獨是相去五百里間,數十年傾想,不獲一見顏色,易任悵結。數聞子元昆仲之言,每歲小陽閣下必解館于里。昨得杭州戚友書,招為西湖之游,且候舍侄京旋再定。
薖園風月,想像久矣,他日維舟奉謁,得盡平生之言,何快如之,何幸如之!
蘄州陳愚谷所著《湖北文載·詩載·叢聞·舊聞》,符南樵《正雅集》謂悉毀于兵火,不知果否?尚有藏本可假閱否?希留意及之。[5](P721)
“數十年傾想,不獲一見顏色”,可見二人未曾晤面,希望“他日維舟奉謁”。李對時局頗為憂慮,尤其關注文獻毀于兵燹,向王借閱書籍。
因李杭早逝無子,李桓將己子李輔耀過繼給他,改稱輔耀為“侄”。同治九年(1870),李桓將李輔耀的試卷寄給王柏心,請他“刊政”。信中還涉及對張之洞詩集的評價。
前閱大著古文各體已編輯開雕,景星慶云,先睹為快。子元昆仲開春來湘,務祈賜寄一部,俾得奉為圭臬,幸甚幸甚!
張香濤學使散體,昨始得見一篇,古雅可誦,未知有刊集否?四省合刻廿三史,己未告成,均求便中留意。
弟夙有目疾,尚無甚苦,本年以一藥之誤,左只幾致失明,頃始得親筆墨,而痛定之思,刻虞過費,案頭益少新知,大好時光,坐任駒疾,殊恨恨耳!
耀侄幸與優科,深愧非分,外呈試卷,尚乞刊政為荷
李桓致王氏最后一函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其時適有次子之戚”[5](P713),故此札凄涼沉痛,與王柏心同病相憐,盛贊其子王家仕之才華及夫婦愛情之堅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