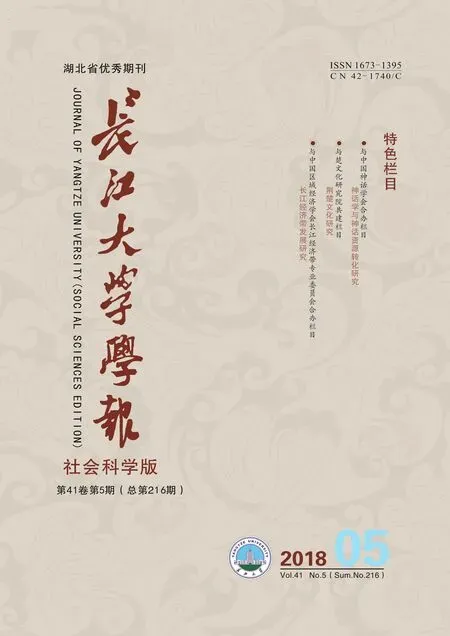安德烈·別雷《灰燼》中的俄羅斯空間與意義生成
郭靖媛
(北京外國語大學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100089)
安德烈·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是20世紀前20年俄國最為活躍的象征主義作家之一,在小說、詩歌和文學批評等領域著述頗豐。作為“年青一代”象征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別雷認為象征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文本以及符號系統,更是一種存在本質。他希望象征主義超越審美范疇,肩負起創造新人、創造新生活,最終通向神圣永恒的使命。因此,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在神秘主義的光影交錯下,依舊有一些現實性的元素在閃動,這就是“滿目瘡痍”的俄羅斯。別雷用象征主義者的方式來重現混亂時期的俄羅斯空間,并試圖回答一個永恒的問題——“俄羅斯未來的出路在何方?”
別雷對空間的迷戀不僅僅體現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小說創作中,從其早期詩歌中可以窺見空間對于意義生成的重要作用。其中以其第二部詩集《灰燼》(Пепел)最為顯著和特別。《灰燼》收錄了別雷于1905~1908年創作的詩歌。題目“灰燼”包含著象征意味,寓意詩人心靈經痛苦燃燒后的剩余之灰,因此也有人將詩集的名字譯為“骨灰”。同時,“灰燼”也寓意混亂中的全部秩序和整體空間的存在都化為虛無。與其同時代的詩人維·伊萬諾夫(В.Иванов)認為:“《灰燼》是別雷最成熟的作品,見證了作家在藝術上的急劇變化,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內心的自由。”[1](P237)
《灰燼》創作于別雷個人生活與民族悲劇激烈交織的時期,作者在詩集中通過不斷重復的意象——俄羅斯、田野、鄉村、城市、鐵路、道路等,構成了一個有組織的空間結構。然而,這一空間是以混亂黑暗的色調以及彌漫的死亡和絕望情緒為背景的。別雷通過空間的構建,不僅旨在描繪俄羅斯空間與個人情緒,更在此間探尋空間與象征主義的神秘關聯。因此,對空間的建構是《灰燼》意義生成的關鍵環節。
“空間問題不僅在洛特曼的符號學理論中占據著突出的地位,而且應視為貫穿其整個理論的一根紅線。”[2]在《藝術文本的結構》中,洛特曼認為,空間聯系的語言其實也是理解現實的基本方式之一。同時,藝術文本具有空間模擬機制,能通過文本中的高低、遠近和內外等空間對比來傳達一種更深刻的文化意義。詩歌作為若干結構的組合體,空間結構在詩歌意義生成的機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筆者從空間文本的角度對別雷的詩集《灰燼》做一種結構化的解讀,試圖從中解釋別雷所展現的“俄羅斯圖景”。
一、水平空間與虛無存在
與《碧空中的金子》(Золото в Лазури)中所傳達的樂觀的神秘主義激情不同,《灰燼》僅題目就充滿了衰頹之感。在詩集完成的前一年,俄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整個俄羅斯陷入無秩序的混亂。別雷在祖國彌漫的死亡與絕望以及自身情感的悲劇中發現了一種神秘的關聯,這一系列痛苦的掙扎與苦悶的思考都被囊括在詩集《灰燼》所構建的空間之中。
在文本之中,空間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力場的形式,將內容與充斥其中的書寫客體囊括其中。如果說藝術文本參與構建了世界模式,那么空間作為世界模式中的基本元素,其在文本中展示的結構成為建構世界模式的基礎。因此,恰恰是空間的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決定了文本的形象和隱喻體系。“對于特別的主題來說,其語義生成與文本中的時空概念有關,而主題的結構本身則包含空間的語義特征。”[3]
在詩集《碧空中的金子》中,高空的太陽(蔚藍天空中的金子)是作為大地上世俗的對立面而存在的。整部詩集的空間是垂直結構,這也決定了其語義主題在本質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因而賦予了詩歌以崇高色彩。《返航》一詩完整地展現了《碧空中的金子》垂直的空間結構:
身在高處,我任憑命運的擺布。
漫長歲月從頭頂急速飛逝。
我在山洞中無拘無束地生活。
碧空漸暗,星光散落。
我的朋友們從高高的星空墜落,
他們在低處生活,遺忘了我。
深淵上我點燃帶血的火把。
遙遠的山頂繁星閃爍。[4](P79)
詩中出現了高低對立的結構,“我”身在高處,與太陽比肩,手持金色的權杖,以先知的形象俯瞰山下。先知在征服了山所象征的精神高峰后,再向下墜入塵世。先知形象將兩個不同層次的世界結合為一體。高處是神秘的、金色的,閃爍著象征主義的光芒;而低處的塵世在此時被宴會的狂歡氣氛所籠罩,帶有強烈的世俗化色彩。可以說,“我”這一先知所持的權杖,成為垂直空間結構的軸心。詩歌沿著這個軸心朝著兩個方向運動:先知和他的兄弟們落入塵世;在先知的召喚下,小矮人們向山頂奔去。這便是返航的內在意義,即通過垂直運動,使塵世中的矮人們(也就是我們自己)獲得向象征主義的崇高山頂進發的可能性。垂直結構不僅意味著空間中的高低之分,也意味著語義結構中的高低差別。先知所在的高空被賦予了崇高的意義,詩中的一切運動都可以分成向上的飛翔與向下的墜落。
然而,在詩集《灰燼》中,別雷卻塑造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空間,詩中的抒情主人公以水平方向的運動代替了向上或向下的運動,作為背景的空間也是在水平的維度展開的。與第一部詩集中崇高且神秘的碧空不同,占據《灰燼》主要空間的是“原野”。無邊無際的俄羅斯原野,成為詩歌中構建的新世界圖景。與原野相關的一系列詞語形成了空間語義的中心,如равнины(平原)、раздолье(遼闊)、 даль(遠方)等,而與平原相連的語義則代表著混亂與死亡。別雷在《灰燼》的序言中寫道:“……整體是一個無物的空間,其中是日漸衰落的俄羅斯中心。……詩集的主導動機是一種不由自主的悲觀主義,它產生自對當代俄羅斯的看法(空間在壓迫,無物性在威脅——生成的是幻景:苦艾、山楊、野蒿,等等)。”[5](P167)
從詩集《灰燼》中的代表作《羅斯》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空間怎樣在水平方向延展開來,而這樣的延展喪失了遼闊的氣度,卻凸顯出無窮無盡的虛無:
我赤貧大地上的曠野,
那里充滿了悲傷。
遠方空曠的平原啊,
聳立起,聳立起山崗!
……
抑制劑是p H值調節劑與強絡合能力物質的混合物,通過控制p H值來抑制交聯劑中心離子的釋放速率,且早期釋放的部分中心離子也能被強絡合性物質快速絡合,最終使得膠塞緩交時間大為延長。
綿延不斷的遼闊中,
空間連綴著空間。
俄羅斯啊,我該跑向何方,
逃脫這瘟疫、醉酒和饑荒?[4](P142)
洛特曼在分析扎博洛茨基詩歌中的空間結構時說道:“垂直軸的倫理特征就得到最大限度的暴露……把高處與遠方相聯系,把深處與近處相聯系,這使得‘頂端’成為空間擴展的范圍:升得越高的一方越無限廣闊,降得越低的一方越狹窄。”[6](P309)可見,垂直結構中不止存在高低兩個對立空間,水平方向的遠近同樣包含著層級的概念。然而,在《灰燼》中,我們看到的只是水平空間的延綿不斷和遼闊,“空間連綴著空間”,喪失了遠近的結構,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循環往復,邊界也在不斷的重疊中模糊起來。因此,在這一空間中的運動失去了方向,只能在空間的怪圈中茫然地尋找出路。
“道路”成為《灰燼》空間結構的重要語義核心,但此處的道路沒有盡頭,它的伸展更像一個致命的怪圈,引領主人公走向無盡的虛無,唯一的出路是死亡。詩中抒情主人公對于俄羅斯空間的最初體驗是通過鐵路來實現的。在“俄羅斯”這一節中,《從車窗看去》《車廂中》《火車站》直接與鐵路有關。鐵路是俄羅斯文學中鮮明的文學意象,火車因其龐大的外表和驚人的速度,被認為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進步與邪惡的混合體。火車在文學作品中也成為各種矛盾的展開之處,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中梅什金公爵的初登場,以及《安娜·卡列尼娜》中作為悲劇開始與終結的車廂和鐵軌。別雷詩歌的主人公并不知道行駛的終點在何處,或許他明白,鐵路延伸的前方便是空洞的中心,他連同全車苦難的人民都將在那里墜落,摔得粉碎。在《從車窗看去》中,這一情緒表現得最為透徹:
火車在哭泣。遙遠的家鄉
綿延著電報網。
我掠過田野——奔向死亡。
我掠過:如此空曠,如此荒涼……
掠過——每一個角落,
掠過——天地間萬物,
掠過——無盡的村莊。[4](P120)
一切都融入廣闊之中,一系列排比句(Там…Там…Там)加劇了速度感。而主人公在這趟幾近失控的列車上,獲得了逃出空間的可能性——走向死亡。
然而,鐵路并沒有作為勾連俄羅斯歷史與未來的紐帶,而是喪失了任何崇高的意義,作為漫游俄羅斯空間的一種機械化方式存在。別雷并不想在這趟運行的列車上思考如何重建俄國的歷史道路,只是將鐵路與火車共同凝結成混亂時期俄國的縮影。主人公在這條沒有方向的鐵軌上疾馳,最終走向滅亡。即使是死亡,也失去了悲壯的意義,成為人與其所在扁平化空間的存在的終止。
二、城市與鄉村的二元空間
二元結構是空間語義的重要特征。別雷在《灰燼》中塑造了城市與鄉村這個二元空間,它們具有互相對立的語義內涵:城市象征著革命時期瘋狂的進步力量,以及現代的、非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帶來的急速變動;而鄉村遠離喧囂,仍保存著古老俄羅斯的傳統意蘊。城市與鄉村依舊是對立的兩極,代表俄羅斯未來的兩種方向——與城市的混亂一同滅亡;或是轉身,孤獨地回到鄉村的靜謐中去。
別雷在《灰燼》的“序言”中寫道:“資本主義在我們這里還沒有把像西方那樣的城市中心建立起來,但卻已經在把農村公社進行解體;正因為這樣,逐漸擴大的、布滿雜草和小村子的沖溝所構成的圖畫乃是宗法制生活方式毀壞和滅亡的活生生的象征。這種滅亡和這種毀壞浪潮般地席卷著村落、莊園,而城市里資本主義文化的囈語正在勃然興起。”[4](P116)城市與鄉村圍繞著日漸衰落的俄羅斯中心,共同構成了整個空間。
毀滅和沖突首先席卷了城市空間。在別雷筆下,城市的首要特征是虛無: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產生了動搖,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城市中具有活力、生機,以及顯示出強大進步動力的力量都消失在黑暗之中,火熱的激情被冰冷的靜謐所取代。在“城市”一節的《憂郁》中,就渲染出了這樣的城市氛圍:
手指穿過煤煙,
鉆石般在鏡中閃亮……
那里——煤油燈
用火紅的眼看向窗外。
大地升起一團煤煙,
在城市與街道上空飄蕩。
一曲無人應和的詠嘆調,
從頭頂飄向遠方,遠方……[4](P170)
在這里,具有工業文明色彩的煤油燈取代了神秘的金色光芒,成為不祥的城市之光的代表。在《碧空中的金子》中,具有主體地位的太陽以燈的形式出現在城市空間之中,光明由此失去了隱喻的象征意義。
“城市”這一節中,空間更加具體,處于變革最為激烈時期(1904~1906)的莫斯科形象被集中展現在這一章節中。在苦難的俄羅斯深淵之上,莫斯科正沉浸于最后的歡愉。與此同時,與這最后的瘋狂一同呈現的,是城市中破舊的房屋與赤貧的人民。這宣告了彼得大帝改革以來城市乃至俄羅斯的滅亡。進步的力量在這一空間中毀于一旦,城市在視線中漸漸消失:“悶熱的傍晚時刻,/喧囂的城市在我身后。/風灌進敞開的衣襟,/獻上清涼的親吻”[4](P174)。
與《彼得堡》中井然有序的城市空間不同,《灰燼》中城市的最大特點是混亂。首先體現于空間中充斥的狂歡化場景中,這讓城市蒙上了一種異教色彩。在“城市”一節中,就描寫過酒神節以及小丑戲的場景。雖然城市曾經過彼得大帝改革后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洗禮,但異教的狂歡因素仍是城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城市空間,仿佛是一個巨大的宴會,其中有“向著火熱的天際,/工廠的煙囪冒出濃煙”,也有“年輕的匈牙利女人忘我旋轉”,同時也有著死亡的氣息,“黑黝黝的罪惡炮口痛哭著,/低沉的轟鳴隆隆作響”。其次是敘述對象的混亂。一切高雅和低俗的存在都被混亂地納入城市空間,在一種反標準化的語境中展開。這就是主人公身后“喧囂的城市”,它混亂、虛無,又充滿致命的誘惑,是漫游者“已回不去的故鄉”,也是整個空洞俄羅斯空間的一種具體形式。
相對于城市的虛幻和混亂,《灰燼》中對鄉村的描寫則更具有日常性和現實性。鄉村中的俄羅斯空間雖然同樣籠罩著破敗和死亡的氛圍,卻不再是一個“空中”的形象,而是充滿了生活的各種細節。這種日常性和現實性在“鄉村”一節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相遇》一詩中:
洗吧,在瓦罐和木盆之間,
一頭豬在刨地。
那門框上鮮紅的
印花布更加鮮艷。
……
在懸掛的破舊衣服間,
雙腳踩踏著污泥。
把一捧過了篩的谷糠
撒向拴馬的木樁。[4](P145)
這首詩是別雷獻給大學時期的好友、他的神秘主義導師弗·索洛維約夫的侄子——謝爾蓋·索洛維約夫(С.Соловьёв)的。他倆都曾是弗·索洛維約夫的追隨者,弗·索洛維約夫筆下的索菲亞形象,是他們在尋找基督和神秘主義之路上的領路人。在這首詩中,別雷將這場相遇置于一個過于“塵世”氛圍的鄉村之中,“一排茅草覆蓋的小屋/出現在曠野四方”,遠離過去的神秘主義追求,投入日常性的細節中。
別雷試圖展示一個現實的俄羅斯空間,但這并不代表其寫作具有現實主義和敘事性,或是如伊萬諾夫所說:“在《灰燼》中,別雷藝術創作的重心已經由唯心主義轉變為現實主義”[1](P246)。別雷筆下的鄉村也不是傳統意義上寧靜質樸的心靈歸宿,而同樣充斥著死亡的陰影,是已經失去了精神內核的農村。“鄉村”詩節中的《絞刑架》一詩,描寫了絞刑者行刑的過程,這首詩中對死亡畫面的刻畫十分直白,“絞刑架前,我瞇著眼睛,——是否在/混沌地思索。/絞索中伸出/我血紅的舌”[4](P149)。在鄉村生活中,死亡成為一種日常的生理性行為,成為一只血紅的舌,成為一個具體的物象。
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別雷感受到了無法遏制的毀滅與衰亡。無論是城市的虛幻,或是鄉村的現實,都籠罩著死亡與空洞帶來的不安。如學者鄭體武所說:“一方面,他(別雷)看到城市里日益膨脹的‘資本主義文化夢囈’;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鄉村特有的‘宗法制生活遭到破壞和死亡’。”[7](P232)別雷與詩歌的主人公無法回到過去的宗法傳統,更不知道前路通向何方,他們只能在這個混亂的空間中,在時空的火車上,急速奔向死亡。
三、《灰燼》中的“俄羅斯圖景”
洛特曼認為,藝術文本具有空間模擬機制,能夠模擬現實生活中的“世界圖景”。“世界圖景”已經超出了文本空間所代表的文學意義,顯露出世界面貌最基本的一面。空間反映著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人類思維邏輯天生有著將地理空間概念觀念化的趨勢,人們借助世界上最一般的、社會的、宗教的、政治的模式來理解他周圍的生活,這個模式不可避免地帶有空間特點。[8](P212)洛特曼在解釋但丁《神曲》與布爾加科夫《大師與瑪格麗特》時,挖掘出了空間文本中蘊含的道德文化意義,他因此提出“世界圖景”(картина мира)不可避免地具有空間特征。“現實的空間成為了符號圈的圖像形式,成為了表達各種非空間意義的語言。同樣,符號圈也按照自己的形象改變了人周圍的現實空間。”[8](P320)
在《灰燼》的空間塑造中,同樣包含著一種“俄羅斯圖景”,它展示了革命年代的社會圖景,并通過這一空間解釋了彼時俄國社會的主要文化特征。別雷試圖找到俄羅斯的未來出路,而擺在他面前的似乎只有死亡。
空洞是別雷筆下“俄羅斯圖景”的主要文化意象之一。在《灰燼》的空間中,云朵是鉛色的,樹枝是枯槁的,眼睛是冷酷的,月亮是晦暗不明的。一切都在空間中得以無限延伸,卻沒有盡頭,消失在無盡空間的重疊之中。如此空洞的俄羅斯中心使人陷入巨大的絕望,別雷才會怒喊,讓苦難的人民“去墜入那個空間,摔得粉碎”。正如茨維塔耶娃所說,“別雷詩歌中最親切也是最可怖的部分——是空洞的空間……”[9](P284)這一空洞同樣也是在描繪一種痛苦的人生境遇:當人無處安放其尋求自由的靈魂時,便陷入無盡的墜落。
詩集《灰燼》的第一部分“俄羅斯”正是對空洞的空間與空洞的心靈的整體書寫。正如別雷在《灰燼》1925年版“序言”中概括的:這一部分描寫的正是從城市中逃離的主人公來到田野,希望在這片開闊的空間尋找自由。然而,他不但沒有找到自由,展現在他眼前的卻是當下的日常生活:充滿威脅與自殺,隨處可見鐵路與電報網。主人公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空間,其中充斥著病痛、饑餓與死亡。[4](P116)
“永恒的往復”(вечный повтор)是這一空間所代表的另一主題,也是前文所出現的“返航”的反題。《灰燼》所構筑的圖景中,不僅空間是沒有盡頭的,在這空間之中的運動同樣沒有休止,沒有方向。與“返航”的目的性不同,“永恒的往復”失去了運動的意義,使作為背景的空間失去了價值維度,成為虛無的存在。這在《電報員》一詩中得到了極致的體現:
車廂,包裹,帆布
與落日的余暉……
電報機嗒嗒作響,
伸出一條紙帶。
……
無聊的白日,
無聊的白日
與無聊的黑夜
相交替。[4](P120)
電報機的噠噠聲和不斷伸出的紙帶,以及電報員不斷重復的轉動輪盤的動作,便是一種永恒的往復。與機器重復性運轉的節奏相應和的,是無盡交替的白日黑夜,這一切都染上了“無聊”的氣氛,從而展現了“永恒的往復”所代表的虛無的語義特征。
面對這個空洞,在永恒往復的俄羅斯空間中,別雷似乎已無力思考如何重建俄羅斯未來的道路,如何實現自我和民族精神的復活。他認清了籠罩一切的死亡力量無法戰勝,他從城市的監牢中逃脫,卻注定踏入另一個監牢——內心徹底的絕望和瘋狂所鑄成的監獄。“我注定活在這監牢。/哦,是的——監牢多么美麗。”
別雷在1925年版“序言”中將《灰燼》的主題概括為:“這是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的曲折路線。這是為了尋找‘自由’而途經城市、鄉村與田野的逃亡。但不接受沙皇-富農制的俄羅斯最終會以個人主義的混亂而終結。這一混亂就是——絕望的瘋狂。”[4](P114)別雷,或者說《灰燼》中的抒情主人公,最終正是陷入了這種絕望的瘋狂中。《灰燼》中的許多詩是以死人、瘋子或囚徒的口吻書寫的,抒情主人公或是展現了對命中注定的死亡的安寧姿態,或是扮演了不被世人理解、處于邊緣地位的瘋子,或是表達了對難以企及的自由的無望追尋。在《碧空中的金子》中,別雷常常以先知的身份自居,預言著神秘主義的未來世界。但在《灰燼》的末尾,先知也不得不流浪于田野,為衰敗的俄羅斯哭泣,“我以田野為家,以沙土為床。/沾滿露水的草地上,煙霧是我的幔帳”。
在《灰燼》中,田野就是俄羅斯大地的象征,它荒蕪、空曠,被黑暗籠罩,又遍地哀鳴。但田野上照常升起的月亮、輕輕擺動的柳枝,總是給人以慰藉,使人們在最為深重的危急關頭找到心靈出路。別雷筆下的俄羅斯空間正是消失在這一片田野之中,最后化為了灰燼——包含著歷史的煙塵和個人經驗的余煙。
整片田野——四周隆起的田野,
在一切的靜謐中——我遇到:
盤根錯節的枯莖,
當我墜向尖銳的長矛。[4](P202)
別雷將個人的情感與民族的命運相結合,投入到一種徹底的空洞和絕望之中。面對滿目瘡痍的俄羅斯,涅克拉索夫式的現實主義情懷使他陷入憂患,而神秘主義的未竟的理想使他無法沖破個人主義的狹小空間。因此,他筆下的“俄羅斯圖景”充滿混亂與空洞,并無法遏制地走向死亡。這便是處于別雷文學創作轉折點的《灰燼》所表達的狀態——在經歷了一場大火之后,空洞的俄羅斯空間最終成為苦難的余灰,并陷入看不到盡頭的永恒往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