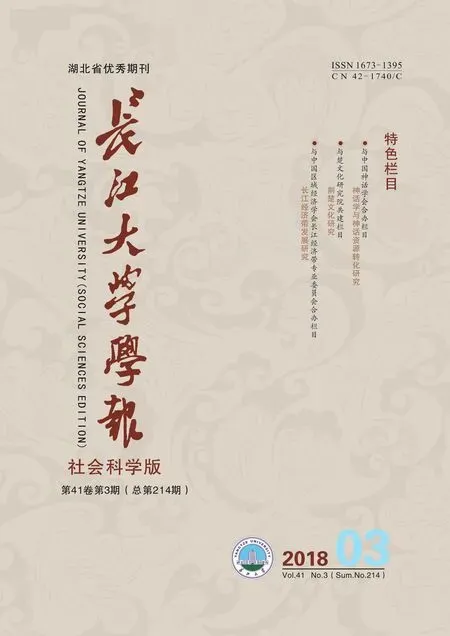神話與現代性問題①
馬修·斯滕伯格[著] 王繼超[譯]
(1.早稻田大學 國際研究與教育系,日本 東京;2.華中師范大學 文化產業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
一、奧登的評價
現代性(modernity)的首要問題是意義的缺失。這是W.H.奧登(W.H.Auden)在1948年反思現代生活的挑戰時得出的結論。他解釋道,20世紀人們:
面臨現代性問題(the modern problem),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沒有意識到已經不再受傳統的支持,因此,想給源自內部或外部并進入到自己意識里的種種感覺、情感、觀念帶來秩序和統一的每個個體,不得不有意親力親為以前家庭、習俗、教堂和國家為之所為之事,也就是說,依靠規范和預設(principles and presuppositions)的選擇來理解他的經驗。[1]
奧登的評價是中肯的。 “現代性問題”的確存在,或者至少與奧登同時代的許多人也都相信其存在。英國當時的文化觀察家們也注意到某種創造意義的結構缺失令人迷失方向,這無疑引發了一大堆現代的苦難。盡管這一連串的苦難以不同方式描述了現代性問題,但對現代性錯誤的評價卻傾向于強調同一類的不滿:科學認識論的自大、現代生活精神的貧瘠、過度消費主義、大眾文化的平庸、當代城市生活的異化效應以及大眾媒體制造的情感疏離。一戰結束到二戰早期,英國人普遍的感覺是,“現代性”或“現代”(the modern age)使人們共同的一套“規范”和“預設”(引用奧登的話)喪失了。并非巧合的是,1922年人們同時見證了T.S.艾略特(T.S.Eliot)《荒原》(TheWasteLand)的出版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成立。兩件事都表達了人們試圖基于共同的被認為在向現代性過渡中已經消失的規范與預設重建或替代文化統一(cultural unity)的愿望。[2]
英國20世紀思想史很大部分可以視為應對現代性問題的一系列努力,只不過回答各不相同。例如,像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K.Hammond Chesterton)或歷史學家J.L.哈蒙德和芭芭拉·哈蒙德(J.L.and Barbara Hammond)希望回到更加質樸的時代,希望重獲已消失的社會及道德的和諧。這些思想家認為,如果采取合適的步驟,消逝的黃金時代會失而復得。另一些思想家,如改信高教會派或羅馬天主教的小說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和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認為,基督教的這些傳統主義形式是防御現代性的保障。還有一些人,如文學評論家F.R.利維斯(F.R.Leavis)及其追隨者認為,對現代性問題的正確回答是,用古典文學代替基督教成為文化價值的主要來源。甚至英國廣播公司的發起人預見現代科技使文化統一成為可能時,也深受鼓舞。這些對現代性問題的回答大體相似:無論是想象的一去不復返的社會和諧的黃金時代,還是古代信仰抑或文學“偉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方式雖有不同,思想家們都從過去汲取靈感,形成了自己對現代性的闡釋和回答。相似的還有:意識到現代問題實際上是意義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代社會發現或構建意義的問題。
然而,對現代性問題的回答還有一個是與眾不同,極為普遍卻大多被忽略,并且不依靠過去尋找靈感卻重視意義問題的,可以稱之為“神話思維”(mythic thinking)。神話思維可以如此定義:相信神話——應對終極問題的永恒關聯性(perennial relevanc)的解釋性敘事(explanatory narratives)——是意義的至關重要的來源,是理解經驗不可或缺的架構,是應對現代性必不可少的工具。《20世紀英國的神話思維》(MythicThinkinginTwentieth-CenturyBritain)旨在描述英國20世紀文化和思想生活中神話思維的起源、特征和影響。
神話思想家(mythic thinkers)多把現代性視為歷史的斷裂(a rupture in history),因此他們認為,努力復興過去以應對現代性問題的方式是過時的,注定以失敗告終。舊的思維方式過時、歷史發生徹底斷裂的認識,把所有神話思想家聯系了起來:無論是1920年代現代主義的重要人物艾略特、1930年代奇幻作家J.R.R.托爾金(J.R.R.Tolkien)、1960年代的先鋒小說家J.G.巴拉德(J.G.Ballard),還是1970年代的神學家約翰·希克(John Hick)。神話思想家認為,人們需要一種把現代性的獨特性加以考慮的創造意義的新的思維方式,而且相信這一任務可以由神話來實現:一個既含糊不清又富有意義的概念。實際上,神話思想家給現代性問題的定義正是神話逐漸的缺失。奧登自己也表達了這個觀點,他指出現代文化是如何以“普遍神話的消失”為特征。艾略特描述現代狀態(modern condition)為“神話貧乏”——一種他試圖以遍布神話的詩歌去改變的狀態。[3](P141)
《20世紀英國的神話思維》試圖描繪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神話的文化與思想史,解釋神話作為英國文化中反復出現的模式的意義。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分析始于文化模式的識別的洞見為例,《20世紀英國的神話思維》追溯1900~1980年神話思維的維度和重要表現形式。這本書的中心論點是20世紀早期出現的神話思維,是各種思想家和重要文化團體表達和講述對于超驗意義(transcendent meaning)缺失的現代時期憂慮的一種方式。因而神話思維最佳的理解是被奧登證明的對現代性問題的回答。同時,神話思維本身也是一個現代性課題,其發生、取決、存在于與現代性的基本傳統、特征與原則的有效平衡中。其在20世紀英國文化的流行因此成為現代性對超驗問題根本上是祛魅和敵意(disenchanted and inhospitable)這一觀念的挑戰。
1900~1980年的整個時期,神話思維存在于文學、藝術、文化批評、哲學、心理學作品中,試圖說明,無論是古代神話還是更多后創作的神話敘事,都對現代生活具有啟發性。更為根本和重要的是,神話思維聲稱神話傳達了理性和科學無法解釋的永恒的真實,因而被認為是借助想象力創造意義的新方式。神話因此表達了它的支持者在現代性中和在對現代性的不同回答中發現的缺失的東西:神話既非根植于過去也不是現代,而是永恒的。它提供智慧而非知識,統一而非碎片,秩序而非混亂,精神慰藉而非不信,意義而非困惑。正如奧登所言,若現代性問題來自特定或承襲的強加統一于經驗之上的假設和元敘事的缺失,那么神話思維就是填補這個空白的新穎大膽的嘗試,并且很多方面都是成功的。
二、神話的范疇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英國社會科學的大本營——不可能成為最先追溯神話思維現象概觀的地方,然而在1952年,古希臘哲學與宗教史家、劍橋大學教師W.K.C.格思里(W.K.C.Guthrie)卻站在那里的講臺上爭辯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講堂里產生的基于實驗的知識需要不同的知識去平衡——這種知識只能來自神話。以“神話與理性”為主題,格思里認為,希臘神話學比任何時候都更具關聯性,原因就是其傳達的永恒智慧。因為“神話思維絕不會徹底消亡”,發現恰當利用神話資源的方法就至關重要了。當然這要避開“壞神話”(bad myth)——打著當代“主義”(isms)的名號,實則利用“模糊抽象語言”的掩蓋讓非理性合法化。他繼續說:“好神話卻相反,它的主要特點是理解簡單的故事和圖像等象征方式傳達的深刻而普遍的真實。由于表達方式具體、獨立且富有想象力,故事及圖像很容易被獻身‘科學方法’的人或者最新的并不存在的‘主義’所無視。”*W.K.C.Guthrie.Myth and Reason:Oration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on Friday,12 December,1952.
格思里的演講極好地總結了20世紀神話思維的兩個主要特征:其一,相信神話提供了理解普遍的形而上學的真實的方法,而這種真實與現代狀況有著深刻的聯系;其二,相信這種真實與科學真實互補而非沖突。
在格思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演講的前一年,特德·休斯(Ted Hughes)開始了他在劍橋的學習。身為學生的休斯完全可能聆聽了格思里關于神話思維的演講,并且很明確的是,由于對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白色女神》(TheWhiteGoddess)入迷以及對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理論和其他資料的興趣,休斯對神話的興趣逐年加深,因此他向兒童文學會議的與會者贊揚神話的價值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話日后會被編入各種選集:
神話與傳說——柏拉圖提出是年輕公民完美的教育材料——可以看作是對內部世界的力量和男人女人不得居于其中的難以應付的外部世界之間博弈的龐大敘述。它們是對理解兩個世界可能性的宏大且極詳細的敘述。它們準確有用,因為它們是對真實認識的原始的真實投射……它們是對兩個世界相互碰撞的地方即內心之事的真實講述。這一點被隨后各個年代富于想象力的人們求助于基本的圖形和圖像所反復驗證。而希臘神話不是唯一的真實神話。神話的定義不言而喻是它承載此種真實。在闡述“隨后的各個年代”的特點都是求助于神話資源時,休斯是在肯定格思里的論點,即“神話思維絕不會徹底消亡”。他們都強調神話的永恒意義,其實是在強調神話作為應對現代生活挑戰的方式其當下的關聯性。[4](P151~152)
因為對這個現代世界里似乎缺失的真理與意義的渴求,格思里和休斯都被神話所吸引。他們的研究和個人經歷使他們確信,神話通過激發想象,總是擁有帶來真理與意義的獨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強調這種聯系的時候,所使用的語言是深入透徹,清楚明白的。格思里認為,神話通過“想象”的方式理解“普遍而深刻的真理”。對休斯來說,神話提供了一種“富于想象的人類”所理解的“真實的認識”。他們提出這個結論,部分基于他們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關于神話的人類學作品的研讀。格思里與一個名為劍橋儀式學派(Cambridge Ritualists)的學者們有一些私人的和專業上的接觸。這個學派學者的著作大多結合了古典文學、考古學和人類學,以期提出神話在古代希臘文化中的作用及其在現代生活中可能的功用等種種新問題。在劍橋大學期間,休斯由英語改學人類學,這一轉變使他越來越癡迷于人類學。通過對人類學的了解,格思里和休斯對神話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們絕對不是此類神話研究者的典型,而是20世紀英國神話思維模式的代表。他們認為,古代神話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認識論效力,且這種效力使得神話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當然,他們也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典型。
機敏的文化評論家們開始注意到20世紀50年代這種普遍存在的神話研究。其中有一些學者,如美國評論家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堅決反對這種傾向。拉夫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他譴責神話研究者們(mythic thinker)不負責任,是違背歷史的“神話狂”(mythomaniacs)[5]。美國文學批評家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則更為公正。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理解神話的吸引力以及這種吸引力的程度。他是二戰后英國最專注、最敏銳的研究者之一。面對眾多如格思里和休斯這樣的思想家和作家對神話價值的贊頌,克默德總結道,“我們的文學文化充滿著神話學思考。”對他而言,這種情狀既是他著迷的源泉,也是他矛盾心理的癥結所在。20世紀60年代,他在這個主題上傾注了大部分精力。他深刻理解神話在當代的吸引力,并試圖用語言來表述自己對神話價值的理解。他的理解幾乎算是對格思里和休斯神話觀的注解。
在神話范疇內,我們可以簡化思考,釋放想象。而這都是科學主義(scientism)所壓制的。……神話所及比智力所及的更為真實。它的天衣無縫取代了現代思維的支離破碎。[6]
在此,克默德強調了幾個重點:神話對想象的吸引力,神話可以表達更高程度的真理,以及現代思想極度缺乏這種真理的理念。他的評價深入到了神話思維現象的核心。
“神話思維”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但還不是歷史學家所熟知的術語。因此,為了證明其運用的合理性,也許有必要給予其一個更為詳細的解釋。無可否認,這個術語是模糊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神話”這個術語本身就是模糊的。筆者無意于提供一個規范的神話定義,或者為神話有著獨特力量或者權威這一論斷而辯白。大量引人入勝的跨學科文獻致力于“神話”這一范疇的定義以及眾多神話理論、神話例子和神話應用的分類。*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defining myth see Chapter 2 of William Doty,Myth:A Handbook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4).Other key works in this body of literature include Bruce Lincoln,Theorizing Myth:Narrative,Ideology,and Scholarship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Robert A.Segal,Theorizing about Myth (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9);idem,ed.,Psychology and Myth,vol.1 of idem,ed.,Theories of Myth:From Ancient Israel and Greece to Freud,Jung,Campbell and Lévi-Strauss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6);idem,ed.,Literary Criticism and Myth,vol.4 of idem,ed.,Theories of Myth:From Ancient Israel and Greece to Freud,Jung,Campbell and LéviStrauss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6);Laurence Coupe,Myth (London:Routledge,1997);and Eric Csapo,Theories of Mythology (Malden,MA:Blackwell,2005).在某些語境下,這一研究是有價值的。所以本研究將試圖論證、量化并分析所謂的“神話永久的力量”(myth’s abiding power)。[7]或者更加明確地說,這個研究的焦點在于解釋為什么在20世紀的英國有這么多研究者相信神話有這種持久的力量。因此,筆者不會為神話下定義,而是如自己所了解的人物那樣來使用這個術語。這是一種研究終極問題的永恒關聯性的解釋性敘事。為了進一步研究神話定義,多數神話研究者都會一致認為,神話是一種神圣的、基本的或者說是原型敘事。這種敘事涉及神靈、英雄、宇宙學或超驗。這些敘事內容回答永在的問題,調和矛盾,引導行動,表達卓絕真理,分散心理壓力,規范文化價值觀。
這無疑是一個靈活的定義,為神話留下了充分的自由。的確,這個概念的模糊性恰恰就是它的部分吸引力所在。舉例來說,人們通常認為,當代的作家能夠創作出具有神話功用的小說。正是這種見解促使神話學者羅伯特·西格爾(Robert Segal)注意到:“‘神話’甚至可能沒有過時,而是在科幻小說中繼續發展,或者融合進了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因此,神話思維不一定限定于原始主義,或者是對創造了遠古神話的古代文化的理想化。
然而從本質上來看,神話研究是一種結合神話或者通過神話研究,探討假定的神話獨特屬性的嘗試。其目的在于創造一種原本缺乏的意義。奧登認為,神話成為現代人需要為他們自己建構的一種用于闡釋經驗的框架。神話研究都基于一種假設,即神話是一種敘事體裁或者思維模式,有著難以定義卻又真實存在的重要性,能夠傳達通過其他方式無法表達的真理。一位神話研究者試圖把這些用語言描述出來,“神話有著深遠的、暗示性的意義,遠非我能掌握。”[8](P976)神話具有一種力量。這種觀點得到普遍認同,因此,“神話”這個術語成為一種有著重要意蘊的修辭手段,進而成為20世紀文化政治學的有效工具。不管是在學術領域還是非學術領域,這個術語的使用都會不可避免地引起爭議。致力于宗教和神話研究的歷史學家布魯斯·林肯(Bruce Lincoln)認為,使用“神話”這一術語的人都堅定地認為,神話的有效性和權威性與其他語篇類型有關聯。這些論斷的得出,是基于對神話原始的真實或者神話作為文化一致性的根源的研究。我們也可以退一步,將神話歸結為原始人的世界觀。在后續的章節中,本研究所涉及的神話研究者們的觀點絕不是僅僅揭示神話的真相,或者將神話只歸結為虛構的故事。
神話研究有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往往是重疊的。第一種正如格思里和休斯所言,神話研究是一種文學研究、藝術研究和哲學研究。這種研究試圖說明,古代神話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然而,這種研究也試圖創造新的神話或者神話敘事。第二種神話研究主要存在于作家的創作領域內。這種研究的典型作家是托爾金。他坦言自己試圖在小說《指環王》(TheLordoftheRings)中創造一個英格蘭神話體系。托爾金認為,英格蘭沒有自己的古代神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嚴重缺失。他的這一信念揭示了神話研究的本質。托爾金認為,英國文化需要與神話緊密結合,以保持文化的穩定和健康發展。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并不只有他一人。這種神話觀是這個時代神話研究的基本前提。
那么,對神話研究者來說,神話不是一種敘事體裁,而是一種強有力的話語形式,其內涵是無法通過其他途徑來傳達的。在文化批評中,研究者們以與神話相對照的方式巧妙揭示其內涵。神話研究者們的文化批評集中于對特定歷史語境中科學至上主義、過度理性主義、世俗化、大眾文化以及現代都市生活的異化等的批判。神話轉向是有道理的。神話比歷史或者科學解釋更能深入地接近真理。而且它還為應對現代性導致的個體心理問題提供了一種解決途徑。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神話思維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模式。通過這種思維模式,人們可以明確地表達現代性焦慮,并且為修正現代性缺陷提供思路。因此,神話研究者們在批判現代性的同時,也在利用神話來建構現代性。對他們而言,在向現代性轉變的過程中,神話表現了所有被壓抑、被消解或者被碎片化的一切。與此同時,神話研究以現代性的理性原則為指導。這并不是H·斯圖爾特·休斯(H.Stuart Hughes)所描述的“對實證主義的反叛”。[9]比如說,托爾金曾不無痛心地強調,他創作并倡導的神話小說“沒有破壞或者侮辱理性;它既沒有削弱對科學真理的渴望,也沒有掩蓋對科學真理的認識”[10](P72)。
三、神話的含義
理解神話研究的本質和范疇,能夠幫助我們通過多種途徑深化并重塑我們對20世紀英國文化的理解。從最根本上說,識別和定義神話研究現象,為我們討論20世紀英國文化政治學提供了一種新的必要的分析方法。盡管從事英國研究的學者們很早就意識到,很多20世紀的研究者都對神話感興趣。然而,他們并不了解這種研究興趣的廣泛性和意義。20世紀英國的神話研究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研究神話的應用如何成為現代主義美學,比如艾略特(Eliot)詩歌的核心特征。*For some recent examples see Michael Bell,Literature,Modernism and Myth:Belief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Roslyn Reso Foy,Ritual,Myth,and Mysticism in the Work of Mary Butts:Between Feminism and Modernism (Fayetteville,AR: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2000);Randall Stevenson,Modernist Fiction:An Introduction (Lexington,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2);Jewel Spears Brooker,Mastery and Escape:T.S.Eliot and the Dialectic of Modernism (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4);Milton Scarborough,Myth and Modernity:Postcritical Reflections (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Laurence Coupe,Myth (London:Routledge,1997).盡管這樣的文學為我們理解現代主義者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并不能幫助我們在更高維度上理解神話在英國文化中的作用。相比之下,第二種研究方法的視角則更為寬廣,比如,試圖追溯J.G.弗雷澤(J.G.Frazer)的《金枝》(TheGoldenBough)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融合了現代主義者的觀點,同時超越了他們。*Examples included John B.Vickery,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Golden Bough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Robert Fraser,ed.,Sir James Frazer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and Brian R.Clack,Wittgenstein,Frazer,and Religio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See also Martha Celeste Carpentier,Ritual,Myth,and the Modernist Text:the Influence of Jane Ellen Harrison on Joyce,Eliot,and Woolf (Amsterdam:Gordon and Breach,1998) is a work in the same vein,though it traces Jane Harrison’s influence rather than Frazer’s.然而,第二種方法也有局限性,在于其關注點很大部分局限于單個文本。盡管這些文本是標志性的、有著重大意義的文本。除了這兩種主要方法,文學研究者當然也甄別出了其他若干文學例證。這些例證說明,神話的自覺應用已經成為英國文學文化的特征,但是并沒有研究者嘗試系統分析這些例證中神話的自覺應用成為文化模式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并沒有看到這樣的研究,比如說,研究類似艾略特和托爾金這樣看起來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因對神話的共同癡迷而產生關聯。*Margaret Hiley’s recent The Loss and the Silence:Aspects of Modernism in the Works of C.S.Lewis,J.R.R.Tolkien and Charles Williams (Zollikofen,Switzerland:Waking Tree Publishers,2011) is perhaps an indication that scholars are beginning to take an interest in how seemingly disparate instances of mythic thinking might,in fact,be part of the same broader pattern.神話研究的范疇允許我們開始挖掘這些聯系,進而將英國文化中那些被遮蔽的研究模式明晰化。
一旦神話研究現象被識別并定義,我們就可以對在任何領域出現的神話研究現象進行研究,并描述它在塑造英國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更具體地說,對神話研究的檢視,為我們理解20世紀英國人如何建構和體悟現代性增加了一個維度。神話轉向是有道理的,因為神話成為了治愈現代性缺憾的“萬靈藥”。神話研究成為定義20世紀英國文化斗爭中的關鍵修辭武器。這個斗爭就是現代性的倡導者和批判者之間的斗爭。透過世俗主義的棱鏡和“兩種文化沖突”(two cultures controversy)來看這場斗爭,相關史學撰述(historiography)一方面把它看作是科學之間的對抗,另一方面把它看作是一種信仰、想象的過去,或者人文學。*Francis Mulhern,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New Left Books,1979).See also Ian MacKillop,F.R.Leavis:A Life in Criticism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and Stefan Collini,“Cambridge and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Cambridge Contributions,ed.Sarah J.Omr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2~64.傳統上,宗教話語為批判現代性提供了基礎,但是其合理性卻在這個世紀被侵蝕殆盡。因此,許多人,比如利維斯就和他的弟子們從宗教轉向了人文學。為尋找一種替代來回應現代性,很多研究者和作家都轉向了神話研究話語,而不是昔日輝煌的宗教,或者人類學。這種結合神話研究來檢視這場斗爭的做法,使我們對這場斗爭的理解復雜化。
然而,就抵制現代性和神話的二元闡釋法(binary explanatory scheme)來說,神話研究者的這種做法是復雜的、難以理解的。對他們而言,神話不是現代性的替代或者解藥,而是與之關系緊張。他們轉向神話,不是為了逃避現代性,而是要在神話中為現代性超驗主題找到空間。對于有些人來說,神話研究是一種強化宗教,或者人類學,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策略。這一圖景因此變得更加復雜。如果在前現代文化(premodern cultures)中,神話已經是毋庸置疑的存在,那么批判地、自覺地研究神話一定是現代性的一個標志。神話研究者們在此檢視的活動說明,現代性不是批判神話的過時,或者懷疑神話所揭示的真理。然而,它確實需要那些利用神話的人記住奧登的話,“為了他們自己,審慎對待神話。”
本書的核心問題結合了不斷演進的大量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對現代性特征的合理化過程與人的精神發展(spiritual impulses)的不一致提出質疑。毫無疑問,現代性是一個令人頭疼的術語。歷史學家也無法就其定義達成一致,或者就其在歷史上的發展進行廣泛對比。然而,還是可以粗略地給現代性下一個定義。現代性通常被喻指為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世俗主義、城市化、專業化、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等的綜合發展。并不是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用相同的方式來闡述或者強調這些過程。但正如邁克爾·沙羅(Michael Saler)最近在對相關史學的評價中指出的,“現代性有這樣一個特點,……自18世紀以來,這個特點被知識分子們一再論及:現代性是‘祛魅’(disenchanted)。”[11]換句話說,理性、科學的進步和合理化過程導致人們認知世界方式的改變。這些認知方式關乎超驗意義、精神追求、疑惑和超理性。現代世界是一個祛魅的世界。這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1917年表達的一個非常著名的觀點[12]。但在此之前,這種觀點就已經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晚期的浪漫主義時期。在整個19世紀,這種觀點持續發展。從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到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這些文化悲觀主義論者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在此之后,沙羅又提出了一種新的對現代性“反唯名論”(antinominal)理解,旨在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邏輯。而這一邏輯一直以來都是現代性研究的典型特征。然而,新的跨學科研究文獻告訴我們,“現代性的特征是,各種看似矛盾的力量與觀點之間存在著內涵豐富的張力。現代性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包含著懸而未解的矛盾、對立或悖論。現代性是一體兩面。”此類新的著作有對為現代性祛魅的范例敘事,如簡·班尼特(Jane Bennett)《現代生活的賦魅》(TheEnchantmentofModernLife)的切中剖析;也有更為具體的歷史案例研究,這些歷史案例研究通過現代性賦魅的有趣實例揭示了此種敘事的不足。[13]
在對神話思維的研究中,新的研究對象的加入會引發對現代性和賦魅新的理解。研究現代英國歷史上現代性與賦魅之互動的最新作品包括:艾莉森·溫特(Allison Winter)的《被催眠: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心靈力量》(Mesmerized:PowersofMindinVictorianBritain)、丹尼爾·皮克和斯文加利(Daniel Pick and Svengali)的《網絡:現代文化中的異形魔法師》(Web:TheAlienEnchanterinModernCulture)、埃里克斯·歐文(Alex Owen)的《賦魅之地:英國的神秘主義和現代文化》(ThePlaceofEnchantment:BritishOccultismandtheCultureoftheModern)以及邁克爾·薩勒(Michael Saler)的《仿佛:現代賦魅和虛擬現實的文學史前史》(AsIf:ModernEnchantmentandtheLiteraryPrehistoryofVirtualReality)。*Alison Winter,Mesmerized:Powers of Mind in Victorian Britain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Daniel Pick,Svengali’s Web:The Alien Enchanter in Modern Cultur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Alex Owen,The Place of Enchantment:British Occultism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odern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and Michael Saler,As If:Modern Enchantment and the Literary Prehistory of Virtual Rea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Though not limited to the British context,see also Joshua Landy and Michael Saler,eds.,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Secular Magic in a Rational Age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這些作品通過對催眠術、神秘主義以及嘲諷性想象(ironic imagination)的分析,對英國現代性的輪廓提供了非凡的見解。但這三個研究對象遠不是現代賦魅唯一的表達方式。筆者認為,神話思維可以與它們同時作為對現代性的創新回應,一種在“世俗時代”保持超驗的策略。*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phrase are dealt with perceptively and exhaustively in 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但是,神話學更多地是為現代性中的超驗創造可能而不是反對它。因為神話可以簡單定義為不被經驗驗證的話語范疇,神話思維以一種被認為與現代理性相容而非對立的方式表達精神驅動。
最后,本研究也可以被看作是對神話與現代性關系的新生史學撰述(historiography)的貢獻。如上所述,研究20世紀文學的學者長期以來意識到,神話的自覺和有意使用是現代主義文學文化的核心,現代主義關于神話的思考持續吸引學者的關注。也許除了與這些最新著作一樣有價值,它們還強化了一種認識:現代主義者在20世紀似乎獨享神話學。然而,近年來有一些跡象表明,歷史學家開始著手研究神話與現代性的相互作用,這些方式超越了我們對英國現代主義者的了解。似乎這種將神話作為應對現代性的靈丹妙藥的看法是18世紀末以來西方思想史的共同特征。也許,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喬治·威廉姆森(George Williamson)的《德國神話的渴望》(TheLongingforMythinGermany),其中詳細介紹了自浪漫主義時期開始,知識分子如何利用神話作為一種話語,來闡明對過渡到現代社會失去的東西的遺憾,以及對未來社會將審美、宗教和公共生活融為一體的憧憬。*George S.Williamson.The Longing for Myth in Germany:Religion and Aesthetic Culture from Romanticism to Nietzsche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For other examples of the emerging intere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th and modernity see Andrew Von Hendy’s sweeping,impressive study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Myth (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Dan Edelstein and Bettina R.Lerner,eds.,Myth and Modernity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which focuses on uses of myth in modern France;and Angus Nicholls,“Anglo-German Mythologics: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and Modern Theories of Myth in the Work of Baldwin Spencer and Carl Strehlow,”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no.1 (February 2007):P83~114.威廉姆森似乎相信——根據什么理由尚不清楚——神話在德國比其他地方表現得更突出。這個觀點似乎尚有爭議,但它卻突顯出比較歷史研究的機遇:在其他背景下神話思維是如何形成的?它在不同地方的變化如何?本書是向比較研究方向邁出的一步,與威廉姆森的《神話的渴望》等研究相結合,對英國神話思維的研究能夠為神話和現代性問題貢獻新的見解。
參考文獻:
[1]W.H.Auden.Yeats as an Example[J].Kenyon Review,1948(2).
[2]Dan LeMahieu.A Culture for Democracy:Mass Culture and the Cultivated Mind in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3]Lawrence Rainey. The Annotated Waste Land with Eliot’s Contemporary Pros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4]Ted Hughes.Winter Pollen:Occasional Prose[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4.
[5]Philip Rahv.The Myth and the Powerhouse[J].Partisan Review, 1953(20).
[6]Frank Kermode.The Myth-Kitty[J].Spectator,1959(September 11).
[7]Elizabeth M.Baeten.The Magic Mirror:Myth’s Abiding Power[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8]Walter Hooper.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C.S.Lewis:Family Letters 1905—1931(Volume I)[M].London:Harper Collins,2000.
[9]H.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58.
[10]J.R.R.Tolkien.On Fairy-Stories [A].C.S.Lewis.Essays Presented to Charles William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11]Michael Saler.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A Historiographic Review[J].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6(3).
[12]Max Weber.Science as a Vocation[A].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13]Jane Bennett.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Attachments,Crossings,and Ethic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