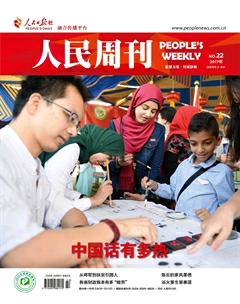中共的抗戰經費從何而來
南晨
2017年是抗戰全面爆發80周年。在艱苦卓絕、全民奮起的抗日戰爭中,中日兩國較量的不僅僅是軍事,還是包括經濟在內的綜合實力。面對經濟實力強大、蓄謀已久的日本侵略者,面對艱苦異常的抗戰環境,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堅持下來并取得最后勝利的呢?在抗戰經費問題上,從依賴外援到生產自救,中共在領導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自身也走過了一條從發展到蛻變的路。
初到陜北,毛澤東為中央紅軍四處借錢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長征后到達陜北吳起鎮。雖說當時紅軍的目標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陜北,連生存下去都困難。毛澤東、周恩來讓當時的紅軍采辦處主任楊至成盤點了中央紅軍的家底,7000多人的中央紅軍只有1000多塊大洋。周恩來很著急:這么多人要吃飯,將來還要打仗,從哪里去找錢?
這時,毛澤東突然想到了幾天前見過的紅15軍團(原為陜北的紅軍部隊)軍團長徐海東,就寫了個2500元的借條,讓楊至成拿著去找徐海東。
徐海東看到借條后,立即叫人把供給部部長查國楨找來,問他:“咱們現在總共還剩多少錢?”“還剩7000塊大洋。”“那好,留下2000,5000給中央。”
第二天,紅15軍團供給部就派人把5000塊大洋送到中央紅軍后勤部,并抽出許多重要物資和大量駁殼槍送去,而且命令每個班挑一把最好的機槍送給中央紅軍,就連最精銳的騎兵團,都直接交給中央指揮。
為了渡過難關,1936年3月,毛澤東又想到了宋慶齡,希望通過她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借一筆錢。然而,此時的宋慶齡與宋子文早已分道揚鑣。宋慶齡只好將孫中山逝世撫恤金全部取出,又將自己唯一的一處寓所——莫利愛路寓所典押出去,這才湊夠了5萬美元寄給中共中央。
中共到底領了國民政府多少抗戰經費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應中共的要求,1937年1月,蔣介石指示顧祝同:“在政府立場,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萬元軍費,由楊虎城間接領發,共軍番號暫且照舊。”后來,顧祝同派人將善后款50萬送抵西安,經楊虎城交送給周恩來。
1937年8月,國共合作抗戰后,八路軍(4.5萬人的編制)1937年度月領經費30萬元(法幣,當時法幣1元合抗戰前一塊銀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費5萬元,醫藥補加費1萬元,米津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合計月發63萬元,后略有增加,但總數沒超過75萬元。
新四軍方面,按照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時的要求,每月應發給新四軍經費18萬元。實際只給8萬元,后經葉挺和項英多次要求,自1938年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萬元。1939年開始,每月另發臨戰費2.2萬元。
此外,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戰場時國民政府還分別撥發了20萬元和1萬元的開拔費。
但是,隨著八路軍和新四軍隊伍的迅速擴大,再加上物價飛漲,這些費用越來越不夠用了。以八路軍為例,1940年八路軍已發展到40多萬人。其間,中共多次向國民政府要求擴大編制,增加軍餉,但國民政府始終不予批準。由于經費嚴重不足,國共兩軍待遇相差很多。當時,國民黨軍隊師長每月一般發800元,連長發100多元,而八路軍師長每月只發5元,連長發3元,即便這樣低的薪餉標準也常常不能按時發放。對此,毛澤東激憤地說,“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同(日軍)四十個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卻只領到七十三萬塊錢餉”,而且“票子跌價,打個二折半,每人每月不上一塊錢”。
1940年12月,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宣布停發延安方面的軍餉和物資。新四軍的軍費,則是1941年1月以后停發的,因為這個月新四軍領完最后一筆軍餉和物資后,就爆發了皖南事變。此后,中共所屬部隊的經費、給養都靠自己解決。
對此,毛澤東曾回憶說:“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數十萬兩黃金送延安
全面抗戰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總計221萬多美元,扣除英鎊匯率下降造成的損失和沒有兌現的40萬美元,中共中央總共收到180多萬美元。
1937年秋,八路軍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等一系列的勝利,為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國內各階層及一些海外華人華僑紛紛解囊捐助。據陜甘寧邊區的統計,僅從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個月時間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達法幣130多萬元。
當時,各部隊(包括一些敵后抗日武工隊、縣大隊、區小隊)的經費不但要自己解決,有條件的還要上繳支援中央。另據八路軍供給部的統計,在1937年至1941年,各部隊上繳的捐款有賬可查的共計892.4萬元。
說起地方對黨中央的經費支持,山東的膠東特委貢獻很大。招遠盛產黃金,是中國第一個年產萬兩黃金的縣,可惜七七事變后淪陷于日軍之手。為了虎口奪金,中共膠東特委成立了一個特殊的常設機構——膠東黃金工作委員會。在這個組織的領導下,礦工們有時用爛石頭換下高品位金礦石,有時干脆在礦井下將金礦石砸碎帶出來,甚至出現“同一座礦山,鬼子在南邊掘進,中共在北邊挖洞”的狀況。
中共膠東特委還通過創辦秘密金礦,組織地方武裝伏擊日軍的運礦車、運金車,同時,秘運礦石到中共控制的煉金廠,再將成品金通過地下交通站運往延安。
由于一路上要穿越敵人的封鎖線,因此選派的八路軍戰士一般都身穿特制衣服,將黃金裝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攜帶10兩左右。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招遠人民為中共領導的抗戰貢獻黃金多達數十萬兩。僅1940年,工會書記蘇繼光和陳文其等人就秘送兩萬多兩黃金至延安。
開展生產自救,支援前線
接受援助之外,1940年春,任弼時還作了一番調查,向政治局提出一個方案:一是軍隊實行屯田制,生產自給;二是開荒;三是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延安著名的大生產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大生產運動開展3年后,邊區財政開支的64%實現自給。為了解決抗戰經費困難和邊區財政困難,中央和邊區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給各機關部隊一部分生產資金讓其各自經營以解決經費困難;西北鹽池、定邊、綏德是有名的產鹽區,邊區政府發動群眾馱運食鹽出口,如計劃出口60萬馱,其中6萬馱為公鹽,分配各縣,由群眾義務馱運;統一產銷鹽價,其收入歸軍委,作為軍費和軍委生產保證;發行建設救國公債618萬元;征收救國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解決人員和馬匹糧草;禁止法幣,發行邊幣1054萬元。稅收也是1941年后邊區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
延安時期的生產自救,一方面解決了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中共所屬抗日部隊的經費問題;另一方面也為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培養了一種自我造血的功能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后者,在解放戰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1946年,蔣介石用30萬大軍將6萬人民解放軍中原部隊壓縮在鄂東宣化店為中心的狹小地區,新四軍五師的李先念一再向中央告急:“財經給養有朝不保夕之慮。”“年關在即,無米為炊,萬萬形勢,生活危險之至。”為了救急,任弼時屢電各解放區多方籌款接濟,毛澤東也指定華中、山東、晉冀魯豫、晉察冀4區“負擔五師一個月經費”,五師才渡過難關。應該說,沒有抗戰時期打下的經濟基礎,各解放區也沒有能力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
得道者多助。8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主動扛起全民族抗戰的大旗,無論環境多么艱難,為將日本侵略者趕出國門,無數共產黨人以命相搏,血灑戰場,得到了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擁護和支持。
特別是1941年后,中共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逐步探索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抗戰時期也是中共經濟管理史上的一個轉折期。
到1945年春,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武裝力量達到91萬人,不脫產民兵200萬人,抗日根據地總面積達到95萬平方公里,總人口9550余萬。這些就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敢于同國民黨正面交鋒,并最終贏得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