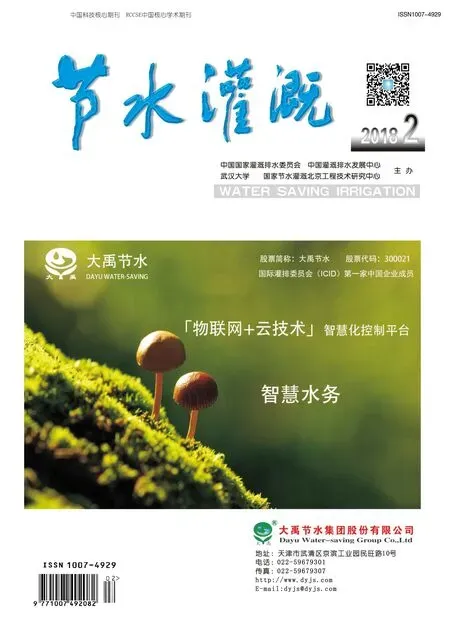基于灰色理論—BP神經網絡方法的表層土壤容重預測
郭李娜,樊貴盛
(太原理工大學水利科學與工程學院,太原 030024)
土壤容重一般指土壤干容重,又稱為土壤密度,是干的土壤基質物質的量與總容積之比,是表征土壤物理狀況指標的重要參數。表層土壤容重一般指地表以下20 cm深度范圍土層的土壤容重,是影響水分、鹽分及養分隨徑流在土壤中運移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獲取土壤容重的常用方法為傳統環刀法,在農田中用標準環刀取樣后帶回實驗室烘干稱重后計算土壤容重,此種測量方法雖然操作過程簡單,但對于大面積農田土壤容重的持續跟蹤采樣與監測不僅工作繁重,而且耗時耗力,無法實時且快速地采集農田信息。近年來,國內外一些學者致力于通過利用土壤常規理化參數對土壤容重進行預測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Rawls、Adams[1,2]等研究發現,土壤質地和有機質是影響土壤容重的主要因素;Curtis和Post[3]、Huntington[4]和Kaur[5]等多位學者根據土壤質地、有機質含量等資料,相繼提出13種土壤傳遞函數用于預測土壤容重;韓光中[6]等利用現有的土壤數據庫回歸分析建立了我國主要土壤類型最適宜的容重傳遞函數。田耀武[7]等利用蘭陵溪流域森林土壤調查數據庫,建立了土壤有機碳、有機質與容重之間的回歸模型。劉繼紅[8]等指出對于不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剖面垂直深度和不同發生層次的土壤,其容重PTFs的預測變量及相應參數各不相同。BP神經網絡方法已被廣泛地應用于眾多領域的預測研究,李昊哲[9]等以土壤基本理化參數為輸入變量,建立了鹽堿土壤Kostiakov入滲模型參數的BP預報模型。侯澤宇[10]等利用小波神經網絡的分析方法建立了降雨量的BP預測模型。王巧利[11]等以復合圓錐指數儀為工具,建立了BP神經網絡的土壤容重預測模型。
目前,現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對自然土壤容重的預測,且輸入變量少,導致預測精度較低。在實際耕作條件下,影響表層土壤容重的因素涉及多個方面,除了土壤質地和有機質以外,降雨量、灌溉水量、全鹽量及黃土的結構變形對表層土壤容重也有明顯影響[12]。灌溉和降雨后由于表層土壤含水量增大,黃土的濕陷性和壓實性使其結構改變,導致表層土壤容重發生變化;表層土壤隨灌溉和降雨的進行經歷著反復的脫鹽和積鹽過程,改變了土壤的理化特征和結構,從而影響表層土壤的容重。
本文針對大田耕作土壤,考慮增加累積接收水量和全鹽量等因素,采用灰色關聯理論方法,從分析表層土壤容重與各影響因素之間關聯關系入手,利用BP模型在非線性映射和表達不確定性關系能力方面的強大優勢,建立基于灰色關聯理論的表層土壤容重BP預報模型,實現利用常規土壤理化參數和累積接收水量對土壤表層容重的多變量預測,一方面豐富了土壤傳輸函數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可為科學進行農田農事和灌溉管理提供技術支撐。
1 樣本的獲取
1.1 試驗區及土壤條件
本文所涉及的樣本數據來源于大田耕作土壤的年度跟蹤試驗。項目試驗在山西省黃土高原區的15個縣市區進行。數月長度的試驗期內,試驗區各試點總降雨量變化范圍在300.50~428.05 mm之間。種植冬小麥的試點在作物生長期內灌水3次,分別在10月和第二年的4月、5月,平均灌溉定額為265 mm;種植蔬菜的試點約20 d灌溉一次,平均灌溉定額為360 mm;種植玉米的試點多數無灌溉,部分試點在7月和9月灌溉兩次,平均灌溉定額為170 mm。
試驗區土壤種類多樣,有紅黏土、棕壤土、栗鈣土、栗褐土和黃綿土等,土壤質地包括砂質壤土、粉砂質壤土、砂質黏壤土、壤土等,其中表層土壤黏粒含量、粉粒含量、砂粒含量的變化范圍分別為0.01%~17.54%、30.20%~66.14%、28.63%~69.57%;表層土壤含水率的范圍為7.81%~39.02%,有機質含量變化范圍在0.18~2.74 g/kg之間;全鹽量含量變化范圍在682.30~5 606.28 mg/kg之間,表層土壤容重變化范圍在1.09~1.63 g/cm3之間。
1.2 試驗方案與方法
試驗對大田耕作土壤表層容重和基本理化參數進行跟蹤測定,測定項目包括:分層(0~2、2~10、10~20 cm)土壤干容重、體積含水量、有機質含量和全鹽量等,并配套監測試驗期內試驗區降雨量和灌溉量等。試驗從2015年4月下旬開始到2015年11月中旬結束,監測頻次15 d左右。
表層土壤容重采用環刀法進行測定,并計算以土層厚度為權重的加權平均容重作為樣本中采用的表層土壤容重值;土壤含水率測定采用烘干稱重法,再經容重值換算成體積含水率;土壤質地通過篩分+比重計法得到篩分曲線,然后分析土壤的顆粒級配得到;土壤有機質含量的測定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來測定,土壤有機質含量乘以0.58得到土壤有機碳含量[13];土壤累積接收水量即為試驗區累積降雨量和灌溉量之和,其中試驗區降雨量采用氣象站設施觀察得到,灌溉量通過記錄當地農戶農事作業資料獲得;土壤全鹽量測定通過殘渣烘干質量法測定[14]。
1.3 樣本數據的建立
基于對試驗數據的整理,建立了148組具有代表性的土壤樣本數據,并隨機預留10組數據用以模型精度檢驗。在全部試驗數據資料中隨機選取3組來自不同試驗田的土樣,表層土壤容重和相對應的土壤黏粒、粉粒和砂粒含量、有機碳含量、體積含水率、全鹽量和累積接收水量等參數如表1所示。

表1 3組試驗點樣本數據
2 BP神經網絡模型的建立
2.1 影響因子模糊關聯度分析
定性分析認為,土壤質地、有機碳含量、體積含水率、全鹽量和土壤累積接收水量等是影響土壤容重的重要因子,但各個影響因子對土壤容重的影響程度如何需要研究分析。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可以樣本數據為依據,利用灰色關聯理論求出灰色關聯度,以此來描述因素間關系的強弱和次序。灰色關聯度的分析結果可為合理地選擇BP神經網絡預報模型的輸入因子提供依據。
在試驗數據資料中隨機選取30組數據作為計算樣本,分三步進行影響因子模糊關聯度分析。
第一步確定分析序列,將土壤容重值作為母因素Y,將土壤黏粒、粉粒和砂粒含量、有機碳含量、體積含水率、全鹽量和累積接收水量作為子因素X1、X2、X3、X4、X5、X6、X7,建立公式(1)和(2)所示的分析序列。
Y=(y1,y2,…,yk,…,yn)
(2)
式中:m為樣本數量,本文樣本數量為30;n為子因素數量,本文選取7個子因素;k為第k組樣本。
第二步,對所選樣本序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
(4)
式中:1 ≤i≤n,1≤j≤m,k為第k組樣本。
第三步,計算關聯系數,R=(ξij)m×n,其中:
(5)
式中:ξij為關聯系數;R表示關聯系數的m×n階矩陣;ρ為分辨系數,一般取0.5。
各因素關聯度計算公式為:
(6)
式中:φ0i為關聯度。
將選取的 30 組樣本數據代入上述公式,計算出表層土壤容重各個影響因子間的關聯度如表2所示。

表2 表層土壤容重影響因子關聯度計算結果表
一般關聯度大于等于0.8時,子序列與母序列關聯度很好;介于0.6與0.8之間關聯度好;小于0.5時,基本上不相關[15]。由表2可知,影響土壤容重的7個參數對于表層土壤容重的關聯度都大于0.6,關聯度屬于好和很好,關聯度排序為:φ1>φ2>φ7>φ4>φ5>φ6>φ3。為保持輸入變量之間的獨立性,從總和為100%的黏粒、粉粒和砂粒含量中選擇關聯性較好的粉粒含量和砂粒含量作為表征土壤質地的參數。據此最終選定土壤粉粒含量、土壤砂粒含量、累積接收水量、體積含水率、有機碳含量和全鹽量6個影響表層土壤容重的參數作為BP神經網絡預報模型的輸入變量。
土壤容重與質地有密切關系,土壤中黏粒、粉粒和砂粒含量決定了土體中大孔隙數量和疏松程度,從而影響土壤容重;隨著土壤中有機碳含量的增多,土壤微生物活動更為劇烈,土壤孔隙率增大,土質疏松多孔,土壤容重值較小;耕作層土壤由高含水量到低含水量的變化過程中,土壤干容重呈增大趨勢;灌溉和降雨改變了表層土壤含水量,黃土的濕陷性和壓實性使其結構改變,導致表層土壤容重發生變化;表層土壤隨灌溉和降雨的進行經歷著反復的脫鹽和積鹽過程,改變了土壤的理化特征和結構,從而影響表層土壤的容重。
2.2 BP神經網絡的設計方法
(1)BP神經網絡的結構。BP神經網絡是一種使用較為廣泛且成熟的人工神經網絡模型,一般具有3層或3層以上的神經網絡結構[ ]。本文建立的BP神經網絡模型由輸入層、隱含層及輸出層組成。根據前文灰色關聯度的分析結果,確定的輸入參數有6個,故輸入層的神經元個數為6,輸出參數為1個,輸出層神經元個數為1;中間隱含層神經元數目需要經過多次迭代計算才能得出,通過逐漸增加隱含層節點數,反復計算與迭代訓練,當模型隱含層的神經元數目等于20時最終達到模型的目標精度,因此建立的關于土壤容重的BP神經網絡拓撲結構為6∶20∶1。
(2)樣本預處理。為了確保輸入輸出變量的同等重要性并加快樣本的迭代運算速度,需要對輸入的樣本值進行標準化處理,使輸入值落在(0,1)之間,選取公式(7)對輸入參數進行預處理。
(7)
式中:y為處理后樣本值;x為輸入樣本值;xmin為建模樣本最小值;xmax為建模樣本最大值。
(3)函數選取和參數設定。分析所要處理的數據后,基于Matlab7.0神經網絡工具箱中newff函數,選擇學習速度較快且單次迭代誤差較小的trainlm函數作為學習函數;基于sigmoid函數非線性映射能力強的優點加之輸入值進行了標準化處理,選取正切函數tansig作為隱含層的激活函數,線性函數purelin作為輸出層的激活函數。本文所訓練的模型參數設定如下:最大學習迭代次數為1 500次,學習率0.01,訓練精度為0.000 5。
2.3 表層土壤容重BP預測模型的建立
本文根據已測得樣本利用軟件Matlab7.0建立的BP網絡模型如下所示。
net=newff(minmax(trainput),[20,1],
{'tansig', 'purelin'}, 'trainlm')
(8)
式中:net為所建立的BP神經網絡;newff為Matlab7.0生成的BP神經網絡函數;trainput為輸入向量;min max(trainput)為表征輸入向量范圍的向量矩陣;[20,1]表示隱含層與輸出層神經元個數,本文的輸出值為表層土壤容重;{‘tansig’,‘purelin’}分別為隱含層和輸出層的激活函數形式;‘trainlm’為網絡的訓練函數形式。
BP神經網絡的訓練結果如下所示。
γ=purelin(iw2(tansig(iw1p+b1))+b2)
(9)
p=[β1,β2,θ,Q,ψ,L]
(10)
式中:γ為輸出的表層土壤容重值;iw1、iw2分別為模型輸入層到隱含層的權值和隱含層到輸出層的權值;b1為模型輸入層到隱含層的閾值;b2為模型隱含層到輸出層的閾值;β1為粉粒含量;β2為砂粒含量;θ為體積含水率;Q為有機碳含量;L為累積接收水量。
BP神經網絡預報模型iw1、b1、iw2、b2組成的矩陣數值表見表3。

表3 預報模型矩陣數值表
3 BP模型的預測結果與精度檢驗
3.1 建模樣本的BP模型的預測結果與精度檢驗
對建模的148組樣本數據進行BP神經網絡預測,根據程序運行的結果得出:當訓練步數為200步時,訓練精度為9.997 4×10-5,小于5×10-4,達到設定的目標精度要求。計算預測值與實測值間的絕對誤差和相對誤差并進行精度對比,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表層土壤容重預測結果與誤差分析表
從表4可以看出,表層土壤容重預測值與實測值的平均值相同,說明本文選用148組數據建立的BP模型整體上預測效果較好,其相對誤差平均值為0.414 2%,最大值為12.368 6%,最小值僅為0.000 6%,通過148組表層土壤容重預測值與實測值的誤差精度對比可知,本文選定灰色關聯度較高的土壤粉粒含量、土壤砂粒含量、累積接收水量、體積含水率、有機碳含量和全鹽量6個影響土壤容重的參數作為輸入參數建立BP預測模型是合理的,與實際情況相符,并且預測模型精度很高。
3.2 驗證樣本的預測結果與精度檢驗
為了檢驗模型的預測精度,計算隨機預留的10組數據預測值與實測值的相對誤差和絕對誤差,計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預報模型檢驗結果分析表
由表5可以看出,隨機預留的10組數據表層土壤容重的預測值與實測值的平均值基本一致,相對誤差的平均值為1.046 3%,最大值為4.300 8%,最小值為0.006 2%,精度較高,誤差完全在可接收的范圍之內,計算結果表明,利用表層土壤粉粒含量、砂粒含量、累積接收水量、體積含水率、有機碳含量和全鹽量對表層土壤容重進行預測是可行的,預測值與實際相符且預測精度很高,可滿足實際農業生產活動需要,為獲取黃土高原區土壤參數提供依據。
4 結 語
(1)基于灰色理論—BP神經網絡的方法建立表層土壤容重預測模型是可行的。灰色關聯理論的方法,量化各因素對表層土壤容重的影響程度,有針對性地對影響因素評判和取舍,降低了輸入樣本的維數,優化了模型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神經網絡模型的預測精度,為土壤容重的預測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2)以表層土壤粉粒含量、土壤砂粒含量、累積接收水量、有機碳含量、體積含水率、和全鹽量作為輸入變量的土壤傳輸函數預測可獲得較理想的預測精度。以關聯度較好且相互獨立的6個影響參數作為輸入因子所建立的BP神經網絡模型,預測值和實測值之間相對誤差的平均值為0.41%,預留10組檢驗樣本相對誤差的平均值為 1.05%,預測精度高,預測誤差小,實現了利用常規土壤理化參數和累積接收水量對土壤表層容重的有效預測,豐富了土壤傳輸函數理論的發展,為科學指導農田農事和灌溉管理提供理論支撐。
本文所建立的灰色BP神經網絡預報模型,實現了對黃土表層土壤容重的高精度預測,但所預測是0~20 cm土壤的加權平均容重,為提高表層土壤容重預測在農田農事和灌溉管理中的使用價值,應對分層土壤容重的預測還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1] Rawls W J.Estimating soil bulk density from particle size analysis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J].Soil Science,1983,135(2):123-125.
[2] Adams W A.The effect of organic matter on the bulk and true densities of some uncultivated podzolic soils[J].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1973,24(1):10-17.
[3] Curtis R O,Post B W.Estimating bulk density from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some vermont forest soils[J].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1964,28(2):285-286.
[4] Huntington T G,Johnson A H,Siccama T G.Carbon,organic matter and bulk density relationship in a forested spodosol[J].Soil Science,1989,148(5):380-386.
[5] Kaur R,Kumar S,Gueung H P.A pedo-transfer function(PTF)for estimating soil bulk density from basic soil data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existing PTFS[J].Australian Journal of Soil Research,2002,40(5):847-857.
[6] 韓光中,王德彩,謝賢健.中國主要土壤類型的土壤容重傳遞函數研究[J].土壤學報,2016, 53(01):93-102.
[7] 田耀武,黃志霖,肖文發,等.三峽庫區蘭陵溪流域森林土壤有機碳、有機質與容重間的回歸模型[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16,37(1):89-95.
[8] 劉繼紅,蘭傳賓,陳 杰.區域土壤容重轉換函數構建與預測結果評價——以河南省封丘縣為例[J].土壤通報,2013,44(1):77-82.
[9] 李昊哲,樊貴盛. 鹽堿土壤Kostiakov入滲模型參數的BP預報模型[J].中國農村水利水電,2017,(7):49-53
[10] 侯澤宇,盧文喜,陳社明.基于小波神經網絡方法的降水量預測研究[J].節水灌溉,2013,(3):31-34.
[11] 王巧利,林劍輝,許彥峰.基于BP神經網絡的土壤容重預測模型[J].中國農學通報,2014,30(24):237-245.
[12] 程詩念,樊貴盛.玉米生育期內不同覆膜對黃土表層容重變化特性的影響[J].節水灌溉,2017,(6):26-29.
[13] WANG S Q,ZHOU C H,LIU J Y.Carbon storage in northeast China as estimated from vegetation and soil inventories[J].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2,116(1):157-165.
[14] 南京農學院.土壤農化分析[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80.
[15] 郝彬彬,李 沖,王春紅.灰色關聯度在礦井突水水源判別中的應用[J].中國煤炭,2010,36(6):20-22.
[16] 趙西寧,王萬忠,吳普特,等.坡面入滲的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研究[J].農業工程學報,2004,20(3):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