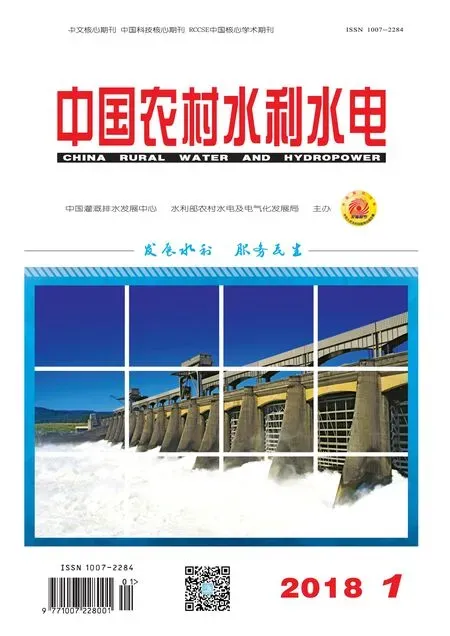基于區域排水模型的地下空間內澇危險性評估
王 渲,劉 柳,方 正
(武漢大學土木建筑工程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0 引 言
城市建設向地下空間擴展是緩解建設及交通用地緊張的必由之路。據統計,發達國家地下空間利用率已達40%~60%[1]。近年來,暴雨頻繁造成地鐵、隧道等地下空間內澇事件,如2012年颶風“桑迪”導致美國曼哈頓數條隧道被淹沒。面臨暴雨侵襲,地下空間發生內澇的危險性大、防澇難度大、損失慘重。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2-8]對城市地下空間內澇開展了長期研究:Tada K在2005年提出地表及地下空間聯用的蓄水池模型較準確地重現了福岡市內澇事件,并在2009年提出地面采用2D非穩定流水力模型、地下空間沿用蓄水池模型,得到的耦合模型能夠預測城市內澇風險性;Ishigaki T、AsaiY對地下空間內澇中的人員逃生課題開展試驗研究,得到各類人員逃生的臨界水深及流速條件,提出逃生路線及策略;Yoneyama N通過模型實驗及VOF數值計算對比研究了小型地下空間洪水演進特性及危險性。Hashimoto H[9, 10]提出的2D城市內澇模型考慮地面阻力及建筑物拖曳力兩項阻力,通過實測的積水深度率定模型中的曼寧糙率n及建筑物拖曳力系數CD,并提出對于小型地下空間而言,澇水侵入體積、流量、充滿時間為風險評估的重要參數,而對大型地下空間而言,內澇風險評估的重要參數為積水深度及水流速。Oertel[11]將地下空間分為洪水、地下室、樓梯、出入口四個模塊,劃分計算網格求解。莫偉麗[12]采用VOF模型模擬地鐵站雨水入侵過程;申若竹[13]采用全尺寸樓梯模型及VOF模型研究出入口樓梯的水流特性。
現有地下空間的內澇研究多用水動力學方法直接求解地下空間雨水入侵特性,極少做區域排水過程的產匯流計算。一方面,內澇由超過城市排水能力的暴雨造成,故排水系統是城市內澇風險評估的主體。另一方面,地下空間區域排水管網的排水能力、出入口檢查井溢流及地面積水情況是導致雨水入侵地下空間的直接因素。因此,將區域排水系統納入地下空間內澇計算模型,完整計算雨水產匯流及侵入地下空間的水文水力學過程是必要的。基于區域排水模型的地下空間內澇模擬方法能夠預測不同降雨強度下地下空間的內澇危險性,可為內澇防治及應急救援提供依據。
1 理論基礎
1.1 區域排水模型
利用區域排水模型對城市內澇進行計算包括4個部分:降雨產流計算、地表匯流計算(水文學模型)、管網匯流計算及內澇演進計算(水動力學模型)。

圖1 區域排水模型計算流程Fig.1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drainage model

圖2 非線性水庫模型示意Fig.2 The nonlinear reservoir model
1.1.1 地面產匯流模型
城市下墊面分為透水、不透水面兩部分。對于不透水面,產流為雨量扣除填洼、蒸散發等損失量[14],模型中采用徑流系數法表征徑流量。對于透水面如綠地等,除蒸散發外,主要初損來自于土壤下滲,采用Horton下滲模型計算。集水區總產流量即為透水及不透水表面產流量的總和。
地表匯流計算中應用最廣泛且效果較好的是非線性水庫模型[14],它采用運動波方程計算坡面流,通過聯立連續方程(式1)和曼寧公式(式2)求解:
(1)
(2)
式中:V為地表滯蓄水量,m3;d為水深,m;A為地表面積,m2;i*為凈雨強度,mm/s;Q為出流量,m3/s;W為集水區漫流寬度,m;n為地表曼寧系數;dp為地表最大洼蓄深,m;S為集水區平均坡度,%。
1.1.2 管網匯流模型
為了模擬管渠的回水、逆流及有壓流等復雜流態,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完整的一維圣維南方程組(動力波法)[15]:
(3)
(4)
式中:Q、A、h分別為過水斷面流量、面積、水深;K為流量模數,m3/s。
1.1.3 內澇演進模型
降雨超過城市排水能力時,雨水從管網溢出形成內澇,積水極易沿地勢侵入地下空間。內澇在地表及地下空間的演進過程具有典型的淺水波特性,因此采用有限體積法求解二維淺水方程組[式(5)~(7)]。此外,緩坡連接的地下空間出入口亦可由淺水方程組求解,需對出入口緩坡計算網格加密處理。對于臺階及其他形式的地下空間出入口,可以概化為相應的水力模型,通過經驗公式確定地下空間內澇模型的流量邊界條件。
(5)
(6)
(7)
式中:h為水深;u、v分別為x、y方向的速度分量;Sx、Sy分別為x、y方向的底坡源項分量。
1.2 城市內澇風險評價方法
城市內澇風險評價方法逐步由定性研究(歷史災情統計法、指標體系評估法)轉向定量研究(情景模擬評估法)[16],研究方法從宏觀關注災情數理統計方法發展為注重災情實時動態變化的情景模擬分析方法。情景模擬評估內澇災害風險動態將成為今后研究發展的必然趨勢。城市內澇風險由內澇危險性及敏感性共同決定,本文基于區域排水模型模擬研究區域內澇過程,獲得淹沒范圍、水深、歷時等成災特性,以此為依據評價研究區域的內澇危險性;內澇敏感性由下墊面、用地性質及區域重要性等因素確定,在文中不作討論。
地下空間暴雨內澇危險性取決于出入口積水深度、雨水侵入體積、自身排水能力等因素,對于不同形式的地下空間,應當按照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內澇危險性評價指標及評價等級。
2 研究實例
2.1 地下空間內澇模型構建
應用區域排水模型評估武漢長江隧道漢口段的內澇危險性。隧道所在區域排水系統集水范圍大,管網拓撲結構復雜,研究區域總面積約為254.66 hm2。隧道有出入口三處,分別為A、B、C,如圖3所示。出入口阻水反坡墊高分別為0.22、0.28、0.24 m,通道內均設有雨水橫截溝及雨水泵房,橫截溝攔截雨水輸送至泵房集水池,水泵排放能力分別為420 m3/h(2用1備)、300 m3/h(1用1備)、300 m3/h(1用1備),采用分級水位逐檔啟泵抽排,泵房出水直接接入市政排水管道。隧道排水系統平面布置示意圖如圖4所示。依據區域實際情況進行模型構建,包括管網系統搭建、子集水區劃分、地形高程模型搭建、2D計算網格劃分、降雨數據輸入、邊界條件設置及水文水力參數選取等。

圖3 計算區域街區及管網Fig.3 Blocks and pipe networksofthestudy area

圖4 隧道及其雨水排放系統Fig.4 Thetunnel and its drainage system
武漢市2016年7月6日暴雨致使中心城區200多處漬水,最大4 h降雨量達到132 mm。該次暴雨導致過量雨水由出入口C侵入隧道,而A、B通道排水系統未超負荷,有效阻止了雨水入侵。為校核模型的可靠性,對該次暴雨內澇事件進行模擬重現。圖5所示為地表區域最大積水深度(t=14 h)分布情況,A、B口反坡前積水深度最大約為0.25 m,而C口達到0.3m以上,與實際觀測值相近。圖6所示為日降雨過程線及各出入口雨水入流量,A、B口入流量小于泵房抽排能力,而C口入流量大于泵房抽排能力,雨水由C口侵入隧道內部。模擬結果與實際吻合良好。

圖5 地表最大積水深度分布圖Fig.5 Maximum water depth of the surface

圖6 降雨過程線及出入口入流量Fig.6 Rainfall process line and entrances′ inflow
《武漢市排水防澇系統規劃設計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給出重要地區及路段在20年設計暴雨重現期下應保證城市功能。《室外排水設計規范》要求特大城市內澇防治重現期宜取50~100 a[17]。故分別評估隧道在設計重現期為20、50 a暴雨下的內澇危險性。設計暴雨強度由《標準》給出[式(8)],降雨過程線由芝加哥合成暴雨過程線法得到,降雨歷時取為180 min,雨峰系數取0.5。
(8)
式中:P為設計降雨重現期,a;q為降雨強度,L/(s·hm2);t為降雨歷時,min。
2.2 內澇危險性評價
基于區域排水模型在重現期P=20 a及50 a的降雨下分別模擬長江隧道漢口段內澇情況,得到地表最大積水深度分布圖(圖7)。模擬結果顯示:不同強度降雨造成的地表積水深度差異顯著,最大積水深度出現在第110 min。P=20 a時,出入口A、B、C反坡前積水深度分別約為0.3、0.25、0.35 m,降雨達到峰值后,出入口附近積水開始漫過反坡侵入隧道內部。P=50 a時,隧道出入口附近較大范圍地面積水嚴重,A、C口反坡前最大積水深度達到0.4 m以上,B口深度約為0.3 m,積水向隧道入侵流量增大。各出入口雨水入流量(圖8)模擬結果顯示:P=20 a時,A、B口最大流量為0.36、0.16 m3/s,接近其泵房抽排能力(0.35及0.17 m3/s),C口最大流量達到0.45 m3/s,遠超其抽排能力(0.17 m3/s),導致雨水侵入隧道內部,最大時入侵水量達90 m3(表1),接近隧道內部廢水泵房集水池體積(95 m3)。P=50 a時,A、B、C口最大流量均超過其泵房抽排能力,隧道內部最大入侵水量達到124 m3。入流量峰值均出現在第110 min,即峰現后20 min。

圖8 降雨過程線及出入口入流量Fig.8 Rainfall process line and entrances’ inflow
由模擬結果對武漢長江隧道漢口段內澇危險性進行評估,考慮隧道所受影響的嚴重情況,確定了其內澇危險性評價等級(表2)。對于多個出入口的地下空間而言,應分別評估各出入口危險性。本例中取各出入口積水深度、雨水入流量作為出入口危險性評價指標。此外,以隧道內部雨水侵入體積為指標評價隧道整體的危險性。評估結果見表3。

表1 隧道最大侵入雨水量Tab.1 The maxvolume of rainfall into the Tunnel

表2 武漢長江隧道漢口段內澇危險性評價等級Tab.2 Inundation risk assessment rating in WuhanChangjiang River Tunnel(Hankou)

表3 隧道內澇危險性評估結果Tab.3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tunnel inundation
根據評估結果,武漢長江隧道漢口段自身排水系統在應對城市暴雨內澇時能力不足,為了使隧道達到標準要求的內澇防治目標,在暴雨時保證一定的通行能力,應進行一定的工程改造并制定內澇應急預案。
3 結 語
基于區域排水模型的地下空間內澇模擬依次采用徑流系數法、Horton下滲模型表征不透水及透水地面產流過程;采用非線性水庫法表征地面匯流過程;采用動力波法表征管網匯流過程;最后以淺水方程求解內澇演進過程。該方法能夠完整描述雨水產匯流及侵入地下空間的水文水力學過程,能夠針對不同降雨強度下的內澇情況進行模擬計算,進而評估地下空間內澇危險性。地下空間暴雨內澇危險性取決于出入口積水深度、雨水侵入體積、自身排水能力等因素,對于不同形式的地下空間,應當按照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內澇危險性評價指標及評價等級。運用上述模型對武漢長江隧道漢口段內澇危險性進行情景模擬評估研究,由2016年7月6日實測暴雨內澇事件驗證了模型的可靠性,并以隧道各出入口積水深度、雨水入流量及隧道最大侵入雨水量為評價指標,得出隧道在重現期為20年、50年降雨下的內澇危險性等級,為地下空間防澇管理及應急救援提供支持。
□
[1] 高 瑆. 地下空間開發利用中規劃問題淺析[J]. 建筑工程技術與設計, 2014,(19).
[2] Keiichi T, Kuriyama K, Oyagi R, et al. Inundation Analysis of Complicated Underground Space[J]. Proceedings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2003,47:877-882.
[3] Ishigaki T, Onishi Y, Asai Y, et al. Evacuation criteria during urban flooding in underground space: 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C]∥ 2008.
[4] Ishigaki T, Kawanaka R, Onishi Y, et al. Assessment of safety on evacuating route during underground flooding[J].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2009:141-146.
[5] Toda K, Kawaike K, Yoneyama N, et al. Underground inundation analysis by integrated urban flood model[J].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2009:166-171.
[6] Yoneyama N, Toda K, Aihata S, et al. Numerical analysis for evacuation possibility from small underground space in urban flood[J].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2009:107-112.
[7] Asai Y, Ishigaki T, Baba Y, et al. Safety analysis of evacuation routes considering elderly persons during underground flooding[J]. Journal of hydroscience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2010,28(2):15-21.
[8] Ishigaki T, Ozaki T, Inoue T, et al. Drainage system, rainwater flooding and underground inundation in urban area: Proc. of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Drainage[C]∥ Porto Alegre/Brazil, PAP005466.(on CD-ROM), 2011.
[9] HASHIMOTO H, PARK K. Two-dimensional urban flood simulation: Fukuoka flood disaster in 1999[J]. WIT Transactions o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8,118:59-67.
[10] HASHIMOTO H, PARK K. Inundation risk assessment of underground spaces in the downtown of Fukuoka City, Japan[J]. WIT Transactions o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0,133:143-153.
[11] OERTEL M. Flooding of underground facilities in urban re-gions after malfunction of flood protection measures: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lood Defense[C]∥ Toronto, Ontario, Canada, 2008.
[12] 莫偉麗. 地鐵車站水侵過程數值模擬及避災對策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學, 2010.
[13] 申若竹, 楊 敏, 劉 鵬. 地下空間出入樓梯洪水動力特性試驗研究[J]. 水資源與水工程學報, 2012,(6):124-127.
[14] 胡偉賢, 何文華, 黃國如, 等. 城市雨洪模擬技術研究進展[J]. 水科學進展, 2010,(1):137-144.
[15] YEN B C. Open-channel flow equations revisited[J]. Journal of the Engineering Mechanics Division, 1973,99(4):979-1 009.
[16] 王 磊, 周玉文. 基于投影尋蹤的城市排水系統洪澇風險評估模型[J]. 中國給水排水, 2011,(23):78-82.
[17] GB-50014-2006,室外排水設計規范(2016修訂)[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