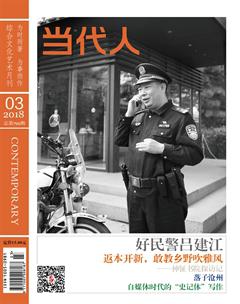埃林·彼林與新的文學倫理
凸凹,本名史長義,著名散文家、小說家、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北京市房山區文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慢慢呻吟》《大貓》《玉碎》《玄武》等8部,散文集《以經典的名義》《風聲在耳》《無言的愛情》《夜之細聲》《故鄉永在》等30部。
幽密的清水灣,歡躍的赤楊樹,金色的陽光,雪白的胴體,憂郁的人心,都是“無罪”之大美,卻在冥冥之中成了同期到達的“兇手”。這就是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標準和社會綱常無法指認、無法評判。
經年的閱讀與書寫,使我強烈地感到:書籍與人的關系,正如人與人的關系一樣,也是一種宿命關系。
保加利亞的作家埃林·彼林有很好的鄉土文字,我愛得不能釋手;但他不是一流的作家,作品在中國的流布很是寂寥,許多文壇名宿竟不知道他是誰,每一提及,我都要費很多的口舌。
其實我得到他的著作,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那約略是1984年夏天的一個午后,因燒酒喝得多了一些,總想在街頭走路,便任性走下去。走到一棵街樹下,發現那里有一個書攤,便停了下來。那是一棵矮矮的龍爪槐,樹冠很小,灑下的陰涼就那么小小的一塊;一個垢面者正坐在那塊陰涼之下,微合著雙眼。書攤上大多都是花花綠綠的雜志,像樣兒的書,就那么三兩本。那本《埃林·彼林選集》就躺在其中,土黃的封面,書角已有些翻卷,蒙著薄薄的一層風塵。
我拿起書來,漫不經心地翻著。那個垢面人睜開眼皮斜了我一眼,就又合上了。
看得出,他已習慣了書攤上的寂寥,已不抱有絲毫的期待了。
但躺在書頁中那土地上的情仇,雖不露聲色,卻也藏著機鋒;像個笨拙的刺客,動作雖然有些遲緩,但刺中的位置卻十分準確。我眼睛一亮,覺得埃林·彼林等待的中國伙伴就是我,因為他的敘事和語言,跟我這個山地人的性情與習俗、悲喜與好惡是相通的。
“多少錢一本?”我問。
“你撂下一塊錢走人吧。”垢面人懶懶地說。他的口氣不像是賣書的,倒像是設卡打劫的,有注定了的味道。
掏出一元錢給他,他卻不接,抬手指了指腳下,那里有個空紙盒子,意思是讓你自己把錢放在那里。
走出了很遠,我回頭看了一眼,原來放埃林·彼林書的地方空著,酒眼朦朧中,我覺得那不是小小的一個空白,而是一個巨大的黑洞——埃林·彼林的靈魂被攝取走了,不會再有對等的精神來補充了。
突然就刮起了一陣風。垢面人紙盒子里那張紙幣被吹了起來,朝著街頭飄零。那個人卻無動于衷,任紙幣兀自飄零。
真是個詭異的人啊!
不過這正是埃林·彼林的氣味,因為他即便是寫著殺人的兇險故事,筆調卻也是那么漫不經心,像田壟上的小麥,一定要被收割一樣。
被一種好奇心支配著,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個書攤,發現在昨天的空白處,又出現了同一本埃林·彼林。我很掃興,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回到書房之后,居然就沒有了閱讀埃林·彼林的興趣,因為心情被街頭的那一個埃林·彼林攪亂了——難道在這個彈丸小城,還有埃林·彼林的另一個同伴?
之后,我又去了幾次那個書攤,那個埃林·彼林還靜靜地呆在那里,呈現出一種無奈的樣子。我預感到,他的另一個伙伴是不會再來了。
最后的一次,在我即將邁過書攤的時候,那個垢面人叫住了我:“你等等。”
他指了指那本埃林·彼林,對我說:“這個,你拿走。”
我搖搖頭。
“你真的不拿走?”他追問道。
我依然搖搖頭。
他詭異地笑笑,猛地站起身來,一把將埃林·彼林薅在手里,點著了。
在熾熱的陽光下,幾乎看不到火焰的樣子,只見到紙頁漸漸地卷了起來,且越縮越小了。
“這回,你該滿意了吧。”他居然懂我的心思,讓我大吃一驚。同時,我竟無端地興奮起來,從器官到內心。
當我的“唯一性”被垢面人證明之后,我與埃林·彼林的感情關系才真正上路了,且在短期內發展得如火如荼,乃至終身難解了。
他的文字真好,好到像刀子輕輕地刮著我的骨頭,在真切的痛癢中,讓我思念肉的包裹。
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他的小說是土地上的生命敘事,能讓我找到自己的來路——雖荒山野土,蠻人陋事,卻是人性生成和繁盛的地方。或者說,在閱讀他的同時,我竟能感到他也在閱讀我,并且在互相進入的狀態下,建立了一種在“無罪之罪”中承擔“共同犯罪”之責的文學倫理。
王國維認為,人生總的來說是一場悲劇,悲劇的形成有三種樣相——
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于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于前二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
埃林·彼林的小說呈現的就是這第三種悲劇。一切的悲情與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也非盲目的命運使然,而是由鄉土中的每一個人共同制造的——他們都不是壞人,也根本沒有制造悲劇的本意,他們只是本分地扮演著生活“分配”給他們的角色,每個人都有為何如此行事、如此處世的理由,每個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會確立的人情與倫理——一切都是順乎自然的發展,無可無不可,無是也無非,既無善惡之對立,也無因果之輪回;然而,正是這種自然狀況下的“無罪之罪”,這些“通常之人情”,毫無預謀地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悲劇。
與中國的敘事傳統,即懲惡揚善、因果報應的陳舊模式作比,埃林·彼林提供了一個超越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價,而進入到經驗的內部、人性的深度的全新文本。他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卻是家常的。正因為是家常的,便有質樸而準確的價值趣味,即:人性之真。
比如他的《割草人》。拉佐由于娶了村里的美人潘卡,便總是擔心她紅杏出墻。在外出割草的路上,伙伴們圍著篝火,也多是拿潘卡來插科打諢——既然是鄉村美人,自然就會成為議論的話題。然而,伙伴們不經意的議論,就更增加了拉佐的疑心,他眼前總是出現這樣一個情景:在一片茂密的矮樹中,露出了潘卡雪白的漂亮臉蛋兒,一只男人的手——這是一個野漢子的手,撫摸著她的臉……于是,拉佐再也沉不住氣了,悄悄地踏上了返鄉的路。從此,即便是家里窮得叮當亂響,即便是潘卡的漂亮臉蛋因積聚了厚重的菜色而一天天變丑,拉佐再也沒有勇氣走向謀生之路。
一個本該興旺的家庭卻陷入困境,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這種悲劇的形成,不是因為“意外的變故”,而是因為“通常之人情”。是潘卡的美,拉佐的疑心,伙伴們的議論,這些“無罪之罪”共同制造的。悲劇中的人物,都可以被指摘,但又都沒有理由被指摘,他們都陷在“無物之陣”中,身不由己。
還比如他的《列波》。退伍兵列波老實能干又美,和他能般配的姑娘便只有“村花”伏依卡。不幸的是,他身份低微,只是富農家的一個雇工;更不幸的是,伏依卡竟在城里當了三年的保姆,對生活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于是,她不再接受他了。伏依卡“是一頭游走在鄉間的美麗的小獸”,既單純又善良,身上的美,是鑲嵌在列波的身心之上的——假如列波是骨頭,伏依卡就是附著于上的肉。所以,在猝發的變故面前,一種致命的憂郁便在他心中凝結了起來。在一次打獵的途中,他看見伏依卡在赤楊樹隱蔽著的一個清水灣里戲水,“她赤裸的身子,白得就像剛落下的雪”。更要命的是,“陽光穿過歡躍的樹葉,仿佛金色的鱗片落在伏依卡身上”,美得令人心痛,美得令人絕望,在一種“混沌”的狀態下,他扣動了扳機。
幽密的清水灣,歡躍的赤楊樹,金色的陽光,雪白的胴體,憂郁的人心,都是“無罪”之大美,卻在冥冥之中成了同期到達的“兇手”。
這就是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標準和社會綱常無法指認、無法評判。
埃林·彼林不是圣人,但他卻讓人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學。所謂文學,就是用最柔軟的方式,建立一種道德之上的道德、倫理之上的倫理。
“每束陽光都有照耀的理由啊!”我憂傷地感嘆道。
從街頭垢面人的手里,居然拿到了這樣一本《埃林·彼林選集》,真是一種天意啊!就像昆侖山上的大師,透過劍雨刀林,一眼就看準了在角落里的一個傳人,而把江湖秘笈獨授于斯一樣,不堪究竟、無法言說。
于是,躲在窄仄而昏暗的書齋里,我的心豁達起來,且竊笑不止。
因為此時的我,正面臨著一個困擾,就是如何解決一個寫作者的身份問題。
埃林·彼林的“秘笈”告訴我,一個寫作者,不是規則的制定者,也不是生活的評判者,而是人間信息的記述者和傳遞者,要按照生活的“邏輯”寫作,而不是把自己的理由強加給生活。生活的邏輯是什么?已發生的、正在發生的、將要發生的,都是自適自足的——是不此不彼,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我沒有必要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態,能夠準確地呈現人間的真相便是寫作的意義了。
這是一種“文學的境界”,它能夠使寫作者,從道德的困境、經驗的困境中解放出來,走向自如、寬廣而人性的世界。
我輕裝而行,一路歡悅,且一路收獲——以我的出生地為素材,寫了幾百萬字的“山地筆記”。這些筆記,既有散文,又有小說,既有寫生,又有工筆,體例不拘,任性而為。在我的筆下,山地人事,既原始又開放,既固守又曠達,既質樸又復雜,既高貴又卑賤,既寬容又褊狹,既正經又淫褻,既善良又惡毒……總之,都體現著對生活的照拂與尊重。
我何嘗不想做高于生活的“塑造”?但山地之上,只能生長那樣的植株。人工的培植,只會制造假象、制造怪胎,甚至是死亡。身后,埃林·彼林那雙憂郁的眼睛在始終注視著我,我哪敢自以為是呢。于是,我極力克制住自己站出來講話的欲望,以“無差別的善意”寫人的悲哀和生之喜悅,讓“天道人心”自然而然地說話。
許多讀者告訴我,讀你的文字,有身臨其境之感,能讀出“我”來;因為書中的人物并不比“我”高明,所以,閱讀的過程,就是建立自信與自尊的過程,我們很受用。同時,我們也增強了對生活的承受能力,因為善惡是在相互涵養中的,罪與非罪是相伴而生的;有的時候,不公之中卻蘊含著公平,絕望之處,未必就是絕境,相反,或許就是新生之地。因此,我們感謝你,對你有新的期待。
他們還說,讀了你的文字,我們對世事的憤懣竟漸漸地平息了,竟漸漸生出一種溫厚的情緒,就是做人要厚道,要寬容,要有悲憫心——人生于世,都是在扮演被命運“催眠”的角色,可憐見地,許多,許多,是身不由己的。
這或許就是對寫作者最好的回報了——因為,大地道德最核心的支撐便是良知、愛與悲憫啊!
于是,我歡喜于自己的寫作生活——我既制造著文字,文字又加固和溫暖著我;我不再擔心破碎,也不再畏懼寂寞——生命因此而強壯起來。
編輯:耿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