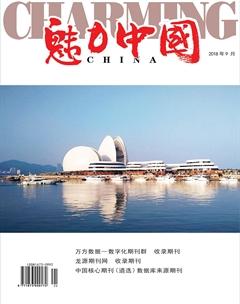論低保制度中的“福利污名”
尹婉霞
摘要:在我國(guó),以現(xiàn)金補(bǔ)償為主的低保制度極大緩解了貧困群體的生活壓力,同時(shí)基于家計(jì)調(diào)查、具有選擇性的低保制度又容易產(chǎn)生“福利污名”,繼而延伸出社會(huì)排斥與瞄準(zhǔn)偏差等社會(huì)問(wèn)題。福利污名不僅來(lái)自“低保對(duì)象”的標(biāo)簽效應(yīng)(身份污名)和認(rèn)定受助者的家計(jì)調(diào)查程序(程序污名),更是由于“福利依賴”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刻板效應(yīng),以及低保制度非積極賦權(quán)型的救助模式。緩解福利污名需通過(guò)消除低保對(duì)象的標(biāo)簽歧視、重視就業(yè)救助、完善社會(huì)救助的遞送程序、增強(qiáng)民眾受助的權(quán)利意識(shí)等對(duì)策實(shí)現(xiàn)。
關(guān)鍵詞:低保制度;福利污名;身份污名;程序污名
一、“福利污名”的研究緣起及其內(nèi)涵介紹
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轉(zhuǎn)型,貧富差距擴(kuò)大、失業(yè)人數(shù)增加,貧困群體數(shù)量大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簡(jiǎn)稱低保)應(yīng)運(yùn)而生,其是國(guó)家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社會(huì)成員,提供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質(zhì)幫助的一種社會(huì)救助制度[1]。以現(xiàn)金資助為主的低保對(duì)緩解貧困群體的生活壓力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guó),低保制度遵循選擇性原則,主要依靠家計(jì)調(diào)查制度確定受助者資格,福利污名常常被認(rèn)為是家計(jì)調(diào)查建構(gòu)與實(shí)施的結(jié)果[2]。許多研究已經(jīng)表明,“福利獲取”與“福利污名”間存在聯(lián)系;如果貧困與羞恥感緊密相連,就有可能產(chǎn)生福利污名[3]。
美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戈夫曼最先使“污名”概念化:當(dāng)一個(gè)陌生人所具有的特質(zhì)使得他被歸類到壞的、危險(xiǎn)的、虛弱的類群時(shí),他的形象就會(huì)從一個(gè)完整的普通人減損成一個(gè)玷污的人;當(dāng)這個(gè)特質(zhì)使得擁有它的人遭到貶損的影響越大,則這類特質(zhì)就是一種污名[3]。“污名”是人們對(duì)群體或自己的刻板印象而導(dǎo)致的認(rèn)知偏頗、消極情緒以及行為反映的綜合結(jié)果。福利污名是受助者接受福利時(shí)遭遇的污名歧視和被排斥的過(guò)程,包括身份污名和程序污名[4]。一方面是社會(huì)對(duì)受助者存在貶低性、侮辱性的標(biāo)簽歧視,另一方面是部分嚴(yán)苛的申領(lǐng)條件有損受助者的尊嚴(yán),受助者由此會(huì)產(chǎn)生羞愧恥辱心態(tài),并導(dǎo)致社會(huì)對(duì)其不公正待遇的結(jié)果出現(xiàn)。
作為一個(gè)人口大國(guó),2016年我國(guó)城市和農(nóng)村居民低保人數(shù)已達(dá)6066.7萬(wàn)人,研究這一龐大群體乃至所有社會(huì)救助對(duì)象面臨的“福利污名”具有深切的價(jià)值意義,旨為緩解受助者“福利污名”和完善現(xiàn)有的社會(huì)保護(hù)政策提供思路。
二、“福利污名”的延伸問(wèn)題
(一)“福利污名”與社會(huì)排斥
回顧學(xué)者的研究,社會(huì)救助政策通過(guò)福利污名有導(dǎo)致社會(huì)排斥的風(fēng)險(xiǎn)。1974年,法國(guó)學(xué)者勒內(nèi)·勒努瓦最先使用“社會(huì)排斥”概念來(lái)說(shuō)明被排斥在就業(yè)崗位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會(huì)邊緣群體的“被排斥”狀態(tài)[5]。救助對(duì)貧富差距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有限,且可能帶來(lái)福利污名和福利依賴,肖萌、梁祖斌[6]認(rèn)為社會(huì)救助不但不能解決社會(huì)排斥,反而會(huì)加重社會(huì)排斥。社會(huì)排斥即是社會(huì)對(duì)被貼上污名標(biāo)簽的人所采取貶低、疏遠(yuǎn)和敵視等態(tài)度和行為,是污名化的結(jié)果,包括在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主流社會(huì)關(guān)系及主觀層面的社會(huì)排斥。
社會(huì)救助的兩大目標(biāo)是:為貧困者提供物質(zhì)幫助、消除對(duì)貧困者的社會(huì)排斥。本意是促進(jìn)社會(huì)公平、緩解貧困者社會(huì)排斥的社會(huì)救助政策卻在實(shí)際運(yùn)行中因福利污名加劇了社會(huì)排斥,使得貧困者喪失了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和被剝奪參與的資格,在機(jī)會(huì)上被長(zhǎng)期排斥在外。此為典型的福利悖論——在解決原問(wèn)題的同時(shí)產(chǎn)生了更大的問(wèn)題[4]。
(二)“福利污名”與瞄準(zhǔn)偏差
部分貧困者由于羞恥感和污名感放棄了社會(huì)救助申請(qǐng)從而導(dǎo)致瞄準(zhǔn)偏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這便是福利污名給貧困者造成的阻礙效應(yīng)。當(dāng)羞恥感和污名感被作為一種政策工具時(shí)(政府利用負(fù)面標(biāo)簽合法地阻止非貧困者申請(qǐng)社會(huì)救助,防止福利依賴),政策實(shí)施的意外后果往往是導(dǎo)致兩種類型的瞄準(zhǔn)偏差的產(chǎn)生,一是排斥性偏差:真正貧困者放棄申請(qǐng)低保;二是內(nèi)含性偏差:非貧困者由于感受不到深刻的羞辱而積極申請(qǐng)低保,從而使瞄準(zhǔn)偏差現(xiàn)象更突出[3]。
社會(huì)政策的制定與實(shí)施中如何削弱福利污名、提升瞄準(zhǔn)精度,讓貧困者更有尊嚴(yán)地獲取社會(huì)援助已經(jīng)成為西方社會(huì)政策研究中富有生命力的重要話題。但目前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還較少?gòu)母@勖嵌确治雒闇?zhǔn)偏差。
三、“福利污名”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原因
(一)身份污名:“低保對(duì)象”的標(biāo)簽效應(yīng)
身份污名是指作為選擇性救助的低保制度“認(rèn)定身份”時(shí)伴隨的恥辱感。受助者的身份認(rèn)定與貧困狀況有關(guān),而貧困往往會(huì)帶來(lái)羞恥感和污名化,“社會(huì)救助接受者”的標(biāo)簽會(huì)構(gòu)成受助者的心理障礙并使得貧困者失去與其他社會(huì)成員的平等性[3]。貧困者在申請(qǐng)低保時(shí)就處在弱勢(shì)狀態(tài),成為低保對(duì)象后,會(huì)被貼上困難戶、拿政府的錢(qián)等標(biāo)簽,或會(huì)被周圍人用異類眼光看待,人際關(guān)系上經(jīng)受歧視和排斥。總之,“低保對(duì)象”是一個(gè)很明顯的標(biāo)簽,需承受一定的心理壓力。
(二)刻板效應(yīng):針對(duì)“福利依賴”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福利污名
處于勞動(dòng)年齡具有勞動(dòng)能力但寧吃低保不愿就業(yè)的“懶漢”,被歸為不值得救助的低保對(duì)象,其依賴行為具有強(qiáng)烈的污名化。學(xué)者桑德斯認(rèn)為,福利依賴具有文化上的驅(qū)動(dòng)力,他將過(guò)去用于形容窮人的詞匯,如自控能力差、好逸惡勞重新拿來(lái)形容福利依賴者,試圖使人們相信受助者具有懶惰的生活習(xí)性和較低的自尊,形成了依賴文化[7]。當(dāng)福利依賴風(fēng)氣盛行,人們?cè)谡J(rèn)知某一個(gè)低保對(duì)象時(shí),便會(huì)產(chǎn)生刻板效應(yīng):該受助者是一個(gè)好逸惡勞、欺詐低保的“懶漢”,從而加劇了福利污名。
(三)程序污名:基于認(rèn)定受助對(duì)象的家計(jì)調(diào)查程序
我國(guó)低保的申請(qǐng)程序是較為嚴(yán)格和復(fù)雜的,申請(qǐng)者需接受家庭收入和財(cái)產(chǎn)狀況調(diào)查。程序污名是指受助者在接受救濟(jì)時(shí)遭遇的“民主評(píng)議”和“張榜公示”等不友好的家計(jì)調(diào)查程序及工作人員的無(wú)禮對(duì)待等。大量學(xué)者在社會(huì)救助的申請(qǐng)程序、申請(qǐng)者與執(zhí)行者的互動(dòng)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了導(dǎo)致污名化的具體邏輯[3]。貧困者為了換取物質(zhì)上的利益,需損害自尊承受一定的社會(huì)壓力。同時(shí),程序污名或會(huì)使貧困者產(chǎn)生退縮心理而放棄申請(qǐng)低保,這其實(shí)是低保制度的異化。
(四)低保制度:一種“基于回應(yīng)的援助”救濟(jì)模式
我國(guó)城市的低保政策主要是為了緩解當(dāng)年下崗潮工人的生活壓力而設(shè)立的,旨在維持社會(huì)的穩(wěn)定。該制度與美國(guó)學(xué)者蘇黛瑞提出的“基于回應(yīng)的援助”模式類似,是消極回應(yīng)而非積極賦權(quán)型的福利供給模式,以有限的物質(zhì)救助為主,較少關(guān)注貧民的權(quán)利及精神需求[4]。然而我們應(yīng)該意識(shí)到接受救助是貧困者的權(quán)利,是其生存權(quán)和發(fā)展權(quán)的重要體現(xiàn),國(guó)家必須予以保障和滿足。目前,社會(huì)各界包括救助主體、救助對(duì)象和普通群眾對(duì)受助權(quán)利的意識(shí)皆相對(duì)模糊,這無(wú)疑是福利污名化的原因之一。
四、“福利污名”的緩解思路
(一)消除“低保對(duì)象”的標(biāo)簽歧視
1.加強(qiáng)受助對(duì)象的心理輔導(dǎo)
積極開(kāi)展心理救助服務(wù),加強(qiáng)受助者的心理輔導(dǎo),鼓勵(lì)其多與外界溝通交流,培養(yǎng)受助者在人際交往中的自信,增強(qiáng)權(quán)利意識(shí),積極正面地對(duì)待標(biāo)簽歧視,增強(qiáng)心理承受能力。
2.營(yíng)造良好的受助環(huán)境
落實(shí)政府層面對(duì)救助弱勢(shì)群體的義務(wù)和責(zé)任,提升工作人員的素質(zhì),并做好受助宣傳;鼓勵(lì)普通大眾多與受助者接觸,充分了解他們的生活困境,感同身受,消除對(duì)貧困者的歧視心理。攜手營(yíng)造良好的受助環(huán)境,共建社會(huì)支持網(wǎng)絡(luò),消除“低保對(duì)象”的標(biāo)簽歧視[8]。
(二)重視就業(yè)救助,避免“福利依賴”現(xiàn)象
通過(guò)就業(yè)培訓(xùn)、就業(yè)補(bǔ)貼、崗位提供等方式積極開(kāi)展就業(yè)救助,提升受助者的人力資本和自身素質(zhì)使之?dāng)[脫困境。構(gòu)建就業(yè)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減少“懶漢”數(shù)量,謀求獨(dú)立發(fā)展。社會(huì)救助理應(yīng)向發(fā)展型救助轉(zhuǎn)變,除了要為貧困者提供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質(zhì)救助外,更應(yīng)該為其創(chuàng)造發(fā)展機(jī)會(huì),讓其有機(jī)會(huì)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勞動(dòng)不斷發(fā)展自己,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進(jìn)而消除在受助過(guò)程中的“污名感”。
(三)完善社會(huì)救助的遞送程序,優(yōu)化社會(huì)救助模式
加快建設(shè)居民家庭收入核對(duì)機(jī)制,運(yùn)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強(qiáng)化瞄準(zhǔn)機(jī)制,削弱不友好的家計(jì)程序帶來(lái)的污名感。培育專業(yè)的社會(huì)救助機(jī)構(gòu)和人員,充分發(fā)揮社會(huì)工作者的優(yōu)勢(shì),為受助者提供社會(huì)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導(dǎo)等專業(yè)服務(wù)。嘗試以政府購(gòu)買(mǎi)服務(wù)的方式,引入市場(chǎng)力量,改變以民政部門(mén)為主逐級(jí)遞送的社會(huì)救助方式。貫徹“人性化”的服務(wù)理念,優(yōu)化救助模式,使社會(huì)救助真正滿足受助者的需求。
(四)增強(qiáng)民眾受助的權(quán)利意識(shí)
與西方成熟的福利國(guó)家相比較,東亞國(guó)家的社會(huì)權(quán)利意識(shí)還處于初步發(fā)展階段[3]。我國(guó)的救助范式應(yīng)向賦權(quán)型福利模式轉(zhuǎn)變,政策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應(yīng)該意識(shí)到消除貧困的途徑在于賦予貧困者利益表達(dá)和實(shí)現(xiàn)自身權(quán)利的途徑[4]。通過(guò)宣傳教育,讓公眾認(rèn)識(shí)到接受救助是貧困者享有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突破傳統(tǒng)的“施舍”和“感恩”心理,減弱貧困者申請(qǐng)低保時(shí)的污名感。民眾受助權(quán)利意識(shí)的增強(qiáng),將成為貧困者申請(qǐng)救助的“拉力”。
參考文獻(xiàn):
[1]劉娟、何少文.社會(huì)救助政策與實(shí)務(wù)[M].廣州:廣東經(jīng)濟(jì)出版社,2015:31
[2]祝建華、林閩鋼.福利污名的社會(huì)建構(gòu)--以浙江省城市低保家庭調(diào)查為例的研究[J].浙江學(xué)刊,2010,(3):201-206
[3]李棉管.技術(shù)難題、政治過(guò)程與文化結(jié)果--“瞄準(zhǔn)偏差”的三種研究視角及其對(duì)中國(guó)“精準(zhǔn)扶貧”的啟示[J].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17:230-238
[4]王錦花.福利悖論:中國(guó)社會(huì)保護(hù)中的社會(huì)排斥--基于廣州市的實(shí)證研究[J].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69(2):39-45
[5]熊光清.歐洲的社會(huì)排斥理論與反社會(huì)排斥實(shí)踐[J].國(guó)際論壇,2008:14
[6]肖萌、梁祖彬.社會(huì)救助就業(yè)福利政策研究[J].社會(huì)保障研究,2010:96
[7]劉璐嬋、林閩鋼.“福利依賴”:典型與非典型的理論透視[J].社會(huì)政策研究,2017:4-6
[8]汪亦泓、柯仲鋒.論“福利污名”及其應(yīng)對(duì)策略[J]. 內(nèi)蒙古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13(58):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