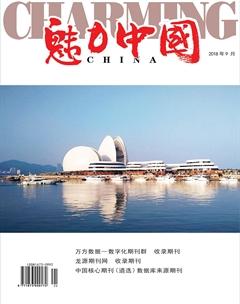商鞅變法之剝奪人格與創(chuàng)立專制
楊敬舜
一、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變法及商鞅、韓非和李斯之死
商鞅(前395—前338)公元前356年推行變法。商鞅變法內(nèi)容全面徹底,簡(jiǎn)言之有這么幾點(diǎn):第一,明確“君(王,主)”與“民”之間的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關(guān)系,變法以“君”為出發(fā)點(diǎn),變法的目的就是讓“君”有效地“使民”;第二,變法的目標(biāo)就是“富國(guó)強(qiáng)兵”;第三,變法的具體內(nèi)容就是圍繞上述目的和目標(biāo)采取的各項(xiàng)措施。主要有:一是全民從事農(nóng)戰(zhàn),不得從事其他職業(yè),不得議論變法,不得讀《詩(shī)》、《書》,不得經(jīng)商,徹底消除“六虱”(孔子“六經(jīng)”)和“十有”(有禮、有樂(lè)、有《詩(shī)》、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二是重新評(píng)定公族爵位。爵位只能世襲兩代,按爵位高低配給家奴和土地。任何人不得買賣家奴、土地和糧食。被廢爵位的公族為平民,自行耕種分得的土地;三是改革戶籍制度。父子必須分別立戶。所有人必須定點(diǎn)居住,不得流串;四是按軍功定爵位。爵位共分二十等,按殺死敵軍士兵數(shù)目定軍功、爵位;五是實(shí)行嚴(yán)刑峻法、輕罪重罰和什伍連坐。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戶戶之間相互監(jiān)督,一戶犯法如不舉報(bào),一伍一什都受連坐;六是任用奸人為官。從上到下,大到九卿、小到伍長(zhǎng)都由奸人擔(dān)任,因?yàn)榧槿瞬粫?huì)姑息罪人。不能任用好人(善者)為官,因?yàn)椤吧菩摹睍?huì)影響法律的執(zhí)行,會(huì)給世人以僥幸,久而久之必定天下大亂。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歷時(shí)二十余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秦惠文王羅織商鞅謀反之罪準(zhǔn)備將其下獄。商鞅出逃,但是因?yàn)楹ε逻B坐竟然無(wú)一國(guó)或者一家敢收留他,最后,他逃到自己的封地商郡被殺死,尸首被運(yùn)回咸陽(yáng)車裂示眾,并被夷三族。
韓非是韓國(guó)公子,與李斯同為荀子的弟子,對(duì)“偽學(xué)”研究之深,亙古無(wú)出其右,所以被認(rèn)為是“最大的法家思想家”,所著《韓非子》更是歷代帝王奸臣必讀之書。他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了“君”的獨(dú)立性,把“君”置于萬(wàn)民之上,占居社會(huì)頂點(diǎn)。他從“君”的立場(chǎng)和利益出發(fā),精辟的論述了如何精致運(yùn)用“法、術(shù)、勢(shì)”來(lái)“馭民”。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讀到了他所著的《孤憤》和《五蠹》,嘆為觀止,于是對(duì)韓國(guó)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逼韓國(guó)把韓非送到了秦國(guó)。韓非在秦國(guó)滯留了一年,盡管深知“當(dāng)今之世,人主無(wú)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shù)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而明己之法術(shù)哉。”(《韓非子·和氏》)意思是,“當(dāng)今天下沒有人能象楚悼王和秦孝公那樣聽取臣下之言的,哪個(gè)懂得‘法和‘術(shù)的人敢冒商鞅和吳起之險(xiǎn)講‘法和‘術(shù)呢。”但是他還是明知故犯,把他的精致之“術(shù)”全部獻(xiàn)給了秦王。他的同窗李斯感覺到了威脅,伺機(jī)向秦王進(jìn)讒說(shuō),韓非只為韓國(guó),對(duì)秦國(guó)沒有忠心。秦王于是下令將其下獄,旋即李斯逼其服毒自盡。
李斯在秦國(guó)為官四十余年,先后任郎官、長(zhǎng)史、客卿、廷尉、左丞相,享爵左庶長(zhǎng),一直在秦王左右。人們因?yàn)樗泄τ诰喸臁般筱蟠髧?guó)”,而忘記了他是秦朝苛政、暴政時(shí)間最長(zhǎng)、規(guī)模最廣、層次最深、影響最大的決策者和執(zhí)行者。秦始皇死后,趙高鼓動(dòng)李斯廢太子扶蘇立二皇子胡亥。趙高是胡亥的老師,胡亥對(duì)趙高言聽計(jì)從。不到一年,李斯連續(xù)幾次中趙高奸計(jì),被罷職入獄,受盡毒打折磨,屈打成招,終被夷族。
變法只有商鞅取得了成功,韓非完善了法家的基于“馭民”法家理論,李斯只是商鞅嚴(yán)刑峻法的踐行者,但是面對(duì)他們自己創(chuàng)立的“術(shù)”下場(chǎng)是徹底的失敗。
二、商鞅變法剝奪了“民”的人格
如上所述,商鞅變法是從“君”這個(gè)源點(diǎn)出發(fā)的,變法是圍繞“君”展開的,“君”是最終的受益者。變法的內(nèi)容就是“君”“馭民”之“術(shù)”。《商君書》開宗明義就說(shuō),“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商君書·更法》)又說(shuō)“錯(cuò)法務(wù)明主長(zhǎng)”(《商君書·更法》)。換言之,世道變了,變法才能有“使民”之法,要變法就必須明確主人(主子),就是首先要明確為誰(shuí)變法。這里道出了變法的指導(dǎo)思想,即為君(主人、主子)“求使民之道”。
孟子說(shu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無(wú)疑是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從愚昧走向文明或者理性的艱難歷程的總結(jié)。可是法家認(rèn)為“君”為天下之主,天下為君主之私。他們制定法律,把“君”與“民”各自的地位和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規(guī)定下來(lái):“君”是主人,“民”是“君”的財(cái)產(chǎn),“君”有權(quán)“使民”、“馭民”。在中國(guó)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從三皇五帝以來(lái),人與人之間,人格是平等的。雖然之前出現(xiàn)過(guò)很多“高貴的人”,那不是他們自封的,而是由于他們?cè)谏鐣?huì)實(shí)踐中用仁德和對(duì)社會(huì)所作的貢獻(xiàn)而贏得的尊敬,與其他人都是人格平等的。孔子說(shuō):“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君王與大臣之間都依禮而行,臣子對(duì)君王就忠心。法家顛覆了這些主張:“君”規(guī)定自己是“主人”,其他人,包括官和民,都是“仆人”、“下人”、“屬民”、“奴才”,如有不服就犯了“謀逆大罪”。更有甚者,不僅官和民本人是,他們的子子孫孫都是,永世不得翻身。董仲舒做奴才做得好,悟出了“三綱五常”,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與民的人格在法理上被剝奪。
在商鞅制定的“王法”框架下,本質(zhì)上“君”就是國(guó)家。行政區(qū)內(nèi)的任何人或者物都屬于“君”,“君”是所有者,有權(quán)使用和處理,或者禁止別人使用和處理。草木山川,飛禽走獸,人口人力等等組成這個(gè)國(guó)家的任何人或者物都?xì)w“君”所有。當(dāng)然國(guó)民似乎可以分享他們所需的東西,可以擁有財(cái)產(chǎn)。那是因?yàn)椋环矫婷褚载?cái)養(yǎng)命,民擁有財(cái)產(chǎn)是保障“民”作為經(jīng)濟(jì)人能發(fā)揮其社會(huì)職能;另一方面,民擁有財(cái)產(chǎn)對(duì)“君”而言只不過(guò)是藏富于民。取民之財(cái)亦如取己之財(cái),如“和珅倒,嘉慶飽”。高明的法家把“君”與國(guó)家、社稷(江山、政府)等同起來(lái)。“君”就“使民”有名,就可以以“國(guó)”的名義任意“弱民”、“馭民”、“使民”、“掠民”、“虐民”。“君”兩腳就踩在了法律和道德這兩個(gè)致高點(diǎn)上,無(wú)人能夠超越。自然而然,忠君愛國(guó)就成了國(guó)人的天職。
“賞軍功”被認(rèn)為是商鞅變法的最大亮點(diǎn)。它打破了原有的社會(huì)層級(jí),面向全體國(guó)人,做到了軍功面前人人平等,給人的錯(cuò)覺好像是解放了人格,從古至今不乏自欺欺人之輩為之高唱贊歌。但當(dāng)人們?cè)谝呀?jīng)喪失人格的前提下,在“名為國(guó)、實(shí)為君”的欺詐中,在你因軍功而獲得名與利仍不能從本質(zhì)上改變你的奴才身份時(shí),這何曾是人格解放,不過(guò)是“君”給他豢養(yǎng)的牲口加的一點(diǎn)飼料而已。康德說(shuō):“人實(shí)則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個(gè)目的,并不只是供這個(gè)或者那個(gè)利用的工具。”商鞅右丞相,爵位左庶長(zhǎng),李斯左丞相,爵位左庶長(zhǎng),名副其實(shí)一人之下,萬(wàn)人之上,可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把他們劃分到“民”的范疇,而“權(quán)”由君一人專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商鞅、李斯同樣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yùn),最終只能是“他以他血薦君王”。
三、商鞅變法引導(dǎo)中國(guó)社會(huì)和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向?qū)V粕鐣?huì)和專制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轉(zhuǎn)型
西周建立之后,在周公旦的理想主義和姜尚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中華文明經(jīng)過(guò)六、七百年的長(zhǎng)足發(fā)展,到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出現(xiàn)了中國(guó)歷史上構(gòu)成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核心的最光輝的鼎盛時(shí)期----百家爭(zhēng)鳴。這一時(shí)期,天子虛王,七霸稱雄,諸侯并存,世族共治,政治環(huán)境寬松,社會(huì)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繁榮,人員流動(dòng)自由,由于孔子的卓越貢獻(xiàn),文化下移,私學(xué)勃興,教育普及程度較高,不僅僅是士大夫就連平民都有很多的自由發(fā)展機(jī)會(huì),比如,莊子、晏子、呂不韋、李斯等很多人都出身平民,形成了以仁愛禮義為核心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以孝悌忠信、禮儀廉恥為主要內(nèi)容的社會(huì)道德標(biāo)準(zhǔn),以“修身、養(yǎng)性、治國(guó)平天下”為代表的社會(huì)價(jià)值觀,在中庸哲學(xué)的引導(dǎo)下提出了“民為貴”、“無(wú)為而治”、“以德治國(guó)”、“以人為本”、“制民之產(chǎn)”、“天人合一”等永恒的治國(guó)理念和人文思想,基本形成了相對(duì)的自在的共生社會(huì)形態(tài),萌生了有限共生君主制政體。
誠(chéng)然,這些近乎穿越的理想主義人文思想在君主制政體下是局限而脆弱的。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發(fā)展了系統(tǒng)的國(guó)家治理枝術(shù),徹底顛覆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形態(tài)和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從思想上、法理上和體制上一步到位地構(gòu)建了功能社會(huì)形態(tài)和專制君主制政體,君主集立法權(quán)、行政權(quán)、司法權(quán)和國(guó)家所有權(quán)四權(quán)于一身,而且永不回頭。
商鞅變法首先在秦國(guó)建立了較完善的專制的社會(huì)形態(tài)。美國(guó)功能主義社會(huì)學(xué)家塔爾科特·帕森斯(1902-1979)認(rèn)為,社會(huì)形態(tài)就是社會(huì)成員的社會(huì)身份和社會(huì)角色的總稱。身份是社會(huì)地位,角色就是與地位相應(yīng)的規(guī)范行為。如前所述,商鞅變法完成了社會(huì)成員的身份和角色的劃分,也就是規(guī)定了全民功能。君主是國(guó)家的所有者,是主人,占居社會(huì)系統(tǒng)的頂點(diǎn),而其他人都是“被馭者”,服務(wù)于君主,按照君主的意志從事各項(xiàng)職業(yè)。君主的意志和目標(biāo)就是全國(guó)共同的意志和目標(biāo)。君主要富國(guó)強(qiáng)兵,那富國(guó)強(qiáng)兵就是共同的意志和目標(biāo)。人力作為資源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職能就是農(nóng)戰(zhàn),即創(chuàng)造社會(huì)財(cái)富和參加戰(zhàn)爭(zhēng),君主(由政府代替)管理財(cái)富。《商君書·弱民》中說(shuō):“民富則六虱生而國(guó)削”,“民貧富之,民富貧之。”不能想當(dāng)然“富國(guó)強(qiáng)兵”就等于“富國(guó)富民”。管理財(cái)富也包括控制財(cái)富,要強(qiáng)兵就不能富民。“民”的功能就是“富國(guó)強(qiáng)兵”,而不是“富國(guó)富民”。這是專制的特性。
君主專制的社會(huì)形態(tài)必然同卵孿生出君主專制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意識(shí)形態(tài)是統(tǒng)治奠定的思想基礎(chǔ),是社會(huì)性格,是社會(huì)無(wú)意識(shí)。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仁義禮智信、君子品格、圣賢理想構(gòu)成了較為普遍的社會(huì)價(jià)值觀,仁政是統(tǒng)治奠定的思想基礎(chǔ)。商鞅變法改變了業(yè)已形成的社會(huì)意形態(tài),奠定了“嚴(yán)刑峻法”、“賞軍功”、“奸行天下”、服從共同意志和目標(biāo)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和價(jià)值觀。商鞅提出:“國(guó)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guó)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qiáng)。”(《商君書·去強(qiáng)》)一個(gè)國(guó)家用好人統(tǒng)治奸人,國(guó)家一定會(huì)動(dòng)亂,最后衰弱,反之,則一定會(huì)治理好,并且變得強(qiáng)大。韓非也說(shuō),“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劫其君。”(《韓非子·二柄》任用賢能之人,就會(huì)被他依仗賢德之名而掣肘。商鞅認(rèn)為只有奸人才可以做到違法必舉,刑罰必重。“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韓非子·奸劫?gòu)s臣》)依賴別人出于愛為我效力就危險(xiǎn)了,依靠使人不得不為我效力才能平安。有了這些思想基礎(chǔ),在重罰、賞功、尚奸、禁“六虱”、“十有”、“五蠹(儒家、縱橫家、帶劍者、逃兵役者、商工之民)”多管齊下的情況下,民皆只盼望打仗立功,戰(zhàn)場(chǎng)上,個(gè)個(gè)如狼似虎。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是統(tǒng)治奠定的思想基礎(chǔ),統(tǒng)治者尚力不尚智,尚奸不尚善,“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勇猛、殘暴、奸險(xiǎn)、棄文從武等社會(huì)性格接踵而來(lái)。不過(guò)力足可以勝天下,然則智有不足了。自商鞅至秦滅亡150年,右丞相14人:商鞅、公孫衍、張儀、樗里疾、樓緩、魏冉、范雎、蔡澤、呂不韋、熊啟(楚公子)、隗狀、王綰、馮去疾、趙高,最后一任左丞相:李斯,共15人,只有樗里疾1人是秦國(guó)人。
四,結(jié)束語(yǔ)
古語(yǔ)有云:“始作俑者,其無(wú)后乎?”答案是肯定的。中國(guó)后來(lái)歷代帝王無(wú)一例外地采用了商鞅的君主專制體制,傳承了專制思想、專制社會(huì)形態(tài)和專制意識(shí)形態(tài)。這場(chǎng)變革從主流政體中徹底驅(qū)除了儒家思想。法家的實(shí)用主義戰(zhàn)勝了儒家的理想主義,占領(lǐng)了中國(guó)政治的法統(tǒng)。法家得到了當(dāng)權(quán)者的支持,有法律的武器,有富國(guó)強(qiáng)兵的綱領(lǐng),有權(quán)代表共同意志和共同目標(biāo),而儒家只有為民請(qǐng)命的天職。從這時(shí)開始,中國(guó)傳統(tǒng)和中國(guó)文化分裂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是法家的君主專制政治傳統(tǒng);中國(guó)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諸子百家思想。董仲舒并沒有真正恢復(fù)儒家的法統(tǒng)地位,而是鞏固了法家的法統(tǒng)地位,發(fā)展了君主專制思想。“罷黜百家”就是法家的共同意志論。“獨(dú)尊儒術(shù)”講的是“術(shù)”,即“禮、樂(lè)、射、御、書、數(shù)”,主要是教化百姓。他基于法家、道家、陰陽(yáng)五行學(xué)說(shuō),裝神弄鬼,提出“天人感應(yīng)”、“君權(quán)神授”、“天命所歸”,“三綱五常”,只是跪舔,絕不能代表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