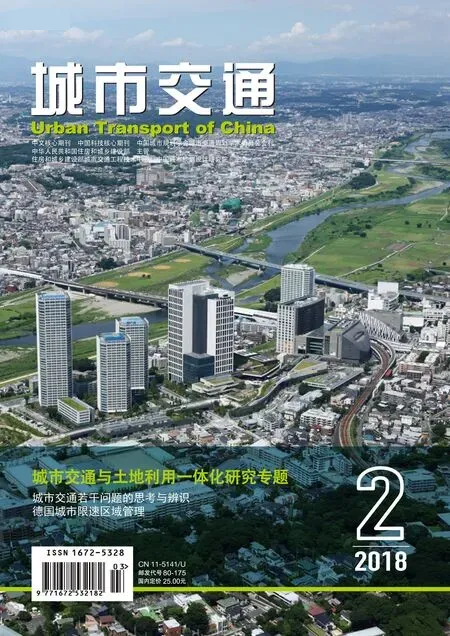城市交通若干問題的思考與辨識
(北京交通發展研究院,北京100073)
0 引言
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變革的關鍵時期,城市發展模式、社會經濟增長模式、科技發展模式均在轉變中,城市交通系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生態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一是城市發展模式的變革。《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發布,明確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1]。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推進,意味著城市發展將擯棄過去粗放的城鎮化模式,進入以提升質量為主的轉型發展新階段。
二是社會經濟增長模式的變革。經濟新常態下,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增長模式將從依靠資金、土地、人力等要素驅動向依靠知識創新、技術進步、管理制度變革等創新驅動轉變。《關于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2]的出臺,將進一步推進國家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而其著眼點之一就是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這意味著國家行政體制也將面臨改革。
三是科技發展模式的變革。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和通信技術(Communication Technology,CT)的深度跨界融合(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引發科技發展模式革新。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新技術的蓬勃發展促使新業態不斷涌現。國家創新體制的改革,首次提出把科技創新的主體界定為市場和企業,改變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以來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
上述三方面發展模式的變革,重要的共同點在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尋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體性和諧發展;其次,更加關注以質量、效益、品質為核心,以創新驅動的內涵改造,而非以數量、規模為著眼點,以資本(資源)投入為驅動的外延擴充;第三,明確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毋庸置疑,社會經濟形態與城市發展模式的轉變必然引發城市交通體系的深刻變革。這不僅涉及對交通服務宗旨、交通服務產品的社會經濟屬性的重新界定,還包括供給模式、供給策略和供給制度的變革。而現代信息通信領域技術的創新和突破,將為城市交通發展模式變革提供很好的技術支撐條件。
1 建立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新規劃模式
1.1 交通規劃的技術困境:不確定性
當前城市交通規劃面對諸多不確定因素。這種不確定性包括城市空間形態與功能配置、土地利用、社會人文與經濟等規劃客體,也包括規劃編制與實施過程中不同利益主體意志的博弈[3]。在空間和社會劇烈變遷的背景下,傳統的調查—分析—預測—規劃方法和過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傳統的確定性規劃基于過去的規律外推以預測未來的發展狀況。囿于既有知識的局限性,無法全面把握影響未來發展的多重復雜驅動因素變化規律。
其次,傳統城市規劃著眼于終極目標理想藍圖或愿景,而非關注實現遠景目標的過程。規劃給出的所有對策和布局方案未能充分顧及漫長實施過程中影響交通需求的相關因素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導致規劃預測的可靠性大打折扣,甚至會帶來錯誤的結果。這種確定性思想指導下的一站式規劃不具有可塑性,與未來實際難免成南轅北轍之勢。
第三,交通系統狀態無論是與系統內在結構因素的關系,還是與其外部環境各類因素之間的關系,既不是固定不變的自變量與因變量關系,更不是單純的線性因果關系,而是更為復雜的互為因果的關聯關系,很難采用基于線性因果關系建立的模型進行模擬和預測。
因此,要以持續規劃和動態調整的新理念,取代一張終極藍圖定乾坤的傳統舊觀念,并對傳統的調查—分析—預測—規劃的方法和工作模式要有針對性的合理揚棄。
1.2 城市不確定演變過程的跟蹤、規劃響應與戰略調控
大數據在交通領域的應用為監測城市與交通系統的互動演變過程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基于大數據應用優勢,充分發揮規劃師的洞察力和協調能力,尋求建立各種不確定性環境下的不確定規劃模型(models with deep uncertainty),對城市不確定性演變過程進行跟蹤并做好規劃響應和戰略調控,將成為規劃模式變革可行的新途徑。
1)建立應對不確定性環境下的不確定規劃模型。
既有的三大類不確定規劃模型有:期望值模型、機會約束模型和相關機會規劃模型。另外還有一種是把終極規劃改變為過程規劃的基于交通與城市互動發展態勢全面感知的“證-析”規劃模式。在諸多不確定性規劃理論方法中,情景規劃方法被認為是處理動態、復雜、非線性和不確定的環境的最好方法之一[4]。情景規劃是在預測不足和預測過度之間找到平衡,即通過一系列定性或定量的變量組合描述未來系統的狀態以及由當前形勢發展到未來狀態的路徑,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外推、未來終端狀態鑒別和預測事件的綜合考慮得到關于未來的場景[5]。情景規劃注重規劃與不確定性環境的互動過程,因而是真正的過程規劃。
2)對城市不確定的演變過程進行跟蹤并做好規劃的響應和戰略調控。
規劃實施演變進程遠比最終的結局復雜,規劃期中采取的戰略舉措可能有別終期規劃戰略,二者的分寸兼顧與時機把握需慎之又慎。例如,新區和副中心疏解中心城功能的終極目標實現是極為漫長的過程(至少10~20年),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依賴中心城的公共資源支持,勢必要強化與中心城的交通聯系,難免會進一步強化中心城的吸附力。若策略分寸與時機把握失當,依附關系將被固化,疏解中心城功能、引導人口和產業由特大城市主城區向周邊和其他城鎮疏散轉移的目標終將落空。因此,亟須基于現代信息通信技術對交通與城市互動發展的態勢,以及決定這一態勢走向的驅動因素的變動進行跟蹤監測評估。基于對不確定性環境的持續跟蹤監測,評價交通跟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協調適配度,評估規劃方案編制與實施過程中規劃調整的合理性;對規劃實施效果的成功經驗以及偏差原因進行剖析,在預測未來不確定性環境多種趨勢的基礎上,提出規劃、政策設計和規劃運作制度的修正方案。面向不確定性的規劃是一種動態前進的開放性戰略調控過程,而戰略調控的關鍵是資源配置與交通供給模式。
2 交通服務屬性的重新界定與供給模式變革
2.1 城市交通服務的社會經濟屬性
正確界定交通基礎設施及交通服務產品的社會經濟屬性是決定城市交通資源配置模式的關鍵,目的在于厘清交通服務的提供主體和生產主體。文獻[6]對城市交通設施及交通服務的社會經濟屬性進行了詳細闡述。根據公共經濟學理論對社會產品屬性的界定,城市交通基礎設施以及所提供的服務基本都屬于準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具有明顯競爭性和排他性,應該按照市場化原則或政府與市場共同分擔的原則提供[6]。
2.2 對現行交通供給模式的反思
政府統包的交通服務供給模式源于中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經濟社會制度體系,其理論基礎正是深深打上計劃經濟烙印的《財政學》而非現代《公共經濟學》。現行交通供給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在于以下幾個方面:1)市場主導的城市土地開發與政府主導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彼此無交集是導致TOD模式無法落地的根本原因,交通與城市的協同發展關系難以建立和維系。2)無法擺脫資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低下(甚至錯配)、市場價格扭曲、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財政負擔過重的尷尬困境。3)受制于資本(資源)投入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以公共資源投入為主要驅動力的發展模式必然導致供給增長的不可持續。
2.3 供給模式變革目標、方向及難點
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目標是從深度和廣度上推進市場化、創新資源配置方式、放松政府規制,構建交通供給服務競爭機制,形成交通供給服務體系的多元化和適度規模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效益,給消費者創造更多的交通服務選擇機會。
城市交通供給模式改革的方向是以滿足公共服務需求、增加有效供給、提升服務品質為首要前提,堅持交通供給的公平與效率兩大標準,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交通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在規劃引導、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等方面的職能。其難點在于政府供給與市場供給是公平與效率的博弈與平衡,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風險共存。因此,供給模式變革的核心是法治環境與社會誠信體系建設,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避免政府和市場雙失靈。
3 城市綜合交通體系結構重組
3.1 對現有二元結構體系的反思
當前區域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邊界模糊不清,而城市綜合交通體系在城市行政邊界范圍內,兩者服務宗旨各異、規劃—建設—經營—服務主體不同、系統制式和技術標準自成體系、運行與服務模式不兼容。現有的區域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和城市綜合交通體系二元分割的格局存在諸多問題。
1)各種交通方式只在中心城區“界面握手”(換乘樞紐)而沒有“跨界融合”。
以軌道交通為例,由于系統制式不兼容、管理和規劃主體不統一等因素,城市軌道交通與鐵路缺乏有效融合,各種軌道交通系統之間難以優勢互補和有機銜接,難以充分整合網絡通道資源。銜接界面多家經營主體彰顯各自的領地意識,實行領地割據,而置乘客利益于不顧。以北京西站為例,以鐵路站房、進站系統等為主的地上部分和以出站系統為主的整個西站地區分別隸屬于北京鐵路局和北京市政府兩個不同的管理主體。各管理主體之間基本保持獨立運營,在換乘銜接、運力配置以及面向乘客的服務信息等方面均缺乏有效整合。
2)介于城市與區域兩大系統之間的空間圈層(30-70-120 km)成為系統服務盲區。
從都市圈層面看,城市(中心城)軌道交通系統由地鐵獨占鰲頭,然而,近年來隨著城市建成區不斷向外拓展,居民通勤距離不斷增長。以北京市為例,以燕郊為代表的環京城鎮已經融入北京都市圈發展范疇,但30~70 km圈層依然缺乏相應的快速軌道交通網絡的支撐。從城市群層面看,京津冀城市群內各城市之間的聯系主要通過既有國家鐵路干線(普速鐵路、高速鐵路等)承擔,在車站設置、發車頻率、服務水平上難以滿足城市間頻繁交流和高效出行的需要,城際鐵路建設亟待加快。此外,軌道交通系統制式選擇隨意、服務定位與市場需求背離、通道資源錯配等問題亂象叢生。顯然,這種二元分隔自成一統的割據和失衡的結構體系,不僅無法為大都市圈提供高效的出行服務,更難以實現資源整合共享、系統互聯互通,無法滿足城市群的發育和發展需要。
3.2 重構“區域—城市”綜合交通運輸結構體系
城市群的發育及同城化趨勢使區域交通與城市交通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重構“區域—城市”綜合交通運輸新結構體系勢在必行,必須打破體制和權屬關系藩籬,滿足區域一體化發展及資源整合的需要。
一方面,重組后新的城市綜合交通體系結構必須實現不同空間圈層多種交通方式功能兼容互補、服務需求共擔的高度融合,而不只是界面上的“握手”銜接。另一方面,不同空間圈層交通需求構成是決定未來系統功能結構的唯一依據。不同的客流特征構成決定了不同的服務標準要求,進而決定了與之適配的運營模式和系統制式。因此,在通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軌道交通系統制式、運營模式的選擇絕不可隨意,需合理配置線路及站位,同時細化運營組織規劃,將不同交通需求在有限的通道內予以滿足[7]。
4 對城市交通規劃目標和控制指標的思考
4.1 交通規劃目標制定存在的錯誤傾向
中國各大城市在交通規劃編制過程中,無論是制定規劃目標還是確定規劃指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錯誤傾向,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1)忽視交通發展目標的戰略理念與內涵,規劃目標與規劃指標泛化。
一方面,羅列和堆砌空洞概念,例如高效、便捷、安全、經濟、綠色等。由于規劃實施(執行)主體對規劃目標內涵理解的不同,必然導致戰略方向游移不定。另一方面,交通發展目標和指標盲目效仿,無視大中小城市、東中西部城市交通發展階段和基礎條件的顯著差異,千城一律。實際上僅就交通結構規劃指標而言,即便是同一城市,對應不同時空范圍(市域、中心城、核心區等)也有不同的交通結構標準。
2)規劃目標和控制指標缺乏科學論證。
受急功近利的行政干預,規劃目標和控制指標大多未經必要性和可行性論證,且與規劃對策無關聯。僅以交通結構為例:在確定這一規劃指標時,既未認真研究出行方式與需求特征的內在依存關系以及不同出行方式之間相互制衡關系,也未認真論證分析交通結構優化的充要條件及規劃期內具備這些條件的可能性。不僅如此,在許多城市的綜合交通規劃中,規劃編制者并未把這一指標作為基礎設施供給規模論證、布局方案及運營模式選擇的依據,實際上對規劃并無約束力。
3)以車為本理念根深蒂固,陷入戰略目標與策略悖論。
大多數城市把公共交通出行分擔率、高峰時段道路通行效率(速度)一并列入規劃指標。公交優先戰略的目的是通過資源配置的合理傾斜,在提高公共交通與個體機動交通(小汽車)競爭優勢的同時,最大限度壓縮小汽車使用空間和使用成本。然而,許多城市治堵的著眼點在于提升小汽車行駛速度和使用條件。
一方面,以治堵的名義不斷增加機動車道供給,甚至不惜擠占行人和自行車通行空間;另一方面,把大量技術與財力資源集中用于車路協同技術研發與成果孵化應用。本文無意全面否定其學術價值與社會現實意義,但就其以提升小汽車出行服務水平主要著眼點而論,確有檢討之必要。
4)對“堵”的界定和“治堵”著眼點與著力點陷入誤區。
在各城市治堵過程中,政府對道路通行效率(速度)的敏感與關注度實際上遠高于公共交通出行分擔率。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代表的超大城市道路網高峰時段平均車速為20~30 km·h-1,已經明顯高于許多歐美城市(16~20 km·h-1),而且小汽車出行速度已遠高于公共交通。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下歐美大力推行“道路瘦身”,不斷壓縮小汽車使用空間,而中國的城市政府決策者在道路擁堵排名強烈地刺激與誘惑下,掀起一波接一波非理性的治堵大比拼浪潮,結局便是城市公共資源錯配及交通結構畸形化趨勢愈演愈烈,小汽車出行需求無節制膨脹。不禁要問,當今各地盛行的這種治堵與公交優先,究其實質,二者豈不是目標自相矛盾、行為相互掣肘嗎?如此尷尬比拼何日是盡頭?
4.2 交通規劃的主要目標和著眼點
城市交通規劃的目標應該與城市環境、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相適配,以城市流動性(Urban Mobility)表征的可持續增長活力逐步成為交通規劃的方向和戰略著眼點。
1)堅持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
一方面,尊重不同群體出行選擇權的公平與公正,在交通資源配置方式、服務模式上,使市民以最低的代價(頻次、距離、時間、服務費用)滿足日常所需要的出行。另一方面,以人的需求出發構建規劃控制的指標體系,例如相比于公共交通出行分擔率和道路通行效率(速度),以全方式日均出行時耗或廣義可達性作為主要規劃控制指標或許更具戰略價值。
2)促進城市交通空間重構。
以滿足城市公共空間功能多元化和包容性為前提,推廣完整街道(complete street)設計理念及方法[8],從道路設計回歸到街道設計,秉持安全、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交通理念,保障所有交通方式出行者的通行權,為所有出行者提供一個公平的道路交通空間。不僅如此,城市交通空間歸屬于城市公共空間范疇,城市交通空間的重構要充分顧及城市公共空間的多樣性功能需求,處理好不同場合二者主次功能目標與協同關系。
3)實現多種交通方式融合與協同發展。
以客觀資源和環境容量作為交通系統構建與擴展的約束條件,充分發揮不同交通方式滿足居民不同出行目的、出行距離和出行要求(舒適性、時效性等)的優勢,最大限度地實現多元交通方式融合與系統整體協同效應。
5 公交優先和公交都市
5.1 公共交通發展現實瓶頸
中國城市公共交通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難以逾越的瓶頸階段。從北京、上海、廣州等超大城市交通結構來看,公共交通出行分擔率的提升進程舉步維艱:北京是全國唯一一個公共交通全方式出行分擔率(中心城,不含步行)連續多年每年持續上升約2個百分點的城市,但是付出的代價也非常巨大(每年新增軌道交通線路40 km,按8~10億元·km-1的造價計算,建設成本高達三四百億元,且每年政府還要支出大量運營補貼)。上海市公共交通全方式出行分擔率從2009年18.5%上升至2014年20.7%,五年僅上升2.2個百分點。廣州市2010—2015年市區公共交通在機動化中的出行分擔率基本沒有變化(僅增加0.3個百分點)。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小汽車出行分擔率卻居高不下,作為綠色交通重要出行方式的自行車出行比例反而逐年下滑。與此同時,公共交通面臨著另一窘境,即中國大城市在大力發展軌道交通的同時,公共汽(電)車的資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運力逐年提升而客運量卻持續下降。
中國城市公共交通發展之所以面臨上述瓶頸,關鍵在于服務宗旨和服務屬性定位的偏差,主要表現在:
1)經營服務觀念與宗旨的偏差。
長期以來過于片面強調公共交通的社會公益性和社會基本出行保障服務,對日益增長的非公益性公共服務市場需求未給予應有重視。
2)經營服務模式單調與客觀需求多樣性之間的矛盾。
按固定網絡和運力配置、定時定線運行這一傳統運營服務模式從計劃經濟時代延續至今。隨著出行需求的多樣化和復雜化,既有的公共交通運營服務方式從未按細分的(為不同時空環境、不同目的出行的不同用戶群體服務)客觀市場需求做合理配置,且信息不對稱的“坐店待客”服務模式更無法為出行者提供多樣化服務,導致公共交通愈來愈難以與小汽車競爭,服務吸引力每況愈下。
3)政府壟斷的經營體制與市場多層次差異化需求的矛盾。
絕大多數的國有公交企業長期受傳統經營觀念與體制的束縛,加之經營服務市場競爭環境的缺失,久而久之企業便養成事事依賴政府的經營惰性,漸漸喪失主動拓展客運市場空間的積極性,以致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與社會實際要求之間不平衡的矛盾日趨尖銳。
5.2 公共交通服務市場化改革
中國城市公共交通系統面臨戰略轉移的十字路口,必須進行戰略性的變革。首先,要重新界定公共交通服務宗旨和服務定位。將公共交通的服務定位從提供市民基本出行服務保障調整為:面向社會不同階層,為凡適合公共交通的各類出行提供全面且可供選擇的服務(包括個性化增值服務)。其次,打破壟斷經營傳統格局,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全面改革系統配置和運營服務模式。此外,借助現代信息通信技術,全面提升網絡化運營的實時響應服務能力及可靠性;同時支持發展個性化、定制化及一站式統籌共享服務的多元化模式。
5.3 對建設公交都市的反思
中國政府部門與交通規劃人員在公交都市本質與內涵認識上存在誤區,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1)公交都市不等于都市公交。
根據羅伯特·瑟夫洛對“公交都市”的定義[9],公交都市的本質是城市發展模式和交通發展模式的融合。因此,公交都市的建設絕非等同于都市公共交通系統或公共交通行業建設,需要突破交通行業發展層面的局限,從城市發展模式的戰略高度,更加關注公共交通與城市的協調發展。
2)公交都市建設的責任主體不是公交企業,應該是地方政府。
公交都市實際上是城市的一種發展模式,因此單純地從公共交通系統著手并不能真正建成公交都市,公交都市建設的責任主體不是公交企業,應該是地方政府。公交都市建設的重點應該是如何促進公共交通與城市建設的融合發展,而不是僅僅關注對公共交通自身的考核,目前交通運輸部印發的《公交都市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及考核辦法均需改革。
3)不存在通用的發展模式和無差別的評價考核指標。
公交都市的發展模式與城市形態息息相關,不同形態與特點的城市適宜的公共交通系統有所區別,不存在通用的發展模式和無差別的評價考核指標,應鼓勵不同規模、形態和發展階段的城市因地制宜地去探索與其相適配的發展路徑。
6 理性對待大數據和互聯網+背景下的新業態
6.1 關于共享交通
近年來在共享經濟的旗號下,名目繁多的共享交通、共享出行的經營服務新業態井噴式的爆發。關于共享經濟(亦被稱為分享經濟、協同消費),目前尚無統一定義。一些觀點認為共享經濟是指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對閑置資源的整合、分享,目標是實現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10]。但也有學者對共享經濟給出了不同的見解,認為共享經濟的本質不是閑置資源的共享,而是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不求擁有但求服務。不可否認,當前不僅對共享經濟的內涵尚存爭議,各類鋪天蓋地而來的共享交通服務也還處于試水階段,難免魚龍混雜。如何正確面對商業創意的美好包裝或多或少帶來的誤導性,需要更加理性的獨立思考,切忌盲目跟風。
首先,當下熱門的網約車、分時租賃共享汽車和共享單車等各種共享交通形式,并非都是調動和利用閑置資源,而是投入了更多的增量資產。例如網約車催生私人小汽車駕駛人投入運營,實際上是通過增量服務釋放了潛在需求,其中包含有悖于出租汽車在城市出行服務體系中合理定位的非理性需求。
其次,忽視空間資源共享,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共享出行。共享交通利用的交通資源除交通工具外,還占用了有限的城市公共空間(停放和道路空間)。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共享出行服務,都涉及公共資源的配置效率與社會公平。市場規制以及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尚未真正到位。
6.2 值得關注的問題
對任何新業態既不能以墨守成規的態度拒之千里,也要充分評估它對整個城市交通系統帶來的后續連鎖影響。要以城市交通基本戰略價值觀認真審視各種交通(出行)方式的服務群體效率與公平性是否得到確切保障。有幾個問題值得認真對待:
1)合理、區別對待不同的共享交通模式。
堅持城市交通基本戰略原則,對不同的共享交通模式區別對待,合理揚棄。處理好存量共享和增量共享的關系,提倡和鼓勵存量共享優先;著眼于資源與環境效益,堅持去私人小汽車化的可持續性發展原則,按照交通方式的公共性大小以及集約化程度進行排序,鼓勵綠色共享出行優先,處理好個性化出行共享服務與集約化出行共享服務的關系。
2)充分評估各類共享交通模式的負外部性。
充分顧及城市資源環境約束條件和社會現實治理能力,防止負效益轉嫁帶來的問題,防范公地悲劇與市場失靈,同時處理好新業態與傳統業態融合共存共進關系。
3)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無論何種城市交通服務業態都必須建立在有嚴格規制的市場環境中。政府要整合社會各種資源、動員社會多個主體來共同參與交通服務行業管理,搭建利益相關方協商機制和平臺;實行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管理;積極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法治管理手段的創新,降低管理成本。
4)關注城市交通真正的、最需要的共享。
城市交通真正需要的共享,應該是以人為本、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城市公共空間資源合理共享,是既有不同層級、不同權屬交通服務設施閑置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共享,是為區域交通一體化發展而開放的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及社會資源共享,以及政府與社會信息資源的開放、融合、共享。
7 城市智能交通發展目標與主流方向
7.1 智能交通發展存在的偏向
目前中國城市智能交通研發與應用與城市交通發展模式、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方向出現了偏離,主要體現在:
1)應用領域有待拓展,厘清信息服務與智能決策本末關系。
當前對智能交通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與信息技術系統(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ITS)兩個不同的ITS概念常有混淆,以致迄今智能交通研發與應用仍多偏重于公路與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服務信息化以及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領域,而在戰略與規劃決策層面上的智能化應用則是乏善可陳。此外,片面強調新技術的研發,忽略交通戰略、規劃、決策理論的創新;尤其是交通與城市互動關聯理論的研究幾乎還是空白。
2)著眼點更多關注治標而非治本。
無論車路協同系統還是無人駕駛固然有助于改善行駛安全,在特定時空范圍有條件地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但對城市交通系統全局而言發揮的作用無異于揚湯止沸。試圖以車路協同系統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效率,從而解決交通擁堵的策略恐難以如愿。這是因為其有悖于城市交通發展戰略原則與基本規律,忽視交通供給與需求相互制約的關聯性,尤其是供給對需求的引導與調控作用。現代城市交通戰略主張擴大集約化運輸和綠色出行服務供給,而不是一味增加供給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此外,即便僅就車路協同關系而言,道路功能結構-拓撲結構的動態改變以及對車輛駕駛人行為(即實際需求)的反制也不容忽略,其他非道路類的交通基礎設施配給結構與分布同樣潛移默化地改變道路使用者的行為。
3)忽視不同空間范疇智能交通需求差異以及子系統協同關聯性。
不同空間范疇的智能交通需求存在顯著差異,城際、區域(城市群)以及城市(都市圈、市域、中心城)不同空間層次的智能交通需求、發展目標、系統構成均有各自特點,而迄今中國的智能交通系統研發與應用缺乏細致考慮。此外,目前各個交通子系統的智能化建設均采取了分而處之的策略方式,尚未充分考慮智能交通系統與城市功能大系統以及綜合交通系統各子系統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功能協同,例如交通與城市發展的互動關聯和協同互惠、基于交通大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相互依存關聯性和系統整體協同效應等。
7.2 智能交通發展的目標和方向
中國智能交通發展的正確目標是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全面感知、泛在互聯、普適計算、集成應用與人工智能應用為支撐,實現對城市交通與城市發展的智能化協同,對人的各類個性化活動與物流需求做出智能響應、實現城市智慧管理和運行、保障城市可持續發展。
智能交通戰略方向應該以城市交通發展戰略方向為導向和基本著眼點,側重關注:1)城市交通發展模式問題,如交通發展與城市土地利用、社會經濟發展、環境、資源的協調關系等;2)出行結構演化趨勢及關聯因素的智能辨析;3)城市空間拓展、功能布局演化動態及其與交通供求關系相關性跟蹤監測評估;4)以人為本的交通服務宗旨、客觀資源與環境容量對系統擴展的約束、多元運輸方式融合與協同效應以及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解決系統穩定性問題。
具體發展方向應為:1)基于交通與城市發展互動響應,以人機交互方式實現交通戰略、規劃、政策智能決策;2)基于需求實時響應的城市出行與物流配送交通運行組織一站式智能服務;3)城市交通運行風險監測、智能規避與應急處置;4)基于城市交通服務資源配置的智能化動態需求調控管理;5)主動式交通安全智能保障。
8 結語
本文從建立不確定性的規劃模式、交通服務供給模式變革、綜合交通體系結構重組、交通規劃目標和指標創新、公交優先和公交都市、理性對待新業態、智能交通發展等方面提出當前交通體系發展需重點審視的若干戰略方向性問題。面對城市交通規劃面臨的現實問題和未來需求,本文認為還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技術創新和方法探索:1)城市空間功能結構演進與交通發展的互動規律;2)出行結構演變規律與優化途徑;3)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市與區域綜合交通功能融合及結構體系的重塑;4)服務需求與供給的自適應與反制雙向作用理論;5)基于出行行為與空間特征映射關系的規劃模型體系;6)面向情景規劃(scenario planning)的不確定性模型研發;7)交通子系統運行水平關聯性理論及系統內外影響因素關聯度量化評價技術。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國務院.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EB/OL].2014[2017-10-05].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
[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EB/OL].2017[2017-10-05].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11/content_5159007.htm.
[3]全永燊,潘昭宇.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J].城市交通,2017,15(5):1-7.Quan Yongshen,Pan Zhaoyu.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J].Urban Transport of China,2017,15(5):1-7.
[4]王睿.基于情景規劃的城市總體規劃編制方法研究[D].武漢市:華中科技大學,2007.
[5]赫磊,宋彥,戴慎志.城市規劃應對不確定性問題的范式研究[J].城市規劃,2012,36(7):15-22.He Lei,Song Yan,Dai Shenzhi.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of Urban Planning Responding to Uncertainty[J].City Planning Review,2012,36(7):15-22.
[6]全永燊,潘昭宇.中國大城市交通市場化發展戰略研究[C]//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交通規劃學術委員會,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交叉創新與轉型重構:2017年中國城市交通規劃年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7.
[7]全永燊,劉劍鋒.區域軌道交通規劃若干問題與思考[J].城市交通,2017,15(1):12-19.Quan Yongshen,Liu Jianfeng.Issues and Thoughts on Regional Rail Transit Planning[J].Urban Transport of China,2017,15(1):12-19.
[8]葉朕,李瑞敏.完整街道政策發展綜述[J].城市交通,2015,13(1):17-24.Ye Zhen,Li Ruimin.A Historical Review of Complete Streets Policy Development[J].Urban Transport of China,2015,13(1):17-24.
[9]羅伯特·瑟夫洛.公交都市[M].宇恒可持續交通研究中心,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Robert Cervero.The Transit Metropolis[M].Chin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er,translated.Beijing:China Architecture &Building Press,2007.
[10]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6[R].北京: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