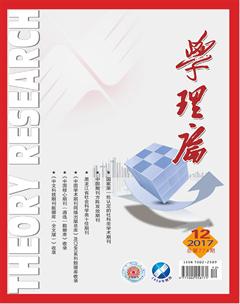集體行動邏輯視域下社會契約訂立可能性分析
陳強
摘 要:自然狀態是霍布斯與洛克社會契約訂立的基石。霍布斯所持接近敵對狀態的自然狀態和洛克所認為的有缺陷的自然狀態,二者都不約而同地把自然狀態的不完美性看作是社會契約訂立的必要條件。但社會契約的訂立不僅受到除自然狀態之外的諸多因素影響,在執行過程中也存在風險。分析霍布斯與洛克對自然狀態的闡述,發現二者對社會契約訂立過程中的主體、目的、權利轉讓等方面的認識存在差異與聯系。以集體行動邏輯為視角檢視兩者社會契約能否訂立的可能性,有利于霍布斯與洛克關于社會契約思想的互動,這為理解社會契約理論提供新的方法論依據。
關鍵詞: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論;集體行動;霍布斯;洛克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12-0075-03
霍布斯與洛克對自然狀態即社會契約訂立的依據的描述盡管有著不同程度的差異,但二者對社會契約得以訂立的基石有著本質的一致性。自然狀態的不完美性是二者社會契約得以訂立的基本前提。同時自然狀態下社會契約訂立的目的、參與主體、權利讓渡的份額以及因接受全體公民所讓渡權利、在達成社會契約基礎上而建立的集共同權利、共同意志于一身的國家的差異性即偉大的“利維坦”以及“有限政府”的差異。不完整的自然狀態使人民權利無法得到保障甚至生活難以維系是霍布斯與洛克社會契約得以訂立的前提。然而,社會契約作為保障人民權利、維系人民生活的前提仍需訂立契約的所有主體都能自覺遵守契約作為前提。同時,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的社會契約的訂立,仍需要作為理性計算個人利益得失的人不僅能夠在道德上,而且能在制度上自愿地或強制地接受社會契約,并依此行事,從而使得社會契約的訂立執行以及一種依社會契約行事的良序生活得以維系。
一、霍布斯與洛克自然狀態之比較
人類原本自然地生活在怎樣一種狀態之中即人類原初生活的自然狀態是何種狀態?自然狀態是霍布斯所認為的人們為了自身利益、安全、榮譽而形成的“人人相互為戰”的戰爭狀態,還是洛克所說的人們只聽從自身的意志而行動的一種完備無缺的、平等的、自由的卻不是放任的狀態。基于此,霍布斯與洛克的自然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異性。然而洛克同樣認為這樣完備的自然狀態亦存在缺陷。因此自然狀態的不完美性即接近敵對狀態的以及存在缺陷的自然狀態也使得霍布斯與洛克社會契約有著相似性。
(一)自然狀態的差異性
人們為何要通過轉讓自身的權利訂立契約、建立國家即社會契約訂立及契約建國的前提是什么?霍布斯與洛克對此達成了一致:自然狀態。然而,霍布斯與洛克對社會契約訂立的前提自然狀態有著不同的看法。霍布斯從“人性惡”的角度出發,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是“人人相互為戰”的戰爭狀態,人是自私自利、野蠻殘暴的,人們處于相互爭斗與恐懼不安的狀態之下,但是人性還是在理性的控制與支配之下,所以人們為了自身利益、安全希望擺脫這樣一種狀態、尋求安定的生活,因此人們愿意放棄原有的自然權利,訂立一種人們之間相互認可、共同遵守的社會契約。洛克從“人性善”的角度出發,認為自然狀態下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人們在自然法的范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1]3。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是和睦相處的、穩定有序的局面。
(二)自然狀態的相似性
霍布斯與洛克對自然狀態的描述并非對立的。盡管洛克所闡述的自然狀態是與霍布斯所描述的接近敵對狀態有別的穩定的狀態,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是和睦相處的、穩定有序的局面。然而,洛克也指出自然狀態是有缺陷的。因此,洛克才會尋求社會契約的訂立、通過契約建立國家,同時人們愿意放棄自然狀態下所享有的自由權利。洛克認為,即便自然狀態或許是穩定的,但是人們在自然狀態下所享有的權利卻是不穩定的、容易受到威脅的。同時,自然狀態同樣是有缺陷的。其一,自然狀態“缺少一種確定的、規定了的、眾所周知的法律,為共同的同意接受和承認為是非的標準和裁判他們之間一切糾紛的共同尺度”;其二,自然狀態“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來裁判一切爭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其三,自然狀態“往往缺少權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使它得到應有的執行”[1]77-78。故洛克才會想要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國家,從而使人們在自然狀態下所享有的權利更加有保障,人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才能得到更有效地保證。因而霍布斯與洛克對自然狀態的看法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其相似之處。這種缺陷的表現也體現在人人都有權與執行違反自然法的懲罰權,人人都有違反自然法的可能,沒有一個高于所有人的執行自然法的權力,洛克筆下的自然狀態同樣會淪為如霍布斯所說的人人相互為戰的戰爭狀態。
二、自然狀態下的社會契約訂立
自然狀態既是霍布斯認為的混亂不安的戰爭狀態,又是洛克認為的人們對自然權利的享有的不穩定的局面,為了結束這種“戰爭狀態”,也為了保證人們穩定地享有自然權利,人們就應該愿意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轉讓出自身所享有的權利,即便霍布斯和洛克在轉讓權利的份額上有一定的差異,人們依然會如此行事,訂立契約,從而保障自身的權利。
(一)社會契約訂立過程中的趨異性
首先,霍布斯與洛克不僅在權利讓渡的份額上有不同的意見:霍布斯認為人們應當將其除生命權以外的所有自然權利轉讓出去;洛克則認為,人們在訂立契約的過程中,只需將自然權利的一部分讓渡出去,同時認為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轉讓、不可剝奪。
其次,霍布斯與洛克在訂立契約的主體上的看法也同樣存在差異:霍布斯認為,社會契約訂立的主體是人民,是人民之間基于共同的意志和利益、為了自身安全而訂立的,進而把政府排除在訂立契約的主體范圍,從而產生了一個凌駕于所有人意志和權利之上的主體,即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洛克認為,社會契約的訂立不僅包括人民之間的契約的訂立,還包括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的訂立,訂立契約的主體還應包括政府,公民讓渡權力服從政府,政府同樣應當承諾保證人民的權利與安全。
最后,霍布斯與洛克在對轉讓出去的權利能否收回問題上表面上觀點一致,但實質上存在差別。霍布斯認為,擁有主權者(政府)不是契約的訂立者,人民是社會契約的訂立者,因而人民需要絕對地、無條件地服從主權者。即使是暴君,人民也沒有反抗和革命的權利。洛克雖承認權利讓渡出去不能收回,但是卻沒有否認人民有權反抗和革命的權利,因為主權者是訂立契約的一方,當主權者濫用職權違反社會契約時,人民是有權反抗和革命的,從而建立新的政府,同時將人們讓渡的權力重新交付于新的政府,表面上讓渡的權力沒有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實質上,人們是將讓渡的權利重新奪回再轉交與另一主體。在這一權利收回與否的過程中由于時間差極小以及程序上并沒有將讓渡出的權利通過一定的方式交還給讓渡權利者,因而不易察覺洛克對所讓渡出去的權利能夠收回這一潛在的事實。由此也可以看出霍布斯在這一政治思想理論上的現實局限,同時也能看到洛克這一政治思想理論對現實的(尤其是代議制政府)貢獻意義。無論從理論和現實,洛克的這一政治思想都比霍布斯更為成熟。理論上,洛克認為人們的生命權是不能轉讓的,但是當遭遇暴君的濫用職權而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安全時,人們為了自身生命安全有理由反抗和革命,即使洛克也提出人們讓渡出懲罰權,但并不否認人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沒有反抗政府的權利,而且人民讓渡權力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因此,當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脅時,社會契約訂立的前提就被推翻了,人民也就不再承認所訂立的社會契約。
(二)社會契約訂立過程中的國家觀
霍布斯與洛克在試圖通過社會契約的訂立建立一種怎樣的國家的看法上以及政府的權力構架上存在意見分歧;霍布斯認為,國家就是偉大的“利維坦”,他具有絕對的權力和至高無上的權威。其權力是不可分割,不可剝奪的。因為他不是契約的一方,不受契約人的制約,推翻他是毀約的、不合法的行為、是違反自然理性的叛亂。然而,人們轉讓或者放棄他們的權利的目的是為了自身的安全,結果卻產生了一個凌駕于所有人權力之上的暴力機器——“利維坦”。原本個體只受到來自單獨個體的威脅,當每個個體將權利轉讓給同一主體即“利維坦”時,一旦個體安全受到來自“利維坦”的威脅時,人民就受到了最為強大的威脅,因而,成立主權至高無上的“利維坦”來保障人自身的安全就會適得其反、事與愿違。洛克倡導的通過社會契約建立國家、成立“有限政府”與霍布斯所持的建立一個至高無上的“利維坦”有著本質差異。人們建立有限政府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自由、生命和財產安全。有限政府的權利是有限的,政府只能根據人民的同意、人民所轉讓的權利行事,超出權利范圍,人民即有權推翻并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并將權利轉交與新的政府。
霍布斯與洛克通過社會契約建立國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二者對所建立的國家態度上的差異。霍布斯所倡導的通過社會契約的訂立建立一個凌駕于所有人意志之上的國家機器利維坦,人們在利維坦統治的重壓之下不敢違背契約從而保障現有權利,但同時也不敢在利維坦的統治之下追求更完備的權利享有,這也正是霍布斯所認為的作為人類的最普遍的傾向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無止境的權勢欲。人之所以如此,并非人總是得隴望蜀、不知足、不滿足于一般的權勢,而是如果不如此行為去不斷地追求,他甚至會失去現有的財富、權勢等。就如同道德有最高的道德標準和最低的道德底線之二分一樣,人類的追求也有一個最低的欲望底線——維持現狀即保證既得利益的不喪失。因為既得利益者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消極對待周圍存在變革傾向的一切事物。洛克所認為的通過社會契約的訂立而建立一個在人民授權范圍內的有限政府讓人們不僅能夠保障既享權利的不喪失,同時也使得民眾能夠合理地追求更加完善的權利。有限政府治理下的人民不僅是既得利益者更是完善權利享有的追求者,因為有限政府存續與否取決于人民授權與否,超出人民授權之外行事的有限政府終將被取而代之。霍布斯為了保證自然狀態下的既享權利而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國家的消極國家觀和洛克為了追求更完善的權利享有而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國家的積極國家觀也是二者社會契約思想的重要差異所在。
三、集體行動邏輯視角下社會契約的訂立的風險與可能
作為理性計算個人得失、意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使社會契約訂立這一集體行動存在著巨大的風險性,從而使得社會契約的訂立難以形成,人們重歸于一種不安的、權利無法得以保障的自然狀態下的生活。然而,非純粹理性的、受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影響的、現實的社會人以及受到強制力(如規則、法律、武力)約束的法律人不僅在道德上,而且在法律上遵守契約并且依照契約行事,從而增強了社會契約的訂立及執行的可能性。
(一)社會契約訂立的風險
霍布斯與洛克,甚至后來的盧梭都不約而同地認為通過社會契約的訂立來保證人民的權利。然而,社會契約能否訂立本身就存在著諸多風險,社會契約的訂立不是簡單的權利主體雙方就某事達成一致意見即可。社會契約的訂立主體廣泛而不可控使其存在一定的風險。讓渡權力、訂立契約作為一種集體行動本身就存在許多障礙,也極易造成如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困境”,從而造成社會契約訂立困境。只要訂立契約的過程中存在不愿讓渡自身權利或少讓渡權力的主體,那么社會契約的訂立就會存在威脅。因為“除非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2]2。人是會計算利益得失的理性人,集團中的個人采取行動是為了自身利益,因而在訂立契約的過程中,只要有一部分人經過理性計算發現通過投機的方式可以盡可能讓渡比別人少的權利來建立國家,保障自己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契約的訂立不僅存在風險,而且即便以此種方式訂立契約、建立國家也同樣會是“少數剝削多數”的局面。因為只要人們認為自己只讓渡比別人少的權利也同樣能促成契約的訂立,從而建立國家保障自己的安全和財產時,作為理性的所有人都會如此行動,所以,由此產生的兩種結果就是:契約無法訂立、國家無法建立以及通過契約建立一個少數剝削多數的不公正國家。
契約訂立后何種力量能夠保證其得以實施?在霍布斯看來,“沒有武力,信約便只是一紙空文,完全沒有力量使人們得到安全保障。要是沒有建立一個權力或權力不足以保障我們的安全的話,以個人利益得失為計算標準的理性人就會合法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計策來戒備所有其他人”[3]128。因而霍布斯主張建立集所有人意志于一體的利維坦來保障人們的安全。然而,利維坦同樣需要一種力量來維護自身的安全。正如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主張的“一切國家的基礎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軍隊,而且軍隊最重要”[4]57。如果沒有良好的軍隊,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法律必須靠強制力得以保證實施,軍隊就是最為有效的強制力。因而,社會契約作為一種規則要保證實施同樣需要建立“最良好的”軍隊。這與前面說到的建立“利維坦”可能會置人民于更大的不安全之中并不矛盾,良好軍隊的建立不僅是對外保證國家自身獨立與安全的利器,而且也是對內保障人民權利與自由的最強有力武器。
(二)社會契約訂立的可能
盡管在集體行動邏輯視角下社會契約的訂立存在著諸多風險,然而,社會契約的訂立并非不可能,集體行動邏輯也并非毫無漏洞。無數未經過理性計算的個人在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支配下采取了諸如罷工、游行示威等集體行動的現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撼動了奧爾森在《集體行動邏輯》中的“集體行動困境”,因而社會契約的訂立作為全體人民的一種集體行動也有了可能。畢竟人并非純粹的理性人,人同樣也會在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的基礎上,在感性思維以及主導意識形態力量的支配下,為了社會或國家共同利益的實現而積極地采取行動。
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就成了社會契約能否訂立的關鍵。首先,全體人們要在社會契約訂立之前達成一份全體社會成員能夠遵守此契約的契約,否則將受到嚴厲懲罰;制定嚴厲的因不遵守或違反社會契約的懲罰性措施,從而使即便是理性計算個人利益得失的人也沒有搭便車的可乘之機,從而使社會契約的訂立成為可能,甚至是必然。其次,一種支配性的意識形態能夠消除社會成員通過理性計算個人利益得失而采取在社會契約訂立過程中投機取巧讓渡比其他社會成員相對較少權利的“搭便車”行為。最后,在社會契約訂立的過程中設置一種如羅爾斯所說的“無知之幕”,“無論他們最終屬于哪個世代,他們都準備在這些原則所導致的結果下生活”[5]136。簽訂社會契約的每個人也同樣如此,在無知之幕下簽訂全體簽訂社會契約主體所共同遵守的原則,并依此行事。為了共同利益的必然性必然戰勝為了個人私利的偶然性,訂立契約的每個人在只關注共同體利益之外對其他人包括個人私利一無所知,每個人在無知之幕下只服從內心公平正義的原則為共同體利益的實現訂立契約。
四、結語
社會契約論思想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在強調建立法治社會的當代中國,契約精神彌足珍貴。契約精神對現實法律規范、制度設計等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制定規則的人、受規則約束需遵守規范的人依然需要在契約精神的影響下、在契約道德規范影響下、在法律強制力約束下為了集體的或國家的共同利益而行動。法治國家的建立不僅需要法律底線的保障,更需要自覺遵守契約精神的行為人的道德支持。
參考文獻:
[1][英]洛克.政府論:下篇[M].葉啟芳,瞿秋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美]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英]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28.
[4][意]馬基雅維利.君主論[M].潘漢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5][美]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