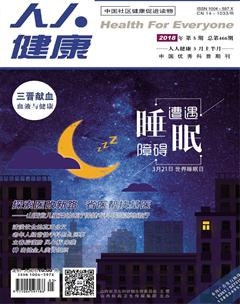林巧稚:一生只做一件事
本刊綜合

3月8日是第93個國際勞動婦女節,本期我們將帶領大家走進一位為現代婦產科學作出巨大貢獻的女戰士——林巧稚的世界。
林巧稚,20世紀中國著名的婦科醫生、婦產學家,是中國現代婦產科學的奠基人之一,是新中國首屆中國科學院唯一的女院士。她沒有婚姻,沒有孩子,守著一家醫院,一待就是六十多年。
1983年4月22日清晨,在婦產科忙碌了大半輩子的林巧稚在昏睡中發出囈語,急促地叫喊:“產鉗,產鉗,快拿產鉗來!”過了一會兒,她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又是一個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3個,真好!”這是“萬嬰之母”林巧稚留下的最后的話。
“我想當醫生”
在林巧稚5歲那年,母親就因為宮頸癌去世。她永遠無法忘記那個夜晚的臺風和海浪,母親的離世在幼小的林巧稚心中種下了成為一名醫生的種子。1919年,林巧稚畢業于廈門女子師范學校,但是她并沒有沿著做一名鄉村教師的軌跡繼續走下去。“如果不能繼續讀書,以后就是等著嫁人生子,平平淡淡地過生活”。林巧稚不想這樣度過自己的一生,她憧憬著成為一名醫生,在亂世中去醫治拯救千千萬萬被病痛折磨的人們。在老師卡琳的幫助下,林巧稚得到了父親和大哥的支持,決定報考協和醫學院。就這樣,她第一次走出鼓浪嶼,坐上了駛向上海港的輪船。
好不容易考上協和醫學院,經過8年的艱苦學習,林巧稚終于實現了當初的理想,穿上了神圣的白大褂。可是這僅僅是林巧稚在醫學道路上奮斗的開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醫院被迫關門。為了謀生,林巧稚—邊在北京東堂子胡同10號掛牌看病,一邊到中和醫院上班,還被聘為北大醫學院婦產科系的主任、教授。當時物價飛漲,在北大醫學院讀書的一些窮學生交不起學費和伙食費,不得不幫人打工甚至賣血來支付這筆費用。山河破碎的年月,生活本就無比拮據,但林巧稚聯合醫學院的其他教授,把在醫學院的全部收入都捐獻出來作為醫學獎學金,幫助那些生活貧困的北大醫學學生。1946年,她又受聘兼任北大醫學院婦產科系主任。到1948年重返協和的時候,林巧稚在北大只度過了短短的6年,但她為北大醫學教育作出的貢獻是歲月不可磨滅的。1949年,林巧稚收到了開國大典的觀禮邀請函,但林巧稚選擇留在醫院。安靜的產房里可以聽到天安門廣場上的歡呼聲和口號聲,林巧稚和病人一起度過了本應在天安門的時光。
晚年林巧稚不幸得了高血壓、動脈硬化、腦血栓和心臟病,在醫院里忙活了大半輩子的她不得不成為一名病人,躺在了病床上。她望著天花板,清點著那些沒有來得及做完的事情。林巧稚心中一直掛念著那本《婦科腫瘤學》的撰寫,只要身體一好轉,她都會在床上一頁頁地批閱初稿,仔細地標注自己的意見,為這個畢生的事業做著最后一點貢獻。
“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受父親和老師的影響,林巧稚自小就皈依了基督教。虔誠的信仰與醫生的職責完美結合,林巧稚一直告訴自己:“病人進了醫院,就是把整個生命交給了我們,我們要從每件細微的事做起,關懷體貼她們。我們不僅要解除病人身體的痛苦,更要解除他們心靈上的痛苦。”從醫幾十年,林巧稚遇到過各式各樣的病人,無論他們是富有還是貧窮,在林巧稚眼中,所有病人都是平等的。
每當林巧稚在門診的時候,她都會把當天掛號的所有病人看完才下班。如果她看到普通門診的某位病人表情痛苦,她就會放下手里的事情,直奔那位病人而去。有時候,待診室里有早已約定好的特殊病人,有時是某位要員的太太,有時是外國使領館的夫人,但林巧稚總是說:“病情才是真正的特殊。”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專程到醫院,希望結識林巧稚,想不到林巧稚以工作忙碌為由讓彭真吃了一個閉門羹。彭真的女兒傅彥后來說起:“我母親大概有點不舒服,后來以這個為借口,把她(林巧稚)請到家里來了,我父親才見到林巧稚大夫。”彭真的妻子還開玩笑說道:“我這個病人比你這個書記有面子哈。”
曾經接受林大夫診療的病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回憶:林巧稚從不會三言兩語打發病人,總是把病人當成親人一樣看待。病人董莉懷孕時,檢查發現宮頸有乳突狀腫物,專家會診建議切除子宮,以免乳突狀腫物變成腫瘤引發癌癥。切除子宮是不能重復的試驗,林巧稚體恤董莉結婚6年才懷上孩子的不易,對她反復進行仔細檢查,最終推斷這很有可能是妊娠反應,決定暫不進行手術。事實證明林巧稚的判斷是正確的,董莉生下了一個3公斤重的女孩。“孩子好,大人好,一切都好!”林巧稚走出產房,微笑著向董莉的家屬道喜。那個在林巧稚守護下出生的女嬰,父母給她起名為“念林”。
朱德夫人康克清回憶起與林巧稚的交往,深有感觸地說道:“她看病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論病人是高級干部還是貧苦農民,她都同樣認真,同樣負責。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我的唯—伴侶就是床頭那部電話”
大學畢業那年,林巧稚接到了協和醫院條件苛刻的聘書:“茲聘請林巧稚女士任協和醫院婦產科助理住院醫師。聘期一年,月薪50元。聘任期間凡因結婚、懷孕、生育者,作自動解除聘約論。”林巧稚雙手接過聘書,想起畢業時許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想到只有留在協和醫院她才能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她說服了自己,在聘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用一生的婚姻換取一生的醫學。
林巧稚的侄女婿周華康回憶起她時感嘆道:“她平常按時回家吃晚飯,是很少的。她每天下班以前到病房轉一下,一個個問一下情況怎么樣,如果有病人有問題,她就不回來了。她住在醫院的院子里,一旦有事,小跑就去了。”偶爾難得回家休息,她都要把家里的電話放在床頭,如果醫院有嚴重的病例,她就整夜地守著電話等消息。她曾經自嘲般說過:“我的唯一伴侶就是床頭那部電話喲。”
對于自己一直沒有結婚成家生子,她是這樣解釋的:“健康應從嬰兒抓起,我一輩子沒有結婚,為什么呢?因為結婚就要準備做母親,就要拿出時間照顧好孩子,為了事業,我決定不結婚。”在“萬嬰之母”林巧稚的世界里,醫院才是她唯一的家,而陌生的病人,則是她最放不下的至親。她的生活乃至她的心中,似乎再也沒有地方放下一個叫作“丈夫”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