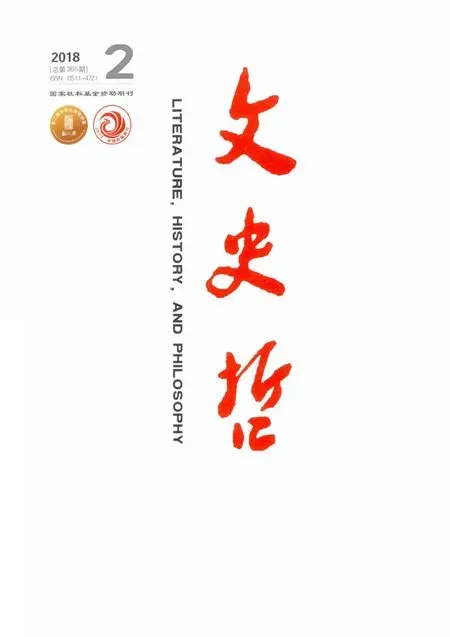唐令復原所據史料檢證
——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
趙 晶


一、《開元禮》的版本

只不過,對于某一條唐令復原而言,《開元禮》并非唯一的史料依據,因此還需要仔細比勘其他文獻。仁井田陞在復原唐令時,對于不同文獻的文字性差異以雙行夾注的方式予以標出,這就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而《唐令拾遺補》的執筆者則在《唐令拾遺》的基礎上提供了更多可供參照、比對的資料。對于《開元禮》而言,這種復原唐令的方法其實就是施以“他校法”,“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陳垣:《校勘學釋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120頁。。在“他校”的同時,自然也應運用“對校法”,“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陳垣:《校勘學釋例》,第118頁。,這樣或許能夠解釋部分文獻記載的不同之處。
根據張文昌的整理*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年,第103、106頁表二“臺灣與日本所藏《大唐開元禮》版本及收藏地一覽表”、表三“中國大陸所藏《大唐開元禮》版本及所藏地一覽表”。,目前所存的《開元禮》版本有十余種,分藏于海內外各個機構。學界通常使用的版本是作為洪氏唐石經館叢書之一、出版于清光緒十二年(1886)的公善堂校刊本(以下簡稱“校刊本”)*目前中、日學界所影印出版者,皆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庫藏光緒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刊本,即汲古書院1972年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僅稱“《大唐開元禮》”者,皆出自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若是引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或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則分別稱為“《大唐開元禮》(文淵閣本)”、“《大唐開元禮》(文津閣本)”。,而目前業已影印出版者,還有《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以下分別簡稱“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由于《四庫全書》所收《開元禮》為兩淮鹽政采進本,洪氏曾任兩淮鹽運使等官,校刊本卷首又載有四庫提要,所以池田溫曾推測,校刊本所據或許是《四庫全書》本。但是校刊本每半頁10行、每行20字,而《四庫全書》本是每半頁8行、每行21或22字,二者行款并不相同*[日]池田溫:《大唐開元禮解說》,古典研究會出版:《大唐開元禮》,東京:汲古書院,1972年影印本,第828頁。。高明士比勘文淵閣本與校刊本,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若干差異,認為并非出自一個版本*高明士:《戰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96年,第293頁。。張文昌根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朱紹頤撰《大唐開元禮校勘記》所附《校勘樶要》,指出洪氏校刊本出自朱紹頤之手,朱氏以陸本為底本,參校《通典》、丁本、浙本、李本、婁本、上海本等*張文昌:《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第105頁。。劉安志撰文指出,校刊本卷三十九《吉禮·皇帝祫享于太廟》“饋食”脫漏了有關高祖、太宗的祭儀,而文淵閣本依然保存相關文字*劉安志:《關于〈大唐開元禮〉的性質及行用問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現查文津閣本,此段亦存在脫漏*《大唐開元禮》,《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15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影印本,第691頁。。
總之,目前我們雖然無法得見散諸各地的不同版本,從而梳理出《開元禮》的版本源流,予以系統的比對校勘,但在復原唐令時,應該盡量綜校各種可入手的版本,并參考朱紹頤所撰《大唐開元禮校勘記》*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朱紹頤撰《大唐開元禮校勘記》共150卷,并附《校勘撮要》一卷,共為8冊,為清宣統元年(1909)溧水朱氏子弟據朱紹頤手稿所為謄清本。內有朱紹頤之弟朱紹亭所撰《大唐開元禮校勘記跋》,敘述此書來源梗概,可供參考。本文以下引用則簡稱以“《校勘記》”。,以免因版本訛誤而發生錯誤判斷。如校刊本《開元禮》卷二《序例中·大駕鹵簿》載:
次玉輅,(青質玉飾,駕青騮六,祭祀、納后則乘之。)……次乘黃令一人,丞一人,騎分左右,檢校玉輅等;次金輅,(赤質金飾,駕赤騮六,饗射還、飲至則乘之。)次象輅,(黃質,以象飾,駕黃騮六,行道則乘之。)次木輅,(黑質,漆之。駕黑騮六,田獵則乘之。)次革輅,(白質,鞔之以革,駕白騮六,巡狩、臨兵事則乘之。)各駕士三十二人。*《大唐開元禮》卷二《序例中》,第22頁。

覆檢文淵閣本和《通典》,僅見玉輅、金輅、象輅、革輅,并無上引校刊本的“木輅”及其注文*《大唐開元禮》卷二《序例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1頁;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一○七《禮六七·開元禮纂類二·序例中》“大駕鹵簿”,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781頁;長澤規矩也、尾崎康編:《宮內廳書陵部北宋版通典》第四卷,東京:汲古書院,1980年影印本,第545頁。;文津閣本在“革輅”及其注文之后作“次木輅(闕)”*《大唐開元禮》(文津閣本)卷二《序例中》,第608頁。;《校勘記》卷二以“次木輅”為條項,其下記有“次木輅并注黑質以下十三字,《通典》、浙本皆脫”。雖然現在已經無法確定在《開元禮》編纂完成時此處有無闕文,但起碼可以推知的是,杜佑撰寫《通典·開元禮纂類》時所參考的《開元禮》文本,可能已經缺漏了“木輅”及其注文;這一有所缺漏的文本傳至清代,《四庫全書》的兩個本子分別對此作出了不同的處理,文淵閣本一仍其舊,而文津閣本則以標記有闕的方式進行提示。至于洪氏校刊本,雖然補全了所闕之文,但卻插錯了“木輅”所在的次序。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乘黃令”條載:
凡乘輿五輅,一曰玉輅,祭祀、納后則乘之;二曰金輅,饗射、郊征還、飲至則乘之;三曰象輅,行道則乘之;四曰革輅,巡狩、臨兵事則乘之;五曰木輅,田獵則乘之。(凡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駕六蒼龍;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駕六赤駵;象輅黃質,以黃飾諸末,駕六黃騮;革輅白質,之以革,駕六白駱;木輅黑質,漆之,駕六黑騮也。……大駕,則太仆卿馭;五輅駕士各三十二人……)*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80481頁。《舊唐書》亦將之列為“唐制”,見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321933頁。
如上文字與《開元禮》基本相同,結合《太平御覽》所載《鹵簿令》節文,《唐令拾遺補·鹵簿令》一丙[開七]的相應文字應該調整為:“次革輅,(白質,之以革,駕白騮六,巡狩、臨兵事則乘之。)次木輅,(黑質,漆之。駕黑騮六,田獵則乘之。)各駕士三十二人。”
二、《開元禮》所載之制的年代
當排除因版本不同帶來的文字訛誤、缺省之后,就需要思考“他校”所帶來的信息。如《開元禮》與《唐六典》都是復原唐令所依據的最重要的基本文獻,二者成書的時間相差不遠,承載的也都是開元之制。然而,即使是如此相近的文獻,就相同事項所作的記載也存在許多細節性的差別,更何況還存在許多可據以復原同條唐令的其他史料。數種文獻之間,或摘錄的文字詳略不一,或關鍵性的字詞略有差別,這就給唐令復原工作造成了若干困擾。






由此再來反觀《開元禮》所反映的唐制年代,若無其他確切證據,我們也不應將吸收新制的文字徑直斷為《開元二十五年令》。事實上,即便是法令中標有類似于“著令”的用語,也存在隨時被廢棄的可能性,未必會被修入未來的律令格式。
如開元七年以后,朝廷屢屢發布詔敕,申令在部分祭祀中停止牲牢血祭、改為使用酒脯。以下逐一列出相關詔敕:
(1)開元十一年[九月七日]: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自今已后,永為常式。]*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二十四《禮儀志四》,第919頁;《通典》亦見相同記載,唯詳略有差;而《唐會要》所載之文則與此有異,“開元十一年九月七日敕: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府并停牲牢,惟用酒脯。自今已后,永為常式”,《舊唐書》與《通典》所載皆指州府依舊用牲牢、屬縣改用酒脯,而《唐會要》所載則意指州府停用牲牢,未知孰是,暫從《舊唐書》與《通典》之說。參見《通典》卷五十三《禮一三·沿革一三·吉禮一二·釋奠》,第1475頁;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五《釋奠》,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642頁。此外,[]為據相關文獻所作的文字補入,下同。
(2)(開元十八年)八月丁酉詔曰:祭主于敬,神歆惟德,黍稷非馨,蘋藻可薦。宣尼闡訓,以仁愛為先;句龍業官,以生植為本。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祀惟殷,封割滋廣,非所以全惠養之道,葉靈祇之心。其春秋二祀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并停牲牢,唯用酒脯,務在修潔,足展誠敬。自今已后,以為常式。*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三十三《帝王部·崇祭祀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359頁。《唐會要》卷二十二《社稷》系此詔于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日,且“春秋二祀”作“春秋二時社”(第424頁)。
(3)(開元)二十二年四月詔曰:春秋祈報,郡縣常禮,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已后,州縣祭社,特[以牲]牢,宜依常式。*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三十三《帝王部·崇祭祀二》,第360頁;錄文校以《唐會要》卷二十二《社稷》,第424頁。又,《唐會要》卷二十二《社稷》系此詔于三月二十五年(第424頁)。
(4)其年(開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余并用酒脯。*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二《社稷》,第424頁。
根據詔敕(1)和(2),自開元十一年九月始,諸縣釋奠不用牲牢,而到了開元十八年八月,所有州縣的春秋祭社和釋奠都不再用牲牢。然而,依據詔敕(3)、(4),開元二十二年四月,對于州縣祭社使用牲牢一項,采取全面解禁的措施,兩個月后又再次明令重申。簡言之,自開元十一年起,釋奠不用牲牢的規定逐步由縣擴展至州;而州縣祭社不用牲牢則始于開元十八年,廢止于開元二十二年。
在成書于開元二十年的《開元禮》中,《序例》明確規定:“祭中山川及州縣社稷、釋奠亦用少牢。……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皆犢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去犢,減酒一斗。”*《大唐開元禮》卷一《序例上·俎豆》,第19頁。其中,“州縣社稷、釋奠”的祭祀使用少牢,而少牢包括羊一、豬一、酒一斗、脯一段、醢四合。此外,根據《開元禮》的五禮儀注,諸州祭社稷*《大唐開元禮》卷六十八《吉禮·諸州祭社稷》,第352頁。、釋奠*《大唐開元禮》卷六十九《吉禮·諸州釋奠于孔宣父》,第355頁。與諸縣祭社稷*《大唐開元禮》卷七十一《吉禮·諸縣祭社稷》,第362頁。、釋奠*《大唐開元禮》卷七十二《吉禮·諸縣釋奠于孔宣父》,第366頁。等所適用的禮儀,也與《序例》保持一致,如“祭器之數,每座尊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臘各一俎)”。由此可見,《開元禮》并沒有吸收上述停止牲牢的新制。對此,筆者擬討論三個問題:
第一,即使詔敕中明確標記“永為常式”、“以為常式”、”宜依常式”等字樣,也可能被新的詔敕所廢止,而無法被修為“常法”(即“律令格式”),如詔敕(3)、(4)之于詔敕(2)中的州縣祭社部分。而且前敕即使沒有被后敕廢止,也可能為之后的立法者所拋棄,如詔敕(3)、(4)并不涉及詔敕(1)、(2)有關州縣釋奠不用牲牢的規定,那么它們有無被吸收入開元二十五年的立法?劉禹錫《奏記丞相府論學事》載:
開元中,玄宗向學,與儒臣議,由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后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腶脩、腒、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劉禹錫:《劉禹錫集》卷二十《奏記丞相府論學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53254頁。
劉禹錫通過追溯開元之例,論證釋奠祭孔不必拘泥于牲牢衣幣,希望能夠在縣一級按照“開元敕旨”,推行薦以酒脯的祭祀方式。從“罷郡縣釋奠牲牢”一句來看,因涉及州縣兩級官府的釋奠,所以玄宗所發“德音”(即“開元敕旨”)應是上引開元十八年的詔敕(2)*若詔敕(1)的原文如《唐會要》所載,此處所指應追溯至開元十一年(723)。。在劉禹錫看來,由于開元二十五年的立法者“不涉學”(李林甫)、“非文儒”(王敬從)*《舊唐書》卷五十《刑法志》載:“(開元)二十二年,戶部尚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林甫遷中書令,乃與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與明法之官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見、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刪緝舊格式律令及敕……二十五年九月奏上。”(第2150頁)此外,王敬從的生平事跡不詳。《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制科舉》所載景龍二年茂材異等的及第名單中有“王敬從”;《文苑英華》卷三九三《中書制誥一四·憲臺一·御史中丞》收有孫逖所撰《授王敬從御史中丞制》“中書舍人上柱國王敬從……可中散大夫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采訪處置等使,勛如故”。分別參見王溥:《唐會要》,第1387頁;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第2000頁。,導致“明衣牲牢”被編入《學令》。由此可見,釋奠不用牲牢的新制雖然在開元二十五年立法之前并未被廢止(否則便無需歸罪給李林甫和王敬從了),但也沒有修入《開元二十五年令》。
第二,從前引詔敕(1)、(2)、(3)的“常式”和詔敕(4)的“依式”可知,釋奠不用牲牢而用酒脯的規定在“式”,但從劉禹錫所述可知,“明衣牲牢”之法在《學令》。那么其法源究竟為何?
日本《養老令·學令》“釋奠”條載:“凡大學、國學,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于先圣孔宣父,其饌酒明衣所須,并用官物。”*黑板勝美編輯:《令義解》,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第129頁。劉禹錫所謂的“明衣牲牢”即與《養老令》中的“饌酒明衣”相應;《唐六典》卷二十一《國子監》“祭酒司業”條載:“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釋奠于先圣孔宣父。”*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十一《國子監》,第557頁。這一表述亦與《養老令》“釋奠”條大致相同;劉禹錫所論為“罷郡縣釋奠牲牢”,并不涉及太學,由此可以推斷,他所批判的開元二十五年《學令》應當包括州縣官學,這一點也可從《養老令》此條以“大學、國學”作為規范對象來加以印證,因此《開元禮》卷一《序例上·神位》所載“仲春仲秋上丁,釋奠于太學”*《大唐開元禮》卷一《序例上·神位》,第16頁。并非《學令》的全文;《令義解》卷十五《學令》“釋奠”條所載《古記》稱:“釋奠儀式,并所須物等事,具有別式。”*黑板勝美編輯:《令義解》,第446頁。也就是說,《養老令·學令》此條只是一個概括性規定,至于“大學、國學”的釋奠儀式、祭祀之物等都由“別式”規定。結合前文所引唐代史籍中的“常式”、“依式”之語便可推測,開元年間的立法應該也與此相似。

第三,如前所述,開元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的《開元禮》已將同年四月頒布的《許士庶寒食上墓詔》吸收入內,為何沒有采用前引詔敕(1)、(2)所載新制?


1.開元九年五月頒布的祭祀名山大川的詔敕尚未出現以酒脯代牲牢的要求,“諸州水旱時有,其五岳四瀆宜令所司差使致祭,自余名山大川及古帝王并名賢將相陵墓,并令所司州縣長官致祭,仍各修飾灑掃”*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一四四《帝王部·弭災二》,第1751頁。,但到了開元十二年十一月,玄宗頒下敕旨,要求“有司所經名山大川、自古帝王陵、忠臣烈士墓,精意致祭,以酒脯時果用代牲牢”*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三十三《帝王部·崇祭祀二》,第359頁。。根據前引詔敕(1),玄宗改革縣學釋奠在開元十一年九月,由此便可推測,改革的意向醞釀于開元九年到十一年之間。據《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司馬承禎傳》載:“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箓,前后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臺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一九三《隱逸·司馬承禎傳》,第5128頁。因此,從時間上看,司馬承禎確實有可能在血祭問題上對玄宗發生影響。
2.在前引開元十二年十一月詔之后,玄宗又于開元十四年六月“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詔曰:……但羞蘋藻,不假牲牢,應緣奠祭,尤宜精潔”*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一四四《帝王部·弭災二》,第1752頁。。這種因旱祈祀不用牲牢的做法,并非沒有被《開元禮》接受,如《開元禮》卷三《序例下·祈禱》載:“凡京都孟夏已后旱,則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云雨者于北郊,……祈用酒脯醢”*《大唐開元禮》卷三《序例下·祈禱》,第32頁。;同書卷六十六《吉禮·時旱祈岳鎮于北郊》所載祝文稱:“謹以清酌、脯醢,明薦于東方山川,尚饗”*《大唐開元禮》卷六十六《吉禮·時旱祈岳鎮于北郊》,第348頁。;同書卷六十七《吉禮·時旱就祈岳鎮海瀆》所載祝文稱:“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神,尚饗。”*《大唐開元禮》卷六十七《吉禮·時旱就祈岳鎮海瀆》,第350頁。因此,在血祭問題上,《開元禮》雖然在州縣釋奠和祭祀社稷之儀上“仍準舊禮”,但在山川祭祀上已出現了折衷儒、道的傾向。雷聞認為:“對于國家祭祀,道教一直試圖加以改造,然天地、宗廟之祭祀直接涉及王朝的正統性,難度太大,從岳瀆祭祀開始改造或許要容易些。”*雷聞:《五岳真君祠與唐代國家祭祀》,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第64頁。從《開元禮》的編纂來看,此點確實有所體現。但是若將它歸結為儒家與道教之間的角力,為何體現尊崇儒家圣人的釋奠之禮最先被施以改革,且遲至開元二十五年立法,州縣釋奠才改用“明衣牲牢”?
劉禹錫提倡縣學不用牲牢祭祀的理由是“《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于舊饗,孰若行其教道”*《劉禹錫集》卷二十《奏記丞相府論學事》,第253頁。,亦即祭祀不必奢靡浪費,尊仰孔子之道不在繁文縟節的祭儀,而應是推行夫子的“教道”。他以開元敕旨作為立論依據,認同玄宗推行酒脯之祭的做法,這便提示了玄宗改制的崇儉用意。早在先天二年(713)八月,玄宗曾頒布敕旨稱:“《禮》曰寧儉,《書》戒無逸。約費嗇財,為國之本……自徇于奢,是不戒也;心勞于偽,是不經也。”*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五十六《帝王部·節儉》,第625頁。開元十二年正月,又下敕曰:“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綺羅;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大帛之衣,德雖謝于古人,儉不忘于曩哲。庶群公觀此,當體朕之不奢。”*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五十六《帝王部·節儉》,第626頁。這種崇儉之風,完全符合孔子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卷五《八佾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45頁。的儒家之道。只不過,這種崇儉之道一旦與更高位的儒家原則相沖突,如不用牲牢祭祀對于血祭傳統的違反,便會遭到抵制,上述開元中期有關牲牢祭祀的政策反復即為體現。至天寶三年(744),玄宗再度頒布詔敕:“祭必奉牲,禮有歸胙。將興施惠之教,以廣神明之福。比來胙肉,所進頗多,自茲以后,即宜少進。仍分賜祭官,及應入衙常參官廚共食。”*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三《牲牢》,第447頁。這或許體現出玄宗的無奈:既然祭祀用牲是禮的要求,不能更改,那么就減少供給的胙肉數量,以達到“不資于廣殺”*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三《牲牢》,第447頁。的目的,在崇儉與守禮之間實現平衡。
總之,筆者以為,開元年間有關祭祀方式的改革,既有道教、儒家之間圍繞血祭進行斗爭的背景,亦需考慮玄宗的崇儉傾向。
三、《開元禮》的《序例》與五禮儀注

《天圣令·喪葬令》宋十八載:
諸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方相四目,魌頭兩〔目〕,并深清(青)衣朱裳,執戈揚盾,載于車。*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以下簡稱《天圣令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55頁。以下凡涉《天圣令》條文者,皆引自該書“校錄本”。
對于此條,用以復原唐令的基本資料有以下兩種:
《開元禮》卷三《序例下·雜制》:凡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大唐開元禮》卷三《序例下·雜制》,第34頁。
《唐六典》卷十八《鴻臚寺》“司儀署”條注:其方相四目,五品已上用之;魌頭兩目,七品已上用之。并玄衣、朱裳,執戈、楯,載于車。*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十八《鴻臚寺》,第508頁。

《開元禮》卷一三九《兇禮·三品以上喪之二》“陳器用”載:
啟之夕,發引前五刻,搥一鼓為一嚴。(無鼓者,量時行事。)陳布吉兇儀仗,方相、(黃金四目為方相。)志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于柩車之前。*《大唐開元禮》卷一三九《兇禮·三品以上喪之二》,第664頁。
同書卷一四三《兇禮·四品五品喪之二》“陳器用”載:
啟之夕,發引前五刻,搥一鼓為一嚴。(無鼓者,量時行事。)陳布吉兇儀仗,方相、(黃金四目為方相。)志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于柩車之前。*《大唐開元禮》卷一四三《兇禮·四品五品喪之二》,第678頁。
同書卷一四七《兇禮·六品以下喪之二》“陳器用”載:
啟之夕,發引前五刻,陳布吉兇儀仗。魌頭、志石、大棺車(六品以下設魌頭之車。魌頭兩目。)及明器以下,陳于柩車之前。*《大唐開元禮》卷一四七《兇禮·六品以下喪之二》,第708頁。


《唐六典》卷十八《鴻臚寺》“司儀令”條注載:“其纛五品已上竿長九尺,六品以下五尺。”而《天圣令·喪葬令》宋十九載:“諸纛,五品以上,其竿長九尺;以下,五尺以上。”*《天圣令校證·喪葬令》宋19,第355頁。按照前述學界對《天圣令》所據藍本的通說,據此復原的《開元二十五年令》應該也是“六品以下五尺”*仁井田陞復原為《開元七年令》,參見《唐令拾遺》,第823頁;吳麗娛先是認為應從《開元禮》之文復原唐令,即“六品以上長五尺”,后來又修改了這一看法,傾向于按照“六品以下長五尺”復原,分別參見《天圣令校證》,第689頁;吳麗娛:《唐朝的〈喪葬令〉與唐五代喪葬法式》,《文史》2007年第2輯;吳麗娛:《關于唐〈喪葬令〉復原的再檢討》,《文史哲》2008年第4期。。從常理而言,“五品以上……六品以上……”的結構只能導致后一種情況僅適用于六品這一個等級,既然如此,徑稱“六品”即可,“以上”便是贅文。若是采用前文所述“對校法”,便可發現《開元禮·序例》所載“六品以上”的記載源自洪氏公善堂校刊本*文津閣本亦同。參見《大唐開元禮》(文津閣本),第613頁。《校勘記》則記為“婁本九下脫尺六二字”,換言之,婁本的原文應是“五品以上纛竿九品以上長五尺”,若以此句脫“九尺”二字為思路,則可標點為“五品以上,纛竿[九尺];九品以上,長五尺”,這就與“六品以下,長五尺”同義。,根據文淵閣本,此處為“六品以下”*《大唐開元禮》(文淵閣本),第66頁。。

喪葬規格雖然所涉細節都顯得相當瑣碎,但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故而唐廷不惜犧牲法律穩定性的要求,一再地進行調整。如《唐會要》卷三十八《葬》載: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于舊數內遞減。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請減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請減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請限十五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八《葬》,第693頁。
而《唐六典》卷二十三《將作監》“甄官令”條載:“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十三《將作監》,第597頁。《開元禮》卷三《序例下·雜制》載:“凡明器,三品以上不得過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大唐開元禮》卷三《序例下·雜制》,第34頁。
其中,開元二十九年所頒之敕稱“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因此若非史籍有誤,開元二十五年《喪葬令》的規定可能是“七十事”,而《唐六典》與《開元禮》所載“六十事”,就可能是開元七年《喪葬令》的規定。若暫且不論此點,開元二十五年定令以后,至開元二十九年便迅即以敕改令,那么前述開元七年至開元二十五年之間的變動,便也在常理之中了。
而且,根據開元二十九年敕,原本唐令并未涉及庶人使用明器的情況,這并非是對庶人不加限制,而是秉諸“禮不下庶人”的心態,不把庶人置于使用明器的行列之中。敕文之所以規定庶人使用明器限十五事,只能是因為庶人仿照有品之官,大興厚葬之風,立法的目的是讓庶人在法定的范圍內使用明器,從而貫徹儉葬,“古之送終,所尚乎儉”。與此同理,前述《開元禮》兇禮儀注規定六品以下無纛,《序例》與《唐六典》規定六品以下纛長五尺,這也未必是提升六品以下官的喪葬待遇,毋寧是通過法定的方式來加以限制。所以,無論是將使用方相的官品下限從五品提升至四品,還是規定六品以下用五尺之纛,或許都是《開元二十五年令》抑制厚葬之風的一種措施,與前述玄宗的崇儉之道相合。
此外,喪葬規格涉及諸多方面,并非每個層面都保持同步增減的勢態,相關標準亦隨時被加以調整。如《唐會要》卷三十八《葬》載:

據此,使用方相的群體被限縮到三品以上,但使用魌頭的群體則擴大至庶人;而使用九尺之纛的群體被限縮至三品以上,六品以下所用之纛卻加長到七尺。至于明器的數量規格,除了庶人以外,又回歸到《唐六典》和《開元禮》的標準。到了會昌元年(841)十一月,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喪葬事時,喪葬規格又是一變:
在這一規格中,方相的使用群體被擴展至五品以上,而且各個群體所能使用的明器數量則較開元、元和為多。
總之,法定的喪葬規格無法保持固定不變,調整的內容、幅度會隨著社會現實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即使是為了達到抑制厚葬的相同目的,所采用的標準也會有高低起伏,若非如此,便會發生“雖詔命頒下,事竟不行”*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八《葬》,第695頁。的后果。由此可見,前文推測《開元七年令》所定“五品以上用方相”與《開皇禮》的“四品以上用方相”有別,而《開元二十五年令》修改《開元七年令》,再次回歸《開皇禮》的標準,如此反復的修法過程其實并非唐代立法的特例。
四、結 語
《開元禮》作為唐令復原所依據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在唐令復原研究進入精耕細作的今天,尤應被更加細致地加以利用。本文立足于對若干復原成果的檢證,提供一些可能性的猜測,大致可以作如下總結:
第一,當《開元禮》所載文字與其他文獻出現差異時,首先應當綜核各種可入手的版本,從而確定其記載本身是否存在訛誤或缺省,如前文所列舉的《唐令拾遺補·鹵簿令》一丙[開七]和《天圣令·喪葬令》宋19的復原。
第二,在考慮記載本身是否有誤的同時,亦應注意《開元禮》所載之制并非純粹是開元七年的立法成果,其中雜糅著開元二十年以前隨時頒布的新制。而且,面對隨時頒布的新制,《開元禮》的《序例》與五禮儀注的更新也未必完全同步,存在《序例》適時修改而五禮儀注未曾修訂的可能,如前文所列舉的《天圣令·喪葬令》宋十八的復原。
第三,對于開元七年之后頒布的、明確標有“永為常式”等字樣的新制,無論是《開元禮》的《序例》還是五禮儀注,都可能不加吸收,仍然“準舊禮為定”,而且這些新制有可能隨時被廢止,未必會成為開元二十五年立法的一部分。由于史籍缺載,當時紛繁復雜的立法爭議或已湮沒無聞,如開元二十五年有關“明衣牲牢”的《學令》。
總而言之,當不同文獻針對同一事項出現記載差異時,我們至少需要考慮兩種可能:文字錯訛與制度變遷。若可通過版本比對、輔以相應理據而判定為前者,則予以簡單訂誤即可;若是文獻中留有蛛絲馬跡,通過邏輯推演,足可證成后者,那么便可將它們標記為年代不同的兩條唐令。只不過,在具體的研究當中,因為存在太多“變量”,如令、式難辨和禮、令不同等,我們很難找到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也未必能夠排除其他各種可能性。更何況,目前學界對于《開元禮》的細致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尚未進行梳理版本源流、通校文字差異等基礎性的文獻工作,因此本文所述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