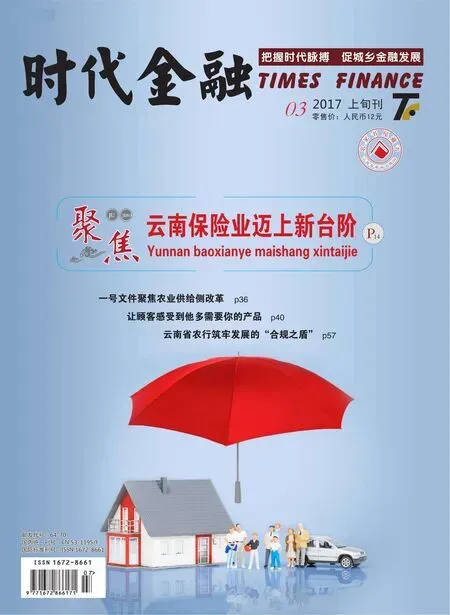中國藝術品市場步入低谷期
聞之
中國藝術品市場在行業調整帶來的持續波動中送走了2017年。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過去一年是挑戰與機會并存的一年。特別是在歲末年初之際,拍賣行、畫廊等藝術品經營機構都或多或少已感受到,從樓市、股市等其它領域流入藝術品市場抄底的資金明顯增多。與此同時,場內的新老買家在審美取向和價值標準方面的碰撞交流也變得空前活躍。2018年,不同的細分市場在投資風向上將如何轉變?收藏者又該以什么樣的心態和思維去把握未來的投資機會呢?
這個冬天,可以說京城藝術市場出現了有趣的“蹺蹺板效應”——這邊廂拍賣場人氣火爆,那邊廂古玩城門可羅雀。曾幾何時,到北京潘家園古玩市場淘“寶”還是件挺時尚的事兒,如今卻已是大相徑庭的一幅“冬眠”畫風。一度被視作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的古玩藝術品到底該如何尋找出路? 對于市場“身陷囹圄”,全國工商聯民間文物藝術品商會會長宋建文認為,全國范圍的古玩城都在走下坡路,市場經營額不斷縮水,近兩年更是跌至谷底。他分析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需求少了,“雅賄”現象急劇減少,稍有實力的買家也從這個市場撤離轉向拍賣會;再就是“扎堆兒”式古玩市場到了回歸理性的時候。
藝術市場分析人士馬維也認為,離場的不會只有商戶,一些古玩城也會被洗牌出局。據他介紹,上世紀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京城一哄而起建了不少古玩城,總數一度達五六十家。“一些地產商將觸角伸向古玩行業,導致市場虛火過旺。”在京城叫得響名號的大鐘寺古玩城近期的遭遇比較“慘烈”,目前整個一層通道,很少能看到客人進出,絕大多數時候都是看店人獨自等待,整層樓店員數比顧客還要多。選擇在寒冬里堅守的,大多是那些入行早,擁有不小實力客戶的商家,早年間以低價購入的精品可以支撐他們頂住目前的壓力。不過,至于能扛多久,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據了解,這里的古玩集市已存續近30年,規模在全國范圍也難有出其右者。不過,這里的商戶顯然更在乎每天的客流量。“前幾年行情好的時候,還得從老家請人幫忙看店。現在店里安不安排人守店區別也不大,談成一樁生意太難了。”從福建舉家遷居北京的黃炳輝主要經營古典家具,兼售手串、玉器之類,他說,如今賣出一件古玩就像“碰運氣”。相比成交量,人氣偏低更是不少商戶心中的痛。“有些店鋪都快成擺放貨品的倉庫了,常常是連著好幾天都不開門。不是人家不想做生意,主要是走進店內的客源實在少得可憐。”與黃炳輝緊鄰的一位經營書畫的店主透露,自己現在都是吃老本兒,已經好幾個月沒談成有意向的新客戶了。
“對虛火過旺的行業只有適度降溫,才可能讓它走出病態。各方歷經多輪洗牌后,還能屹立不倒的必然是有實力又專業的商家。”在藝術市場分析人士看來,國內古玩市場以前就是個什么都可以往里裝的筐,今后它會走向兩極分化,一端走精品化路線,甚至可能與品牌拍賣行合作推展銷會;另一端是面向大眾群體的工藝品市場。那么古玩市場到底該向何處去呢?有專家開出的“藥方”是,走專業化運營之路。專家認為,無論是經營者還是淘寶客,在市場爆發期都只是把古玩、文玩當作可以爆炒的普通商品,只有當市場轉向沉寂,人們才不得不靜下心思考出路。
在業內人士看來,那些充斥坊間的“淘‘寶者一夜暴富”“憑幾頁泛黃的紙張就身家百萬元”之類的故事,無疑給這個本就不那么透明的市場平添了傳奇色彩。其實它的平均利潤并不比普通商品高,不少闖入者實屬誤入歧途。與此同時,與古玩城相伴相生的贗品問題也是阻礙其發展的一大頑疾,市場行情好的時候,贗品也有人接盤,當市場萎縮之后,曾經的熱錢必然選擇離場。
此外,作為全球藝術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當代藝術風風雨雨走過了20多年,成為具有當代全新語境的藝術新生兒。必須承認的是,國內的部分收藏者對當代藝術的認知還比較膚淺,甚至很多人連概念都還沒搞清楚,看到油畫就以為是當代藝術。當代藝術首先是一個藝術史概念,但更重要的是它必須具備顛覆性、革命性的藝術觀念、內容題材以及表現形式、藝術圖式。從目前狀況看,當代藝術有庸俗化傾向,一些人樂此不疲,大多數人嗤之以鼻。總的來說,2017年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也處在谷底緩慢平行的狀態,近幾年的行業大調整,當代藝術是首當其沖,未來多久會觸底反彈,沒有人能說清,或許三五年,或許兩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