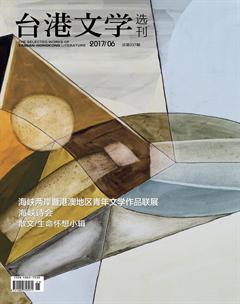坐中多是豪英
陳義芝(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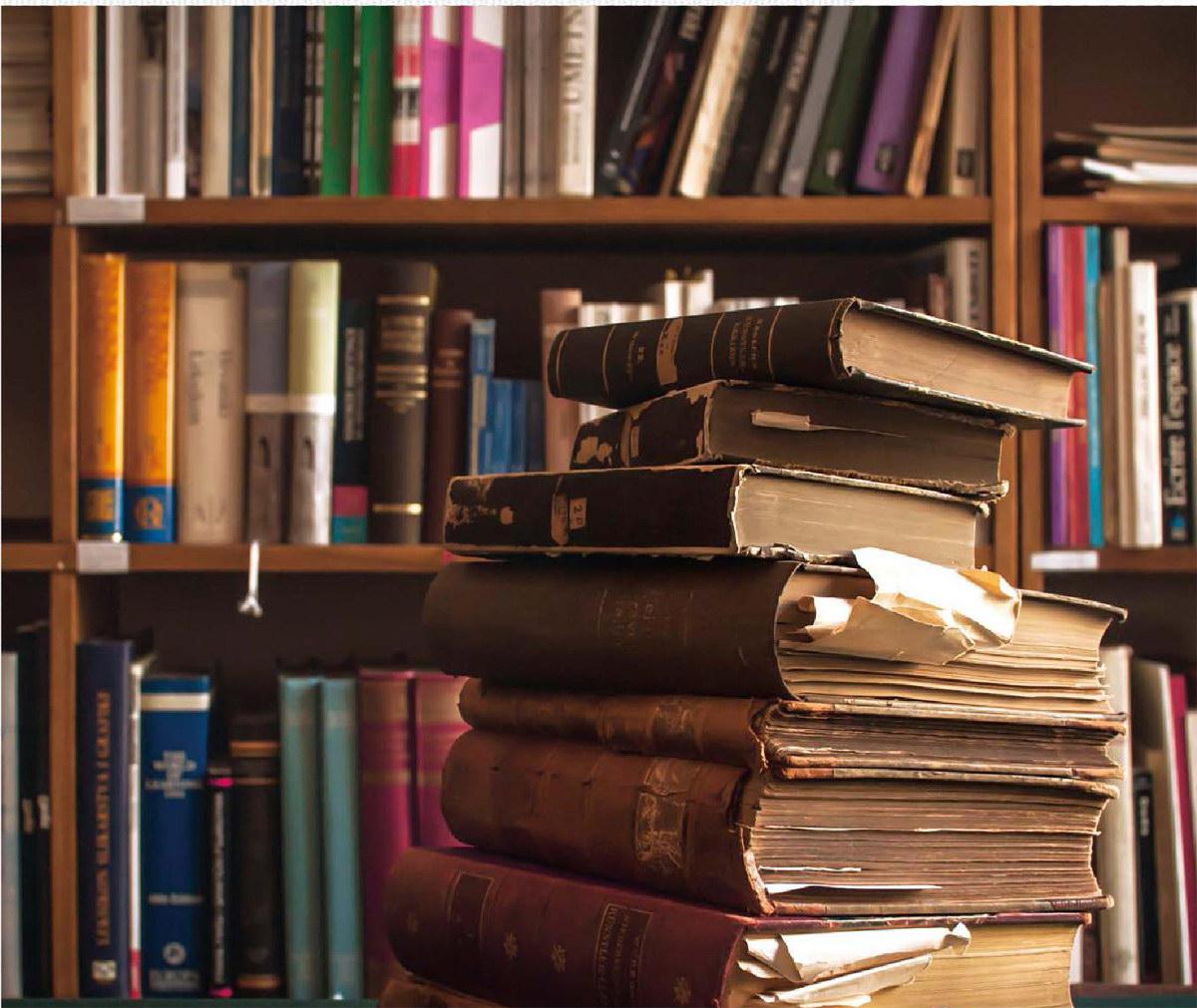
著名詩人、散文家、臺灣師范大學教授
恭喜兩岸青年文學交流會在福州盛大舉行!
看到來自各地的文學菁英,讓我想起年輕時的自己,對文學不計一切的追求。三四十年時光一晃眼就過了,“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陳與義《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我們那一代出了不少文學豪英;現(xiàn)在我眼中的是另一批豪英。文學的發(fā)展就這么在一代代人接棒中推進、完成。
我與年輕的創(chuàng)作者世代雖有別,但寫作的原理與目標,古往今來并無兩樣。藉著今天這個場合,我想重提幾個與文學寫作有關的關鍵詞:
第一個是“孤獨”。孤獨與寂寞不同,寂寞的人心里發(fā)慌,孤獨的人卻是淡定的。孤獨,不晾給人觀看,孤獨為的是明白自己身在何處,面對任何時空些微的變化,都能激發(fā)情感的反應,做出自己的決定。
法國小說家杜拉斯說,寫作的人永遠應該與周圍的人隔離。身體的這種實在的孤獨,成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獨。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也說,作家成長的過程常有個共通點:安于獨處,樂于閱讀。
所以第二個關鍵詞是“閱讀”。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描述十七歲時,她那一顆文青腦袋里總裝著“凡夫俗子所不能解的隱秘思緒”。她說:
你當然必須熟悉福克納、費茲杰德羅和海明威。喜歡戲劇的得加上田納西·威廉斯和尤金·奧尼爾,還有寫《憤怒的葡萄》的史坦貝克。惠特曼和狄金森也要多少知道一點。能弄到地下出版品的得熟悉亨利·米勒——他的作品是禁書;搞民權運動的得熟悉詹姆斯·鮑德溫。艾略特、龐德、喬伊斯、吳爾芙、葉芝等等當然是一定要的。但克爾凱郭爾、赫爾曼·黑塞、貝克特、加繆、薩特、卡夫卡、尤奈斯庫、布萊希特、伯爾和皮蘭德婁才夠有魔力。福樓拜、普魯斯特、波德萊爾、紀德、左拉,以及俄國的大作家——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有人讀……
這是一張文學閱讀的大地圖,涵括了不同國度,各種主義流派與風格。這段話的意思是什么呢?——沒有閱讀,就沒有創(chuàng)作!
被動接收的閱讀,凡人都在執(zhí)行,睜開眼睛過日子,就是一種“閱讀”。從街坊鄰居的閑談,電臺、報章雜志獲得訊息,也是閱讀;在學校為了應付考試,也要閱讀。但這些都不算“文學閱讀”,文學閱讀是與杰出作者交流內在經(jīng)驗,要用想象了解情境、體貼人情、回應自己生命的真實——獲得啟示激發(fā)憐憫,或是產(chǎn)生憧憬、勾連哀思。深刻的文學閱讀,不僅是一種浸淫陶醉,更能從中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事理,自我提升改造。進到如此層級的閱讀,才足以形成心靈的判讀坐標,才能夠鑒別好作品與壞作品。
于是,這就進到第三個關鍵詞“批評”的境地了。
庸俗流行的作品,無法詮釋真相,自然不值得推薦,不值得浪費批評筆墨,除非它已威脅遮蔽了正常有深度的閱讀,則挺身而出對抗流俗,指出其膚淺,正是批評家的本分。
俗話有所謂“眼高手低”一詞。“眼高手低”雖令人扼腕,總比眼低手低要高明。
各位作為一個眼高手也高的創(chuàng)作者,須知“作家”這頭銜具有深刻的象征意涵,意指能承載人生各種追求與擔當、憂患與恐懼,不是能寫一點人生經(jīng)歷的人就是。司馬遷提示我們,作家須是能成一家之言者,“成一家之言”這是何其莊嚴神圣的事。
二十一世紀,世局多變化,干擾誘惑之事更多于從前,但我相信我們既選擇了文學寫作,必定是被創(chuàng)造性藝術深深吸引的人。真正追求文學的人不以“維持生計”為念,也不爭一時的掌聲。杜甫死后一百三十年,才有詩集選錄了他的詩,至今一千三百年,時間越久,光芒越盛。梵高生前窮困潦倒,畫作無人青睞,而今他一幅畫的拍賣價高達一億美金。
文學藝術的價值,果真是由“永恒”這條時間軸來衡量的!
我很榮幸受《臺港文學選刊》之邀,參與此會,謹以此與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