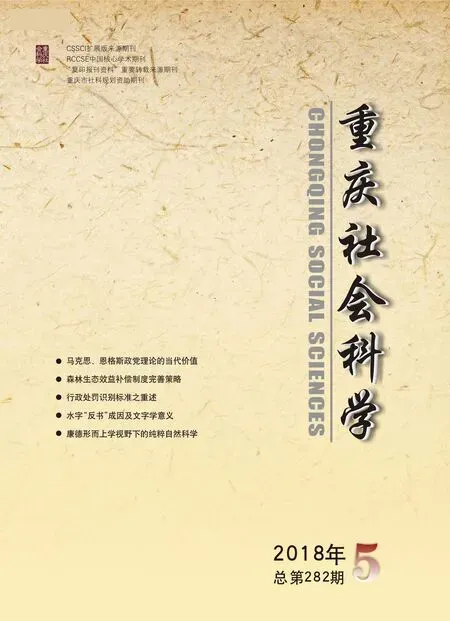“和諧社會”的主體理想性和現實性意蘊
孫乃龍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上海 201204;復旦大學科研流動站,上海 200433)
哲學的基本問題歸根到底是人的問題。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離開社會談論人或者離開人談論社會都是沒有意義的。和諧社會說到底是人的核心問題。因此,在探究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將主體人作為視角和基本內容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主體:“和諧社會”的主題
作為主體的人是“和諧社會”的核心。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和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關系是和諧社會的目的和歸宿。現實中,不同群體之間利益的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問題,都以實現人的和諧為前提。
(一)主體:和諧社會提出的邏輯起點
從“現實的個人”來考察社會是所有歷史唯物主義者的立足點。社會的發展進步就是建立“適應于更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新的交往形式”[1]。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是“人”的社會。和諧社會也是基于人的活動和發展而提出的。它也遵循馬克思從“現實的個人”活動來考察社會狀態的觀點。這一點我們從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界定中就能清晰地看出。《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國家全體人民都能夠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占主體地位的非對抗性矛盾一般不采取對抗和沖突的形式,能夠達到矛盾各方互相促進,良性運行,和諧共存,共同發展的社會。”[2]這一界定的核心就是圍繞主體——人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等各個方面的矛盾來展開的。這一點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有明確的體現:“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3]
(二)主體:和諧社會的特征要求
關于和諧社會特征的表述中也明確地表達了主體的主旨地位。“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2]民主是人的民主,公平是人與人的基本關系;誠信友愛、充滿活力、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的存在狀態的基本要求;正義、安定是社會的基本維度。這既是對社會的要求,也是對主體的要求。
(三)主體:和諧社會的要義
和諧社會的要素包括“物質財富相對寬裕、追求公平正義、穩定有序和民主法治”[4]。這些要素實際上都落實到主體上,即人的物質財富相對豐富,人們生活水平相對提高,人與人之間公平正義,人們民主法制意識提高,遵紀守法,社會也才穩定有序。
(四)主體:和諧社會的哲學意蘊
從哲學的視域來解讀和諧社會,可歸納為“社會系統內部諸種基本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要素之間關系的和諧,人與人之間關系或人際關系的和諧,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5]四個方面。每一個方面圍繞人這一主體展開。
二、理想性與現實性:“和諧社會主體”的兩個層面
和諧社會的主題是“主體”,主體——人的和諧是和諧社會一以貫之的思想,那么,具體到主體這一語境,我們不禁要問主體的什么和諧呢?換句話說就是,主體和諧的內在結構是怎樣的?主體和諧自身的內涵是什么?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從和諧社會的理論根基——歷史唯物主義出發來探討這一問題。主體概念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概念之一。對主體概念的探討也應該從歷史唯物主義來進行。透過歷史唯物主義,我們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主體概念。
歷史唯物主義存在“類哲學”和“類科學”兩個層面[6]。在“類哲學”層面上,歷史唯物主義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6];在“類科學”層面上,歷史唯物主義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7]。這兩個層面是一般和個別的關系且是有機統一的,其中“類哲學”是“普遍性的或一般性的”層面,“提供一般的范導性原理”[9];“類科學”是“具體的或個別的”層面,“進行具體的描述性建構”[6]。這就是說,“一般性”層面是從對具體人類活動方式的研究中抽象概括出來的,而“個別性”層面是在一般層面揭示的普遍原理的指導下對現實的生活過程的具體解釋。
主體是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一個基本的向度,在不同的層面上,對主體的規定也各有側重。這一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著清晰的表現。主體的個體性層面在于人是處于實踐活動中的、現實的、社會的、活生生的個人。主體的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層面在于人是自由自覺的類的存在。自由體現著人的普遍性本質,標志人的普遍性實現程度。于是一方面,主體作為現實的、社會的存在物受現實必然性的制約,是外在的現實層面的主體;另一方面,主體作為自由自覺的類的存在物,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人存在的最高理想目標,是內在性的理想性層面的主體。
(一)人是自在自為的存在:“和諧社會主體”的理想性層面
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馬克思首先考察了歷史上人的存在形態的演進,即從“自在的人”到“自為的人”到“自在自為的人”,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不同階段。
馬克思指出,人類的初始狀態是自在的存在。在這種狀態下,人與其他動物一樣都是自然界的一種自在的存在物,人沒有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同其他的自然物沒有區別。人的存在表現為人的活動受自然規律、客觀必然性和異己力量制約,人的主體性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無意識的生存本能——求生存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并不是真正的主體性,因為作為主體的人并沒有同其他自然物區分出來,此時的主體既可以說是人,也可以說是其他任何一種自然物。而把人作為主體進行探討時無疑都是立足于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分展開的,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人的本質,是和自我意識等同的”[8]118,自我意識的活動是“人的自我創造的活動”[8]128,即“想象的主體想象的活動”[7]31的觀點,指出“不應當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識相并列[9],”強調人的自我意識的能動性和獨立性。在這一時期,馬克思第一次在本質上把人界定為具有自我意識的、自由的存在物,從而把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開啟了從人自身、從內在性維度界定人的本質,規定主體內涵的道路。此后,在研究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寫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其中明確指出“人是類存在物”,其本質特性就在于它的類特性,而類特性就是“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10]。”此時,馬克思已經意識到具體的物質利益是人活動的出發點,開始了對現實的人的關注。但是,馬克思仍然用抽象的人的類本質作為立論的基點,仍然從內在性維度規定人的本質,界定主體的內涵。此時的主體本質上是一種自己意識到自己存在的“自為”主體。這種主體雖然明確了人作為主體的思想,但是由于它過分強調人作為個體的“自我”意識,并把其擴展到普遍性的層面,所以,這種普遍性只是一種抽象的規定,缺乏現實性,而且這種普遍性在本質上僅僅是個體性的無限擴大化。顯然這不是人類理想的存在狀態,馬克思認為人的理想性的存在狀態是自在自為的自由狀態。
為此,馬克思先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了這種只是把“人的本質”理解為“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所以,他不得不:(1)撇開歷史的進程,孤立地觀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類個體;(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質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系起來的共同性”[7]18的思想。接著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人的真正的本質在于“生產勞動”,“首先是勞動,然后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變成人的腦髓[11]。”“人不是簡單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具有理智的人的自然存在物。人不像動物那樣無意識地適應自然界,而是在適應自然界的同時使自然界適應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正是這種雙重的適應性,即環境對人和人對環境的不斷作用與反作用,決定了人的活動的本質。”[12]由此,人的這種實踐活動使人類自身的二重化為人自身的“自在性”與“自為性”的對立統一:人的自在性表明自然對人的“束縛性”(或稱之為“必然性”);而人的自為性則表明了人對自然“必然性”的“超越”(或稱之為“解放”)。離開自為性的自在性,人只能像動物一樣去適應自然。離開自在性的自為性,人的自為性只能是一種神秘的、抽象的特性。所以,作為主體的人的理想狀態是自在自為的存在。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為我們描繪了這種理想的狀態: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人都無可爭辯地有權全面發展自己的才能”[13],“每一個成員都能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10]373。在這種狀態下“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擺脫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1]232,人才真正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實現“個人向完整的個人的發展”,人成為自然、社會、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人,主體的個體性真正得以展現。其次,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1]84。”一方面,“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7]273;另一方面,“每一個單獨的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7]42。”這里的個人不是“偶然的個人”,它與類是統一的,個體差異性是在類的統一性的統攝之下的,它的總方向是符合類的普遍性的,人的個體性的充分發展,促進了類的普遍性的生成與發展。因而,共產主義本身內在包含了主體的個體性與普遍性的一致。
(二)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和諧社會主體”的現實性層面
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探討,對人作為主體的界定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理想性層面。他試圖通過對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以及這種對立的實質的揭示,求得無產階級的階級自由和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并在此前提下實現人的個性的全面解放和個人的真正自由。所以,馬克思從這種現實的社會關系的角度來規定人的現實本質,并說明理想的人的現實性,從而把主體界定為作為現實的、社會的存在物,它受現實必然性的制約,是外在的現實層面的主體。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7]18這表明馬克思對人的理解由抽象走向具體,由固定不變的本質走向現實的社會關系;對主體問題的探討,已經突破了抽象的層面,轉到了現實的層面。首先,“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觀點,旗幟鮮明地表達了馬克思從根本上顛覆了歷史上關于人的本質的思考方式。馬克思指出:“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人間上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地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7]73;“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與其他自然的關系[14]。”這表明馬克思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來界定人的本質,界定主體。他把人界定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具體而言就是處于一定經濟范疇中的進行生產生活的人。其次,“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體現了馬克思不滿足于單從以個體面目出現的人實現自由的維度,即從單個的人作為主體的維度來探討人的本質,他同時又從社會關系的角度,從以“群體”①這里的“群體”體現了社會關系的內涵,即馬克思認為:“社會關系的含義是許多人的合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頁。)作為主體的人不僅是作為人種的單元而且同時是一定的社會共同體——階級、民族的代表。面目出現的“大寫的人”即“社會”②馬克思強調“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頁。)作為主體的層面來理解人的本質。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的“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前面”,“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7]67。”沿著這一思路,馬克思考察了現實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關系,特別是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以及這種對立的實質。這樣,馬克思就揭示了“大寫的人”作為主體的現實樣態——資本家與工人,從而闡釋了主體的現實狀況。最后,馬克思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的內容、實質及決定因素的考察,指明了理想性層面的人的本質的實現路徑。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狀況入手,從人與人的關系角度而不僅僅從物與物的關系去考察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所具有的特質:商品價值二重性和勞動二重性。并以此為基點,揭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本質,指出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勞動的二重性,使現實的主體二分為工人與資本家抑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對立的主體;從勞動的異化到勞動成為自由自覺的活動出發,揭示了剩余價值的消亡,闡明了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而使現實的主體由分裂走向統一,由異化的主體走向揚棄異化的主體,由物化的主體走向自由全面發展的主體,由物依賴的社會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亦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性。接著,他又指出正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換,在交換體系中,賦予了主體的個體以自由的特質,使得主體的實現成為必要與可能,最終在現實的交換活動中,把主體的自由特質與社會特質統一起來,使得主體的現實化得以實現。
總之,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樣一個命題,體現的并不是主體完全消融于自身實踐的結果中的那樣一種思想③這是弗朗切斯卡·伊佐的觀點,他認為社會性是對主體性的消解。,而是主體在某一歷史階段的切實實現。馬克思把主體放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去考察,而決不把主體看成一成不變的東西。這就突破了以往哲學中僵化的思維方式,用一種發展展的、歷史的眼光來審視主體。這也正是馬克思實踐哲學所要求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范式。
三、實踐:“和諧社會主體”兩個層面統一的根基
人是處于實踐活動中的,現實的、社會的、活生生的人是主體的規定,是主體現實層面的界定;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自在自為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最高理想目標,是主體在理想性層面的界定。可是,二者如何統一起來呢?關鍵在于如何使表達理想性層面的個人的全面發展與表達現實層面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保持一致,即如何實現個人的發展(個性的實現)與現實社會關系(普遍制度的延展)的一致性。這亦可理解為主體的追求成為自在自為的存在,實現其個體性是主體的實現;同時,主體追求自由在整個社會層面的普遍實現,力圖把作為理想性層面的“自由”“社會化”,即在法律、政治等社會關系層面上將其實現,使其具有普遍制度的效力。
然而,現實中這是一個難題①這一難題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意識到了,也就是馬克思“感到困惑的問題”。只不過當時的馬克思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難題的實質是什么。。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一再強調個人的自由,強調個體性的發展,為此還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使這種自由普遍制度化(也即社會化)。但是,事實是這種以資本為根基,按資本的運作模式展開的社會化,無法惠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主體,尤其是工人。所以,在現實中這種個體性與普遍性的統一是無法真正實現的,即便在某個特定的群體中實現也是有限的。那么,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是否能夠解決這一問題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之前的社會連個體性方面的自由都無法保證,更不用說將其社會化了。此時,問題就變得尤為尖銳了。一方面,無論是個體自由的實現還是普遍的社會化的實現都是主體在不同層面的實現,二者本來就應該是同一的過程;另一方面,二者在現實的社會中的分裂與對立又是如此尖銳,正如卡爾霍恩所說:“現代社會日常生活所發生的最重要的轉變,也許就是個人之間的直接關系與大規模社會系統的組織方式和整合方式之間出現的越來越大、越來越深的裂痕。”[15]那么,我們如何來看待主體的這種個體性與普遍性的統一問題,如何統一主體的現實層面和理想層面呢?
為此,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引導下,從人的客觀物質生產實踐的歷史發展出發,指出現實的人同時就是歷史的人,承認人的歷史性、有限性、暫時性。即:人的理想性的存在狀態與現實的社會歷史發展雖然都是人的本質的表達,都是人最終獲得自由到達自由王國的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二者的存在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一種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其主體的理想性層面在現實中的實現都是有限的,都要受到當下社會的發展狀況及必然性因素的制約,其實現也只是暫時的。
首先,立足于實踐,一切從實踐出發,從人的客觀物質生產實踐的歷史發展出發,得出歷史是人的物質活動和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統一運動過程的結論。“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條件[7]51。”由此,作為主體的現實的人與歷史的關系為:現實的人同時就是歷史的人。一方面,歷史是處于各種社會條件下的現實的人從事實踐活動的過程;另一方面,現實的人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內“可能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具體存在的現實的人,他受到歷史運動所限定的物質條件和各種社會關系的制約。在現有的歷史條件下,“任何人都處在一定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物質生活條件之中,都受到某一生產力發展階段以及與該生產力階段相適應的交往的制約。因此,任何現實的人都是一定歷史階段的人,是處于一定歷史階段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斗爭運動中的人,他只能在這種斗爭、運動、聯系中實現、表現自己的生命活動,他不可能無限制地超越自己的生活條件。這樣,不同歷史時期的人表現為不同運動、活動,不同聯系、關系,表現出不同本質。社會歷史不過是人的本性的不斷變遷而己[16]。”由此,人是歷史中的主體。主體的發展與歷史的變遷保持著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主體的存在與發展獲得了一種歷史的張力。一方面主體在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呈現出一種歷時的絕對變化性,指向其理想性形態;另一方面,主體在歷史橫向上保持其相對穩定性,指向其現實性形態,表現為受當下生產實踐或者說是生產方式限制的現實的、社會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主體的這種歷史的張力使得主體同時具備有限性與無限性雙重特質。主體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表達了主體的有限性;主體追求自在自為的自由狀態的理想性層面的實現表達了主體的無限性。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總是不安心于這種有限性而企圖去追求一種無限的理想的存在。作為主體的人,總是生活于十分現實的與世界的具體關系中,他不得不正視客體的現實性,認同當下的歷史狀況。人作為主體也正是在這種實踐活動所涉及的有限范圍內,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的關系的過程中,才顯示出來人所特有的區別于物的特質——“自由”。當然,這種“自由”是有待完成的、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有限的自由,并不是臻于完善的自由。然而,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有限性并不是物理時間的有終性,而恰恰是真正的時間性。此時的主體表現為在歷史實踐中不斷超越有限性的規定,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使自身無限接近理想性存在,實現真正的自由的過程。事實上“如果我們能洞察并預見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一切的一切,我們也就沒有多少自由了[17]。”人正是不斷地超越在這種流變的有限的規定中,孜孜以求地追尋自己的自由,追尋個體性的全面發展。
最后,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處于歷史視野下的主體具有有限性與無限性、理想性與現實性這些特性,而在于如何實現二者的統一,是個人的全面發展與現實的社會關系的狀況實現統一。在這種情形下,“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關系和觀念關系的全面性”[18],人的全面發展也有一個從“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7]89的過程。“要達到這點,首先必須使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成為生產條件,使一定的生產條件不表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即在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基礎上,單個人的活動才能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包括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7]89。”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1]515,個人能突破外物、他人、地域和民族狹隘性的限制,實現社會交往的普遍性,并在廣泛而深入的社會交往中形成多樣化的豐富的個性。在這種社會制度下才能夠真正談到人的自由。這種制度就是共產主義,它“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19]。”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理想性主體與現實性主體得到了統一。
總之,立足于實踐把主體看作歷史活動的主體,承認主體的有限性,保持主體與歷史之間的張力,不斷地使理想性主體在現實層面得以實現;不斷地使主體個體性的發展與社會普遍制度的延展趨于一致;最終使作為主體的人由“必然王國”上升到“自由王國”,這是解決理想性主體與現實性主體統一的關鍵所在。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1.
[2]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摘編[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龐元正.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幾個基本問題[J].理論動態,2005(2).
[5]侯才.和諧社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內涵[J].科學社會主義,2004(5):7.
[6]王南湜.認真對待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概念——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特征的再理解[J].哲學研究,2010(1):13-22.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
[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3.
[12]科爾紐.馬克思的思想起源[M].王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7:75.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4.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48.
[15]渠敬東.缺席與斷裂:有關失范的社會學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56.
[16]馬克思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74.
[17]霍伊.自由主義政治哲學[M].劉鋒,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7.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
[19]金哲,姚永抗,陳燮君.世界新學科總覽[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