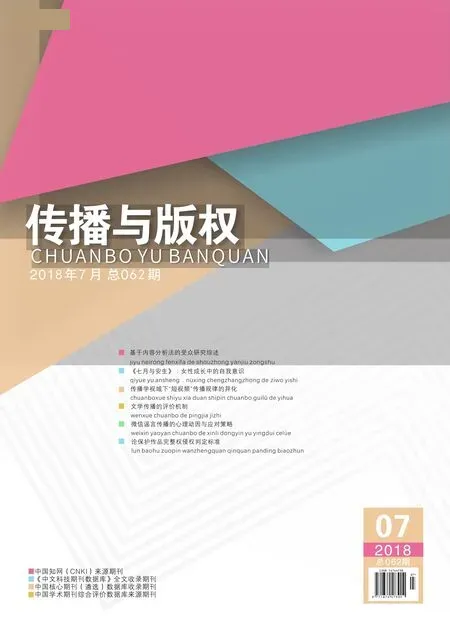論保護作品完整權侵權判定標準
——以“九層妖塔”案為切入點
方月悅
2016年的“九層妖塔”案引起了社會與學界的廣泛關注,該案作為國內第一起原著小說作者起訴改編后的電影作品侵犯其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案例,其將我國學界與司法界一直以來對于保護作品完整權侵權認定標準的爭論又一次引向了風口浪尖。本文將就這一問題從各個角度出發,進行深入探討。
一、對九層妖塔案中保護作品完整權侵權判定標準的分析
本案法院就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判斷標準主要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
首先,法院認為對于判斷復制行為和改編行為是否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應當采取不同標準:
“對于作品的復制,一般是將作品以‘原貌’使用,不改變其表達形式,僅在圖書、期刊、報紙、網絡上進行復制,在此情形下,對于是否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應當堅持嚴格的標準,只要復制后呈現的內容、觀點與作者在原著中表達的不一致的,一般可以認定構成對原著的歪曲、篡改。但是改編行為則不同,改編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礎上再創作的作品,改編作品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利用了已有作品的表達,二是包含著改編者的創作。相對于原著而言,改編作品具有改編者新的創作和表達,必然要對原著的內容、觀點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因此,對于是否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判斷,應當看是否降低了原著的社會評價、損害了原著作者的聲譽。”①《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83號民事判決書》。
其次,法院認為應當考慮原著的發表情況。在作品發表之時,原則上必須尊重作品的全貌,如果此時改動作品,不但會損害作者的表達自由,也會影響公眾對作品內容、觀點的了解,此時關于保護作品完整權構成要件的判斷,應看是否對原著的內容、觀點進行了改動。在作品發表之后,作者的思想、表達已經向社會公開,公眾亦能知曉原著作品的全貌,此時應當重點考慮被訴作品是否損害原著作者的聲譽。
最后,法院認為如果公眾的負面評價主要是針對改編作品或者改編作者產生的,不認為是損害原作品作者的聲譽。即負面評論所產生的后果雖然可能影響電影《九層妖塔》的聲譽,但并未導致對小說《精絕古城》社會評價的降低,因此作者的聲譽沒有因改編行為而受到損害。
結合以上觀點,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在九層妖塔案的一審判決書中認為:
“涉案侵權作品電影《九層妖塔》為特殊的作品類型,涉案電影在法律規定上、表現手法上、創作規律上具有特殊性,應從客觀效果上進行分析,即要看改編后的電影作品是否損害了原著作者的聲譽。電影《九層妖塔》是否損害了原著作者的聲譽,應當結合具體作品,參照一般公眾的評價進行具體分析。根據相關證據,可以看出社會公眾對《九層妖塔》的評論指向的都是電影本身,而非針對作者,未造成原著作者聲譽的降低,不構成對原告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犯。”②《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83號民事判決書》。
該判決理由與結果引發了學界的廣泛爭議,這一現象主要是由于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對于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權構成要件的規定不明所導致的。根據現行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四)款的規定:
“保護作品完整權,即保護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權利。”
該條并未規定何為“歪曲、篡改”,這就導致我國在司法實踐中判定某種具體行為是否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時采用的侵權認定標準的不確定性。因此,筆者認為,須盡快通過立法確定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權認定標準。
二、保護作品完整權侵權認定的兩種標準
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權判定通說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主觀標準,對作者的保護程度較高。一種是客觀標準,對作者的保護程度相對要低。兩種標準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均有所體現,學界也對究竟哪種標準更為合理爭論不休。下文將對這兩種標準進行具體的闡述。
(一)主觀標準
該標準認為,保護作品完整權中“歪曲、篡改”的判斷標準在于是否扭曲了作者的創作意圖或思想感情。一些國家對保護作品完整權采用了主觀標準進行保護,如法國,日本等。日本現行《著作權法》第20條第1款規定:
“作者享有保持其作品和作品標題完整性的權利,有權禁止違反其意思對其作品或作品標題進行的修改、刪除或者其他改變。”
其中,“有權禁止違反其意思”的表述就是典型的主觀標準的表述方式。我國法院在部分案件中也采取了這樣的表述,在確認被告侵權時,其裁判理由多會論及被告的行為是否損害了原作的構思,是否違背了作者的創造意愿。如在“林奕訴中國新聞社”案中,法院在二審判決書中認為:
“中國新聞社未經林奕許可,在其編輯出版的刊物封面上,擅自使用林奕的攝影作品,未給作者林奕署名;在明知作品的主題反映的是海關人員的英勇無畏精神的情況下,為達到自己的使用目的,卻在刊物封面上配印與作品主題相反的圖案和文字,突出了海關腐敗的內容,這種使用嚴重歪曲、篡改了林奕的創作本意。”①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知識產權辦案參考(第5輯)》,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年第85頁。
判決書中沒有說明只有損害原著作者聲譽才構成侵犯完整權,而是認為歪曲作者的創作本意就足以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在“白秀娥訴中國郵政局”案的再審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國家郵政局、郵票印制局對該作品進行的不適當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有損于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故同時構成了對白秀娥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犯。”②《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3)高民再終字第823號判決書》。綜上所述,主觀標準保護作者的是作者的觀點與創作意圖。
(二)客觀標準
客觀標準認為,保護作品完整權作為精神權利的一種,更多地承載著作者的精神利益,如果對作品的使用或者改動達到讓作者聲譽或者人格利益受到損害的程度,則應認定侵犯了保護作品完整權。即只有對作品對改變達到了有損作者對“榮譽或名譽”的程度,才能認定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多數國家采用客觀標準,以美國與英國在版權法中的規定為例,美國《版權法》第106條之二規定:
“某些作者有權禁止故意歪曲、篡改作品或者對作品作可能有損于作者聲譽的修改。對作品所作之任何故意歪曲、篡改或修改系侵犯該項權利的行為。”
英國《版權法》第80條規定:
“享有版權之文學、戲劇、音樂或藝術作品的作者,以及享有版權之影片的導演,有權利在本條規定的情況下使其作品免受貶損處理……如果對作品的處理達到了歪曲、割裂作品的程度,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損于作者或導演的聲望或名譽,則該處理為貶損處理。”
我國法院在司法實踐中也有采取過相同的判斷標準,如在“沈家和訴北京出版社”案中,法院在二審判決書中認為:
“《閨夢》一書存在著嚴重質量問題,該書在社會上公開發行后,必然使作為該書作者的原告沈家和的社會評價有所降低,聲譽受到影響。故被告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有嚴重質量問題的《閨夢》一書,不僅構成違約,同時侵害了沈家和所享有的保護作品完整權。”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高知終字第77號號判決書》。
由此可見該法院認為被告是由于降低了原作者的社會評價與聲譽才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同樣的在“張五常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與新華書店”案中,二審法院也采用了客觀標準來對被告的行為進行認定,認為出版社對原告作品的改動是按照作品的性質及其使用目的和狀況所做的不得已的改動,這種改動無損作者之聲譽和人格利益,并未侵犯作者對其作品的保護作品完整權。④《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2)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09號判決書》。綜上所述,客觀標準保護的是作者的榮譽與名譽。
三、我國應當采用客觀判斷標準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對于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權認定應該采取何種標準,結合九層妖塔案,筆者認為應當綜合一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比較:首先,應當從我國著作權法設立保護作品完整權的立法目的出發。如果認為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作品完整權旨在保護作者的觀點與創作自由,那么采取主觀標準更為適宜;而如果認為我國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護作者的名譽與榮譽不受損害,那么則應該采用客觀標準。其次,該標準應當在合理限度內充分的保護作者的權益。再次,應當從著作權法的本質目的——激勵創新的角度出發,比較那種標準更能起到激勵創新的作用。從次,在考慮采用何種標準時還應當結合國際條約的規定,借鑒多數國家的經驗。最后,應當采用更加具有確定性的標準,減少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從而提高著作權法的確定性。
(一)采用客觀標準符合我國保護作品完整權的立法目的
對于保護作品完整權保護的法益究竟是什么,學界目前有兩種觀點。贊成采用主觀標準的學者認為,保護作品完整權保護的法益為作者的觀點與自由意志,而贊成客觀標準的學者則認為保護作品完整權所保護的法益在于作者的榮譽與名譽。筆者贊同后者的觀點。《伯爾尼公約》第6條之二第(1)款對精神權利做出了如下規定:
“……反對對其作品的任何有損作者榮譽、名聲或利益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更改,或與其作品有關的任何其他行為。”
而在這一條款的制定過程中,各個成員國對于是采用“榮譽或名聲”這一用語還是“心靈利益”這一用語產生了爭論。比利時代表團和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在向布魯塞爾回憶提交的預案中建議將該條中的“其榮譽或名聲”這一用語用“其心靈利益”予以替換。而經過辯論后,許多代表團對該修改建議內容是反對的。①[澳]山姆·里基森,[美]簡·金斯伯格:《國際版權與鄰接權——伯爾尼公約及公約以外的新發展(第二版)》上卷,郭康壽、劉波林、萬勇、高凌瀚、余俊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16-517頁。而除上文提到的美國法與英國法以外,大陸法系國家的德國也將保護作品完整權認為是對作者榮譽的保護。②[德]雷炳德:《著作權法》,張恩民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73頁。
由此可見,對于精神權利保護的是作者的精神利益還是榮譽與名譽這一問題,多數國家與伯爾尼公約都認為保護的是作者的名譽與榮譽。美國在1990年頒布視覺藝術家權利法案(即Visual Artists Rights Act,簡稱VARA)之前,對作者的精神權利直接以民法進行保護。③Mary LaFrance[M].Copyright Lawin a Nutshell,2d.West,2011.74.英國在加入伯爾尼公約前則是通過其普通法中的禁止誹謗規則來保護作品不受歪曲篡改。④Copyright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Trade,Report of the Copyright Committee,1951(Chairman HS Gregory)(Cmd 8662)[R]//劉鵬:《英美法系作者精神權利研究》,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13年,第31頁。由此可見,英美法系國家認為保護作品完整權之目的在于保護作者的名譽與榮譽。
而正如前文所述,大陸法系國家設立保護作品完整權之目的在于保護作者的觀點不受歪曲,造成這兩種法系國家立法差異的根本原因兩者對著作權法的正當性解釋的不同。英美法系國家采取“功利主義”進行解釋,而大陸法系則通過“自然權利說”解釋著作權法的正當性。學者認為,功利主義的正當性解釋更符合現代著作權法的現實。⑤王遷:《著作權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9頁。而我國在精神權利立法上也受到了英美法系版權立法的影響。如我國《著作權法》第48條列舉了一項侵權行為是“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而大陸法系國家并未有類似規定,只有英美法系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國家版權法規定了“禁止虛假署名權”。⑥劉鵬:《英美法系作者精神權利研究》,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13年,第5頁。由此可見,參考英美法系國家對精神權利的規定進行立法在我國存在先例,而“功利主義”正當性解釋也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采用以“功利主義”為指引的客觀主義符合我國保護作品完整權之立法目的。
(二)采用客觀標準符合保護著作權人利益之要求
有學者認為,采取客觀標準會損害到著作權人的權益。不可否認的是,客觀標準的保護范圍必然是小于主觀標準的保護范圍的。因此在九層妖塔案中,法院提出應當針對作品的性質采用不同的判斷標準來擴大作者的權利保護范圍。
贊成主觀標準的學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客觀標準的保護范圍提出質疑:首先,贊成主觀標準的學者認為,對于侵犯未發表的演繹作品的保護作品完整權的行為,由于演繹作品尚未發表,作者無法主張他人對作品的改動對其聲譽造成了影響,故作者只能待作品發表后,其聲譽已經受損時才可以保護作品完整權為由進行起訴,無法做到及時止損。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對于著作權的任何權利而言,其要構成侵權的前提一定是作品在一定范圍內被以某種形式進行了傳播。因此即便是采用主觀標準的德國也認為,作者在作品的完整性方面所享有的人格利益只有在修改后的作品被相當大范圍的公眾所知曉的情況下才值得保護。于是,他不能反對他人在私人圈子內對作品進行更改(Veraenderung imprivaten Kreis)。⑦[德]雷炳德:《著作權法》,張恩民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79頁。而對于該觀點認為的該如何制止“一旦公開就會造成損害”的情形,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條規定的臨時禁令制度就足以解決這一問題。⑧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條規定: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其權利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采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因此,該觀點并不能成為并不能成為支持采用主觀標準的理由。
其次,贊成主觀標準的學者與九層妖塔案中法院認為,對于復制原作品的行為是否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應當采用主觀標準,而對于改編原作品的行為是否構成保護作品完整權侵權則應當采用客觀標準。筆者認為這也是不合理的。復制行為與改編行為的本質性差別在于他人對作品的再現是否添加了具有獨創性的部分,因此,如果是由復制行為導致的對作品的再現發生了改動,那么改動的部分必然是不具有獨創性的。比如運用后期技術處理攝影作品中的瑕疵、臨摹導致的細小的偏差、印刷導致的細微的質量問題等等。而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紙質印刷產業中這類由于人為導致的失誤或者機器技術導致的偏差時有發生。對于這種改動如果認為只要違背作者意愿就可以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將會不合理的擴大作者的權利,增加復制者的義務。因此,筆者認為,不應當對復制原作品行為是否構成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采用主觀標準。即只有當復制行為中伴隨的對作品的改動已經足以影響到作者的名譽時,如上文提到的“沈家和訴北京出版社”案中,由于書籍印刷質量過差導致作者名譽的貶損的情況下,才可認定為構成對作者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犯。
最后,主觀標準的支持者認為客觀標準必須證明造成實際的損害結果,增加了原告的舉證負擔。“九層妖塔”案中法院在判決書中也提出了相同緣由的觀點,其認為觀眾的負面評價是針對電影作品而非針對作者本人,因此沒有導致作者本人名譽受到實際損害而判決不構成侵權。筆者認為,這一理由難以成立。一方面,《九層妖塔》的觀影群眾并不局限于熟知《鬼吹燈》原著小說的讀者,從常理出發,觀眾在沒看過原著的情況下顯然很難將負面評價準確地針對于電影改編者而非原著小說作者。另一方面,如果依照法院的思路,則任何對作品的演繹都不可能侵犯原作作者的保護作品完整權,法院顯然曲解了客觀標準的含義,因此筆者認為法院的觀點難以成立。事實上客觀標準并非要求必須造成實際的損害結果,上述對損害作者名譽與榮譽的解釋不恰當的縮小了客觀標準下的權利保護范圍。采取客觀標準的國家也不認為必須造成了作者名譽實際的損害結果的發生才構成侵權。以英國版權法為例,英國版權法禁止對其作品的貶損處理,在Confetti案中,對“貶損處理”確立了一個較為客觀的認定標準,即“僅有歪曲作品或破壞作品之完整的事實存在無法認定侵權行為的成立,除非該行為有損于作者的名譽或聲望”。①Confetti Records v Warner Music UK Ltd [2003]EWHC 1274(ch)//劉鵬:《英美法系作者精神權利研究》,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13年,第95-96頁。英國版權法采取了“有損于”這一表述表明,需要予以明確的僅是對作品的改動是否具有貶損的含義或者是否可能會造成損害,而不要求實際損害必須發生。②劉鵬:《英美法系作者精神權利研究》,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13年,95-96.因此,客觀標準只要求原告能夠證明被告針對其作品的行為有造成其名譽或聲譽的可能性即可。具體到九層妖塔案,在原告證明了電影確實是由于原作品進行了改動而造成觀眾對影視劇本身大量的負面評價,就足以認為是損害作者的名譽。
綜上所述,即便主觀標準的保護范圍要大于客觀標準,但采用主觀標準不合理地擴大了作者權利的界限。而客觀標準則能夠在合理的范圍內保護作者的權益。因此,采用客觀標準能夠在保護著作權人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實現公眾與權利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三)采用客觀標準符合國際條約的要求與國際立法趨勢
正如上文所述,《伯爾尼公約》對精神權利的規定之目的在于保護作者的榮譽與名譽。伯爾尼公約第五條對國民待遇做出了相關的規定。(1)就享有本公約保護的作品而論,作者在作品起源國以外的本同盟成員國中享有各該國法律現在給予和今后可能給予其國民的權利,以及本公約特別授予的權利。(2)享有和行使這些權利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也不論作品起源國是否存在保護。因此,除本公約條款外,保護的程度以及為保護作者權利而向其提供的補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給以保護的國家的法律規定。(3)起源國的保護由該國法律規定。如作者不是起源國的國民,但其作品受公約保護,該作者在該國仍享有同本國作者相同的權利。因此,《伯爾尼公約》未要求成員國對保護作品完整權達到主觀標準的高度,而是只要達到客觀標準的要求即可。如果我國采取主觀標準作為判斷保護作品完整權侵權的依據,那么根據國民待遇原則,我國則必須給成員國的國民以相同保護水準的待遇。而其大部分國家都是以客觀標準為判斷依據的,根據國民待遇原則,我國作者在其他大部分國家提起保護作品完整權的相關訴訟時只能按照客觀標準判斷是否構成侵權。這種局面不利于我國在世界知識產權貿易中的發展。
此外,縱觀國際立法趨勢,不僅多數國家在保護作品完整權的規定中采用了客觀標準,而曾經采用主觀標準的國家也有修改立法之趨勢。以日本為例,有學者直接主張,不損害作者聲望名譽的改變行為不構成侵害保護作品完整權。③栗田隆:《著作権に対する強制執行(2)》[J]//李揚、許清:《侵害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判斷標準——兼評我國〈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13條第2款第3項》,《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一期,第129頁。由于這是基于對《伯爾尼公約》第6條之2的解讀推演而來的,日本法上并沒有直接依據。因此,通過立法予以解決的呼聲越來越高。比如日本知識產權研究所提出的兩種應對方案中,第二種就是將現行法中規定的“違反作者意思”修改為“損害名譽聲望”,以此限定保護作品完整權控制的行為界限。④知的財産研究所:《Exposure’94 ―マルチメディアを巡る新たな知的財産ルールの提唱》[J]//李揚、許清,侵害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判斷標準——兼評我國《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13條第2款第3項,《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一期,第129頁。綜上所述,采取客觀標準也符合國際條約的要求與國際立法趨勢。
(四)采用主觀標準難以符合著作權法激勵創新之目標
當代知識產權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勵創新。而著作權的激勵創新目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鼓勵從無到有的獨立創做出新作品,二是鼓勵以他人作品為基礎創作完成演繹作品。以他人作品為基礎創作完成的演繹作品即便在獨創性中的“創”的高度上無法達到獨立創作完成作品的高度,但這并不意味著演繹作品就沒有創新性。而要體現出創新性,演繹作品必然要與原作品有所區別,這種區別除了作品種類上的區別外,往往由于作品種類的改變而不得不對原作品本身的內容做出修改,比如,將一本小說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導演編劇在改編過程中往往不得不對原作品對對話、臺詞與劇情做出相應對刪減與修改,如果法院在判斷被告是否構成侵權的情況下僅僅只需要考慮原告的個人意愿,而不是考慮客觀上是否造成了對作者聲譽的損害,那么必將有損改編者從事演繹創作的積極性,與著作權法激勵創新之目的相違背。同時也不利于公眾對知識的傳播與利用。
此外,采取客觀標準并不會導致獨立創作作品的著作權人從事創新的熱情降低。因為即便是采取較低保護水平的客觀標準,作者也可以禁止他人對其作品經行有損其身為作者的聲譽或榮譽的歪曲與篡改行為。如此以來,既不會導致原作者的權利不正當的損害,也不會使得演繹作者由于擔心侵權而限制其對原作品的二次創作。因此,筆者認為,客觀標準在原作者的權利與公眾利用作品進行再創作的自由之間尋求到了平衡點,因此,采取客觀標準是符合知識產權激勵創新之立法目的的。
(五)采用主觀標準難以符合法律確定性的要求
筆者認為,雖然主觀判斷標準在最大限度上保護了著作權人的權益,但是也存在諸多弊端。一方面,以作者個人意志為判斷標準任意性太強,不利于維護著作權市場之交易安全。如果不以造成作者的名譽的損害為侵權構成要件,將勢必導致部分權利人濫用權利,僅因他人對作品微小的修改就以保護作品完整權為由進行起訴,在破壞交易安全的同時也對司法資源造成了浪費。這也是多數國家將“可能對作者的聲譽造成損害”作為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構成要件的原因之一。①Adolf Dietzn.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and Practice[M]//王遷:《著作權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6頁。
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采用相對主觀標準最為恰當,也即以“作品中體現出的作者的意志”作為判斷對作品的修改是否構成歪曲、篡改的標準。認為該標準既保護了作者的權利,以作品中的意志為判斷標準也具有可操作性。但事實上,相對主觀標準仍然具有與絕對主觀意志相同的弊病。以作品中體現出的意志為判斷標準,何為作品中體現出的意志,在實踐中難以判斷。“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品中的意志應該以什么為判斷標準?是以一般觀眾的標準?以行業內部專業人士的判斷為標準?還是以作者本人的意志為標準?采用相對主觀標準最終又將問題引回了是應當從客觀的角度考慮何為作品中的意志,還是以主觀標準考慮何為作品中的意志這一問題,陷入了循環論證。因此,筆者認為相對主觀標準不足以為我國所采納。
四、修法建議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與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尚未對保護作品完整權對侵權認定做具體對描述。筆者認為,應當盡快對著作權法做出相應的修改,并頒布相應的司法解釋,以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
筆者認為,我國應當采用客觀標準作為保護作品完整權對構成標準。因此,我國應當對立法做出修改,明確這一標準。筆者建議,將現行《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四款修改為:
“保護作品完整權,即禁止他人有損作者聲譽的歪曲、篡改作品的權利。”
此外,筆者認為,應當頒布相應的司法解釋對何謂“有損作者聲譽”進行解釋。即并不要求造成明確的損害結果,而是只要原告能夠證明被告的行為有損害其名譽或榮譽的可能性即可。建議新增司法解釋如下:
“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四款所指的有損作者聲譽的情形,包含有可能造成作者名譽或榮譽損害的情形。”
這樣的規定,明確了我國對于保護作品完整權這一問題采用的是客觀標準,解決了認定標準不確定的問題,在給予著作權人充分的保護的同時,也保障了后續演繹者的創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