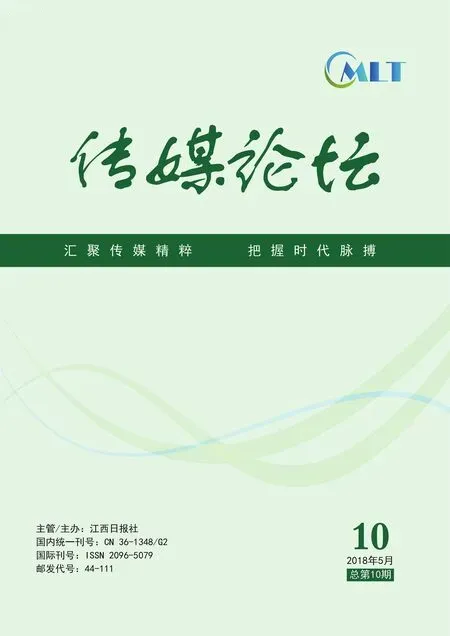秦宋兩朝出版監(jiān)管的研究
(青島科技大學傳播與動漫學院,山東 青島 266061)
秦朝頒布的《挾書律》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頒布禁書的法律,在中國出版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對出版業(yè)的制度化監(jiān)管從宋朝開始,影響了之后的封建朝代。對比分析秦朝和宋朝統(tǒng)治者對出版業(yè)的監(jiān)管,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重要的參考價值,借以分析出版與社會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把握中國出版史發(fā)展脈絡,理解出版與社會的關系。
一、秦朝《挾書律》
(一)《挾書律》內容
在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諸子百家思想大多在此創(chuàng)始,對中國文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中國對圖書的禁止也發(fā)生在這個時期。公元前213年,李斯的提議被嬴政全面采納,始皇帝命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的說法和書籍,并專門頒布了藏書的法律——《挾書律》。它的主要內容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項:第一“史官非秦記皆燒之”。第二“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留《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第三“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第四“所不去者,醫(yī)藥、卜巫、種植之書”。
由《挾書律》內容可知,《挾書律》規(guī)定除了政府有關部門允許藏書外,所有平民和個人全都不得收藏法家以外的書籍。法律也規(guī)定了私人都不能收藏法家之外的圖書,只有國家圖書館允許收藏書籍。司馬遷對此說:“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挾書律》燒光除了秦國之外的諸子百家出版的圖書,先秦眾多意義重大的書籍被燒沒毀掉。因此民眾的思想被禁錮,不會使用某些生產(chǎn)工具無法進行充分的經(jīng)濟活動也限制了秦朝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這也加速了秦朝的滅亡,僅存世15年。
(二)《挾書律》影響
《挾書律》對先秦典籍造成了極大破壞,使得春秋特別是戰(zhàn)國以來的百家爭鳴局面被摧毀,使得出版發(fā)展遭到了嚴重阻礙,也相應限制了秦朝社會的發(fā)展。
秦始皇頒布《挾書律》的最初目的之一是為了加國家強統(tǒng)一,但《挾書律》的實行沒有根據(jù)當時的社會發(fā)展潮流和需要,所引發(fā)的負面結果非常嚴重,比起秦始皇所實施的“焚書坑儒”的負面影響更大、更深刻。《挾書律》直接傷害了當時讀書人的積極性和文化力,影響了當時讀書人22年,使得當時的人才銳減,大師幾乎沒有出現(xiàn),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受到法家思想的嚴重影響,秦朝實行了《挾書律》后,民間藏書看書者受到了很多酷刑,手段之殘暴血腥,前無古人。
西漢初期漢惠帝廢除《挾書律》,平民保留的書籍再次流通,政府鼓勵民間藏書,中華文脈才得以持續(xù)。西漢后期出現(xiàn)了中國古代書肆,相應的書商首次休閑,圖書變?yōu)橐环N商品流通。得益于廢除“挾書律”及其影響,漢朝出現(xiàn)了“文景之治”和“漢武盛世”以及“孝宣中興”,漢王朝持續(xù)了400多年。秦漢不同的出版監(jiān)管所帶來的社會發(fā)展更加凸顯了秦朝《挾書律》對當時社會發(fā)展的危害。
二、宋朝出版監(jiān)管
相比于秦朝的出版業(yè),宋代堪稱是中國出版的“黃金時代”。雕版印刷術的普遍應用是出版史上的“媒介革命”,宋代出版業(yè)取得飛躍發(fā)展。宋代雕版刊印圖書成為利潤豐厚的工作,民間刻印圖書現(xiàn)象普遍,宋代各層官府也刻印銷售書籍,實現(xiàn)了雕版印刊圖書完整的產(chǎn)業(yè)鏈,促進了文化產(chǎn)品數(shù)量的增長,質量方面也得到巨大提升。出版業(yè)的繁榮促進了宋代產(chǎn)生豐富的科技成果以及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財富,宋朝的社會手工業(yè)、商業(yè)異常活躍。
在宋代,民間針對當時科舉考試的需求印刷了應對科舉考試的書籍,有的把科舉考試考題做成小冊子,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舉考試的興盛。
(一)宋朝出版監(jiān)管內容
自宋代開始古代出版業(yè)步入全面發(fā)展時期,出版業(yè)的興起也加大了統(tǒng)治者對文化思想控制的難度。相對于抄寫復制時期秦朝統(tǒng)治者對書籍的毀滅性政策,在印刷本時代的出版業(yè)監(jiān)管,宋代朝廷對出版管理有了“限”和“禁”之分。所謂“限”指的是限制民間個人印刷卻保存政府印刷,在一些方面實現(xiàn)政府出版專權。“禁”是指不允許刊發(fā)、流通有關政策軍事、政府安全、風俗教化重要主題。
(二)宋朝出版監(jiān)管特點
宋朝對出版業(yè)的監(jiān)管有三個方面的創(chuàng)新,這三個創(chuàng)新也與秦朝的《挾書律》有了明顯的不同。
1.通過官方出版為出版活動定基調,完善官方出版機構和體系
宋朝統(tǒng)治者把出版業(yè)作為宣揚封建思想的工具,印刷了大量重要書籍。宋朝由國子監(jiān)和崇文院作為國家出版重要機構,執(zhí)行宋朝統(tǒng)治者的決定,分工明確,相互協(xié)調,組建成官方出版系統(tǒng)。宋代地方各級官署、官學也是官方出版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支流。國子監(jiān)及各軍州對遇有突發(fā)事件,更是及時采取措施,對違法圖書進行清查。與秦朝的《挾書律》相比,為加強出版管理,宋朝統(tǒng)治者設立專門機構,從上到下建立了完善的官方出版管理體系。
2.實行圖書審查機制,提高平民圖書控制力
由于宋代相對分裂的朝代特征,宋對遼、金圖書輸出禁止最嚴,打擊了謀求圖書利潤的圖書商人,體現(xiàn)了特殊的出版時代特點。在政府對出版活動的具體實施中,一整套圖書出版監(jiān)管機制在宋朝得以建立,例如預先審查機制、事后審查機制、獎勵檢舉機制等。其中事后的審查和預先審查是中華法系和世界法系里最早出現(xiàn)的出版審查制度。為使整個出版活動置于廣泛的社會輿論監(jiān)督之下,宋朝還實行舉報獎勵制度。“這些詔令、條例具有權威性、強制性亦即準法律性的特點,體現(xiàn)了宋代封建國家的出版導向和出版政策。”
3.圖書管控制度化,加強對邸報控制
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最早的報紙是邸報。到宋代,印刷技術不斷改進和大力普及,應用到邸報上產(chǎn)生巨大影響。于是,宋朝官方采取措施對邸報加強控制。邸報定本制度實行始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這標志著古代統(tǒng)治者對出版控制邁向制度化、正規(guī)化。
宋朝的出版業(yè)監(jiān)管制度為之后的朝代打好了基礎,元、明、清統(tǒng)治者都懂得利用出版來為政治服務。從秦朝的“挾書律”到宋朝的“限”“禁”令,中國禁書史走過了一條漫長的道路,也對當時的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社會的形成是當時社會所出版的圖書的結果。縱觀古今中外,從秦朝到宋朝,從一部出版法律到一套出版制度,中國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者對出版業(yè)不斷加強控制,其重要目的是控制文化思想的傳播,加強中央集權,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出版對社會的互動影響,相應的出版政策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民眾對于生產(chǎn)工具的使用和生產(chǎn)關系的改善,人們的思想得不到提升,精神世界得不到滿足,從另一個層面反映出封建社會的腐朽和逐漸沒落,因而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
轉型與創(chuàng)新,是當代中國出版業(yè)的時代主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在2017年11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這是十九大后的第一部文化方面的法律,對于進一步健全我國出版法律制度、保障普通人民基本文化權益作用非凡,對于出版業(yè)的轉型創(chuàng)新也提供了法律基礎和重要條件。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的出版行業(yè)也在面對時代的變化不斷進行變革,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針對40年來中國出版的實際情況,中國實施多項法律條文和相關政策,推動中國出版健康有序發(fā)展,例如實行了承包制和內部責任制相結合,進行出版機構轉企改制,建立當代出版企業(yè),集團化發(fā)展,促進出版集團上市等多種管理方式,促進出版業(yè)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服務社會發(fā)展,堅持經(jīng)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結合,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
如今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要遵守出版法律法規(guī),把握出版規(guī)律,提升出版人的專業(yè)素養(yǎng)和綜合素質。面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沖擊,傳統(tǒng)出版企業(yè)也要認清形勢,借助數(shù)字技術和金融資本加速自新,在出版法律的保護下保持出版的活力。
三、結語
身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進全民閱讀,打造書香社會是深化改革開放,推動我國社會全面發(fā)展的重要舉措,中國出版工作者應當以史為鑒,借鑒得失,在中國當前出版法律不斷進步的大背景下,珍惜出版的發(fā)展機遇,更好發(fā)揮出版業(yè)對社會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