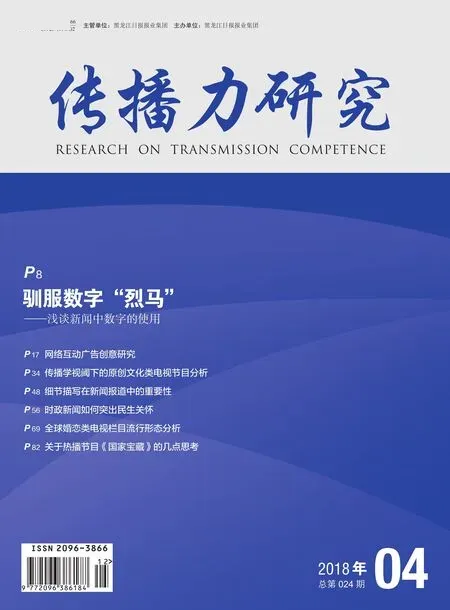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視角下的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
——以紀錄片《彝問》為例
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資源豐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變遷,幾乎聚集了我國所有的少數民族。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作為反映我國西南少數民族日常生活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文化傳播產品,本應得到重視,但由于西南地區特殊的地緣環境和歷史因素,使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紀錄片具有很強的政治元素;作為具有特色的文化產品,西南少數民族的紀錄片拍攝,也應遵循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觀的規律,使其成為具有中國特色和獨特文化風味的紀錄片產品。
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視角下的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的特點
紀錄片《彝問》與2017年3月10日在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欄目播出,拍攝歷時半年,通過活在當下的一個個生動人物,一個個鮮活故事,去搭建一條影像化的路徑,帶著觀眾一起,走近彝族,去探究,彝族的昨天和今天;去感受,彝族的苦樂與悲歡;去描繪,彝族的憧憬與希望。該片以“家園”“血脈”“繁花”和“生機”為構架,涵蓋了彝族博大精深的畢摩文化、節慶、婚俗、美食、服飾、音樂、彝語文教育等文化特質,展現了當下彝族人民對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對精準扶貧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希望和憧憬、對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等多元的一副真實的畫卷。是中央電視臺近期播出的人類學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從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視角觀看《彝問》,主要呈現如下特點:
(一)以人為本
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核心與本質。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彝問》明確的體現了紀錄片中的以人為本。在紀錄片中,以生活在大涼山的彝族人為介紹的切入點,通過德古阿蘇作古來反應彝族的習慣法風俗,即在面對民事沖突時,往往不追求官方解決問題,首先是找到德古來解決;德古解決糾紛的首要依據也并不是法律,而是彝族多年傳承下來的習慣法。通過畢摩曲比拉伙的驅魔法事和婚嫁約定活動來反應彝簇文化傳承的方式,并通過曲比拉伙和兒子曲比的洛的思想沖突,來表現彝簇文化傳承的困境。
(二)從實際出發,始終堅持客觀中立立場,如實反映現實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要求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報道的真實性,從實際出發來看待新聞事實。在紀錄片的拍攝也是如此,尊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生活習慣是在過程中的絕對遵循。《彝問》這部紀錄片拍攝的初衷:原本是想做成一部文化歷史題材較嚴肅的紀錄片,請撰稿人寫出來后不太滿意,又經過反復調研和討論,最終決定建立在發現當代彝族地區,尤其是涼山州彝族現實生活、風情百態的基礎上,做一部人類學的紀錄片。
同時,針對彝族與漢族在法律認同上的差異,如彝族對德古的認同超過法律,那么紀錄片中,就選擇了德高望重的德古作為切入點來紀錄彝族人在面對矛盾時的處理方式,而不是通過政府或是村鎮級機關單位。面對彝族文化對于普通人的陌生,并不回避,而選擇在紀錄片中,用小動畫的形式來訴說彝族先民的歷史和傳統。
(三)堅持與時俱進
堅持與時俱進,紀錄片是一個階段文化發展程度的表現,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紀錄片拍攝同樣具備與時俱進的特點。在《彝問》的第二集“血脈”當中,就有一個板塊從25歲喪夫,獨自撫養三個小孩的小山村村民的日伍子莫作為切入點,描寫涼山地區小山村的精準扶貧情況。通過紀錄片反應了國家的精準扶貧政策,為困難群眾提供建房基金、提供牲畜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并建立幼教所,加強貧困地區的素質教育。
在《彝問》第四集當中,又通過描寫了一個叫月琴的老人,反映了彝族人的工匠精神,對彝畫、彝族傳統服飾和漆器的繼承。緊密的結合了我國當前的政治政策和社會環境。
二、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的存在的問題
(一)經濟落后,制約紀錄片產業的發展
西南地區包括了我國的廣西、云南、貴州、西藏、四川和重慶,地域廣大,雖然有豐富的民族文化和傳統,但地理環境的制約,仍然局限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甚至在如此現代化的社會,仍然存在著農奴制和原始的氏族制。落后的經濟制約了文化產業的發展。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環境不能夠為紀錄片的產業化發展提供條件,類似《彝問》這樣的紀錄片也只能是央視和地方合拍最終才能成型。
(二)對當地文化傳統了解不深入,造成紀錄片拍攝失實
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雖然同一民族的文化在大體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生活習慣和地理位置差異,往往隔了一座山或者一條河,在具體的文化傳承上就會有許多的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在《彝問》當中,雖然都是生活在四川大小涼山的山區,但是不同家支的經文和畢摩的祈福方式就存在著差異,一些紀錄片在沒有完全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后就盲目的進入拍攝和剪輯,而引起了爭議和受眾的不滿。
(三)受眾群體小,專業人才少
西南少數民族畢竟是我國少數民族的一部分,而且許多紀錄片都摻雜了少數民族的文化、語言,對普通受眾來說接受度不高。而且相較于《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等題材,西南少數民族的紀錄片在趣味性和觀賞性上存在劣勢。
人才是紀錄片創作的核心,優秀的創作人才可以策劃出經典大片,然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環境復雜多變經濟相對落后。外面的人才不愿意進來,里面的人才留不住,這也成為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紀錄片發展的一個瓶頸。此外,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的人才分工不合理,優秀的紀錄片人才往往身兼數職,不僅負責撰寫策劃稿,還要負責拍攝、錄音、采訪、后期剪輯等工作,這樣單視角創作出來的紀錄片有其自身的缺陷。
三、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的存在問題的解決路徑
(一)充分利用新媒體平臺
電腦、手機、平板的普及和微電影、短視頻的發展,為低成本紀錄片的拍攝和推廣成為可能,目前,我國各大視頻平臺和短視頻直播平臺都開設了專門的紀錄片板塊,錄片慢慢告別了長期以來對電視頻道和院線傳播的依賴。手機、單反相機等移動數碼的快速發展也為低成本的微電影制作。
(二)建立多元化投資機制
目前,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紀錄片拍攝的資金來源仍然主要集中在政府投資和電視臺投資兩個方面,電視臺投資仍然是紀錄片拍攝的最有力的投資主體,投資渠道的單一,使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紀錄片拍攝資金來源顯得十分有限。我國西南地區電視臺在拍攝少數民族紀錄片時,應該更加主動的與民間資本、視頻平臺、直播平臺溝通,爭取更多的資金來源;或者通過商業定制的模式生產少數民族紀錄片,既達到了品牌的商業宣傳目的,也對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進行了傳播。
(三)培養紀錄片人才,做好受眾調查和地域情況調查
人才是紀錄片創作的靈魂,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人才引進比較困難。但可以通過與當地高校展開合作來培養人才,并開展與少數民族相關的紀錄片比賽,這樣既可以達到挖掘人才的目的,也可以擴大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力,提高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的創造力和活力。
同時,在創作紀錄片時,注意把握受眾的喜好、對計劃拍攝地區做好田野調查,避免因自身的失誤而導致紀錄片失實和流水賬式紀錄片的出現。
欲速則不達,要想真正的將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紀錄片做好,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們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和正確的政治輿論導向的前提之下,促進少數民族紀錄片的商業化和市場化,從而釋放活力,做出更好的作品。
[1]洗卓桑.文化地理學視角下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研究[D].廣西:廣西大學,2015:23-26.
[2]徐夢菊.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產業化研究[D].廣西:廣西大學,2016.16-17: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