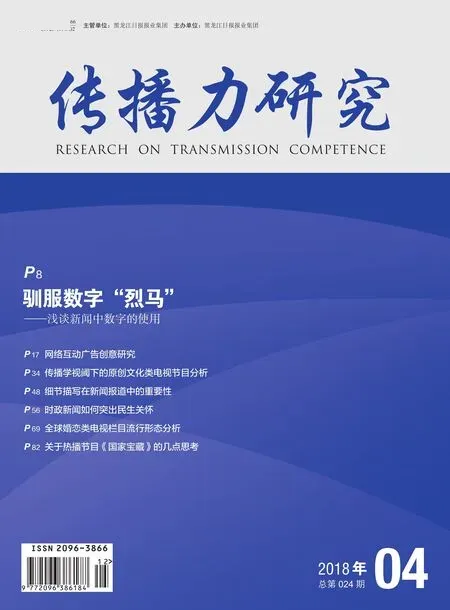淺析《刺客聶隱娘》中的“留白”藝術
侯孝賢在《刺客聶隱娘》運用了大量的留白手法,整個影片就如一首言盡而意不能盡的古詩,初讀時就感覺很美,細讀之后卻又能生出無限的想象與審美愉悅,這也正是獨特的東方審美理想帶給人的獨特的審美感受。
一、極簡的敘事卻帶給人無限的想象
《刺客聶隱娘》中大量的敘事留白給觀眾帶來了最大限度的想象自由,想象對于藝術作品的創作者來說決定了作品的意境。影片講述的故事基于一個十三年前的前程往事,然而導演卻沒有按照傳統的敘事風格,而是打破了傳統的敘事方式,直接從十三年后開始講起,即便從后來人物寥寥數語的對白中我們也很難拼湊一個清晰的前程往事。我們不禁會想象,窈七如何與田季安相戀的,得知嘉城公主欲與元氏結親的時候窈七內心是何感受,山上學劍的時候窈七又是怎么度過的,這些導演統統都沒有告訴我們,需要我們自己去想象,這就是好的作品的魅力,它使人產生豐富的聯想與想象。
影片在人物關系的處理上的留白也是極其耐人尋味的,甚至這些留白直到電影結束也沒有填補。李安導演說過;“我們沒有權利給觀眾下答案,我們做的是如何刺激觀眾的想象力是,設下一個謎面,讓觀眾去猜謎”。①影片中隱娘的性格非常孤僻、沉默,道姑送隱娘回到家中,十三年后母女二人再次相見,彼此都沒有關切和問候。兩人唯一一次交流就是母親告知隱娘嘉城公主的死訊和公主最遺憾的事就是屈判了阿窈,隱娘掩面失聲痛哭,這使我們不禁想象為何隱娘與母親聶田氏的感情如此涼薄。隱娘與磨鏡少年的感情線導演也沒有大肆渲染,這位磨鏡少年的身份背景不甚詳細,他如何愛上了隱娘更是不得而知,然而卻自有一種清風自來的舒適真摯。
二、人物情感上的留白表現出極具中國特色的審美理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審美,追求的是節制,雋永,發乎情而止于禮。此外中國傳統文學特別是言志的詩中,有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孤獨。影片多處使用留白手法和緩慢的長鏡頭表現人物內心的情感,營造出一種感傷、悲愁的意境。嘉城公主和隱娘都是孤獨的,公主只身一人從繁華的長安來到魏博,她應該充滿了孤獨與思鄉之情,隱娘成為一個多余的人遠走他鄉十三年,她們都是政治的犧牲品。青鸞既是嘉城公主,也是隱娘,更是導演內心的表達。隱娘在得知嘉城公主死訊之后,是掩面痛苦,而不是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隱娘為什么會哭,又為什么將巨大的痛苦壓抑在內心深處,一個人沒有同類,隱娘對嘉城公主的死傷心悲痛,因為他們同是為政治利益而犧牲的孤獨者,這壓抑隱忍的悲痛也是隱娘自己內心孤獨的一種表達,如果是嚎啕大哭反倒不美了。在表現隱娘對田季安的情感時,隱娘是隔著重重的屏障窺視田季安與胡姬的,絢麗薄紗后的隱娘靜默不動,畫面里的田季安與胡姬隔著薄紗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就如同隱娘的視線時而被薄紗遮擋。在刻畫隱娘與磨鏡少年的感情時,同樣是淡淡的、有所保留的,而其中的真意卻已讓人心靈神會。
三、畫面構圖中的留白勾勒出中國傳統美學意境
除此之外,整個影片最明顯的就是在畫面的色彩和構圖上運用的大量留白手法,使得整個影片就如一幅精美的中國寫意山水畫,表現出了明顯的中國古典美學傾向。不同于以往的武俠片極盡動作之絢麗,人物飛檐走壁,到處充滿了腥風血雨,隱娘的招式都是干凈利落的,人物在這樣的環境中脫去了喧囂的江湖味道,卻更能使人感受到蒼涼的時間感和寂靜的空間感。畫面中的景物、空鏡頭更是將中國古詩詞里的留白和寫意用電影語言表達了出來,夕陽西下的農舍背靠著遠山,田間阡陌交錯,雞犬相聞,村中炊煙裊裊,這正是陶淵明筆下的田園生活。這詩意的景物,詩意的感情正是隱娘渴望的,也是我們現代人缺少的,我們的精神是疲乏的,我們的生活被各種無意義的瑣碎的東西塞滿,我們缺少對生活的、對精神的、對審美的精致的詩意的追求。結尾處,隱娘和磨鏡少年護送老者離開,人物在明媚如畫的山巒中漸行漸遠,往那蒼蒼茫茫的遠方而去,直到最后只剩下幾個黑點。在這長達七分鐘的長鏡頭中,人物漸行漸遠,整個畫面慢慢的都是山巒和草木的留白,給觀眾一種情感上的抽感,然而這看似是故事的結束,但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呢,隱娘的人生也許才真正的開始,她已經從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走向了自由。
四、結語
《刺客聶隱娘》留白手法在表現中國傳統美學的運用是一次成功的創新,能夠引起人們對于藝術電影的思考,尤其是具有中國本民族特色的藝術電影,怎樣將中國傳統審美趣味同受眾的審美能力統一起來,怎樣將商業利益與藝術價值統一起來既賣好又叫座,是我們仍然需要不斷探索的。這部電影具有極大的藝術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部詩的電影,一部真正體現了中國美學的電影。
注釋:
①張盼.影視留白的美學賞析[J].電影文學,2008,(14).
[1]張盼.影視留白的美學賞析[J].電影文學,2008(14).
[2]宗白華.美學與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