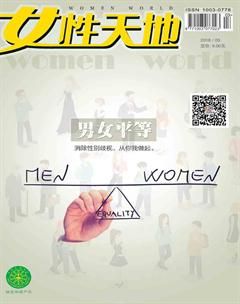不油膩仍清澈
周滿珍

自游學之風興盛,名校之旅仿佛是春日少年游的專利,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風十里,遠方是星辰大海,當然要去最好最強的宇宙晃蕩啊。走到人生中途的中年人,和名校相遇太晚,老到不足以談戀愛,不足以讓人走轉向。
那又如何,曾在生命旅程中出現過的美國名校坐標,于我,是分別經年的少年友人,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我來到你的城市,怎可不給你一杯咖啡、一頓飯敘的時間?
2017年秋,人在美東波士頓,第一站當然給盛名在外的哈佛大學。
說來氣短,我對哈佛光環的初次領略,竟來自一本叫《哈佛女孩劉亦婷》的自傳。那是2000年,劉亦婷的母親劉衛華帶這本書來武漢簽售,我去采訪,急于復制第二個劉亦婷的父母們,擠爆了現場,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拿到哈佛全額獎學金,讓望子成龍的父母們熱血沸騰,這本書據說創下了200萬的銷售記錄,催生了教育類圖書“勵志+素質”新戰場。
我去哈佛的中午,理想的壯懷依然激烈,一撥又一撥初高中生模樣的孩子,無問西東,排著隊摸雕像版哈佛先生的腳,冀此沾點好運。青春的歡聲笑語,給校園內的紅墻綠樹抹上了幾許亮彩。
那日陽光甚好,草坪上安置了不少椅子,供行人休憩,我便和美國友人在此小坐,一邊打望哈佛數百年不變的標志性紅樓。作為美國最老的大學,哈佛名人校友走馬燈一樣在腦波里晃過,梭羅自在其列。20歲從哈佛畢業后,他選擇到田野居住,學會伐木自制家俱,上午去瓦爾登湖湖邊散步,晚間欣賞音樂,在小木屋寫出今日熱捧的佛系生活之圣典《瓦爾登湖》。還有1927年的梁思成,遠道至哈佛人文藝術研究所,研究東方建筑。小紅樓還是舊時模樣,梁先生在此苦讀經典,想要保護的東方建筑,已是滄海桑田,換了天地。
90年過去,哈佛校園里,隨處可見梁先生式東方面孔。朋友說,美國正遇經濟衰敗,全美名校都在爭取中國生源,以救教育經費短缺之困厄。有則八卦可資為證:和80后小女友談戀愛,會做“笨笨牌”紅燒肉的明星老板王石,三年前之所以選擇哈佛就讀,是當他表達出重回校園充電的奇想時,剛好且只有哈佛商學院向他發出了邀請。美東名校行,背著雙肩包疾走的中國少年隨處可遇,充分感受到祖國強大光芒的照拂,幸焉!



但我對哈佛真是“高山仰止”,念茲在茲是后半句“景行行止”,是校園外供人行走的寬闊道路,和路旁各式各樣的書店小店。沿街的小庭院里,主人隨手種植的花草,晚秋仍舊蔥蘢。午后時光,書店里人亦不多,但從老板、服務生臉上,并未窺見暴流一般的生活長河中,浮泛的渣滓,便可想見,此地的營生,足可維持他們基本的生活尊嚴,甚好。
因為這些型格別具的小店,從哈佛到麻省理工的20分鐘路程,我們選擇步行,穿越坎布里奇街。坎布里奇的英文為cambridge,我一度疑心來到了英國劍橋大學分部,查資料才發現,當年是劍橋向新成立的哈佛援建師資,坎布里奇大街由此而來。流經坎布里奇名校的查爾斯河,云在青天水自流,似在提醒后世學子飲水思源。
我們在窗外看風景,窗內的人看我們,眼神交匯的剎那,發現了一家位于地下室的川味餐廳,兼作日本料理。進去時,一桌老外正在分食日式海鮮拼盤,我點了肉沫豆角,食材正宗,烹飪水平放在國內,亦可列入中等。后來在波士頓的幾頓主餐,都在快餐連鎖Dunkin Donuts解決,真后悔當時沒有打包一些飯菜回去。
美國作為移民國度,美食繁盛,但如果想以國內價格甚至翻倍的價格吃到,皆不可能,因為餐廳的稅費及小費,加起來就要占40%左右。在金錢的算計面前,口腹之欲,忍得了一時。
逛回麻省,純粹是一個平庸文科女對學霸理工男的好奇,欲一窺天才們的容貌。麻省的明星校友,遠有錢學森,近有張朝陽。搜孤風頭正勁的年代,男性時尚雜志寫滿了這位麻省理工男的傳說。可惜我一進去就被校園內各色當代建筑所惑,那些造型各異、色彩繽紛的建筑,如旅行指南所言,滿足了你對校園建筑的全部想象。那是第一次,我想撥開一所名校的皮囊,探究里面躍動的靈魂。麻省從不會讓看客失望,設計師們自帶創新基因的建筑作品,美得比表象更有意思。
因為這一點對與眾不同的追求,首府華盛頓城內的大學,重點鎖定喬治城。美國的校園都沒有大門,當迎面而來,背負雙肩包,手握一杯咖啡的年輕面孔越來越多,就可以確定,已經進入大學校園了。喬治城作為最早的天主教大學,是培養外交官和律師的頂級私立學府,曾在此就讀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是他們的明星校友。來到美國,我從不吝向人展示美劇粉的忠誠,《傲骨賢妻》中男女主角Will和Alicia就是從這里畢業的。
喬治城是華盛頓富人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大隱隱于市。如果有天寫理想的小城鎮,喬治城是絕佳范本。它的名物除喬治城大學,尚有舊石頭屋(old stone house)。這座典型的中產階級住宅,因為是較早的原創建筑,一代又一代人如珠如寶地修繕著、保存著,現為禮品店。喬治城大學在一個小山坡上,主體建筑名為healy hall,由幾棟房子一字排開,外觀頗有霍格維茨魔法學洨的范兒,功能上卻集行政、教學、圖書館等為一體。透過遠遠近近的樹從,波光粼粼的波多馬克河,華盛頓方尖碑,在陽光下閃耀。此地逢春櫻花盛開,除了粉白雙姝,尚有垂櫻、玉蘭,小山坡、湖水、櫻花,竟勾起我對母校故園的思念。

“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我總算不是一個無情的人了,對近處的生活,起了相思。
于是,不管在紐約城如何逍遙快活,城內的哥倫比亞大學仍位列必去清單之一。因為哥大盛產媒體明星和新聞界奧斯卡—普利策獎得主。近日寫了《火與怒:特朗普白宮內幕》的邁克·沃爾夫便畢業于哥大。此前,他為媒體大佬默多克寫過一本傳記。我的切膚之感來自楊瀾,從央視離職到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就讀的她,1995年出現在央視春晚紐約外景地,她坐在費翔身邊,隨馬車行駛于中央公園,整個人仿佛經過哥大的點染,變得風華絕代起來。不幾年,她創辦了陽光傳媒,是最早從媒體人向女總裁躍遷的佼佼者。
我坐哥倫比亞環線去哥大時,下錯了地鐵站,誤入一個黑人區。下午四點鐘光景,沿路可見倒地的空酒瓶、蹲在街角的閑人,再無種族偏見的獨行女子,此時的內心也有幾份懼意。有個好心的女孩,用Google幫我識得方向,便縱步狂奔,路之盡頭是個山坡狀公園。一個推著嬰兒車的黑人婦女告訴我,翻過此山便是一所大學,不知道是否哥大?
爬到山坡上的亭子,四下一望,果然是哥大校園。趁著陽光仍好,許多學生席地坐在圖書館前的階梯上看書、聊天,樓與樓之間的草坪上,四處散臥著看書的學子,也有三五學生集會,商量著晚上的某個公開抗議活動。那種民主中帶著活力的氛圍,正是我想象中的哥大。我不由自主調動了全身所有的官能去感受,竟然生出我的人生嘉年華已結束之感。以后,只能凝視這些青春的、靚麗的面孔,來回憶那些逝去的理想和時光了吧。

回程時站在亭臺高處,俯瞰整個紐約城,天光與云影正在交替,腳下的紐約城如夢似幻。在漸濃的暮色中,結束美東名校行最后一站,不快樂也不黯然。
但此行仍有兩大遺憾,一是沒有去成紐約州西北部的康奈爾大學。現代文學史上幾位大人物胡適、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先后留學于此,此校風景佳美,能量高的電子更容易躍出常規,成為現代文學八卦最大的策源地,竟不能至,可惜可惜。另一大遺憾是沒去成瓦爾登湖,對于一個以浪游為終身職業,不油膩仍清澈的文藝中年,梭羅的《瓦爾登湖》是“一生放縱不羈愛自由”力比多最旺盛的年紀,吃過的最早一道充滿維生素的菜肴,沒齒難忘。但學醫的美國朋友的本能反應卻是—一個小池塘有什么好看的?我竟無言以對,因為瓦爾登湖的英譯確實是Walden Pond。
這個小池塘,從波士頓北站坐通勤火車到Concord小城,沿著梭羅街往前直走,再右轉,半小時便可抵達。Concord亦值得消磨時日,涌現了愛默生、梭羅、阿爾考特、霍桑等四位文學名家。霍桑的《紅字》是我一口氣讀完的的第一本英文原著小說,那顆為英文抒寫魅力而澎湃的心臟,仿佛還在跳動,但生命中總有這樣最后的幾十公里,此處彼處,只一個轉身,關山萬里遙。
我只是想站在梭羅小木屋前,告訴他,我已懂得那句“ 我寧愿坐在一個南瓜上擁有完全屬于我的全部,也不愿和別人擠在一個天鵝絨的墊子上”的全部奧義。2017年,我亦活到梭羅離開這個世界的年紀,孑然一身,將都市里的日子過得像農夫,用空前樸素的低度生活,換取著盡可能高度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