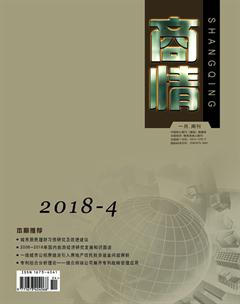財政支出偏向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影響的實證研究
黃獻亮 田園
[摘要]本文選取2007年到2014年中國31個省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研究財政支出偏向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財政支出偏向與企業資本勞動比率均顯著負相關。本文將在財政支出偏向于企業資本勞動比率關系的基礎上,研究對企業長遠發展的影響以及上升到宏觀角度去分析對經濟社會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財政支出偏向 資本勞動比率 動態面板
一、引言
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時期,作為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微觀企業則表現為:企業用資本替代勞動進行生產。在我國,財政支出會偏向于生產性支出。它對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可能會導致企業資本勞動比率不斷提高,宏觀方面看,失業問題會凸顯。
二、變量選取、數據說明、模型設定及估計方法
(一)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2007年一2014年31個省每年末所有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了固定資產占比小的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最終得到565家上市公司2007 2014年共4219個樣本。本文數據來源國泰安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使用Stata12.0進行數據處理與分析。
1、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資本一勞動比率(KL),即企業資本總量除以勞動力總量的值。關于資本的衡量指標,本文借鑒Marina(2009)的觀點,在計算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時使用企業固定資產重置價值來表示資本總量,使用企業年末員工人數來表示勞動力總量。
2、解釋變量的選取
本文設計計量模型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財政支出偏向對企業勞動比率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科教文衛支出和生產性支出的比率,作為解釋變量。
3、控制變量的選取
(1)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KLi,t-1)滯后值:Ln(上期末企業固定資產重置價值/上期末員工總人數)。企業在考量本期的資本勞動投入時,勢必要考慮上期的投入情況。因此本文使用滯后一期的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作為控制變量。
(2)滯后一期的科教文衛支出一生產性支出的比率(PFEDi,t-1):解析變量的滯后值,由于政府行為對企業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用滯后一期的科教文衛支出一生產性支出的比率作為控制變量。
(3)無風險利率(RF):每年一年期國債利率的均值。一方面,國債利率越高,資本價格也越高,因此國債利率與資本一勞動比率呈負相關。
(4)勞動力價格(W):Ln(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一般來說,勞動力價格越低,企業越傾向使用勞動力進行生產。
(5)產品需求(SELL):營業收入/資產總額。企業的營業收入可以反映市場對其產品的需求情況。考慮到我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相對昂貴的資本,本文預測產品需求和資本勞動比率顯著負相關。
(6)成長性(GR):用托賓Q衡量。其計算公式為(每股價格×流通股股數+每股凈資產×非流通股股數+負債賬面價值)/總資產。
(7)地區市場化程度(MKT):本文參考了樊綱、王小魯等所著的《中國市場化八年進程報告》,以各省區的市場化指數總得分為衡量指標,該指數越大,表明公司注冊所在地的市場化相對進程越快。
(8)資產負債率(LEV):即企業總負債和總資產的比率。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償債壓力越大,企業越偏向用勞動生產,因為使用資本不容易變現。
(9)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比(PRICE):該變量用來控制資本勞動的相對價格變化對企業資本替代勞動決策的影響。其計算方法:企業資本成本/企業人均真實工資收入。
(10)企業規模(INSALES),使用企業銷售額的對數來表示。企業規模的異質性特征必然會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產生影響,基于此,本文在計量方程中加入企業規模自身特征的控制變量。
(11)國有企業虛擬變量(SOE):如果是國有上市公司,虛擬變量為1,否則為0。通過SOE虛擬變量與財政支出偏向衡量指標的交乘項來檢驗所有權性質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是否存在影響。
(12)企業所處行業虛擬變量(INDUSTEY):不同行業有不同的行為偏好,對企業資本勞動比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13)企業所在省份虛擬變量(PROVINCE):不同省份政策以及市場環境不同,把企業所在省份作為虛擬變量,考察不同省份財政支出偏好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的影響。
(14)企業所在地域虛擬變量(PLACE):本文按照《中國統計年鑒》對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劃分,以檢驗東、中、西部財政支出偏向對資本勞動比率的影響。
(二)模型設定
根據以上變量選取及數據收集整理,本文對所獲取數據進行大樣本OLS回歸、混合回歸、個體固定效應和雙向固定效應來考察財政支出偏向和企業資本勞動比率之間的關系:其中,i是企業,t是時間。
為了揭示因變量的動態變化特征,本文設定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把因變量的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作為解釋變量引入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之中。
在后續研究中,引入兩個虛擬變量和財政支出偏向衡量指標的交互項來分別檢驗企業所有權性質和所處地區(東部、西部或北部)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財務指標敏感性的影響,分別設定如下模型:
(三)估計方法
為了揭示因變量的動態變化特征,本文設定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由于把因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自變量引入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之中,因此即使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剔除了異質性的企業個體效應,也依然無法解決內生性問題導致的參數估計偏差問題。針對這種內生性問題,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用一階差分廣義矩(first differenced GMM)進行參數估計,然而,用差分廣義矩估計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僅對差分方程進行估計會損失樣本信息量;其次是用滯后水平量作為差分量的工具變量容易面臨弱工具變量問題。為了彌補差分GMM估計方法的不足,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 l和Bon(1998)提出了另外一種更加有效的方法,即系統GMM估計方法。由于系統GMM方法能夠同時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信息,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會更強,因而相對于差分GMM的參數估計結果更加有效。本文使用了系統廣義矩兩步估計方法來對本文模型進行回歸,有效避免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并使用Hansen檢驗來考察選擇的工具變量的有效性。
三、樣本描述及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了2007年2014年8年期間樣本數據,根據數據可以做出以下的分析:
(1)企業的資本一勞動比率的平均值是3.726,最大最小值分別為13.326和-5.673,說明在不同企業在資本一勞動決策時會產生較大的差異,企業對資本和勞動投入的偏好不同。
(2)政府的財政性支出偏向的平均值為1.122,最大值和最小值1.897和0.445,標準差為0.270,說明我國各省的財政性支出偏向差異較大,最大最小值相差比較大。
(3)資產負債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為41.939和0.003以及標準差為1.079,說明樣本企業對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還是抱有不同的態度,存在幾乎無債務負擔的企業,也存在資不抵債的企業。由于企業的成長性、企業規模、所有權、勞動力價格、產品需求以及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比在極差、標準差等方面表現有顯著差異,綜合可以體現為企業的生產率差異,說明本文選取的企業具有企業異質性。
(二)實證分析
1、實證結果
本部分采用系統GMM方法對財政支出偏向和企業資本勞動比率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估計,同時為了進行對比,也采用OLS方法與固定效應法的估計結果列出。如表1所示,第(1)、(2)、(3)和(4)列分別是大樣本OLS回歸、混合回歸、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第(5)列是系統GMM方法估計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結果,在該估計中,還進行了工具變量整體有效性的Hansen檢驗與殘差的序列相關檢驗,其結果通過了工具變量的整體有效性檢驗,同時殘差序列存在顯著的一階序列自相關,但是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
由上表可知:
(1)財政性支出的偏向和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在各種回歸結果中均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若財政支出比原來偏向生產性支出,那么企業偏向于資本性的投入,用資本去替代勞動,資本勞動比率會提高。
(2)滯后一期的財政支出偏向和企業資本勞動比率,在固定效應模型中于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了由于政府行為對企業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性,政府前一年的財政的生產性支出增加,會對企業資本勞動比例有顯著的作用,企業偏向于資本性的投入,用資本去替代勞動,資本勞動比率會提高。
(3)在混合回歸和動態面板數據GMM的估計結果中,產品需求和資本一勞動比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而成長性與企業規模同樣也與資本一勞動比呈顯著負相關。這說明企業產品需求越多,銷售收入增長越快,企業規模越大,企業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力則更多,因為我國的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所以資本一勞動的比率越低。
(4)勞動力價格和資本一勞動比在在固定、雙向固定效應和動態面板模型中,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勞動力價格越低,企業更偏向使用勞動力生產,所以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越低。
(5)企業資本一勞動相對價格的回歸系數在各方程中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資本與勞動的相對價格是制約企業選擇資本或勞動不同生產方式的重要因素。
(6)在固定效應模型中,無風險利率與企業資ak--勞動比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國債利率越高,企業投入資本的價格越高,因此國債利率與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是負相關的。
(7)被解釋變量(資本-勞動比)的一階滯后值在GMM估計結果(5)中,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了由于慣性或部分調整,企業對資本勞動的配置決策一定程度上會取決于過去行為,即企業當年的資本勞動比受企業過去的資本勞動比狀況的影響。其中,資本勞動比率的一階滯后值的系數為正,說明企業前一年的資本勞動比率對企業當年的資本勞動比率有正向影響;而企業資本勞動比率的二階滯后值的系數為負,這可能與企業連續兩年提高了資本勞動比,則第三年會考慮不再提高企業的資本勞動比有關。
2、穩健性檢驗:異質性企業
(1)不同所有制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與政府的財政支出偏向的關系。本文引入國有企業虛擬變量(SOE),如果企業實際控制人是國家,則國有企業虛擬變量(SOE)為1,否則為0,進行了分類回歸,研究不同所有制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與財政支出偏向的關系。結果如表3所示:
在非國有企業中,政府的財政支出的偏向與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的系數為0.428,兩者并不顯著相關。而在國有企業中政府的財政性支出的偏向與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的系數為1.147,兩者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財政支出偏向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的影響有較大的差別,若財政支出比原來偏向生產性支出,那么國有企業偏向于資本性的投入,用資本去替代勞動,資本勞動比率會提高。
(2)不同地域的企業資產一勞動比率與政府的財政支出偏向的關系。本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對我國31省進行了分類回歸。其中,東部11省,中部8省,西部12省。由于篇幅有限,僅列示部分結果。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東部地區,政府的財政性支出的偏向與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的系數為0.895,兩者在10%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在中部地區中,政府的財政支出的偏向與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的系數為1.858,兩者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而在西部地區,政府的財政支出的偏向與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的系數為0.835,兩者在10%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但是東部和中部的系數比西部要大,所以財政性支出偏向對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的影響更大。
這說明了財政支出偏向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的影響與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東部、中部地區,市場化水平高、第二和第三產業較為集中、自然環境、氣候、交通、教育等優越條件,使得當政府增加生產性支出以提高更好地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時,其外部性作用會大大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并且政府為了促進產業改革對企業的生產性補貼,進一步促進企業使用資本替代勞動進行生產。在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單一,企業數量少,投資項目少,在政府繼續提高生產性支出增加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時,由于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低等,使得企業缺少投資去購買固定資產等來提高生產率,并且處于內陸,生產需求不高以及勞動力較為廉價,企業沒有動力去提高資本勞動比。
五、研究結論
關于財政支出偏向的研究,學者大多基于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考察財政支出偏向,很少去研究政府的這種生產性支出偏向對微觀主體的直接影響。本文關于財政支出偏向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的影響的研究則彌補了學者對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文選取2007年到2014年中國31個省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通過建立OLS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模型,研究財政支出偏向(科教文衛支出與生產性支出之比)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財政支出偏向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率均顯著負相關。即政府偏向生產性支出降低,則企業資本勞動比率上升,企業會使用資本替代勞動。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發現:財政支出偏向對國有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有顯著的負影響,對非國有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的影響不顯著;而不同地域的財政支出偏向對企業資本勞動比的影響不同,東部和中部地區財政支出偏向和企業資本勞動比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西部地區則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
財政生產性支出偏向會導致企業用資本替代勞動,每個微觀企業都如此作為的話,放大到宏觀經濟來看會導致失業問題。同時,產業升級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勞動素質,但當前中國的勞動素質提升令人擔憂(陸銘,2016[陸銘——《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財政支出對科教文衛投入相對不足,使我國勞動力素質不高,阻礙了人力資本積累推動技術創新,長期來看降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因此本文將在財政支出偏向于企業資本勞動比率關系的基礎上,研究對企業長遠發展的影響以及上升到宏觀角度去分析對經濟社會發展所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