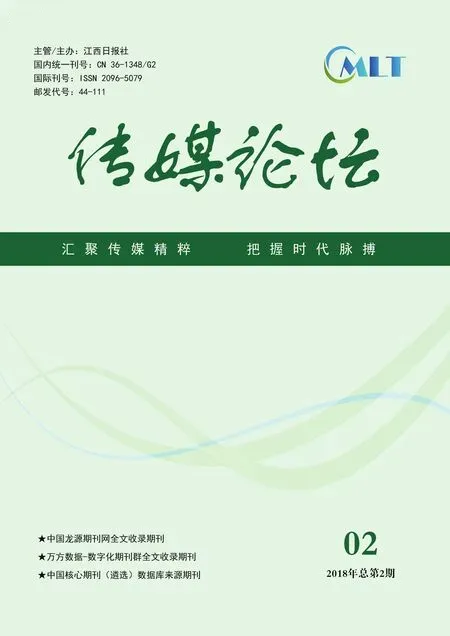從技術(shù)干預角度看不確定性回避理論在影視鏡頭中的體現(xiàn)
彭 娜 程 敏
(四川傳媒學院,四川 成都 611745)
霍夫斯泰德認為,通過技術(shù)對抗未知環(huán)境對預期結(jié)局具有邏輯關(guān)聯(lián)性。這種干預不確定因素的行為屬于文化范疇,能夠體現(xiàn)某一特定文化群體的價值取向。是否選擇技術(shù)干預要取決于個體對于外界壓力的敏感度。不確定性回避意識強的文化中,個體對于未知環(huán)境呈現(xiàn)明顯的陌生或恐懼感,難以包容不可預知的事物;而不確定性回避意識較弱的文化中,個體對于未知環(huán)境陌生感弱,好奇心強,容易接納不可預知的未來。
一、特寫鏡頭下中國英雄的技術(shù)干預
《集結(jié)號》在抗美援朝的敘事中描述了英雄合理運用象征符號來對抗不確定局面的場景。象征符號是被某個文化群體所共識并具有一定復雜內(nèi)涵的語言、圖像、手勢、工具或物體。在朝鮮戰(zhàn)場上,我志愿軍身著敵軍制服執(zhí)行任務時偶遇美國坦克兵,實力懸殊的情況下,英雄決定利用亞洲人外形及語言的相似性蒙混過關(guān)。在特寫鏡頭①中,谷子地模仿美軍盟友李承晚的手下敷衍敵軍:“前轱轆不轉(zhuǎn)后轱轆轉(zhuǎn)思密達”。英雄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了朝鮮語音特點,結(jié)合自己的發(fā)音語調(diào)進行語言特征模仿,從而偽造了自己的身份。
隨著敵人的近距離接觸,谷子地強烈意識到身份被揭穿的可能性,于是他改變干預方式,在鏡頭②中,谷子地答非所問,往腳下一指:“他踩著地雷了思密達”。英雄再次利用技術(shù)手段干預未知環(huán)境,通過工具的殺傷力威懾敵人,從而轉(zhuǎn)移了美軍的注意力。
根據(jù)文化維度理論,在不確定性回避傾向較高的文化中,個體對于未知事物容易產(chǎn)生恐懼感,對威脅或死亡的感知能力較強。因此谷子地制止了戰(zhàn)友們與敵人硬拼的打算,借助環(huán)境條件采取巧妙技術(shù)干預行為:利用服裝、語言、手勢、工具等象征符號蒙蔽了不懂朝鮮語的美國士兵。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技術(shù)手段是用來幫助當事人對抗未知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了短期的可預見性。
二、特寫鏡頭下美國英雄的技術(shù)干預
《血戰(zhàn)鋼鋸嶺》中,多斯堅持“勿殺生”的信仰拒不使用武器。他誤入日軍地道后與一名日軍傷員迎面相遇,而特寫鏡頭③放大了多斯警惕的目光,對視幾秒后多斯決定為敵人療傷。他不僅舉起針管安慰敵人“Morphine,it’s good(嗎啡,好東西)”,甚至還對瞠目結(jié)舌的敵人咧嘴笑。從不確定性回避的維度來看,英雄對于未知環(huán)境的威脅感知力不明顯,甚至對敵人流露出強烈的包容心與好奇意識。在難以預知的敵營中,對窮兇極惡的日軍施以援手的行為容易導致任務全盤失敗,甚至犧牲長遠利益。然而,多斯對于敵人的威脅并未采取積極的抵制行為,更傾向于選擇相信對方。
懷著同樣的信念,多斯在營救美軍中士的過程中拒不使用武器自衛(wèi)。特寫鏡頭④捕捉到多斯僅有的一次舉槍動作,然而其目的并非抵抗敵人而只是輔助救援。他用槍裹住擔架布拉著中士狂奔十多秒,在敵軍槍林彈雨中,全靠中士用機槍掩護才得以逃脫。從不確定性回避的維度來看,英雄在受到生命威脅的時候仍然選擇依靠信仰,完成任務的過程缺乏積極的應對措施。
在以上場景中,多斯在未知環(huán)境中傾向于相信直覺,對威脅幾乎不采用任何技術(shù)干預,完成任務的方式主要依靠內(nèi)心的力量。
三、結(jié)語
根據(j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不同的社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適應不確定性。文化決定一群人的獨特性,而文化特征又可以通過英雄的個性特點來衡量。比較兩部電影中的技術(shù)干預環(huán)節(jié)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英雄對于陌生環(huán)境警覺而敏感,在關(guān)鍵場合對于不確定性因素采取了有力的干預手段,呈現(xiàn)出很強的不確定性回避意識;而美國的英雄對于模棱兩可的環(huán)境容忍力強,面對威脅的恐懼感不明顯,體現(xiàn)出較低的不確定性回避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