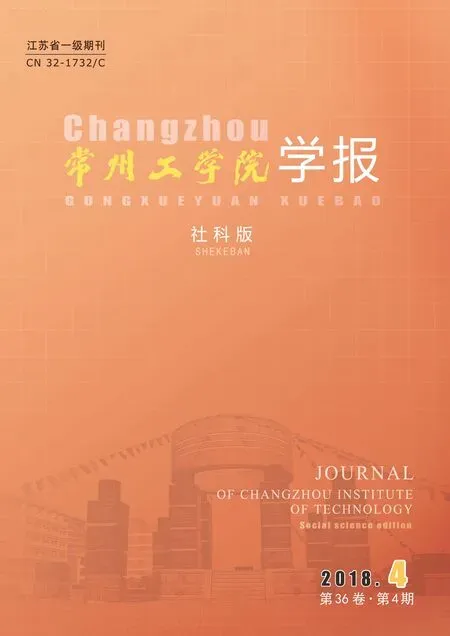劉逢祿經(jīng)學研究綜述
孫娟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401331)
劉逢祿作為清代嘉、道后興起的常州學派之首,其發(fā)揚今文之學的經(jīng)學觀念在清代學術史上不容忽視。因為“劉逢祿在許多方面都是常州今文經(jīng)學發(fā)展至頂峰的象征”,張舜徽先生在《清儒學記》中也說:“清代今文經(jīng)學到了劉逢祿對儒家諸經(jīng)有了比較全面的闈述,也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理論,劉逢祿可說是清代今文經(jīng)學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到劉逢祿,“清代經(jīng)學才有了可以與漢學相抗衡的今文經(jīng)學,并由此經(jīng)過龔自珍、魏源、王闿運、廖平、康有為等人的發(fā)展,而成為晚清最有影響的社會思潮”[1]。
近年來,劉逢祿的經(jīng)學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對劉逢祿經(jīng)學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清代常州公羊學及今文經(jīng)學的思想內涵、流變及其成就與疏失,有益于以小見大地了解清代文化背景,了解劉逢祿經(jīng)學思想的闡釋路徑,以明確當時的學術動態(tài),進而多角度地闡釋清代的價值取向與精神建構。
一、劉逢祿經(jīng)學相關研究
劉逢祿在清代經(jīng)學史上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關于他的材料十分豐富,但多與其生平資料或所屬學派相關。關于劉逢祿的專門論述還不夠詳盡,對其著述和學術思想的研究也還不夠突出,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生平考究、思想考究、學術考究及其他考究等四類,焦點也大多局限于春秋公羊學的相關領域,而缺乏對其他諸經(jīng)的關注和研究。
(一)生平考究
除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2]外,還有豐富的資料提及劉逢祿,且根據(jù)其貢獻賦予了他不同的身份:《蘇省鄉(xiāng)賢特輯(下)鄉(xiāng)賢傳略:劉逢祿》[《江蘇研究》,1935(4)]簡要介紹了劉逢祿的生平及學術;簫一山《清代通史》(中華書局,1986年)將劉逢祿與宋翔鳳、戴望并提;陳鵬鳴《劉逢祿生年及著作略考》[《史學史研究》,1996(1)]專門討論了劉氏的生平及著述;陳吉龍《常州名人》(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可以幫助人們了解重構經(jīng)學傳統(tǒng)、再塑孔子形象——讓常州學派走向全國的劉逢祿,啟示我們去發(fā)掘劉逢祿對地方的影響和貢獻;阮元《疇人傳合編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將劉逢祿、湯洽名并提;等等。不同角度的論述,合之則能展現(xiàn)劉逢祿的全貌,對于研究其著述及思想有一定啟發(fā)。但在交友考及與友人書信往來等方面缺乏整理和研究。
(二)思想考究
首先,思潮背景方面。路新生《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探究了劉逢祿的今文疑古學,提供了一條具有可行性的探究清代文化的路徑,去發(fā)掘經(jīng)學思想與疑古思潮,探析今文經(jīng)學與疑古思潮間的內在聯(lián)系。邱志誠《〈尚書〉辨?zhèn)闻c清今文經(jīng)學——〈尚書〉辨?zhèn)闻c清今文經(jīng)學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認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現(xiàn)代化轉型是以科學化為實質,可啟發(fā)思考劉逢祿經(jīng)學或史學觀念中是否有科學化傾向。蔡長林《〈從文士到經(jīng)生——考據(jù)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導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0(3)]討論考據(jù)學風,以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學派在面對考據(jù)風潮時的應對策略究竟是什么,引人深思。黃愛平《論清代乾嘉時期的經(jīng)世思潮》[《中國哲學史》,1997(4)]、張麗珠《乾、嘉、道從論學到議政的今文學發(fā)揚》[《清華中文學報》,2011(2)]討論了乾嘉時期的經(jīng)世思潮,引發(fā)思考:劉逢祿在這種經(jīng)世思潮下的具體表現(xiàn)是什么?他與其他同時代或不同時代有同種經(jīng)世精神的經(jīng)學家的不同之處有哪些?羅檢秋《從清代漢宋關系看今文經(jīng)學的興起》[《近代史研究》,2004(1)]、《嘉慶以來漢學傳統(tǒng)衍變與傳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王元琪《清代道咸時期的漢學研究》(西北大學,2007年)、武道房《從宋學到漢學:清代康、雍、乾學術風氣的潛移》[《學術月刊》,2008(10)]討論了清代的漢宋之爭,借此研究視角可以探討劉逢祿在解經(jīng)時對漢學與宋學的繼承與變異,等等。
其次,思想觀念方面。李軍《論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創(chuàng)立復興及其思想特點》[《管子學刊》,1998(2)]認為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學術思想特點表現(xiàn)在:繼承發(fā)揚西漢今文經(jīng)學的治經(jīng)傳統(tǒng),反對古文經(jīng)學只重名物訓詁的為學方法,推崇并闡發(fā)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注重利用公羊學的思想理論,以尋求糾治時弊、改良社會的方法途徑,恢復了通經(jīng)致用、明道救世的為學宗旨。上述特點在劉逢祿的經(jīng)學思想中是否全部有所體現(xiàn),劉逢祿是否存在有別于此的其他學術思想特點,可以進一步探究他在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學術特征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孫運君《再論劉逢祿的學術思想特點》[《廣西社會科學》,2004(8)]討論了劉逢祿的人生價值觀與學術理想轉變、提倡《易》《禮》《春秋》三位一體的今文經(jīng)學思想體系、兼容并蓄以全面復興今文經(jīng)學等問題,但似乎沒有涉及“《詩》《書》《春秋》其歸一也”的體系與上述提及的今文經(jīng)學思想體系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許雪濤《劉逢祿〈論語述何〉及其解經(jīng)方法》[《中國哲學史》,2005(2)]認為劉逢祿用深化主題、類比引申、斷章取義的方法將《論語》公羊化,由此而及彼,可以探討劉逢祿在解釋其他經(jīng)書時是否也有公羊化傾向,是否也采用了類似的方法解經(jīng),此方法的利弊又在何處。黃開國《劉逢祿經(jīng)學思想早晚期的變化》[《中華文化論壇》,2006(3)]認為劉逢祿早年并不完全排斥古文經(jīng)學,晚年則極力否定古文經(jīng)學,探討了這種變化是否一以貫之地體現(xiàn)在他的所有經(jīng)學著作中,這種變化的本質應歸根于何處。楊飛《清中期常州學派學術研究》(西北大學,2013年)探究了劉逢祿的學術研究方法,闡述了他的方法究竟利弊在哪,與常州學派其他人相比的特色是什么,方法分別繼承自哪里,又影響到了哪些人,等等。
(三)學術考究
其一,家學淵源方面。蔡長林《論常州學派的學術淵源——以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評論為起點》[《中國文哲研究輯刊》,2006(3)]討論了惠氏學與科舉文人、以西漢為尚的文章策略、轉向漢學家法的契機、考據(jù)風潮下的常州學派、錢穆批評的價值根源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富有創(chuàng)見的觀點。陳其泰《公羊家法與清代今文學復興之統(tǒng)緒》[《齊魯學刊》,2007(4)]也對劉逢祿的家學淵源作了具體分析。劉靜《清代常州莊氏家族家學研究》(揚州大學,2010年)、呂子遠《從墨學到學有專門:乾嘉學術“家法”觀研究》(華南師范大學,2011年)、王明德《常州學派學術譜系探論》[《求索》,2014(3)]認為常州的學術譜系是以常州莊氏家族的家傳和師承為基礎,以今文經(jīng)學治學精神為取向,以常州學者的學術傳承關系為依據(jù)的至少由四代學人所構成的學緣群體:由莊存與開其山,莊述祖?zhèn)髌鋵W,劉逢祿與宋翔鳳張其幟,龔自珍、魏源光大之等等。但多側重其外家莊氏之學,而對劉逢祿經(jīng)學思想中所受的當時漢學的(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和(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及宋學的影響等相關研究不足。對于學術淵源在具體經(jīng)學文本間的異同的分析也存在不足。
其二,常州區(qū)域方面。艾爾曼、車行健《學海堂與今文經(jīng)學在廣州的興起》[《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指出阮元創(chuàng)設的學海堂兼容漢宋古今的學風,探究了這一多元的教育機構的出現(xiàn)與清代經(jīng)今文學的關系,由此衍及關于私塾在家族學術、地方文化等學術傳統(tǒng)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等的相關思考;徐立望《嘉道之際揚州常州區(qū)域文化比較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探究了常州地區(qū)的文化特征、文風、文化成就與產(chǎn)生原因,并討論了以莊有可和莊述祖為代表的莊氏之學的分向,還列專節(jié)論述了作為保守的經(jīng)世者的劉逢祿;申屠爐明《清代常州學派的名義及范圍》[《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1(5)]認為常州學派當以學術宗旨為判別標準,并非同一地的學者都可歸入一派;邵鵬宇《學緣、血緣與地緣——以常州學派為中心的學術史、家族史與地域史的考察》(華東師范大學,2015年)討論了常州學派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源流關系、學人的家族背景關系、學派產(chǎn)生原因和常州地區(qū)文風鼎盛的地域特征之間的關系;等等。
其三,今文經(jīng)學方面。吳義雄《清代中葉今文經(jīng)學派學術思想論略》[《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2)]認為清代今文經(jīng)學在政治哲學和學術思想兩方面對古文經(jīng)學展開了激烈攻擊,而且由于時代變遷,與漢代的今文經(jīng)學有著明顯的區(qū)別;丁原明《清代今文經(jīng)學淺論》[《山東社會科學》,1995(6)]也討論了脫胎于西漢今文經(jīng)學,曾一度受到重視和提倡,并被某些有識之士作為變革中國近代社會的工具的清代今文經(jīng)學;湯仁澤《清代今文經(jīng)學諸問題:兼論莊存與和今文學派》[《學術月刊》,2002(2)]認為莊存與是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開創(chuàng)者,至劉逢祿而奠基,此后龔自珍、魏源也予以發(fā)揚,到了康有為更運用“三統(tǒng)”“三世”學說演發(fā)維新理論,他強調這“三世”進化思想來自今文經(jīng)說,而非源自西方進化論,可由此延伸,討論劉逢祿等人對于經(jīng)學與科學間關系的態(tài)度;黃開國《清代今文經(jīng)學發(fā)展階段略論》[《哲學研究》,2013(11)]認為用“照著說”和“接著說”來區(qū)分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發(fā)展階段,更能準確地說明其中不同階段的特點,劉逢祿被劃入前者,“重大義的照著講”與“重微言的照著講”的本質區(qū)別在哪里,“照著講”和“接著講”有無本質區(qū)別。此外,黃愛平《劉逢祿與清代今文經(jīng)學》[《清史研究》,1995(1)]、康宇《論清代常州學派對今文經(jīng)學的復興:以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為中心》[《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等,強調了劉逢祿對今文經(jīng)學的復興作用;等等。
其四,后世影響方面。許家遠《開一代新學風的常州公羊學派》(曲阜師范大學,2000年)分析了莊、劉等在興起常州學派并進而轉變時代學風等方面的作用;董鐵松《論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歷史作用》[《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認為今文經(jīng)學作為政治、社會解經(jīng)形態(tài),作為具有現(xiàn)實政治指向的政治儒學,復興于晚清,首先是學術主體憂患,即經(jīng)世意識的寄托,其傳播流布對士林的政治主動性和經(jīng)世學風提供支持,并具有啟示和導向作用,其所具有的疑古精神成為分裂和瓦解經(jīng)學傳統(tǒng)的一個助力,尤其是其從學術向政治的跨躍及其發(fā)揮的批判現(xiàn)實政治、榫接西學的作用,更標志著其歷史轉折時期的真理地位;陳福濱《清代公羊學與晚清的變革》[《哲學與文化》,2005(11)]認為它的復興,使得批判性行動和內在道德結合,為批判政治社會環(huán)境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合法性基礎,認為劉逢祿他們把握了由傳統(tǒng)向近代社會轉化的時代精神,提供了經(jīng)世致用與社會改革的新思維;湯志鈞《從莊、劉到龔、魏:晚清啟蒙思想生發(fā)之軌跡》[《學術月刊》,2007(5)]認為莊、劉的“經(jīng)世”之念和所傳授的今文經(jīng)學中的變易思想深深影響了龔、魏,龔、魏啟蒙思想的生發(fā),是與莊、劉有著密切的承繼關系的;武少民《百年清學研究九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除解釋各種學術思潮和學派興衰的內在關系外,還說明了對學風的影響,比如形成樸學派之考據(jù)與常州派之經(jīng)學雙峰對峙局面;等等。
(四)其他考究
其一,詩詞文書等其他作品。詩:錢鐘聯(lián)《清詩紀事(三)》(鳳凰出版社,2004年)提及劉逢祿;《常州三羊詩選》(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8年)有一首當代所作的《詠劉逢祿》。詞:李璉生評注《蝶戀花》(四川文藝出版社,1998年)、錢璱之《劉逢祿題畫詞評析——清代常州詞評析之七》[《常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3)]、朱惠國《論“常州學派”與“常州詞派”之關系》[《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十一輯)》,2003年]在論述常州詞時旁及了劉逢祿;孫克強、楊傳慶、裴哲編著的《清人詞話(中)》(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也提及了劉逢祿;等等。文:傅璇琮總主編《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明清卷》(《清華古典文獻研究叢刊》,2009年)、張舜徽著《清人文集別錄》(中華書局,1963年)皆收錄了劉逢祿的文集。書法:葉鵬飛、潘茂編著《常州書畫》(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評劉逢祿《琵琶仙詞稿》行書“字體雋逸、詞作優(yōu)美”,等等。
其二,其他切入點。文學:楊旭輝《清代今古文經(jīng)學的更迭與文學嬗變》(蘇州大學,2002年)以清代常州文人群體為例,通過學術史上今古文經(jīng)學的消長興替來考索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想傳承與演變中的近代化進程,進而研究文學在這一過程中的流變、發(fā)展軌跡;譚坤《論清代常州今文經(jīng)學與文學的交融對人文精神的影響》[《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09(4)]討論了清代常州今文經(jīng)學的價值理念,常州今文經(jīng)學與文學的交融,最后論及今文經(jīng)學對當代人文精神在崇文重教、經(jīng)世致用、兼容并蓄、開拓創(chuàng)新方面的啟示;馬子堯《論常州詞派的起源與常州經(jīng)學之關系》(山東大學,2011年)梳理了乾嘉年間常州經(jīng)學的脈絡,探討了常州詞派的美學追求及其獨立品格。詮釋學:柳宏《清代〈論語〉詮釋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認為劉逢祿視域獨特、獨領新風;劉偉《王魯例:劉逢祿對經(jīng)學詮釋范式的新創(chuàng)立》(蘇州大學,2008年)也從詮釋學角度切入,可作為一種方法為劉逢祿《尚書》學研究提供借鑒;等等。
由上述學術成果可見,劉逢祿經(jīng)學研究雖取得了不少進展,但仍存在許多可以開拓的空間,包括《易》《書》《詩》《禮》《春秋》五經(jīng)及六書小學等皆值得深入探究和挖掘。在研究時,有許多前人成果可供借鑒。以劉逢祿《尚書》學研究為例,雖無《尚書》學的專門研究,但無論關于劉逢祿的生平考究、思想考究,還是關于家學、學派及后世影響等其他研究,皆可以為研究劉逢祿《尚書》學著述提供視角與方法。
二、新領域:以劉逢祿《尚書》學研究為例
地位顯赫、影響深遠的經(jīng)學大師劉逢祿,其《尚書》學著作卻備受爭議。劉起釪《尚書學史》中批評“他的《尚書今古文集解》達三十卷之多,務申今文說,雖《清史稿》有著錄并收入《續(xù)清經(jīng)解》中,然全書讀之了無精義”[3]。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評劉逢祿多述莊述祖之說解《尚書》,雖“不補《舜典》、不信《逸書》,所見甚卓,在江、孫、王諸家之上”,但其余多臆說不可據(jù),存在“自謂非敢蹈宋人改經(jīng)故轍,而明明蹈其故轍矣”“求新而近鑿”“與今文古文皆不合”“橫暴先儒,任意武斷”“其實莊氏所自矜創(chuàng)獲,皆陰襲宋儒之余唾,而顯背漢儒之古訓”等諸多問題[4]。但譚獻在《復堂日記》中說自己于同治二年讀莊存與《尚書既見》《春秋正辭》、劉逢祿《書序述聞》,服膺莊氏家學而喟嘆“國朝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莊氏一家,皆第一流”。且稱“劉申受《書序述聞》,說《尚書》精深,源于宗伯公。吾故謂莊氏家學精于惠、大于王矣”。他在《復堂日記》中道出了常州學派通經(jīng)致用的為學宗旨——“經(jīng)學皆非空言,可以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國故隱寓其中”。
劉逢祿的《尚書》學究竟有無精義與創(chuàng)獲?在他所建立的以春秋公羊學為中心、囊括五經(jīng)的今文經(jīng)學體系中扮演并發(fā)揮著怎樣的角色和作用?研究劉逢祿的《尚書今古文集解》和《書序述聞》,可全面了解劉逢祿的《尚書》學及其經(jīng)學思想,并由此展開對其《尚書》學在清代常州學派及今文經(jīng)學甚至清代《尚書》學中的地位、影響等問題的討論,從而管窺《尚書》學研究在這一時期的概貌。對劉逢祿《尚書》學的研究,無論是從詳析清代《尚書》學之宏觀發(fā)展出發(fā),還是從厘清劉逢祿《尚書》學思想及經(jīng)學體系考慮,皆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關于劉逢祿《尚書》學研究并無一篇學術論文,遑論專著與碩博論文,僅有其他研究中旁及劉逢祿的《尚書》學。《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jīng)部》(中華書局,1993年)中有《尚書今古文集解》的提要,江翰評論:“是書多本其外王父莊存與之說。雖博采諸家,實有擇焉不精之憾,如‘岳曰:否德忝帝位’一條、‘象以典刑’一條、‘侯以撻之’以下八句等,然其書固非無可取者,如云‘孟子引父母使舜完廩’諸文等等,清代考據(jù)盛行,說《尚書》者于《孔傳》《蔡傳》往往棄若土苴。甚有陰用其說而沒其名者。茲編不惟多取《孔傳》,亦間采《蔡傳》,可謂無門戶之見矣。卷末附《書序》,則罕所發(fā)明,蓋以已有《書序述聞》,別為一書故也。”此外,還有《書序述聞》的提要,江翰曰:“是編題曰‘述聞’者,蓋述其聞于其外王父莊存與者也。間附己意,則曰‘謹案’以別之。存與治經(jīng)主知人論世,而不為名物訓詁之學,往往喜立新說,多不可據(jù)。如書中謂《微子》篇刻子當為亥子,言紂禍當亥子之辰也。”又說:“存與說經(jīng)重在大義,于此可略見其端。莊劉一派,所以有異于同時考據(jù)諸儒者,實浸淫于宋學,特諱言之耳。”[5]闡明了劉逢祿的《尚書》學淵源中莊氏家學的重要地位,但其他淵源則罕有論及。江翰表明了自己對兩書的評價,認為各有可取亦各有疏失之處。其立論例證過簡,是否得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和商榷。此外,其余論述皆是旁及。
劉起釪將清代《尚書》學梳理為七部分:一為清初余波的《尚書》學,如王夫之《書經(jīng)稗疏》《尚書引義》、臧琳《尚書集解》與納蘭氏《通志堂經(jīng)解》等;二為完成疑辨,推翻偽古文,如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三為迷戀偽古文者的徒勞反抗,如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四為清學主力對《今文尚書》的研究整理與清代一般《尚書》著作,如吳派有惠棟門生江聲的《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尚書后案》、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皖派有戴震《尚書義考》《尚書今文古文考》和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王念孫和王引之父子《經(jīng)義述聞》,其他一般著作如牟庭、黃式三、戴鈞衡等人作品……六為清代后期今文學派的《尚書》研究,如莊存與《尚書既見》《尚書說》、莊述祖《尚書今古文考證》《尚書記》、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書序述聞》、宋翔鳳《尚書略說》《尚書譜》、魏源《書古微》等等;七為清末開始的近代《尚書》學。身為“今文學”運動之一員的梁啟超[6]則認為可大致分為兩期,“在前半期為‘考證學’,在后半期為‘今文學’”[7],雖有夸大以劉逢祿為“不祧之祖”的清代今文經(jīng)學之嫌,但也簡潔清晰地標明了清學之分期,對后世研究不無啟發(fā)。
張文穆《尚書今古文篇目表評釋》(民國版影印本,1948年)論及劉逢祿所說逸十六篇或系劉歆輩增竄說之可能;李開、劉冠才編著《晚清學術簡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討論了龔自珍的今文經(jīng)學思想,認為在師承劉逢祿之前,發(fā)揮《公羊》“三世”說,在師承劉逢祿之后,發(fā)揮《公羊》和《尚書·洪范》歷史進化說,凸顯了劉逢祿在今文經(jīng)學思想方面對龔自珍的重要影響,雖涉及《尚書》但并未完全展開,且論述的主體為龔自珍而非劉逢祿;楊運康《今文〈周書〉注釋商榷九則——兼與〈漢語大詞典〉商榷》[《漢字文化》,2014(6)]選取了民養(yǎng)、節(jié)性、耽樂、純佑、慼言、簡代、謀猷、陰鷙、盡傷9個復音詞,結合歷代《周書》注釋及具體語言環(huán)境所凸顯出的詞義進行具體分析,試圖彌補歷代今文《周書》注釋及《漢語大詞典》解釋的一些不足之處,文中提及劉逢祿,并認為他與孔安國、孔穎達、蔡沈、段玉裁、孫星衍、皮錫瑞、顧頡剛、劉起釪、錢宗武等一道,都是《周書》注釋史上的著名學者,但在闡釋中并未就劉逢祿對今文《周書》的解釋作具體分析。
劉德州《清代〈尚書〉學蠡探——今文經(jīng)學背景下的〈尚書〉學研究》(南開大學,2011年)將清代今文經(jīng)學中《尚書》“微言大義”之學的特點歸納為三點:一為以公羊學為根底,二為富有致用精神,三為旁參宋學。論及此一家學乃莊存與“開風氣之先”,莊述祖、劉逢祿借《書序》闡發(fā)“微言大義”(并具體討論了他們重視《書序》的傳統(tǒng)、對《書序》的編排次序與“筆法”的解說、諸經(jīng)互相發(fā)明、議論《書》中史事等),魏源《書古微》乃莊劉學術之流裔等等,但這是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清代《尚書》學和清代經(jīng)文經(jīng)學,對劉逢祿《尚書》學著述本身的發(fā)掘還不夠。劉德州《常州學派與〈尚書〉之“微言大義”》[《天津社會科學》,2013(4)]認為常州諸子治《尚書》不僅有公羊學的影子,還受到宋學的影響,他們通過議論《尚書》中的史事、諸經(jīng)互相發(fā)明、解說圣人筆法、旁參宋學等方式,對《尚書》做了全新的解讀,其宗旨皆在闡發(fā)“微言大義”,這是劉德州在自己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但對劉逢祿《尚書》學的研究還有不足之處,仍有進一步發(fā)展的空間。
研究清代《尚書》學可以具體而微、由小見大地了解清代文化背景和其思想之闡釋路徑以明確當時的學術動態(tài),可以多角度地闡釋清代的價值取向與精神構建;研究劉逢祿的《尚書》學,則又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清代常州公羊學及今文經(jīng)學的思想內涵、流變及其成就與疏失(因為“劉逢祿可說是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奠基者”[8])。《尚書今古文集解》與《書序述聞》作為上述兩系統(tǒng)的交叉焦點之一,應當引起當下學人的重視與關注,而其相關的整理與研究不失為一個可行性較高的切入點。首先,需要關注劉逢祿《尚書》學與今文經(jīng)學之間的關系,重視他在清代今文經(jīng)學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其次,可由征引各家的頻率和引書的主要特征,發(fā)掘劉逢祿治學的學術傾向。最后,需要關注劉逢祿治《尚書》的經(jīng)學觀念。在關注《尚書》學思想本身的同時,也需要挖掘《尚書》學特色觀念與治經(jīng)(貫通五經(jīng))整體思想之間的聯(lián)系。通過經(jīng)學觀念的申發(fā),可以提煉劉逢祿乃至常州學派的精神氣脈。
一言以蔽之,劉逢祿經(jīng)學研究可謂剛剛起步,還有待大力探析和發(fā)掘。以《尚書》為觀察的切入點,貫通劉逢祿各經(jīng)的相關主張,可以窺探經(jīng)學與政治,或者說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之間的摩擦更形顯著。研究劉逢祿的經(jīng)學,有益于學術研究的資料整理與成果發(fā)現(xiàn),對整個經(jīng)學的橫向和縱向(共時與歷時)的深入探究亦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