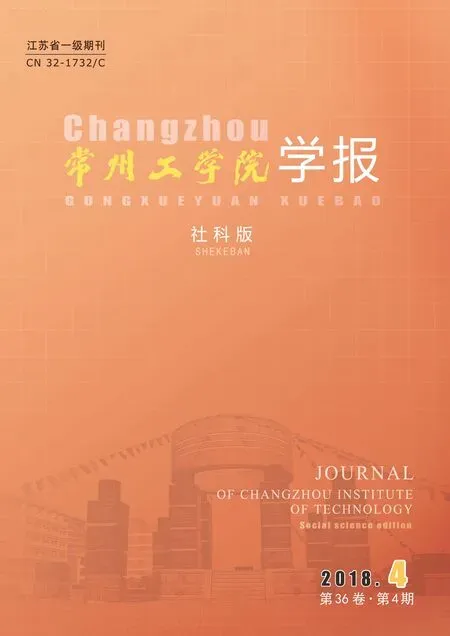殖民—后殖民批評視角下琴凱德的《一個小地方》
邵敏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97)
雅買加·琴凱德(Jamaica Kincaid,1949— )生于安提瓜的圣約翰,后移居美國,是加勒比海女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員。她創作頗豐,作品自傳性強,獲獎無數。作品有短篇小說集《河底》(AttheBottomoftheRiver,1983),長篇小說《露西》(Lucy,1990)、《我母親的自傳》(TheAutobiographyofMyMother,1996)、《波特先生》(Mr.Potter,2002)、《那瞧現在》(SeeNowThen,2013)和非小說《一個小地方》(ASmallPlace,1983,一譯《彈丸之地》)、《弟弟》(MyBrother,1997)、《我的園藝書》(MyGardenBook,2001),還有大量未結集出版的短篇故事和散文作品。
琴凱德在園藝方面亦頗有造詣。“在學校,她最喜歡的是歷史和植物學……這兩個興趣對她的寫作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她的小說和非小說作品,持續地關注如何書寫加勒比地區在奴隸制和殖民主義下的歷史;另一方面,植物學的話題也頻繁地出現在她的寫作中,且自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她便一直在書寫植物學、園藝以及二者與殖民主義、帝國的關系。”[1]3-4在《一個小地方》這部長篇散文中,琴凱德借助景觀描寫,思考安提瓜的過去,展望安提瓜的未來,在“憤怒”中表現出她對殖民—后殖民的認知與態度,以及對國家及自我身份的探尋。
一、“失樂園”:安提瓜的歷史
安提瓜位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恰如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小地方,一座小島,寬9英里,長12英里。1493年,哥倫布發現了這座小島后,便以西班牙塞維利亞安提瓜教堂的名字來命名這塊彈丸之地,并將它拉入了被殖民的歷史長河之中。隨后不久,安提瓜被歐洲殖民者占領了。“這些歐洲人讓非洲人做奴隸,以滿足他們對財富和權力的渴求。”[2]801520—1629年,安提瓜先后遭到西班牙和法國殖民者的入侵;1632年,安提瓜被英國占領;1667年的《布雷達條約》使安提瓜成為英國殖民地;1981年安提瓜宣布獨立,加入英聯邦。哥倫布發現了安提瓜之后,不斷地給安提瓜的事物命名。
其實,對于生活在那兒的當地人來說,這塊土地并不是天堂,因為他們還處于一種較為原始的生活狀態。哥倫布眼里的“天堂”,在當地人眼中只是一塊平常無奇的棲居地。不過,因為安提瓜填補了哥倫布的認知空白,它勾起了哥倫布強烈的好奇心,所以他將自己的到來和命名的時刻視為安提瓜歷史的開端。“這兒有我之前從未見過的東西,我特別喜歡它,因為它沒有先例;但正因為它沒有先例,又使得它令人感到害怕。因此,為了減少害怕,我將以我所知來建造它。我知道一座教堂和它的名字,即使我不喜歡、不知道與這座教堂相關的人,但相對于我腳下的這片土地,我對這座教堂更為熟悉;我腳下的土地改變了,而在我腦海中的教堂卻依舊。”[3]622-623哥倫布既是發現新大陸的探險家,也是殖民者的引路人。他是安提瓜殖民歷史的第一個書寫者。
事實上,安提瓜變為“失樂園”之日即是歐洲白人殖民歷史開啟之時。哥倫布的命名法也為多年后的英國殖民者所效仿,“他們去過的每個地方,都被轉變成英國的地方;他們遇到的每個人,都被轉變成英國人。但是沒有哪個地方能夠真正成為英國的地方,沒有哪個看起來不像英國人的人將成為英國人,所以你能夠想象這些轉變對當地的人和土地的破壞”[2]24。安提瓜曾經的文明和歷史被英國殖民者通過命名而改寫。這一改寫的過程既是扭曲和清除安提瓜歷史的過程,更是殖民化的過程。對此,琴凱德指出:那些她所熟知的安提瓜的街道多是以英國海事罪犯的名字來命名的。通過命名街道,英國殖民者為安提瓜人建造了一個“新英國”,以便于其管理和統治。而那些“罪犯”其實是英國歷史上拓展海上霸業的“英雄”,以之命名實為對英國殖民歷史的頌揚。
在《回到源頭》中,非洲杰出的民族運動領袖之一阿米爾卡·卡布拉爾曾指出:殖民主義者通常會講,是他們把殖民地人民帶進了歷史,但事實并非如此,恰恰是殖民主義者使殖民地人民離開了歷史——他們自己民族的歷史。殖民者往往把殖民地民族描繪成低等、幼稚和軟弱的民族,認為他們沒有能力進行自我管理,需要西方對其加以管理以維護其利益。對此,琴凱德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即使我原先像猴子一樣生活在樹上,也比遇見你們之后,遭遇這些屈辱的事和變成殖民地的奴隸要好。”[2]37殖民者為了實現自己的霸權統治,以文明人的姿態,用看似正當的理由來改寫殖民地的歷史,同時又迫使殖民地人民忘卻歷史,遺忘身份,從主人變為奴隸,墜入黑暗窮苦的“失樂園”。
正如王岳川在《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人的視界是由其現實處境構成的,人們所能看到的事物是處于發展和游移的動態過程中的,所以我們很難找到一種超驗的理論去完全客觀地闡釋歷史,并且歷史也不再是客觀的、透明的、統一的事實對象,而是有待意義填充的話語對象。就此而言,安提瓜的歷史就是這個“失樂園”的屈辱史,是西方殖民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和統治的需要而重寫的歷史,也是殖民者借助命名和話語特權建立起來的歷史。而這被改寫的歷史,不僅使殖民地被迫依附于宗主國,丟掉自己的真實歷史,還給殖民地人民烙上了奴隸印記。
二、安提瓜國家身份的缺失
殖民時期,英國殖民者重寫了安提瓜的歷史,殖民因素滲透到當地的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獨立之后,殖民統治的影響依舊存在于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很長一段時間,安提瓜的國家身份是不完整的,因為它的獨立在本質上僅僅代表一個開端,是從直接統治到間接統治、從殖民統治到非完全獨立的轉變。
經濟方面,安提瓜的自然資源有限,其地理位置不利于發展農業和重工業。甘蔗種植是它主要的經濟來源。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旅游業以及由此帶動的服務業成了半數以上安提瓜人的從業方向。歐洲、北美的游客將安提瓜看作天堂,在此享受度假的愜意與歡愉;而當地人卻無暇欣賞美景,不能踏足觀光海岸,他們替游客開出租,被迫從事服務業。旅游業產生了一定的經濟效益,可并沒有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島上的旅游產業大都被外國人控制著,被企圖謀取私利的投資者支配著;二是為了發展旅游業,政府投重金“修復機場、道路和港口,以此提高安提瓜的形象。但這些方面投入的成本,并未能在改善居民的貧困狀況方面取得相應的回報。也就是說,沒有其他的主導行業,單憑旅游業來使當地人獲益是不可取的”[4]79,即政府進行修繕其實未曾考慮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旅游業和服務業近似于一種變相的殖民,是當地為發展經濟而依附于大國的表現。被稱為非洲“依附理論”代表人物的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曾指出,外圍國家談不上有完整的民族經濟。在安提瓜,市場上可以獲利的買賣全都被政府官員控制,經濟是被壟斷的,商品無法按照市場規則自由流通。這些政府官員與大國合作,允許這些大國在當地發展一些可以謀利的產業,而官員在謀求利益的同時,也間接促進了這些大國經濟的發展。
政治方面,一方面,經濟上的依附性使得安提瓜在政治上也受英國的控制,成為英聯邦的成員國之一。另一方面,雖然前殖民者離開了歷史的舞臺,但其金錢觀與利益觀依舊影響著當地的政府和統治者。琴凱德在這部作品中指出,錢財和權力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容易滋生腐敗現象,如文中提及,一個政府高官因批準某家特殊的化工廠的建立而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賄賂。這些人不僅腐敗,還無視人民的利益:政府壟斷貿易,首相與部長通過非法手段積累資本,統治者實行獨裁專制,軍隊戰斗力較弱,而軍隊人員卻能胡亂射殺無辜百姓,道路和大樓只在女王或公主來訪時才進行修繕,醫院的醫生不夠專業還歧視黑人……“你可曾想過,為什么我們從你那兒學到的,似乎只是如何腐敗和如何成為暴君?……你帶走不屬于你的東西,并且你甚至都不會假裝先問一下。”[2]34-35因而,安提瓜獨立之后,統治者在某種程度上模仿前殖民者的剝削與壓迫方式,在謀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間接地替后殖民者謀利。這種獨立似乎促成了某種權力的轉移,但權力并非轉交給了新建立起來的主權國家的人民,而是轉交給了當地的精英階層,并由這一階層繼承了軍隊、警察、司法、行政等整套殖民體系。就此來看,安提瓜并未完全獲得政治獨立。
文化方面,后殖民者的文化一直在滲入,當地的年輕人深受影響,他們對北美文化的熟悉程度勝于對本土文化的認知。本地的文化事業得不到發展,體育部、文化部、教育部的部長由同一個人擔任,而文化部名存實亡。前殖民者建立的圖書館就是一個具有諷刺性的建筑,自1974年在地震中損壞后,至今仍未進行修繕。雖然圖書館是殖民時期的建筑物,但它是知識和教育的象征。舊圖書館的修繕工作未受重視,新圖書館則坐落在一棟衰老且破舊的大樓的頂部,這足以看出安提瓜在創建自己國家的圖書館、構建反殖民主義的價值觀時很不積極。而這一現象,也間接地反映出當地政府對文化教育的不重視。
不容忽視的是,殖民者對安提瓜事物的命名,不僅僅是改寫歷史的一種方式,還是一種文化上的暴力、占用和“解轄域化”,正如愛爾蘭戲劇家布賴恩·弗里爾在《翻譯》(1981)中提及的那樣,“對風景山水的地理特征進行命名和重新命名也是一種權力和占用行為”[5]144。在傳統的觀念中,復制品往往略遜一籌,但在殖民主義者看來,殖民復制品比當地的原始存在更加強大,他們可以借之貶低當地文化,甚至聲稱這種復制品將糾正當地文化中的缺陷。殖民化最初的行動便是通過命名、教育等途徑,將殖民地有意義的書面、口頭形式的文本翻譯成殖民者的語言,這也是對殖民地文化及當地人民進行統治、施控和施暴的過程。因此,殖民者在將本國的文化植入殖民地后,往往會對殖民地的文化產生持久的影響,從而削弱了殖民地自身的文化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殖民地的身份特征。
“國家如同一個巨大的公司,國家的公民別無選擇地歸屬于它,就這樣,國家變成了一個真空地帶,潛在的各種形式的認同都可以填充進來,比如種族、宗教、語言、文化、歷史和土地。”[5]61安提瓜雖宣布獨立,組建了自己的國家,但前殖民的影響深深地植根于其政治、文化、經濟之中,而后殖民的因素也影響甚至制約著其經濟的發展,這就使它失去了真正的獨立與自主,從而喪失了完整的國家身份。
三、安提瓜人身份的缺失
在被殖民的過程中,當地人變成了“他者”,遭到殖民者的取笑、唾棄,甚至奴役。更可悲的是,他們自身也內化了這種觀點,認為自己就是低人一等的“他者”。正如被販賣至安提瓜的黑人奴隸那樣,他們是像成捆的棉花和成袋的糖那樣的“物資”,而殖民者則是居高臨下的、殘酷的資本家。殖民地人民在潛意識中將自己視為可以流通的商品,他們真正的身份缺失了。
此外,現代安提瓜人一方面意識到自己的祖先曾被奴役,無法原諒殖民者,無法忘卻那段屈辱的歷史,但另一方面,他們卻自視為“好仆人”,認為自己處于無法逆轉的弱勢地位,任由殖民者及后來的統治者壓迫。他們被動,逆來順受,“這個小地方的人任由各事件發生,這些事件壓在他們身上,讓他們無法呼吸和思考……他們也不會主動去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而是任由其發展。”[2]52-53。他們不會主動地選擇或拒絕,對自己的意志和內心想法缺少認知。他們麻木,無法確切地感知和判斷時間,“這個小地方的人并不把時間分成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們不會未雨綢繆,而是走一步算一步,沒有遠見”[2]54。也就是說,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規劃。他們無知,看不到奴隸制、解放和現實之間的矛盾,看不到自己正在被一群腐敗的人統治著,或是被這群腐敗的人拱手讓給腐敗的外國人統治著,也看不到自己對國家、社會乃至自身所應承擔的責任。因而,書中所描寫的這種“他者”形象除了與商品相近外,還處于一種不安的狀態,這種狀況緣于借教育引入的殖民文化與本地的文化之間的矛盾。
由此可見,在殖民化的過程中,西方借助經濟手段、文化及話語霸權,使殖民地人民變成“他者”。為此,“從后殖民理論中生成了一系列相關的理論問題:力圖理解歐洲開拓殖民地所引起的問題及其后果。在這份遺產中,后殖民的體制和經驗,從獨立國家的思想到文化概念本身,都與西方的話語實踐攪到了一起。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文章都在辯論西方話語的霸權和抵制它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以及殖民和后殖民主體的形成:交雜混合的、從相互沖突的語言和文化的堆積中形成的主體”[6]136。而琴凱德則在《一個小地方》中,表現出失去話語權的“他者”的矛盾、掙扎,從語言及文化的角度探尋當地人民的模糊身份,以期找到解決身份模糊這一問題的途徑。
一方面是語言的缺失。在書中,琴凱德描述了一種居間狀態,在安提瓜,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數以萬計的人都成為了孤兒——沒有家園,沒有祖國,沒有上帝,沒有可作圣地的土地,沒有多余的愛,而最糟糕且最痛苦的是沒有語言。在這種狀態中,安提瓜人失去了他們的土地、宗教、歷史、傳統,甚至聲音。安提瓜人所使用的語言只能是殖民者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則傾向于從殖民者的角度來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為:對他們而言,“錯誤”一詞意味著沒有分得應有的掠奪物,而“壞的”一詞則意味著背叛真理。因此,安提瓜人無法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用自己的語言來敘說所受的屈辱。安提瓜人若用屬于自己民族的語言講述,才有可能在西方人面前陳述自我,實現自我身份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缺失。英國殖民者給安提瓜人輸入的歷史,是有關大英帝國歷史人物的歷史,是刪去了擴張、奴隸制等概念的歷史;給他們閱讀的文學作品,則是在文化征服過程中帶有英國特色的小說,是能夠使殖民地人民沉浸于殖民文化之中,并否定他們自己的歷史的文學作品,從而使安提瓜人變得像“英國人”。在國家獨立后,安提瓜人不但沒有發展本國的文化,反而主動地接受他國文化的滲入。到了后殖民時期,他們受到了北美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當地的年輕人在對待本土文化和美國文化的時候,更傾向于接受美國的潮流文化。就此而言,在安提瓜獨立前后,本地人民并未注重文化的發展。從某些角度來看,“奴隸制和殖民主義沒有替代或壓制……而是創造了安提瓜。作者也沒有暗示島上的黑人生成了一種新的文化,即能夠復古或是形成一個真正的安提瓜社會的文化……這種文化空缺,使得她必須反轉殖民者的地位:島上的人除了二手的文化,沒有自己的文化”[7]94。這種文化的缺失,是一種文化歸屬感的缺失,也是安提瓜人缺失完整自我身份的表現。
而就作家本人而言,出生于安提瓜的琴凱德,在青少年時期所讀的書多是19世紀的英國小說,而她在書寫自己的憤怒時,使用的又恰恰是英語。這主要是因為自成為殖民地以來,安提瓜一直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在這種情況下,琴凱德要么選擇保持沉默,要么選擇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很明顯,在這部作品中,她選擇了后者,倒轉了話語權的方向,允許自己被困于殖民者的語言的牢籠之中。縱觀整部作品,琴凱德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實質上是為了表述自己對殖民主義的敵意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英國文化及其語言本身是文明的,但作為殖民化的一種形式卻是殘酷的、非人性的。正是這種文化和語言上的霸權控制了當地人的話語權,模糊了他們的身份,使之變成了沒有名字、沒有聲音甚至沒有文明的“他者”。
四、結語
在《一個小地方》這部作品中,琴凱德以安提瓜之旅的所見為線索,由表及里,借對旅游業現狀的觀察切入到對殖民及后殖民的批評,由美好的度假天堂的幻想過渡到現實,揭示了當地政治腐敗、經濟不發達、文化不受重視的現狀,進而對國家身份及安提瓜人的自我身份進行了探尋,提出了自己的美好期望:“一旦你不再以主人身份自居,不再以主人的姿態行事,你才是一個真正的人。奴隸們也是一樣。一旦他們獲得了自由,也不再把自己視為奴隸,他們也就成為了真正的人。”[2]81為此,琴凱德視安提瓜為新的文學空間,將這塊彈丸之地作為書寫對象,以期打破舊的范例,并給出一種看待世界、立足于世界以及鍛造必要的集體身份的新方式。
同時,和后殖民主義的觀念相近,琴凱德對安提瓜未來提出的美好期望,是建立于國家取得自治權的基礎之上的,“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基礎,對那種約束性的、中心化的文化民族主義霸權進行積極地改造……賦予貧困者、無依者以及社會地位低下者更多的權利,寬容差異和多樣性,在民主和平等的框架內確立少數民族的權利、女性的權利和文化權利”[5]115-116。只有這樣,安提瓜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與自由,國家和人民才能獲得完整的身份,這個世界才能在消除權力等級的前提下平等而自由地對話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