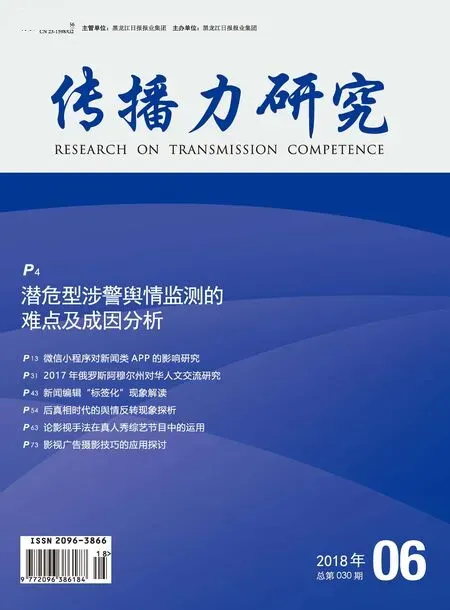十年樹木已長成
——生態紀錄片《森林之歌》特點淺析
廣西師范學院
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遞“正能量”的國家形象是中國紀錄片乃至中國對外傳播事業亟待解決的課題。[2]生態片不同于其他題材的紀錄片,它介紹的是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生命環境,是除了人類自身以外的鮮活生命。在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的今天,十年前的《森林之歌》并沒有過時。這首來自森林的樂曲,傳播著中國故事、倡導著生態建設,同時也滋潤著每個人的心田。
一、內容一體
首先,《森林之歌》講述了一個物種的一生。無論是《竹語隨風》,還是《大漠胡楊》,無論在竹影瀟瀟,還是流沙飛塵,我們全方位的見證了一個物種立體且鮮活的一生。從竹筍的破土萌芽,到頂天立地的一瞬;從隨風而行的胡楊種子,到傲然于沙漠的生死永恒。在鏡頭下,我們見證了不同的生命是如何完成自己的旅程。大部分的畫面通過選擇仰角度拍攝,率直的表現著森林原始的樣貌。風雨后越發的堅韌竹子,“斷臂”后重獲新生的大樹,這些克服困阻的靈魂觸動了我們。
其次,《森林之歌》講述了不同物種的共同生存。碧鳳蝶與毛竹相隨的一生,尺蠖與胡楊的相互依存,竹節蟲躲藏在葉片間的身影,黑鸛飛回胡楊林的本能。各種生命的交織,既讓人領略了環環相扣的生存之道,也儼然折射了萬物與共的自然之本。雖然每一集有固定的主角,但那些不同的過客,讓原有的一種生命姿態呈現出璀璨多變的不同時分。簡單的介紹一種植物稱不上是森林,千姿百態的物種交替才能唱出最響亮的森林之歌。
最后,《森林之歌》連接了自然與人類。竹葉包裹出的粽子,奎麥奇中揉進的胡楊淚,最簡單的飲食透出了人與自然最濃厚的羈絆。作為生態片,《森林之歌》沒有單一的局限于自然風物,而是放眼于整體環境之中。它脫離人類虛有的高姿態,傳達出了一種經常被忽視的情懷——人類對于自然的依賴之情。《大漠胡楊》中,司馬義老人對著獨臂大樹的祈禱既是一個老人希望的寄托,更是象征了人類對于自然的無法抗拒和虔誠敬畏。這一層內容的呈現將本片的文化內涵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二、內涵多義
(一)尊重自然
在作者刻畫的一種植物或動物時,多次運用了特寫,幾乎每一種提到的生物都有特寫畫面。這就像是交代出場人物時給的鏡頭一樣:從正面清晰的拍攝,將生物擬人化,賦予一種儀式感。如此畫面雖不顯眼,卻在細微處體現了作者真切的發自內心的對自然的崇敬與熱愛。
(二)人與自然
每一集的故事中總會穿插人類,這樣的場景似乎提醒著我們什么。而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片中的一些場景:人們運用胡楊淚中的堿制作奎麥奇、人們砍伐竹子去集市上賣,這包含了一份人與自然共處的平衡感。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兩處人物的選擇,一處是孩子們在高大的胡楊樹下用螞蟻釣沙牛的場景。這個的場景的選取,一是喚醒了觀眾的記憶,用懷舊氣氛達到了拉近與觀眾間距離的作用;二是強化了對自然的眷戀之情,啟發人們思考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命題。另一處值得注意的畫面,是《大漠胡楊》中對司馬義老人的拍攝。紀錄片中多次拍攝了老人的活動。看黑鸛飛過、對胡楊祈禱、喂羊小麥……,這些生活化的場景因老人的安寧而顯現的富有詩意。淡然安穩的心靈與嚴酷殘忍的環境,原始、簡單、純粹,卻極具沖擊力。
三、其他特點
《森林之歌》十分講究細節處理,細微的拍攝點選取使片子整體充盈著細膩感。碧鳳蝶的第一次飛行,尺蠖被沙牛吞噬的情景,竹子長高時脫落的外皮,胡楊種子尋找水源的蹤跡……這些不常見到的情節都運用了大量的特寫,清晰展示給觀眾一個未知而新奇的世界。
從科普角度上說,《森林之歌》沒有介紹太多深奧的科學知識,只是簡單的告訴觀眾各種動植物的名字,以及它們的一些習性。不過,即便是這樣簡單的介紹,由于有了畫面與解說的支撐也能讓人對其有了更多的認知。
第三,便是音樂。除了動聽宜人之外,拿捏地恰到好處的背景樂是該片的亮點。悠揚且舒展的音樂伴隨著碧鳳蝶的飛行,伴隨著胡楊種子的飄零。在尺蠖與蝴蝶的幼蟲遭遇到危機時,音樂也隨之變得低沉而充滿緊張的氣息。不同的旋律象征了生命中不同的經歷。
最后一處需要注意的,是本片的開篇和結尾。兩者的呼應并不是依靠畫面的重復,而是巧妙地運用了細節與情節上的銜接。例如,《竹雨隨風》的開頭是幼年時期的竹子等待度過休眠期,結尾則又提到了新的生命即將延續。類似小而精致的呼應,既是完美而隱性的點題,也讓觀眾獲得了一種完美結局的滿足感。
四、結語
《森林之歌》不僅是關于森林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喚起我們對生命態度的思考。在講述中國故事的過程中,我們真心期待著更多優秀的電視紀錄片的出現,讓電視紀錄片能夠承載著中國故事不斷遠行,成為展示中國形象的最為閃耀的名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