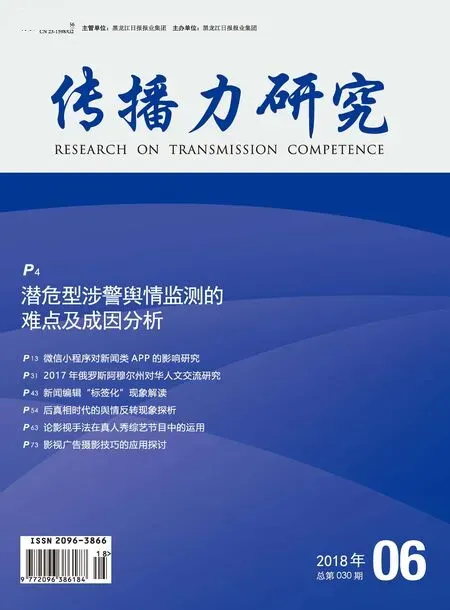“共享”的意義解讀與話語表達(dá)
蘭州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
追溯人類社會物質(zhì)分配方式,從個人、家庭“獨(dú)享”到氏族、部落等有限范圍內(nèi)的“分享”,再到公眾、群體等的大范圍規(guī)模化“共享”,毫無疑問,社會技術(shù)進(jìn)步為“共享”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政治方面,“共享”一詞在十九大報告中出現(xiàn)七次,涉及到發(fā)展理念、脫貧攻堅(jiān)、“一帶一路”建設(shè)、經(jīng)濟(jì)新增長點(diǎn)、社會治理格局、全球治理觀等多個方面;在社會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共享單車”在我國及世界市場的快速擴(kuò)張加劇了“共享”這一概念的傳播,由“共享單車”引發(fā)的“共享”話題一度被熱議,共享經(jīng)濟(jì)在輿論場的傳播聲量始終居高不下。
“共享”正在成為涉及政治、經(jīng)濟(jì)等多領(lǐng)域多層面的一種新態(tài)勢;另一方面“共享”也引發(fā)了諸多問題,“共享”之于不同的訴求主體呈現(xiàn)出不同的話語表達(dá)和概念解讀,商業(yè)企業(yè)對“共享”概念的頻繁借用是否會對政府提倡的“共享”帶來誤解,消費(fèi)者使用“共享”產(chǎn)品對“共享”的理解和對國家“共享”概念的理解有什么差異?“共享”這一符號在不同的話語主體那里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在“共享”潮流下,研究其話語差異,才能為話語博弈中不同訴求主體間建立對話尋求可能。
一、企業(yè)唱響共享經(jīng)濟(jì)
根據(jù)眾多學(xué)者研究,“共享”概念首先出現(xiàn)在商業(yè)領(lǐng)域,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共享經(jīng)濟(jì)”,“共享”也在商業(yè)領(lǐng)域被更為頻繁的提到。也就是說,共享首先的訴求主體是企業(yè)。對企業(yè)來說,“共享”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盈利的商機(jī),是一種新的商業(yè)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jī),多樣化的共享實(shí)踐出現(xiàn),并產(chǎn)生了巨大的規(guī)模效應(yīng)。2011年《共享型經(jīng)濟(jì)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一文發(fā)表,“共享型經(jīng)濟(jì)”被發(fā)達(dá)國家媒體頻頻討論;同年,美國《時代周刊》將共享經(jīng)濟(jì)列入將改變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里夫金認(rèn)為共享經(jīng)濟(jì)將會是與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抗衡并將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新經(jīng)濟(jì)范式。學(xué)者們普遍認(rèn)為,共享經(jīng)濟(jì)將給全球帶來全新的生產(chǎn)模式、消費(fèi)模式和企業(yè)運(yùn)營模式。
共享經(jīng)濟(jì)是指在保留所有權(quán)的情況下,把閑置的資源使用權(quán)暫時轉(zhuǎn)讓給他人,并獲得一定報酬的商業(yè)模式。[1]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共享經(jīng)濟(jì)”模式的多樣化提供了可能。個人閑散物品或服務(wù)得以在第三方市場平臺上呈現(xiàn),物品或服務(wù)的所有者通過讓渡部分“使用權(quán)”與他人“共享”資源,一方面使得個人降低原本所占有物品或服務(wù)的成本,另一方面使得資源得到更充分利用。
企業(yè)“共享”的話語表達(dá)是通過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共享”商業(yè)模式或產(chǎn)品及衍生品實(shí)現(xiàn)的。如“共享汽車”“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共享雨傘”等。對于企業(yè)而言,共享經(jīng)濟(jì)實(shí)質(zhì)上是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的過程。共享經(jīng)濟(jì)的出現(xiàn)使得個人可以直接向最終用戶提供產(chǎn)品或服務(wù),少去了商業(yè)企業(yè)的“中介”作用,而在共享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共享經(jīng)濟(jì)平臺這一“中介”的“搭橋”連接。因此,對于眾多企業(yè)來說,自然不愿成為被去掉的“中介”,這就出現(xiàn)了各類“共享”產(chǎn)品蜂擁而出跑馬圈地?fù)屨际袌觯凇肮蚕斫?jīng)濟(jì)”繁華中分一杯羹、占一席地的現(xiàn)象。
二、政府倡導(dǎo)共享發(fā)展成果
從政府提出“共享”到最新十九大報告中的闡述,可以看出,政府“共享”理念更多地傾向于人民對發(fā)展成果的共享,使得社會資源、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成果的蛋糕“分配”相對公平,以維護(hù)各利益關(guān)系穩(wěn)定。
哲學(xué)政治學(xué)的“共享”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jì)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思想。資本主義的建立與發(fā)展帶來嚴(yán)重兩極分化、經(jīng)濟(jì)危機(jī)和勞動異化,引發(fā)了廣大勞動群眾的不滿與反抗,工人起義和革命運(yùn)動相繼爆發(fā)。這一背景下,馬恩批判繼承了歷史上基于正義、契約、功利等的共享思想,提出了他們的共享思想。
在馬恩看來,實(shí)現(xiàn)共享必須的物質(zhì)前提是生產(chǎn)力的高度發(fā)達(dá),而在生產(chǎn)力尚未達(dá)到高度發(fā)達(dá)狀態(tài)時,要經(jīng)過社會主義社會通往共產(chǎn)主義社會,必須實(shí)行按勞分配原則。可以理解為,按勞分配是實(shí)現(xiàn)“共享”的“過渡階段”。同時,共享的內(nèi)容涵蓋了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一切人類生存發(fā)展的領(lǐng)域。包括政治上,人民群眾共享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經(jīng)濟(jì)上,勞動成果全民共享、生產(chǎn)資料共同占有;文化教育上,人民群眾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全民免費(fèi)享受國民教育,是保障社會發(fā)展的基礎(chǔ)。值得注意的是,馬恩認(rèn)為,共享的實(shí)質(zhì)是實(shí)現(xiàn)公平與正義,但是共享要求人民群眾在享有公正的同時能履行好自己相應(yīng)的義務(wù),最終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目的。
我國對“共享”的解讀主要圍繞“共享發(fā)展”理念展開,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是從“共享發(fā)展”的客體視角來界定“共享發(fā)展”,共享發(fā)展“什么”的問題。尤其是近兩年,對圍繞國家政策對共享發(fā)展理念的相關(guān)研究文章明顯增加,集中于對國家共享理念的解讀,以及共享發(fā)展什么,如何發(fā)展方面。
對于共享經(jīng)濟(jì)這一新生業(yè)態(tài),政府持支持態(tài)度,但對商業(yè)領(lǐng)域的“共享”如何監(jiān)管,如何將政府“共享”理念與商業(yè)企業(yè)“共享”概念良性對接,如何使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與“共享經(jīng)濟(jì)”良性互補(bǔ),確保市場秩序穩(wěn)定,政府監(jiān)管部門還需要更多與市場不同訴求主體的對話,平衡各訴求主體間的關(guān)系,兼顧弱勢群體等易忽略人群利益。
三、消費(fèi)者:樂于“嘗鮮”、駐足觀望
消費(fèi)者對“共享”的訴求在于更便捷更實(shí)惠的產(chǎn)品或服務(wù),同時對于有閑置資源或精力的消費(fèi)者可以在“共享經(jīng)濟(jì)”中實(shí)現(xiàn)身份轉(zhuǎn)變,成為閑置資源或服務(wù)的提供者并從中獲得一定報酬,分擔(dān)個人在獲得某商品及服務(wù)的成本,當(dāng)共享商品或服務(wù)收取報酬超過購入成本,還可獲得額外收益。
在我國共享經(jīng)濟(jì)商業(yè)模式尚不穩(wěn)定,企業(yè)紛紛推出共享產(chǎn)品“試水”的背景下,由于政府對于共享型商品的監(jiān)管尚在探索完善中,部分商品的推出與現(xiàn)有行業(yè)準(zhǔn)入、市場管理等社會準(zhǔn)則有沖突,或在道德倫理約束方面存在問題,消費(fèi)者很可能將為共享經(jīng)濟(jì)的風(fēng)險“買單”。
公眾對于“共享”表現(xiàn)出好奇和新鮮。某些共享產(chǎn)品一經(jīng)推出會有很多消費(fèi)者“嘗鮮”使用,但在后續(xù)出現(xiàn)的如押金糾紛、傷亡賠付等問題,往往得不到及時處理,甚至不了了之,導(dǎo)致消費(fèi)者對共享經(jīng)濟(jì)失去信心。有研究者指出,前期社交網(wǎng)絡(luò)的興起和發(fā)展為分享經(jīng)濟(jì)解決信任問題提供了創(chuàng)新工具和手段。[2]
四、小結(jié)
在國家大力倡導(dǎo)“共享”理念、發(fā)展共享經(jīng)濟(jì)的背景下,企業(yè)、政府、消費(fèi)者對“共享”有著不同的意義解讀和期待。企業(yè)積極唱響共享經(jīng)濟(jì)一方面是搭乘國家倡導(dǎo)“共享”理念的東風(fēng)借勢發(fā)展,另一方面是順應(yī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在當(dāng)前的新業(yè)態(tài);國家倡導(dǎo)“共享”理念,表達(dá)了黨和政府在我國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果、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的背景下,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使發(fā)展成果更好的惠及人民群眾,同時共享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也正符合國家政策鼓勵,為下行的經(jīng)濟(jì)注入了活力;消費(fèi)者對“共享”處于建立認(rèn)知和信任階段,初期是否從中受益或?qū)⒂绊懰麄兒罄m(xù)對“共享”和“共享經(jīng)濟(jì)”意義的理解,及對共享類商業(yè)產(chǎn)品的采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