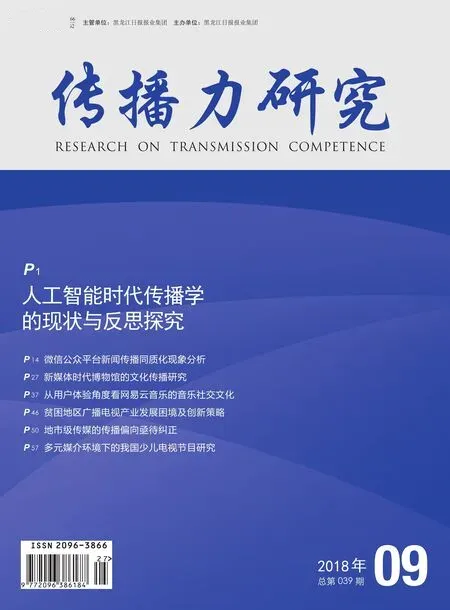地市級傳媒的傳播偏向亟待糾正
周云童 江西新余學院文傳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2015本科班
近年來,在傳媒尤其是地市級傳媒的偏頗語境里,博大、久遠而又豐富的中國鄉土文化正逐漸在“城市化、都市化”的古早文化中被消解和熟視無睹,甚至被遺忘、被摧毀。引人關注和令人憂心的是,原本應該承擔鄉土文化傳播和發展的地市級傳媒,卻由于其在自身的角色身份定位失之偏頗,導致其傳播行為上出現嚴重偏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重視所謂的“都市化、城鎮化”之類知識、信息在傳播時間上的縱向碎片化傳播,乃至大面積、大范圍鼓噪,而忽略現實中國是典型的以農民為受眾主體的“農民中國”,使身處“農民中國”的地市級傳媒忽略了知識、信息在傳播時間上的橫向傳播。地市級傳媒在自身的角色身份定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迷茫與偏頗:根本無視我國現階段依然是以鄉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以農民受眾為主體受眾群體的嚴酷現實。不僅無視現階段的中國已有十多億農民受眾以及“三農問題”矛盾尖銳,而且無視鄉村就是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文化的根。鄉土文化在短時間內絕對不能簡單地使用“都市化、城鎮化”文化范式完全替代。
二是重視在傳播技術上盲目追求視覺上的感受(如電視界面上和報紙標題制作等方面的視覺沖擊,追求所謂的收視率和“眼球效應”),忽略了傳媒在傳播技術對知識、信息的空間管理踐行時受眾群體的城鄉社團信仰、偏好及種族的包容性。不但在傳播技術上的傳播文字、圖片與口語乃至畫面,均發生地市級傳媒角色身份嚴重脫節、失位的現象。尤其是身處“農業大省、農業大市”的“地市級傳媒人在孜孜不倦的鼓噪“都市化、城鎮化”的喧囂中與嚴酷現實脫節。
三是始終漠視身處“農民大市、農業大省”的傳播生存環境而堅持不懈地以“都市化、城鎮化”的話語霸權語境壟斷,根本無視“知識貧困”的中國鄉村深灰在現代生活方式和現代傳媒信息不斷進入后,諸如黃、賭、毒、迷信、宗教(不乏邪教)等域外文化,不但嚴重沖擊原本和諧、平衡的鄉村文化社會體系,而且快速地消解著原本我們引以為傲的數千年的鄉土文化。最為明顯的就是農村、農民的特有生活方式與處事方式乃至民俗風情,卻在“都市化、城鎮化”話語霸權語境沖擊下被斥為“鄉巴佬”、“老土鱉”。載入農村年輕人婚俗崇尚西式婚禮、嗜好過“洋節”。這種不倫不類的鄉土文化正式地市級傳媒的傳播偏向所致。去年底據說某地一個很有名氣的“鄉村旅游景區”花大力氣精心布置了一個“圣誕”景點,讓人看到后猶如吞下一只蒼蠅惡心不止和哭笑不得。
我們的地市級黨政部門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傳媒的主持者、決策者,雖然也反復強調農村文化落后和知識貧困,承認當今社會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及農民整體素質不高,也意識到對農村、農民進行“文化扶貧”、“知識扶貧”很有必要、勢在必行,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作為地市級傳媒離“三農”最近甚至身處“三農”生存環境中,卻總是無視農村、農民、農業的文化貧困、知識貧困的嚴酷現實,僵化的傳媒營運、傳統觀念、習慣思維使他們喜歡喋喋不休惡鼓噪“都市化、城鎮化”這一類碎片化的知識與信息,更有甚者,有些地市級傳媒在所謂的文化扶貧之幌子下將大都市的“棚改”、“私貸”強行塞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用粗暴甚至野蠻的“大拆大建”行為,荒唐地強調讓農民“洗腳進城”。原本和諧、純凈的久遠而有豐富的鄉土文化在地市級傳媒的偏頗傳播語境文化霸權逼迫下被殘忍的撕裂和摧毀!
眾所周知,在知識經濟時代尤其是寬頻化的網絡時代,決定農村、農民、農業的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不是土地和資本,而是知識。未來的農業發展趨勢也必將是知識農業,是信息化、數字化農業。當下地市級傳媒最基本的傳播任務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拓展農民這個最大的受眾群體和受眾主體,對新知識、新技術、新市場的“知識扶貧”與“文化扶貧”,促進農村和農業微觀主體的農業家庭經營組織的運行效率,力促有效節約和降低農民進入市場的交易成本,不斷地提高交易效率。唯這種符合地市級角色身份的“知識扶貧”與“文化扶貧”才是身處“三農”環境的“農民中國”時代背景之下的地市級傳媒的生存之道。
換言之,在當下中國地市級傳媒人思維偏向主導下傳播偏向的輿論語境使“農民中國”(鄉土中國)聲名狼藉、自慚形穢,最后的結果是中國人(尤其是人口最多的農民受眾群體)對自己的歷史自慚形穢。憂心忡忡的傳統文化范式中的“晝出耕田夜織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傳媒人所關心的鄉村消亡的速度正不斷“更高、更快、更強”,以拯救式的偏激輿論關心加速著鄉村的自卑與毀滅。偏頗的地市級傳媒人恰恰因自身的“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的緣故,忘記了人類的歷史經驗有農村經驗和城市經驗,而并非城市經驗就是人類未來的唯一方向。在這些地級市傳媒人所崇尚的西方城市化文明模式中,諸如西歐和美國這些西方城市化高度發達的國家,鄉村文化還是與城市化的都市文明并存,依然是很有生命力的。之所以地級市傳媒人在傳播行為上出現偏向,主要是他們對自身角色和文化身份的定位發生錯位所致。
不少地市級傳媒雖然在冠名上地域性特征明顯,但往往又始終不肯輕易地承認自己是“農民中國”除“農民地市”的地域性傳媒角色與文化身份。在這里,我們借用錯位這個概念,主要從“定位論”來認知和反思。我們也知道,所謂“錯位”,原本指人體上的骨骼錯位、器官錯位,也有人類在地理板塊上的錯位,這里指的是特定事物離開應有的原屬位置,游移到其它位置。人體上的錯位將帶來劇烈的痛痛和應激的痛苦性抽搐;地理上的錯位將帶來地震和海嘯等災難,而人的身份錯位會帶來精神上的痛苦、思想上的反體制與行動上的反社會。當嚴重的身份錯位發生在思想家身上,就會因“錯位”而對社會制度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怨憤和抗拒,并用理論概述的方法揭示其本質的錯誤、存在的非法,進而號召人們摧毀、顛覆之。筆者認為,當下中國的地市級傳媒要從角色身份的錯位中反思傳播偏向的角色身份缺位、失位的錯誤行為。應該重新盡快地為自身的職業崗位角色與文化身份定位。
就職業崗位定位而言,應該著眼于各自地域性如“農業大市”、“農業大省”的地理傳播視角上來確定傳媒的受眾主體——農民。把自己的崗位角色定位于對農村、農業、農民的新知識、新理念、新文化、新技術、新市場的知識、信息傳播者、普及者;定位于對鄉土文化、鄉愁、鄉情、鄉戀、鄉韻、鄉味、鄉俗等傳播者和鼓與呼的踐行者,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體系的踐行者、促進者、建設者。把自己定位于久遠而豐富的傳統鄉土文化的傳承者和承前啟后的橋梁鋪設著者。
就職業崗位文化身份定位來說,始終牢記地市級傳媒從業者的“文化身份”的認同時,不但要牢記自身是位處“農民中國”的“農民地市”的地級傳播媒介在向受眾提供自己的媒介文化產品的同時,能提供讓受眾思考、感受、相信、恐懼和充滿希冀的素材;切記“媒介即是訊息”。并且既要關注實際存在的“客觀社會”,又要關注和有選擇性的提示的“象征性現實”(即虛擬環境),更要關注受眾在自己頭腦中描繪的“關于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社會”。因此,地市級傳媒人要提升自己在職業崗位實踐時“喚醒受眾的認知水平”、對受眾嗜好的感知能力以及已有的傳播經驗三大職業素養。因此,地市級傳媒人在意識到自己在崗位角色和文化身份上的缺位、失位而導致的傳播偏向行為后,應當及時予以校正,積極投身到國家《2018-2022年鄉村振興戰略》之戰略部署實踐中,擺正“農民中國”的地市級傳媒人的角色身份位置,切實關注和重視中國最大的受眾主體——農民,將傳播服務和所提供的文化產品、資源重新優化配置、重新構建鄉村文化的自信與優勢,為自己更有擔當地繼承“農民中國”的久遠而豐富的傳統向鄉土文化添柴加火,在踐行《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擔當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播種機”、“宣傳人”,為鄉村振興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