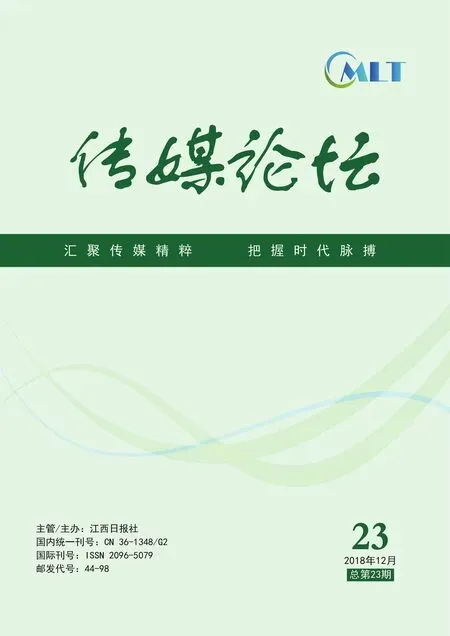西洋畫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早期傳播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西方繪畫東漸的途徑主要有三條:傳教士將西方繪畫帶入中國并且四處傳播;西方畫家進入中國宮廷御用畫家階層,自上而下形成影響;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的通商口岸興起西洋畫,逐漸向內地滲透。還在明代萬歷年間,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便帶了一些西方宗教油畫(彩繪圣像)到廣東,開西方油畫傳入中國之先河。此后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帶來了西方天主教油畫及其銅版畫復制品,將它們送呈高級官僚和皇帝,官僚系統對異國繪畫的興趣和贊助推動了西方油畫藝術在中國傳播。到了清代,朝廷中云集了一批御用西方畫家,北京成為油畫重鎮。南方的通商口岸不斷地向內地輸送傳教士油畫家,西洋畫日益興盛。同治年間上海天主教會創辦了土山灣孤兒院附屬的美術工場,其中圖畫間(習稱“土山灣畫館”)在培養天主教美術人才的同時也培養了任伯年、徐詠清、張聿光、周湘、丁悚、杭犀英、張充仁、徐寶慶等中國第一批系統掌握西畫技藝的近代著名美術家,其西方繪畫寫實的造型體系對中國美術發生了深遠影響。云南清末以前與西方國家經濟文化交流不便,不具備西畫生根的經濟、文化基礎,宮廷西畫亦難對此地造成多大影響。因此,西方繪畫最初入滇主要靠傳教士傳播和內地西洋畫發展起來后向滇緩慢滲透。至于西洋畫在云南成規模地發展,主要依靠教育普及、提高。
一、早期傳教士傳播
唐朝時基督教的分支景教教徒就到過云南,但是直到清光緒以前,零星入滇的督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來去匆匆,未見持久的傳教活動。基督教在云南的傳播和發展主要在甲午戰爭前后到抗日戰爭初期這幾十年間,是隨著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中國、劃分勢力范圍而深入的。基督教最初傳入云南時,采用自上而下、先在城鎮市民和士大夫階層中傳教的傳統方式。由于云南主要城鎮沒有“傳教寬容”,傳教士們同時面對封建統治和傳統儒家文化的強大阻力,傳教活動舉步維艱。這種情形迫使內地會于1895年調整策略,把云南傳教的重心轉移到封建統治、儒家文化薄弱的少數民族之中,形成向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立足的特點。基督教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過程中,改變了部分少數民族社會原有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傳統習俗、價值觀念和思維習慣,既推動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發展,也帶來了西方殖民主義否定民族傳統文化的消極影響。
一般來說,進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受過良好的宗教、科技、文化藝術教育,能力比較全面,具備基本的藝術素養。從中世紀至文藝復興,西方科學、藝術和教育為教會壟斷,繪畫藝術就是基督教藝術。畫家都受教會雇傭和庇護,美術技法在教會活動中孕育發展,作品旨在向文化水平不高的教徒灌輸宗教信條。后來拜占庭美術繼承了早期基督教美術啟迪人們幻想彼岸世界的傳統,成為“基督教歷史上最純然的宗教藝術形式”。文藝復興以后,畫家逐漸擺脫教會庇護下匠人的地位,可以根據自然來創作。但是,直到19世紀末,西方宗教題材繪畫的傳統都未曾中斷,經典繪畫作品中宗教題材比比皆是。正是“藝術傳教”的傳統,造就了一批批具備良好藝術素養的神職人員,催生了燦爛輝煌的西方宗教美術。明代來華的利瑪竇、羅明堅、喬瓦尼、羅儒望、艾儒略、湯若望,清代來華的郎世寧、王致誠、蔣友人、艾啟蒙、潘廷章、安德義、賀清泰,他們都有著名畫家和傳教士雙重身份,受到宮廷、上層統治者垂青或地方官府的禮遇。進入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教士幾乎都有美術、音樂技能,以便利用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吸引百姓,激發民眾信仰基督教的熱情。根據1887年到路南(今石林縣)彝族中傳教的法籍傳教士鄧明德記述,他是充分調動音樂、美術等藝術手段吸引民眾的:“我的風琴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我奏幾段音樂既可自娛,還可以露一手歐洲玩意,所以演奏完了,就拿出一臺望遠鏡、幾張畫和一個萬花筒,把倮倮唬得不知所以。”鄧明德沒有交代“幾張畫”是什么類型的作品,而英國傳教士莫理循記載的似乎是油畫:“1894年在水富休息的那一天,我拜訪了天主教傳教士代主教莫托特神父和伯羅德神父,也拜訪了新近到達水富的美國教會委員會的傳教士。4名美國傳教士居住在一起……他們引我們到一間繪畫室,里面最醒目的裝飾品就是一幅畫,上面繪著一幅盛開的罌粟花。”4名美國傳教士有一個繪畫室,說明他們中至少有1人是專業畫家,或者,這群人對繪畫非常重視。更為難得的是,傳教士的繪畫題材是罌粟花,可見流入云南的西畫并非單一的宗教內容。至于宗教題材繪畫,西方傳教士剛在云南修建教堂就把它作為重要裝飾品帶進來了。1879年建在平政街的御賜天主堂是昆明市最早的天主教教堂,教堂“兩側廊的墻上懸掛14幅苦路像”。到云南修建教堂是西方教會組織的系統工程,所以清末云南的35座天主教教堂外觀設計、內部裝修擺設盡可能統一。根據云南武定縣文化館王勝華先生的研究,伯格理、郭秀峰在武定普灑山苗族地區修教堂后,圣像畫就被帶到那里。無獨有偶,在滇西偏遠高原一隅的德欽茨中教堂內,至今也留有模糊的壁畫痕跡。隨著時光流逝,清末民國時期云南境內的西方繪畫作品,或在裝修粉飾過程中被涂抹覆蓋,或經歷太多的社會滄桑變遷,畫隨人走,留給我們的只是零星破碎的文字記載和模糊的繪畫殘片。但是可以推知,當時云南凡有教堂的地方,都有西方油畫、壁畫的蹤影。至于版畫、水彩、素描作品,一般出現在傳教士帶來的書籍中。不過,這一時期少數民族能看到西畫,但是學會西畫的可能性不大。他們最多在教會學校學到簡單的鉛筆素描,難以掌握繁難的西畫技法。在傳教士的培養下,一些少數民族信徒學會識讀五線譜、唱圣歌、彈風琴,我們不排除傳教士以培養音樂人才那樣的熱情培養美術人才,但是西方寫實主流繪畫需要深厚的素描、色彩修養,其中涉及解剖、透視、形體結構、比例、明暗、色彩原理等一系列的科學、藝術知識,以當時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狀況顯然難以對此深入學習。況且,傳教士的藝術教育活動帶有很強的實效性,核心目標是盡快布道而非提高教徒的藝術素養,他們可以利用晚上禮拜的時間教所有信徒唱歌,邊學邊用,營造宗教氣氛,傳授美術知識則沒有這種宗教價值。繪畫需要多種工具、明亮的場地、安靜的氛圍、寬裕的時間,這一切對于整日為衣食忙碌、起早貪黑勞作的信徒來說也太過奢侈。
二、中國內地畫家影響
隨著天主教、基督教在云南的深入發展,教堂中的壁畫、油畫以及傳教宣傳品中的版畫、素描吸引了一部分云南人對西方藝術的興趣。大量西方商品涌入云南的同時,可能一些西方美術作品也一起入滇。中國沿海、內地的西洋畫起步比云南早,肯定形成向云南順流滲透之勢。這種西洋畫氛圍下,自學為主、多方汲取藝術養分的云南“土西洋畫家”出現了,他們多集中在城市街頭的畫像店鋪、像館、廣告社,運用西方造型觀念、技法畫像招攬生意,并招有學徒。社會上比較流行的是“炭精畫”,用明暗光影造型方法給客戶畫像或者應客戶要求將照片臨摹放大,呈現黑白的立體效果。后來經過技術革新,出現了彩色的“丹配拉”畫像。由于缺乏能夠用雞蛋清調和的水溶性顏料,這種“丹配拉”從材料到技法不同于歐洲文藝復興以前的丹配拉(又叫蛋彩畫),一般是用有限的幾種油漆作畫。1915年董一道在昆明福照街開設的“貫之美術館”,稍后李鳴鶴在華山路一帶開設“鳴鶴畫店”“如真像館”,1925年廖新學在護國路開設“新學美林畫館”,這些館店都在運用西洋畫技術。董一道、李鳴鶴分別去過浙江、上海短期學習西洋畫,更多技法是在使用中自學揣摩。廖新學則是在李鳴鶴“如真像館”當學徒期間獲得西洋畫技能。這批“土西洋畫家”中有無少數民族現在不能確定,但像董一道這樣來自少數民族地區、善于描繪少數民族風俗的畫家,對少數民族繪畫的潛在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三、學校的教育普及
20世紀最初10年,云南教育轉軌改制,新式學堂中出現鉛筆、鋼筆作畫的“圖畫課”,這是一種稚嫩的、普及式的“西式素描”教學。盡管兩級師范學堂、初級師范學堂、師范傳習所、小學師范講習所都開設圖畫課程,但是通曉西畫的人才稀缺,許多畢業生很難勝任西式的圖畫課教學,云南“圖畫課”的質量普遍不高,有些學校甚至沒有能力開出這門課。云南高端的西畫人才是留學生和從國內藝術發達地區院校學成歸來者。從1911年到1938年,云南有16人到日本學習美術,40余人在國內公立、私立大學接受美術教育。李廷英、李長元、史秉彝、黃源煦、張逸飛、陳博子、都在日本接受西洋畫教育,回國后李廷英對云南美術的貢獻比較大,許多畫家聚集在他主創的云南美術專門學校。布青陽、羅家清、尚烈、楊煕、何秉智、康學文1908年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博物實習科,他們是云南最早的一批西洋畫教師。后來,李實清、張菊芬、詹明昌、李承勛、許仁宏畢業于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圖畫科,黃公敵、王旦東到北平、上海學畫,董一道到浙江拜師學藝,他們都掌握了西洋畫的基本要領,個別人很有造詣。
民國初期,云南西洋畫的發展情況可以從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云南預賽美術作品中反映出來。云南博覽會的美術館、教育館共展出繪畫作品100多件,今有案可查的西洋畫法作品有12件,包括鋼筆畫4幅,擦筆畫、鉛筆畫、油畫、用器畫各2幅。當時云南出品協會和勸業會成立的美術作品評審員給出審查評語:鋼筆畫“筆致細密、深淺適宜”“遠近陰陽、具合法度”。擦筆畫“布色渾厚,濃淡合宜”。鉛筆畫“層次分明,筆畫清晰”“清健”。油畫“遠近配置合宜、色澤具鮮”。從參展數量及評語可以窺見,像董貫之這樣的西畫高手可謂鳳毛麟角,許多西畫家帶有很強的民間特點。所謂民間特點,一是指他們的技法比較稚嫩,繪畫語言不純粹;二是他們雖然可能短期受聘到中小學校任教,但主要流落在社會上開畫店謀生,其創作帶有謀生手藝的民間適應性。
盡管現在已知西方傳教士在明朝就把西洋畫帶到中國宮廷,但是西洋畫在中國廣泛傳播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每種藝術都有特定的文化生存土壤,油畫為代表的西洋畫承載著西方人文主義的精神,外來藝術在中華大地生根、成長需要漫長的文化交融。云南作為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域,既有文化多元包容的一面,也有多種文化碰撞融合的復雜性。西洋畫在云南早期傳播是零散、緩慢、不純粹的,它的意義在于為后來云南文化藝術的繁榮添加異質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