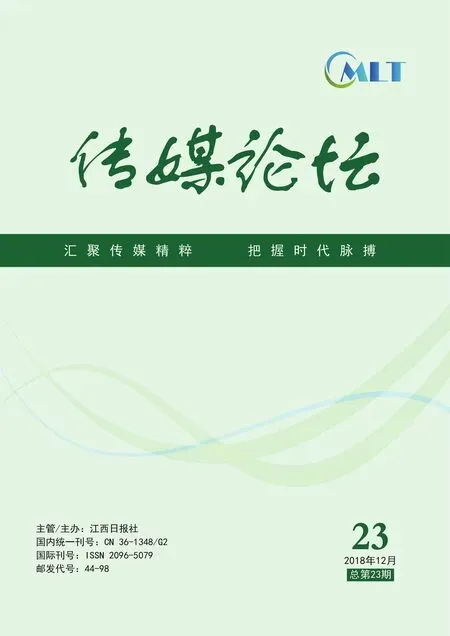探析云南彝族刺繡的保護性開發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信息時代,如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云南彝族刺繡有輝煌的歷史,今天面臨的問題與其它“非遺”別無二致。在人們的美好愿望中,保護“非遺”便是使其保持“原生態”,比如建立民族藝術保護區。而開發就意味著商業化,很可能變異走樣,失卻文化的純正性。實際上,在今天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文化、經濟環境已經大幅度改變的情況下,要做到少數民族藝術的原汁原味非常難了,只能靠多種方式優化民族文化生態,激發出民族藝術的當代活力。商業化給民族藝術帶來的負面影響要警惕,但保護性開發是非常必要的。
一、云南彝族刺繡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傳承人越來越少
彝族最初居住的地方相對偏僻閉塞,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生產、生活更多依賴土地、山林等資源。由于交通不便,稀缺物資依靠人背馬馱運送,商品經濟不發達。農民守著土地耕耘,衣、食大事主要自己解決,刺繡作為“衣”的部類,幾乎是每家每戶必須傳承發展的手藝。現在交通便利,市場經濟大潮席卷每個角落,傳統方式耕種獲得的收益遠遠趕不上從事經營或進城打工的收益,幾千年的“鄉土”開始失落了。青壯年勞力常年進城務工,村里多剩老年人及留守兒童。年輕人是傳承技藝的主要群體,現在他們因生活環境改變而在民藝傳承中缺場了。此外,現代學校教育的標準化、大眾傳媒帶來的審美單一化也使年輕人疏離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他們的服飾跟隨社會潮流而變,快捷、時尚的流行服飾及現代工藝更有吸引力。于是,彝族村寨很難看到姑娘們穿針引線的場景,許多彝族女子不會刺繡了。在火把節等重要的彝族節慶中,年輕人節慶穿戴的衣飾來自市場,手工刺繡品變成了機器繡品。
筆者調查時遇到一位彝族刺繡能手普秀珍,她的女兒、孫女們都不愿意穿彝族傳統服裝,也不愿意學習刺繡。村里愿意穿戴民族服飾、會刺繡的基本上都是老人,而村里老人不斷離世。大娘想趁自己眼睛還看得見,爭取為每個女兒、孫女都做一套繡裝,以免后代看不到文化遺產。這樣的情況其實在今天很普遍。社會是向前發展的,傳統刺繡的生境已經被改變,民間技藝后繼無人,集結在人身上的非物質的、活的文化就消失了。
(二)過度商業化改變民族文化特質
商業化浪潮中,少數民族刺繡對外來人群很有吸引力,但他們外在于民族文化,僅僅在感官上獲得某類印象。旅游景點、特色商店里琳瑯滿目的繡花衣服、包具、飾品,對游客來說就是一個“民族風”的概念。這些帶有刺繡的物品視覺新穎、價錢不高、方便攜帶,隨性買下,不再深究其品質。于是,機器繡品在市場里逐漸驅逐費時費力的手工繡品,東拼西湊、魚龍混雜的繡品擠上貨架。為了降低成本,許多繡品缺乏源自民族文化根系的設計,或拼湊多個民族圖案風格于一體,或截取、夸大能夠帶來噱頭的個別元素。這樣的商業化生產帶來諸多危害,首當其沖便是稀釋了民族文化。彝族刺繡是在民族漫長的生存實踐中積淀成型的,技藝、圖案都彰顯著特定地域環境中人與自然的相互影響,以及特定文化心理對應的審美意識。外界之所以有彝繡、苗繡之稱,就是因為各民族的刺繡有自己的品質。出于商業目的刺繡“大雜燴”,稀釋了彝族刺繡的文化成分,遮蔽了民族文化的特性。
物以稀為貴,機器化快捷高效生產的繡品大批量涌向市場,結果可想而知。機器生產的刺繡難以與純手工刺繡相提并論,更何況市面上有的繡品缺乏合乎民族文化延展的設計。消費者的“胃口”一旦搞壞,反過來會拉動刺繡市場下滑。商家為了求得市場生存,難免拉動生產廉價、低俗的繡品。
二、彝族刺繡保護的舉措
要培養刺繡傳承人、避免過度商業化帶來的惡性變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收藏、創作刺繡精品
博物館、美術館之所以要收藏各畫種的精品之作,就是要把它作為典范供一代代的美術行業人士研習。現在的一些公立博物館、民間民俗博物館也收藏了少量的彝族刺繡精品,但在影響民眾的鑒賞力以及培養傳承人方面作用還不大。所以,目前還要收藏、創作彝族刺繡精品,使之發揮學習、鑒賞、導向的作用。我們可以走訪彝族村寨,收藏一些繡功上乘的經典作品,尤其是不同年代的繡品,方便后人了解本民族刺繡發展的歷史。收集資料,總結刺繡圖案、針法及色彩搭配,形成完整、齊全的范本樣品,培養傳承人就有法可循。他們掌握經典傳統刺繡、制衣的整套程序及技能,能夠避免刺繡在發展過程中產生惡性變異。
(二)創建各級刺繡協會,扶持、培養傳承人
創建省、市、縣各級彝族刺繡協會,聘請高水準的彝族文化學者作為顧問或者理事,吸納民間彝族刺繡高手、傳承人作為常駐理事,這樣有利于培養高質量的傳承人。有了協會這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術制高點,政府相關文化部門可以通過它來宏觀引導彝族刺繡的發展走向,有效地保護繡品文化的純正性。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傳承人保住了,遺產就呈活態化。協會可以重點扶持幾個優秀的傳承人,吸納他們入會做理事,并盡可能申請專項資金予以扶持。同時還應派專人采訪傳承人,以視頻、圖片、文字等多種形式保存彝族刺繡資料,培養新的傳承人時作為口傳身授的重要補充。
(三)鼓勵規范的經營開發
彝族刺繡世代傳承主要因為它是自產自用的物品,與彝族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現在從事刺繡的人越來越少,是因為村寨內部對刺繡的需求減少,年輕人甚至自己都不用了。讓年輕一代繼承刺繡傳統的理由,就是這項技能要能夠安身立命、養家糊口、發家致富。一句話,就是要能產生經濟效益。
政府可以鼓勵、扶持開發商投資建廠,或者建立公司,開發銷售繡品。有的市縣已經有成功的經驗。例如昆明市石林縣的阿著底村,1996年成立了普氏民族民間傳統刺繡廠,由公司統一設計、統一裁布,再分給農戶刺繡。現在該村已經帶動周邊六個村子從事刺繡工作。
談到民族藝術商業化,總容易聯系到它稀釋民族文化及帶來作品低俗化。其實事物都有兩面性,這里邊有“度”的問題。商業化并不必然導致民間藝術變味。日本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諸多措施中都有商業、資本參與,但他們保護非遺的成效走在世界前列。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化,缺乏健全的市場機制和監管,就會陷入唯利是圖的泥沼,帶來繡品惡性變異。政府扶持和鼓勵的商業化有宏觀調控機制,能夠探索出促進良性發展的路子。
(四)開發精、簡運用,提高設計質量
完全追求繡品的“原位性”和“原生態”,容易陷入博物館式保護的困境。完全將繡品放入市場,則有惡性變異的風險。我們可以將繡品分為經營性和非經營性兩種,進行對位互補的保護。在傳播媒體非常發達的今天,民族藝術是否能夠生存關鍵在于能否煥發出活力,必須在傳統文脈的基礎上適度推進現代性轉化,找到新的文化增長點,顯現獨特的美學品質。傳統彝族服飾十分復雜,以花腰彝族婦女服飾為例,有帽子、頭帕、大襟裳、托肩、領掛、腰巾、腰帶、肚兜、褲、繡花鞋等十余個部件,多個部件刺繡密密麻麻,手工精心完成一套繡裝耗時一兩年。這類繡裝只在彝族重要儀式、節慶穿一下,可能會有外界人士購藏,但需求量有限,適合作為非經營性的作業保留。經營性開發利用要精、簡,即保留彝繡的特征,抽取其特質元素,惜“繡”如金,點到為止。這樣既可以保證刺繡的質量,又可以兼顧產量。“簡”和“惜”不是簡單的“少”,這要在設計方面見功夫。
民間彝繡能手、繡娘主要依照千百年來積淀而成的范式開展作業,創新設計要靠新型人才。設計者需要具備設計專業素養,了解彝族的歷史文化,設計創新才能丟掉彝族刺繡的特質元素。這樣的人才可以從高校藝術設計類畢業生中尋找。云南一些高校的藝術設計專業都開設過民族元素設計專項訓練和研究性課程,學生畢業設計不乏運用民族藝術元素的佳作。我們可以校企合作,培養彝族刺繡產品設計人才。
三、綜合優化刺繡生存環境,獲得民族文化增長點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嘗試“監管部門+開發經營者+彝繡協會+設計師+繡娘”的模式,綜合優化彝族刺繡當代生存環境。
開發經營者扮演著推動刺繡再生產的重要角色。他們投資建廠或公司化運作,不斷迭代經營理念和營銷策略,最大限度地把彝繡作品推向市場,擔負起把繡品變為商品的使命。有了訂單,村民在家里繡花就可以有收入,這會吸引一批外出打工的婦女返鄉,重拾這門古老的技藝。如果沒有商業化經營,繡娘們的經濟需求難以滿足,甚至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系,那么這個群體將很快消失。更重要的是,沒有市場的推動,藏在深山的傳統繡品很難參與世界性的交流對話,不能在多元共生的當代文化景觀中顯示自身價值,也難以煥發出當代人喜聞樂見的美學品質。
政府監管部門、彝繡協會必須宏觀調控,從理論與學術的高度把控彝繡發展方向,保障彝繡再生產既適應市場又遵循文化規則,避免單純商業運作帶來彝繡生產跑偏、惡性變異的問題。可由政府、開發經營者出資,招募有刺繡基礎的彝族婦女組成學習班,彝族刺繡傳承人、民間刺繡高手潛心傳授技藝。刺繡協會還要定期舉行各種交流會、展覽及比賽,形成彝族主流刺繡文化。通過這種方式培養的繡娘,才是技術過硬、文化純正的新時期一代繡娘。學習結束后,經彝族刺繡協會考察合格,頒發結業證或合格證。繡娘們只有持證才可以上崗,才有被聘用、被分派刺繡任務的機會。她們要全力以赴地繡好每一針,確保刺繡的質量,擔起彝族刺繡傳承的重任。繡娘可以是工廠的員工,也可以是自由的接單人,總之她們是刺繡的實踐主體。
具有專業水準的高素質設計師,是工廠、公司的產品研發者,是高級人才,其設計質量直接關系到繡品的品位。缺乏設計創造的彝繡產品難以在市場獲得競爭力,設計師要賦予作品新的美學品質,通過提升繡品的品位及市場適應性,使其煥發魅力。因此工廠或公司一定要聘請扎實肯干、專業能力強、業務素質精的設計師,對彝族刺繡傳統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地進行研究,以現代設計意識推動民族文化增殖,多出上乘之作。
綜上所述,在開放、交流成為世界不逆之勢的今天,少數民族文化全球化正在加速,單純博物館式的民族藝術保護難以使其在世界當代文化對話中獲得生長空間。保護彝族刺繡必須進行當代激活創造,重視其當代生存環境的營造。實踐中我們可以嘗試調動各方力量,通力合作,綜合優化彝族刺繡當代生存環境。有了適宜生存的環境,彝族刺繡就有可能良性地發展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