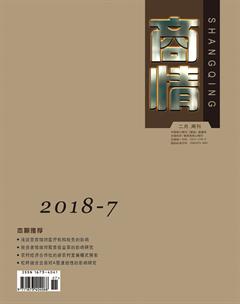論臨時起意取財行為的性質
許雅璐
[摘要]行為人在實施暴力犯罪后,利用被害人被壓制反抗的狀態,臨時起意取財的,主要存在“搶劫罪說”和“盜竊罪說”兩種爭議。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狀態下,應采“搶劫罪說”,不敢反抗是基于前行為對被害人形成的脅迫并沒有消失,行為人對此脅迫的積極利用能夠被評價為搶劫罪的實行行為。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情況下,應采“盜竊罪說”,此時不存在需要壓制反抗的客觀條件,也不存在對于脅迫狀態的積極利用,應當構成盜竊罪。
[關鍵詞]臨時起意 取財 搶劫 盜竊
實踐中存在著行為人出于其他暴力犯罪的目的,在實施暴力、脅迫等行為壓制被害人反抗后,利用被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狀態,臨時起意以平和的手段當場取走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對于該行為的性質在理論界存在著各種觀點的聚訟,其中主要有“搶劫罪說”和“盜竊罪說”。最高人民法院曾針對以上問題,出臺了相關司法解釋,認為行為人在實施傷害、強奸等犯罪后,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覺的情況下臨時起意取財的,前行為與搶劫罪數罪并罰;在被害人失去知覺或沒有發覺的情況下臨時起意取財的,前行為與盜竊罪數罪并罰。但理論界對此問題并未能達成一致意見,針對該司法解釋也存在著質疑,因此,對臨時起意取財行為的定性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一、“盜竊罪說”的理論基礎及存在的問題
(一)“盜竊罪”說的理論基礎
盜竊罪說認為,臨時起意取財行為應當構成盜竊罪,針對臨時起意的取財目的,行為人并沒有基于此實施新的暴力、脅迫等行為,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主要理論基礎在于:
第一,將前暴力、脅迫行為再次評價為搶劫罪中的構成要件違反了刑法中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是行為人實施傷害、強奸等暴力行為所致,如果認定為搶劫罪,則暴力行為既作為傷害、強奸等犯罪的構成要件,又作為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同一情節被重復使用了,這是不容許的。
第二,臨時起意取財行為符合盜竊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盜竊罪不以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為前提,盜竊罪、搶奪罪、搶劫罪的區別,僅僅在于暴力程度不同。那么在實施取財行為時,即使實施了程度不高的暴力時都可能屬于盜竊行為而非搶奪行為,那么,以平和方式臨時起意取財的行為就應認定為盜竊行為。
(二)“盜竊罪說”存在的問題
1.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理解誤區
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是在定罪量刑時,禁止對同一犯罪構成事實予以兩次或兩次以上的法律評價。此原則禁止的是一個犯罪構成內的事實在刑法上被予以雙重評價,而不是單指一個事實不能重復評價,它實際上強調的是犯罪構成內的事實是有法益侵害性的,不能重復評價的是一個事實對一個法益的侵害。就犯罪構成要件個體來說,并不完全排斥重復評價,如果完全禁止重復評價勢必導致刑法的不公正及動搖犯罪構成制度的基礎,相應地影響一罪與數罪的區分,以及引發其他一系列問題。搶劫罪屬于復行為犯,其實行行為由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構成,行為人利用自己先前暴力行為所造成的被害人不能反抗狀態作為搶劫的手段行為與臨時起意取財行為組合成搶劫的犯罪構成事實作為侵犯財產法益的搶劫罪去評價并不屬于重復評價。
2.認為臨時起意取財行為均為盜竊罪具有片面性
前暴力行為與后取財行為是相對獨立的,前暴力行為并非后取財行為的手段行為,取財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犯意也是在暴力行為實施后產生,確實存在構成盜竊罪的情形,比如,將被害人打昏之后,產生奪取財物的意思,趁其處于昏迷狀態而拿走財物;毆打被害人之后,趁其不備竊取其財物,等等。
但是,也不排除存在構成搶劫罪的可能性。盜竊罪不以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為前提,但并不意味著以平和方式臨時起意取財的行為就都構成盜竊罪。搶劫罪的實行行為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其他方法”,例如,強奸婦女后,趁被害人仍處于極度恐懼狀態,當面拿走其財物。表面上看取得財物時似乎沒有進一步的暴力、脅迫行為,但實質上是利用強奸行為對被害人產生的脅迫效果而取得財物的,在此種情況下,行為人利用脅迫手段劫取被害人財物,無疑應當定搶劫罪,而不能定盜竊罪。
二、“搶劫罪說”的理論基礎及存在的問題
(一)“搶劫罪”說的理論基礎
搶劫罪說認為,雖然取財行為是出于暴力犯罪后的臨時起意,但結合整個過程來看,應當認為行為人存在搶劫罪的主觀故意,因而構成搶劫罪。主要理論基礎有:
第一,“不作為構成說”,主要是認為在行為人起意取財前,被害人存在的被壓制反抗的狀態也是由行為人的暴力犯罪行為導致的,行為人如果不對此狀態予以排出,而是利用該狀態進而實施了取財行為的,其不作為的行為與以作為方式實施的暴力、脅迫等行為并無區別。
第二,“留在現場說”,主要是認為只要行為人在實施暴力犯罪后仍留在現場,對于被害人來說威脅就是持續存在的,行為人正是基于這種威脅的持續存在而取得財物的,因此應當構成搶劫罪。
第三,“持續說”,主要是認為在行為人取財時,前暴力行為導致的壓制被害人反抗的狀態仍是在持續中。
第四,“擬制說”,主要是從量刑上來考慮,認為在此狀況下的取財行為的可罰性遠比一般的盜竊罪來得高,如果僅僅以行為人后續并無暴力、脅迫等行為而否定行為人構成搶劫罪的可能性,必然會導致處罰過輕。
(二)“搶劫罪說”的存在的問題
搶劫罪說的理由存在不合理的部分,主要在于:
1.“不作為構成說”及“擬制說”缺乏理論依據
在臨時起意取財的情況下,要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作為義務,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如果行為人不實施一定的作為,被害人的財產是否有被侵害的現實危險。顯然,先前的傷害、強奸行為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行為對象并非被害人的財產。在先前的傷害、強奸等行為實施完畢以后,只要不存在新的侵犯財產行為,被害人的財產就不會有損失。因此,在臨時起意取財的場合,并不存在不作為犯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先前的犯罪行為不能作為不作為犯的義務來源。雖然行為人實施了傷害、強奸等行為,也壓制了被害人的反抗,但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并不存在保護被害人財產的義務。“擬制說”為了避免按盜竊定罪可能出現的處罰上的不均衡,而把本來沒有搶劫的故意和行為的情形,假設或擬制為有,這本身就違反定罪應該以事實為根據的原則,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和責任原則。
2.“留在現場說”及“持續說”在特殊情況下存在不合理之處
在一定情況下,例如行為人將被害人打昏,或者被害人雖未昏迷但完全不具有反抗能力,或者行為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竊取財物的情況下,即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時,暴力、脅迫已完全結束,客觀上已不存在壓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把在這種場合取得被害人財物的行為,也認定為搶劫罪,有不當擴大搶劫罪處罰范圍之嫌。
三、司法解釋對于臨時起意取財行為的定性存在問題
(一)是否失去知覺不能作為定性標準
對于臨時起意取財行為,如果被害人未失去知覺,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處境的,認定為搶劫罪;如果在被害人失去知覺或者沒有發覺的情形下,則認定為盜竊罪。這樣的規定從表面上看似乎沒什么問題,在被害人失去知覺時拿走其財物,認定為盜竊罪,對此刑法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然而,司法解釋對于臨時起意取財行為的定性取決于被害人的狀態,是否失去知覺成了認定行為人行為性質的重要要素,這一點是存在問題的。
(二)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兩種情況不存在區別
司法解釋認為,對于臨時起意取財行為,如果被害人未失去知覺,但不能反抗的,認定為搶劫罪;如果被害人失去知覺的,認定為盜竊罪。但是在客觀上,被害人雖未失去知覺但不能反抗的狀態與失去知覺的狀態并無不同,均已不存在需要壓制被害人反抗的條件,已不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司法解釋之所以作如此區分,主要在于傳統理論將盜竊罪中的“盜竊”理解為秘密竊取,因此,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覺當面取財的行為就定性為搶劫罪,這是存在問題的。
目前通說把秘密竊取作為盜竊罪的本質特征,認為盜竊必須是秘密竊取,但只強調行為人主觀上自認為不為人所知,不要求秘密必須是指不為被害人所知,例如王作富教授就認為:“取財物之秘密性的含義至少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秘密是指行為人自認為沒有被所有者、管理者所發覺。”但是這一通說不能解釋實踐中存在的行為人當面取財的情況,即行為人明知被害人已發覺,仍取走財物的情形。因此,僅憑行為人“自認為”秘密或公開來決定犯罪性質,屬于主觀主義的觀點,必然導致盜竊罪與搶奪罪的區分不具有客觀標準。當面取財的行為當然也不能認定為搶奪罪,首先,搶奪罪客觀上必須具有暴力行為,當面以平和的方式取財不符合搶奪罪的構成要件;其次,也有學者認為,盜竊罪與搶奪罪是相互包容的關系,盜竊與搶奪的區別,僅僅在于暴力程度不同,盜竊行為也可以包含程度上達不到構成搶奪罪的輕微暴力行為。
因此,在被害人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的情況下,是否失去知覺只存在當面取財與秘密取財的不同,而秘密性并不能作為盜竊罪與搶奪罪、搶劫罪的區分。如上所述,在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的情況下不能構成搶劫罪,以和平方式取財的行為也不能構成搶奪罪,在此情況下只能以盜竊罪論處,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即不存在區分,是否失去知覺并不具有區分這兩種情況的作用。
四、對于臨時起意取財行為性質的認定
對于先出于其他犯意而壓制被害人反抗后臨時起意取財的行為在實踐中可能存在兩種情形:一是被害人尚未喪失知覺處于不敢反抗的狀態,二是被害人失去知覺處于不知反抗的狀態,或被害人尚未喪失知覺但已喪失反抗能力而處于不能反抗的狀態。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在此不做討論。
(一)臨時起意取財行為應當分情況討論的理論依據
前行為不能直接評價為搶劫罪的手段行為。客觀上,取財行為與前行為是相互獨立的,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在臨時起意取財的場合,行為人在實施暴力、脅迫或其他壓制被害人反抗的行為時并沒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意思,行為人實施的暴力、脅迫等行為屬于其他暴力犯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并未侵犯財產法益,不能被評價為搶劫罪的實行行為;被害人不知反抗、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的狀態也是前暴力、脅迫等行為的延續。取財行為是在前行為結束后實施的,且前行為不是取財的手段行為,不是為取財行為壓制反抗而存在的,前行為侵犯人身法益、取財行為侵犯財產法益,兩個行為是相互獨立的。主觀上,取財行為犯意的產生既不是在壓制被害人反抗行為實施之前,也不是在壓制被害人反抗行為實施過程中,而是在壓制被害人反抗行為結束后,取財行為的犯意產生是屬于另起犯意,是前一犯罪停止狀態下產生新的犯意。
(二)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場合,應當認定為搶劫罪
在上述兩種情形中,第一種是行為人在實施傷害、強奸等犯罪行為后,利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狀態,臨時起意取財的情形,應認定為搶劫罪。在此情形下,前行為已經實施結束,但對于為失去知覺且有反抗能力的被害人來說脅迫仍是持續存在的。即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被害人仍存在反抗的可能性,前行為對被害人形成的脅迫仍然起到壓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主觀上,行為人在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目的支配下積極地利用了這種脅迫。行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并積極利用持續存在的脅迫而取得了他人的財物的,因此應當構成搶劫罪。
(三)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場合,應當認定為盜竊罪
在上述兩種情形中,第二種是行為人在實施傷害、強奸等犯罪行為后,利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狀態,臨時起意取財的情形,應認定為盜竊罪。在此情形下,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時,暴力、脅迫等行為已完全結束,前行為對被害人也不存在脅迫,因為客觀上已不存在需要繼續壓制被害人反抗的條件,前行為結束后也失去了壓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只是后行為新產生的犯意,與前行為無關,這種情況實質是行為人利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狀態而取得財物,構成盜竊罪。
五、結論
綜上所述,因臨時起意取財行為與先前的暴力、脅迫行為相互獨立,不能簡單地認為前行為是后行為的手段行為而構成搶劫罪,應當分為兩種情況討論。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情況下,客觀上,前行為對被害人形成的脅迫仍然起到壓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主觀上,行為人有積極利用這種脅迫的意思,因而這種情形能認定搶劫罪成立。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情況下,已不存在需要繼續壓制被害人反抗的條件,前行為結束后也失去了壓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不構成搶劫罪而構成盜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