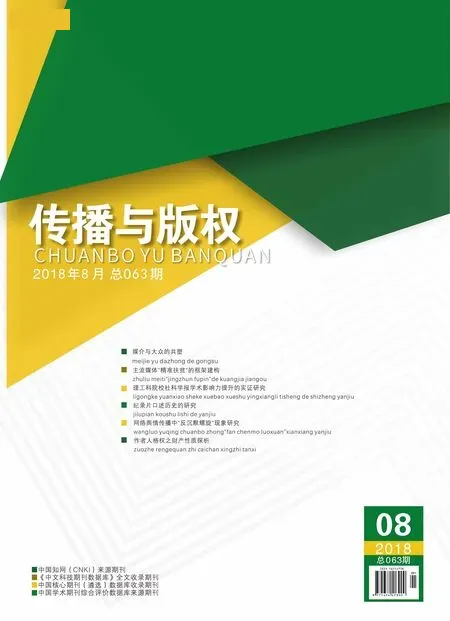“編輯有學”
——戴文葆先生學術成果及其編輯學思想概述
張雅寒
戴文葆先生是我國杰出的編輯學家、出版家、著作家、資深記者,中國首屆“韜奮出版獎”的獲得者,是一名典型的學者型編輯,更是我國編輯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先行人。他對自己的編輯工作抱有極大的熱情,一生追求“工作和學術的高品位、高標準、高境界”,不斷學習,并始終保持“與人為善,待人以誠,胸懷坦蕩”①桂曉風:《懷念戴文葆同志》,《中國編輯》,2008年第6期,第67-70頁。。
一、戴文葆先生編輯工作始末
1923年,戴文葆先生出生于江蘇阜寧。1938年,由于日軍攻打南京,導致蘇北鹽城高級中學解散,戴文葆先生回到老家阜寧,開始在《濱淮日報》做義務編輯,這是他接觸新聞工作的開始。
(一)學生時代的編輯成果
抗戰期間,戴文葆先生就讀于重慶復旦大學法學院,后轉至政治學院。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戴文葆先生于1944年夏和一些進步同學一起主編了《中國學生導報》,這是一份學生報紙,也是其“從事出版工作前的一點實習”②戴文葆、劉瓊:《一生與出版結緣》,《編輯學刊》,2007年第3期,第48頁。。
戴文葆先生一生參與編輯了很多經典書籍,作為一名編輯,他也撰寫了大量文章,為編輯學研究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大學時代的戴文葆先生作為幾種政治墻報的主編寫了一些政治論文,后經張明養教授推薦,在《東方雜志》第四十卷第二十二號上發表了其中一篇,這是他在學術雜志中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45年大學畢業前后的這段時間,他在《新華日報》《群眾》《青年知識》《自由論壇》《華西晚報》等發表過文章,并開始發表一些翻譯的短文,翻譯了五萬字的英國出版的一本從盧梭到馬克思的西方政治思想兩種傳統的簡史。
(二)編輯工作歷程及學術成果
1945年畢業后,戴文葆先生還教過高中文史,后又到上海參加了《新華日報》的工作。1946年5月,戴文葆先生應沈鈞儒之邀到《世界晨報》與袁鷹共同負責要聞版國際小品的寫作工作,但半年后該報被迫停刊。同年中秋節過后,戴文葆先生出任《大公報》國際版編輯、社評委員及管理委員會委員,并編輯了《國際問題》周刊。在此期間,他還經歷了一段教書生涯,在上海圣約翰大學給政治系和新聞系講國際政治課,在上海市軍管會干部學校講中國近代史。戴文葆先生先后在《理論與現實》《讀書與出版》雜志,《文萃》《民主》《世界知識》和《文匯報》上發表了論文,與馮賓符等共同完成了《國際形勢讀本》一書,并由生活書店出版。1946年以后,戴文葆先生在《大公報》發表有關國際問題的論文和社論的同時,也經常為《世界知識》雜志撰稿。1947年,他與朋友一起編譯了《華萊士與美國第三黨》,并與自己所寫的長篇論文編在一起由上海利群書報社出版發行。與此同時,他還擔任了地下油印刊物《火種》的主編,并親自寫一些雜感以補白。離開大學后,編輯和寫作逐漸成為戴文白先生的主要職業。新中國成立后,他編輯了論文集《人民的大鮮章》,并寫了有關對外政策一章的內容。
20世紀50年代,戴文葆先生在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散文集《中國走在前面》和傳記《劊子手麥克阿瑟》。他撰寫的《聯合國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由上海展望雜志社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發行。作為世界知識社的代表,與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的編輯共同編寫了戰后亞洲太平洋區域問題大事記,在《人民日報》發表后,由人民出版社印制成書并出版發行。1954年,戴文葆先生在作為三聯書店編輯部副主任期間,“編輯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國史綱(上古篇)》《中國報學史》《中國古代史》《經濟侵略下之中國》《語言與思維》《國史舊聞》等一大批極具文化價值的著作”①劉洋:《戴文葆的編輯學研究及其思想論要》,《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第150頁。。此外,為配合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戴文葆先生還于1954年春協助吳冷西編輯了《亞洲和平與安全問題大事記要》,并親自執筆完成第一部分的內容。1955年,他協助范長江編輯了《韜奮文集》(三卷本)并撰文《編者的幾點說明》。同年,英國首相艾德禮訪華,他與黃紹湘共同完成了《右翼社會黨》一書的編寫,并由人民出版社以“世界知識社”的名義出版發行。他是《胡愈之譯文集》的主編,并編輯了《胡愈之出版文集》,他還組織翻譯了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在中華書局工作時期,他為吳晗同志最后整理了《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20世紀80年代,戴文葆先生先后出版了《新穎的課題》《尋覓與審視》《板橋雜記》《射水紀聞》以及《月是故鄉明》《號角與火種》,編輯了歷史文物圖錄《鑒真》、長城研究的新成果《中國古長城遺跡調查》、彩色印刷的中英文對照版《長城》圖錄。1981年,他協助美國MeGraw—H ill Book Company編輯《The Great wall》大型歷史文物圖錄一書,并為其寫了三篇署名文章《Why the Wall Was Built》《Neighbors of the Wall》《Trade Across the Wall》,他還為此補充了超過三分之一的解釋說明,并提供和審查了全部圖片,耐心回答美方編輯在工作中提出的相關問題。
1986年出版的由戴文葆先生主編的《編輯工作基礎教程》,是我國有關編輯學的最早的教材之一。1988年,戴文葆先生親自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了“編輯”和“編輯學”兩項條目,這是我國早期較為全面、準確的有關編輯學內涵的界定。2006年,由戴文葆先生參與編輯并寫序的韓國著名出版家尹炯斗的《一位韓國出版家的中國之旅》一書中文本出版,并獲得亞太出版商聯盟頒發的“2007年度亞太圖書獎”金獎。
二、戴文葆編輯學思想概述
編輯活動雖與書籍相伴相生,但是編輯學卻并不是與之同時出現的。戴文葆先生將編輯學與編輯歷史相連,認為編輯這門學問“必先于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諸學。倘若沒有編輯編纂圖書,哪里來的目錄學、按本學、校勘學和輯佚學呢?”②戴文葆:《編輯學二三問題管窺》,《出版與發行》1987年第1期,第14頁。書籍出現之初,編輯應運而生,編輯思想和編輯事業也同步出現,編輯理論也隨歷代如孔丘、劉氏父子等編輯家的編輯活動不斷更新、進步。知識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并沒有編輯工作者將編輯過程中的思想理論編纂成書,因此雖然編輯學根底久遠,但依然是一門新興學科。
(一)編輯學的含義
戴文葆先生認為,編輯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及方法雖然還在探索當中,但是編輯早已是一種獨立的行業,也應將編輯作為一門系統的學問來研究。
對于編輯學的含義,戴文葆先生認為應先觀察“編輯”二字的意義。他將二字分別理解,“‘編’謂串聯皮筋或繩子。……‘輯’涵義甚多,原來謂車箱,用為泛指車子。但亦有聚集、收集之意”,以此總結出其對“編輯”的理解:“編輯是集合簡冊,排列次第,編聯成書的意思。”③戴文葆:《尋覓與審視》,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第401頁。“編輯學”中的“學”字,是“研討一門學科的本質特性和內在的固有規律,以及他在與外部事物相聯系中所具有的特征、地位與作用,經專業工作者在反復實踐中所發現,所證明,并有意識加以總結、提高、上升到理論,形成了一種比較完備的思想體系”④同③,第403頁。。所以編輯學屬于社會科學中的一個部門,是一門主要研究和闡述“促進學術文化發展的編輯工作的性質、過程及其規律性的學科”⑤同③,第403頁。。因此“編輯有學”,他對編輯學進行了如下定義:“編輯學是研究編印書籍、期刊、報紙和圖畫等類出版物以及利用聲音、圖像等宣傳手段的學問,特別著重選題、組稿、寫作、審核、加工整理及美術技術設計等環節。這些出版物及宣傳手段,是以提供知識,傳播信息,積累文化,交流思想為目的,而以文字、圖畫、符號、聲頻、視頻等記錄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述和創作,供人閱讀、聆聽、觀賞、收藏之用,旨在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造福人群。編輯就是生產這些出版物,運用這些宣傳手段的精神勞動者。”⑥同③,第341頁。
不過,戴文葆先生也強調,雖然編輯有學,但是編輯學的研究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需要編輯工作者與社會學、傳播學、法學等相關學者探討切磋,以此共同助力編輯學研究的發展。要做到這些,需要從收集大量資料和嘗試理論分析這兩方面著手。因此不應急于規定編輯學的框架結構或局限于各類范范的編輯學討論中,很可能徒勞無功。他認為,“要從編輯實踐中的各項具體問題,從編輯史的經驗教訓著手,現實與歷史相結合,工作經驗的總結,并升為理論,來逐步積累編輯學理論體系的素材,從而推進編輯學的研究”⑦同③,第393頁。。據此,戴文葆先生提出了當前編輯學研究的一些問題,包括“圖書的性質,編輯的含義,編輯工作與時代環境的關系等等,把這些問題討論清楚,從個別問題到總體設想的練習擺清楚,有材料,有分析,對于編輯學的研究才有幫助”①同戴文葆:《尋覓與審視》,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第393-394頁。。
(二)外部因素對編輯學的影響
戴文葆先生總結了在討論編輯學含義時應考慮的幾個主要問題,即外部因素是編輯學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第一,編輯學與其他各學科一樣,最早的極其簡單的編輯工作,其實是因當時社會統制的需要而產生的。也就是說,編輯學理論的研究具有政治性,其理論探討不能夠脫離社會政治和相應時代的風尚。第二,編輯學的發展也受學術文化發展的制約。“任何學科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②同①,第404頁。,這也決定了各類學科的本質屬性,使其產生能夠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立性,并生成自己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因此,編輯工作是有客觀規律的,“踐行編輯工作應有標準,掉到黑白,指鹿為馬,煸惑人心,羅織學罪的惡劣書籍,不論如何以勢怵人,終將化為灰燼,或回爐造衛生紙了。編輯工作中的這一規律,最值得在編輯學研究中發掘其髓,歸納為原理”③同①,第405頁。。第三,編輯活動是一種腦力勞動,其依靠人類思維活動為主,體現出分散勞動的特點。編輯學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發展和編輯技術的提高,應產生新的編輯學思維。第四,編輯活動既是一種精神生產活動,又是一種物質生產活動。編輯工作具有宣傳教育的功能,同時也是傳播發展的媒介。在此認識基礎上,就應充分考慮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可見編輯的任務和編輯學的研究任務變得更沉重且關鍵了。
(三)編輯學的研究對象、對象屬性和研究范圍
首先,戴文葆先生認為編輯學的研究對象可大致分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兩大類。細分后的作品,第一類是根據作品的形態不同分為原稿和經過加工的各類出版物;第二類按勞動特點劃分,即編輯學研究的對象“既是勞動者個人勞動的結晶,也是它得以成行的特定社會的產物。它受經濟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社會諸條件的制約,經過編輯的尋覓、發現和中介,經過整理印制,成為物化的精神產品”④戴文葆:《編輯學二三問題管窺》,《出版與發行》,1987年第1期,第14頁。。同時,戴文葆先生也認為,編輯學相對而言是一個“狹窄的部門”,主要從事精神產品的物化研究,由于精神產品具有社會性,勞動卻具有個體性,因此編輯在精神生產過程中發揮著極其特殊的作用。
其次,針對編輯學研究對象的特點,戴文葆先生將其屬性分為八點,即雜——社會性,范圍廣泛,無所不包;實——科學性,尊重客觀事實和科學成果;積——繼承性,文化積累依靠編輯出版和保存;公——服務性,文化藝術是世界人類共有的財富,都用來滿足各類讀者的多樣需求;新——啟迪性,作品應能夠傳播最前沿的科學文化成果,注重當代最新穎的、受大眾關注的問題;傳——開放性,一切作品都應廣泛傳播,不應“秘不示人”;優——可讀性,質量高的作品更能滿足受眾需求,且應把最好的內容用最好的方式呈現出來;美——藝術性,編輯活動是精神勞動,因此需要不斷追求作者語言描述之美、審讀加工之美與印刷裝幀之美。這些屬性在一部作品中并不是缺一不可,但都是一部作品所應具備的基本屬性。
最后,戴文葆先生將編輯學的研究范圍歸為六個方向。第一,編輯理論是編輯學研究的中心,“著重探討編輯工作的性質、特點及其內部活動的普遍規律。研究對待各類原告的特殊工作規律”⑤同④,第16頁。。第二,編輯學的縱向發展研究——編輯史。“整理總結前任所做的工作,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引出規律性的事例,為創建編輯學鋪底,以供繼承和借鑒。”⑥同④,第16-17頁。第三,編輯業務的研究,這是編輯學研究的落實。第四,編輯學研究的橫觀內容,包括作者、讀者、編者。第五,有關編輯學的延伸研究,包括版本、校勘、目錄、輯佚等學問的研究。第六,“宣傳、評論與推廣的關注,這是編輯學研究的繼續,也是編輯活動的延長與檢驗。”⑦同④,第17頁。
三、結語
戴文葆先生是我國研究并定義編輯學的先行者,其在編輯學領域的研究成果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研究材料。不僅如此,戴文葆先生還是研究編輯史的第一人,他的編輯史學思想也值得后輩不斷學習。他的研究成果能夠時刻提醒從事編輯工作的各位行業同仁,在現代媒體環境下不忘初心,牢記老一輩編輯學家的編輯工匠精神,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努力為編輯學的未來發展開創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