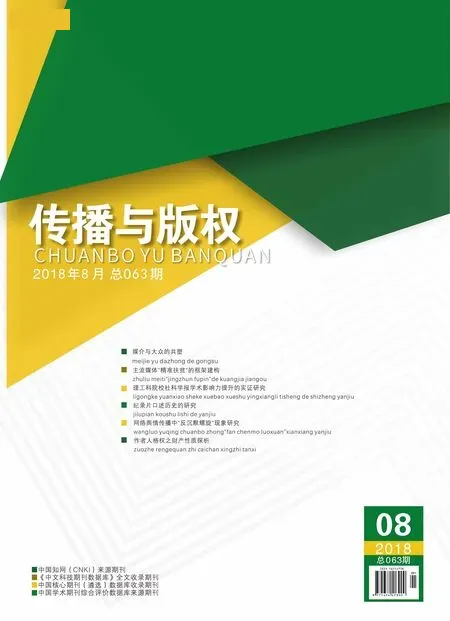執行有限原則對行政機關之適用研究
張 琦
司法執行是運用國家強制力將裁判文書等執行依據付諸實現的制度、是司法審判的延伸、是將紙上正義轉化為現實正義的最后一個環節。通過對裁判文書的執行不僅可以保護權利人的利益,迅速實現權利人的權利,而且還可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正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增進人民群眾對法治的信心。但當被執行人的全部財產不足以全部履行其所負的被執行義務時,司法執行的天平往往會向被執行人做出一定的傾斜,以保障被執行人基本生活的維持,這也是出于對人權保障與和諧社會維護的考慮,這種執行策略被稱作執行有限原則。然從規范的角度來看,在司法執行中能否對行政機關適用執行有限原則還有些模糊,有待進一步明確。
一、行政機關適用執行有限原則之邏輯前提
執行有限原則適用的范圍是司法執行中的被執行人,對行政機關作為司法執行被執行人的肯定是其適用執行有限原則的邏輯前提。而行政機關可否作為司法執行當中的被執行人,可從以下二個方面來理解。
(一)從被執行人的概念出發
被執行人是司法執行當事人中較重要的一方法律主體,要準確理解和把握被執行人的概念應從執行當事人著手。執行當事人是指根據執行依據確定的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即在執行程序中以自己的名義主張權利、履行義務并受執行法院的執行行為約束的利害關系人,[1]是執行法律關系主體之一,也是主要的執行法律關系主體。在執行當事人中,一方是執行權利人,有權根據執行依據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通過強制執行以實現裁判文書確定的實體權利,接受另一方履行的義務,而向權利主體履行義務的一方則為執行義務人,即被執行人,這是從執行法律關系的層面上講;若從裁判文書層面上講,被執行人即為裁判文書中所確定的負有履行義務的一方訴訟當事人,通常稱為債務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或者是第三人。我國法治發展到今天,在行政執法中服務行政的觀念愈加濃厚,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的合作互動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深;而同時公民的法治意識也愈加增強,在與行政機關交往中越來越多的公民通過行政訴訟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行政糾紛流入法院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這就表明行政機關作為一種潛在的訴訟當事人,無論其是原告還是被告,均有可能被法院的裁判文書確定為負有履行義務的一方訴訟當事人,進而成為潛在的被執行人。
(二)從法律制度的發展來看
司法執行作為將紙上的正義轉化為現實的正義的最后一個環節,其本質涉及法律規范中所確立的公民權利在現實中得到真正兌現。在過往司法實踐中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占絕對優勢,與行政機關有關的社會糾紛很難走上司法途徑來解決,從每年法院行政審判庭結案數量與民事審判庭結案數量的對比中就可略見一斑,更不用說根據司法裁判對行政機關進行司法執行了。但“法律隨著它所調整的那個社會運動的主流向前發展。每一個社會都有他自己的必然會通過法律秩序力圖實現的目標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念”,[2]而如今隨著社會的發展,服務行政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另外公民的法治意識和依法維權的能力與過往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有越來越多的與行政機關相關的社會糾紛進入司法機關,而司法機關對這些糾紛的裁判中更多的是給行政機關確定了履行義務。這就表明司法執行制度也應隨著人類對法治價值觀念的演變而不斷變化。因此,為了保護權利人的利益,迅速實現權利人的權利、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正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增進人民群眾對法治的信心,將行政機關為作為司法執行中的被執行人理應是當下法治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
綜上所述,對行政機關可否作為司法執行中的被執行人的問題,應毫無疑問的給予肯定,這也是其適用司法執行中執行有限原則的邏輯前提。但這并不是行政機關在司法執行中適用執行有限原則的充分條件,若要在司法執行中對行政機關適用執行有限原則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二、執行有限原則對行政機關之適用分析
(一)行政機關適用執行有限原則的可行性分析
從規范的角度來看,雖然我國行政法律規范并沒有明確規定行政機關適用執行有限原則,但對此命題的探討我們可以從民事法律中尋找有益經驗。
執行有限原則在我國現有的法律規范中已有體現。《民事訴訟法》第243條和第244條均規定,為了讓被執行人及其家屬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在司法執行中應對其保留必要的生活費用,另外,《民事訴訟法》第257條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對部分被執行人員裁定終止對其的司法執行,即當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無收入來源又喪失勞動能力,卻因生活困難而無力償還借款時,人民法院可以裁定終止執行。這是《民事訴訟法》對執行有限原則的具體表述,而在《刑事訴訟法》中也有執行有限原則的體現。《刑事訴訟法》第219條規定當罪犯確因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而對被判處的罰金不能繳納時,可以裁定減少或者免除。這是《刑事訴訟法》在執行標的上對執行有限原則的體現,在執行方式上《刑事訴訟法》對執行有限原則亦有體現。《刑事訴訟法》第214條規定了監外執行,主要是針對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生活又不能自理,且適用暫予監外執行并不會危害到社會的罪犯,這正是為了保障被執行人能夠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而對執行方式進行的調適,也是《刑事訴訟法》對執行有限原則在中執行方式方面的體現。
(二)行政機關適用執行有限原則的必要性分析
從保護執行依據中權利人的權益來看,執行依據中負有執行義務的一方當事人的所有財產均可作為金錢請求權的執行標的,但從保障人權與維持社會和諧的角度來看,在司法執行中當被執行人的全部財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時應先給被執行人留足維持其基本生活的物質,再對其剩余財產進行司法執行。這在民事司法執行中已被普遍接受,且民事訴訟法對此也有明確的規定,然行政機關的運轉也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對行政機關的司法執行仍應有所保留以免影響其基本功能的發揮。況且公益往往重于私益,對行政機關執行標的的保留形式上看是為了保障行政機關基本功能的運行,實質上則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維護,因為行政機關的運轉目的就是為了給廣大人民群眾提高公共服務。因此需要強調和說明的是執行有限原則作為司法執行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不僅適用于公民這一被執行主體,當行政機關作為被執行人時更應適用。對此在我國臺灣有經驗可供借鑒,臺灣《強制執行法》又規定“公法人經營之事務,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其所管有之公用財產,如為推行公務所必須或其轉移違反公共利益者基于公益重于私益之原則,并避免影響公務之推行或損及公共利益,自應予以限制,不得為強制執行”。即推行政府公務所不可缺少的財產不可被強制執行,比如各機關辦公廳舍、作業及住宿等場所,電話及其他辦公設施等。
因此,基于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人民權益的最大保障,司法執行中的執行有限原則應同樣的適用于行政機關。但是結合我國現有的行政法律規范來看,并非如此。
三、行政法律規范對執行有限原則規定之不足
行政機關作為執行依據中的債務人理應成為司法執行的潛在對象、執行有限原則作為司法執行的一項基本原則,在司法執行中理應對所有的被執行人適用,這已是毫無疑問的。但依法執行是法治理念在執行領域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國的行政法律規范對此確缺乏必要的規定,這主要體現在執行有限原則對行政機關的適用上。
從行政訴訟法中關于司法執行的相關規定中看,我國的行政訴訟法中并未規定行政機關可以作為司法執行程序中的被執行人,更談不上執行有限原則對行政機關的適用了。但前面已經闡述,雖然《行政訴訟法》并未直接規定行政機關可以當作司法執行中的被執行人,然將《行政訴訟法》第101條與《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定相結合可推出行政機關仍屬于司法執行中被執行人的范疇。以這一邏輯來推導執行有限原則對行政機關的適用則是人們的慣性思維,然這種慣性思維并不能解決執行有限原則對行政機關的適用問題。具體來說,雖然《民事訴訟法》第243條和第244條均規定司法機關對被執行人進行強制執行時,為了保障被執行人及其家屬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而應對其保留必要的生活費用,表明了對被執行人執行時要適用執行有限原則,考慮被執行人的基本上需要,但根據這兩個條款的具體表述來看,這里表述的執行有限原則僅適用于普通公民這一類被執行人,并不適用行政機關這一特殊的被執行人。因此,并不能簡單的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01條將執行有限原則適用于行政機關這一特殊被執行人,這也表明執行有限原則能否對行政機關適用目前處于立法空缺的狀態。
四、結語
司法執行基本原則是在漫長的司法執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基本規范,它集中體現了司法執行的基本原理,反映了司法執行的內在價值和特有規律。執行有限原則作為司法執行原則中的一項子原則,理應貫穿司法執行的全過程,適用于每一個被執行人。因此,行政法律規范有必要對行政機關作為被執行人時是否適用執行有限原則作進一步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