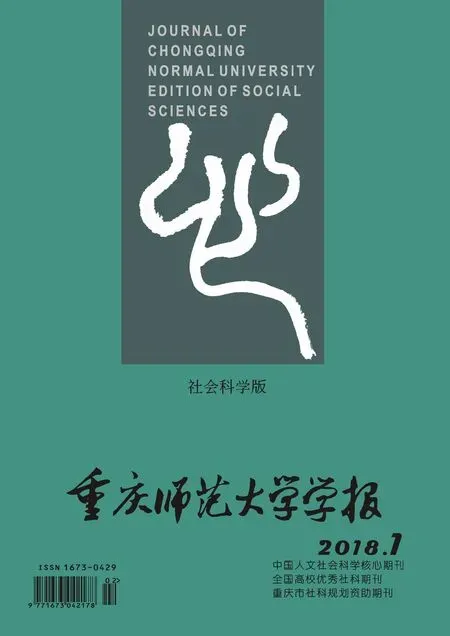視點聚焦、鄉土認同與男性想象:陪都電影女性敘事的三個維度
董 廣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1331)
革命敘事作為一種宣揚意識形態的政治化存在,發軔于20世紀20年代,貫穿于20世紀上半葉,在左翼文學與革命文學中得到廣泛運用,成為“具有政治浪漫主義色彩的‘革命傳奇’”[1],其積淀的歷史經驗恰好契合于陪都電影對戰時重慶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一直以來,學界對陪都電影的研究往往止步于其宏大敘事及其所蘊含的價值訴求或呈現的美學特征,而忽略了陪都電影在理論與實踐中形成的“木蘭從軍”(女性革命敘事)、“革命的羅曼蒂克”(女性愛情敘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長敘事)三種敘事模式,以及女性敘事在視點聚焦、鄉土認同與男性想象三個維度上的顯現。實際上,陪都電影對“革命敘事”經驗的承襲及其對女性敘事效用的發掘形成了其特定的“表象”,成為特殊時期革命敘事話語的新規范,雖在本質上仍是革命敘事的“同質異構”,但卻具有深刻的電影敘事學價值及電影史意義。
一
陪都電影的社會歷史語境及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宣揚顯然與西方經典敘事學的語言結構欽慕失當。西方經典敘事學對特定社會歷史語境的無視和對文本曲射意識形態的忽略使陪都電影及其創作者們集體將敘事視角轉向了女性主義敘事學,并著重強調文本在公共政治參與、社會秩序及話語權建構上的價值與意義。這種敘事視角的選擇,是對性別、語境、意識形態與陪都電影互動關系的一種觀照。毋庸置疑,救亡圖存理所當然地應是抗戰時期陪都電影的元敘事,即敘事的焦點勢必與戰爭親昵。與戰前相比,陪都電影的創作者們因抗戰的發生實現了個體由空間體驗向心理體驗的位移,并自覺完成了對陪都重慶主流意識形態的接納,成為陪都電影頻繁地選擇將敘事視點聚焦于女性的重要源由。
戰時體制需求下的陪都電影賦予了原本受制于男性賞玩之女性以男性同等的社會身份。《青年中國》《中華兒女》《八百壯士》將敘事視點聚焦于“女兵”。《青年中國》中,以女兵身份出現的女主人公沈曉霞憑借其性別優勢成功勸說農婦李母道出村民的隱藏地點;《中華兒女》中,入伍不久的女隊員主動請纓破壞敵方重要交通線;《八百壯士》中,女童子軍楊惠敏冒著生命危險給守軍輸送食物、醫藥等物資……“士兵”本是傳統的男性化身份符碼,但在這幾部電影中,女主人公的性別身份并未被掩飾。這就意味著女性在陪都電影中不再是取悅男性的伎倆,而是被賦予了與男性同樣的社會身份。《火的洗禮》將敘事視點聚焦于敵偽女特務。在影片中,敵偽女特務方茵摩登化出場,在燈紅酒綠的生活中搜集情報,行動受挫后便化身為女工阿瑛。在“阿瑛”的身份掩護下,她騙取了兵工廠工人老魏的愛情。但面對工人全力支援抗戰而忘我生產,目睹無數百姓因敵機轟炸而傷亡。她主動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協助當局搜捕潛伏在重慶的敵偽間諜,最終身負重傷,贖罪而死。《勝利進行曲》將敘事視點聚焦于普通農婦,通過普通農婦的抉擇強化了陪都重慶的主流意識形態,激發了普通民眾的抗戰熱情。異國男性暴力入侵下的女性往往成為侵略者的“戰利品”,淪為被男性賞玩的純粹工具,其地位被進一步邊緣化、“他者化”。而陪都電影賦予了女性身體以民族大義,成為砥礪抗戰的媒介工具。與城市女性相比,農村女性缺乏必要的軍隊庇護,受侵害的程度遠遠高于城市女性。對她們而言,確保身體不被侵害即是對革命的忠誠及對革命氣節的捍衛,即“反對敵寇奸淫,寧死不屈,誓死保持民族氣節、婦女貞操”[2]788。《勝利進行曲》中的農婦面對敵軍的性侵,誓死反抗,并與敵人同歸于盡。農婦的選擇保全了自身的貞節,詮釋了以“身”報國,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民眾“如何在自己本位上努力”。
無論將敘事視點聚焦于“女兵”、敵偽女特務還是普通農婦,陪都電影始終沒有與女性脫離干系,而是與戰時體制下參與任何形式革命的女性休戚與共。“女性與革命,無論作為現代中國性別研究的話題,還是作為反省革命的方法,其所包含的從性別角度考察革命,以及在革命語境中體察性別的特性,都將成為考察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性狀況的有效命題。”[3]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已嘗試將性別敘事融入其中,對陪都電影來說,這顯然是一種歷史經驗,女性之于革命的價值為此在其中也得到了突顯。將敘事視點聚焦于女性貌似是陪都電影創作者們的一場“蓄謀”,在他們手下,女性不再是內斂、柔弱與依附的象征,而是融入了主流話語體系,且獲得了身份認同的主體。陪都電影創作者們在影片中將女性的價值觀念調焦至國家民族層面,自覺引導著陪都重慶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陪都電影在將敘事視點聚焦于女性的同時,也對鄉村、民眾及巴渝重慶的鄉土人文作了適當呈現,無形中暗含著女性敘事的社會效用和對鄉土中國的隱形認同。
二
“城鄉對立”的隱喻不乏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中。與具有“繁華之所”與“罪惡之都”雙重隱喻的城市相比,鄉村在電影創作者眼中形成了兩種極端的空間想象:一種是貧窮與愚昧,一種是自由與舒適。這兩種空間想象實際上都是對鄉土中國局部特質的舛訛放大和認識偏頗。電影工作者們因為抗戰的爆發被迫遠離城市,向鄉村遷徙,向鄉土中國的空間體驗貼近。在這個過程中,陪都電影創作者們重新將集體訴求轉化為個體經驗,使鄉土認同成為女性敘事之維。他們立足于開掘巴渝重慶本土資源,選取鄉土化的敘述,實現了對鄉土中國的隱性認同,同時完成了女性敘事之于主流意識形態言說的使命。
抗戰前的女性很大程度上僅為男性玩賞、審視的對象,被貶抑為現代民族國家中的“他者”。她們一直苦苦找尋著進入主流話語言說體系的途徑,但又一再被擯斥于外。抗戰的爆發,尤其是自國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遷都重慶始,陪都女性最先贏得了建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機會。陪都重慶也成為了國家民族集體訴求和抵御外侮的精神支撐,對巴渝重慶的鄉土認同即意味著對鄉土中國的隱性認同。巴渝女性自古多豪放不羈、勇敢正義,先后兩次率兵抗清的石柱總兵、明末封侯女將秦良玉便是其中的典范。《明史》卷二百七十載秦良玉“為人饒膽智,善騎射……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兼通詞翰,儀度嫻雅。”其事跡亦被國民革命軍將領馮玉祥稱道,提出“紀念花木蘭,要學秦良玉”,更是被后來的郭沫若譽為“石柱擎天一女豪,提兵絕塵事征遼。”陪都電影創作者們既發掘了陪都重慶的鄉土資源,又領略著鄉村女性的潑辣兇悍。于是,他們便將對巴渝重慶的鄉土體驗滲入創作,一個個“花木蘭”躍然紙上,一個個“秦良玉”再度演繹。沈西苓導演的《中華兒女》中,第四個故事寫總部命令青年游擊隊長破壞敵方重要交通線,而隊長不知所措。此時,剛入伍的女隊員主動請纓,由她扮為鄉下姑娘引開敵軍哨兵,最終,成功掩護游擊隊順利完成任務。《八百壯士》中,女童子軍楊惠敏不顧生命危險,為部隊輸送食物、醫藥等物資;《東亞之光》中,政治部婦女工作隊進行了征募寒衣公演;《血濺櫻花》中的立群積極參加難童救護隊;《孤城喋血》中,老農的女兒冒險為姚營長傳送情報……在陪都電影中,女性往往憑借其特有的性別身份從事著超越性別的革命事業,演繹了一個又一個“木蘭從軍”故事。
如果說巴渝重慶鄉土資源的運用是女性敘事鄉土認同之維的天假其便,那么鄉土化敘述顯然是女性敘事鄉土認同之維初衷實現的命運使然。革命文學的開初曾出現過窘態,即“革命的意識形態愿望與其語言的貧困構成驚人的歷史悖論”[4],而后通過文學的“革命”開始將視野轉向鄉土農村,從中汲取資源。與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將農民視為“中國前現代性的代表、被啟蒙的對象”[5]不同,陪都電影創作者們吸取了歷史經驗,起初便將農民融入了其創作實踐。他們毫無例外的在影片中將視線聚焦于農民,以農民的視角講述農民的故事。象征貧窮愚昧的農民史無前例地被抬高為救國者,抗戰熱情得到極大鼓舞。
史東山編導的《好丈夫》以普通農婦的視角貫穿故事始終,是農村影片宣傳的典范之作。影片中,正值四川某縣壯丁“復抽”,村民劉四、王鏢被抽中,去前線為國效命。當時的社會存在一種現象,即一般“有財力有勢力之人士,與不肖士紳之子弟雇工等,多不應征”,鄉紳潘老爺之子便是其中之一。劉四之妻四嫂得知保長故意偏袒緩役且未繳納緩役金的鄉紳潘老爺之子后便告訴了王鏢之妻二嫂,不識字的二嫂糾集一群人去質問保長,哪知卻被反誣。二嫂一怒之下便請某先生寫信向王鏢告不平,而先生實際上寫的卻是勉勵之詞。恰好縣長次日來慰問軍屬,二嫂極力為自己辯白,便將此事和盤托出,哪知縣長卻責令調查鄉紳潘老爺之子,并沒有“官官相護”。二嫂急忙尋找昨日代書先生,見先生醉酒又急忙尋他人寫信鼓勵丈夫奮勇殺敵。故事情節雖簡單,卻蘊含著宣傳兵役這個極為鮮明的主旨。為使影片適應農民的觀影習慣,通俗易懂,導演用字幕代替聲音,用“誤會”制造高潮,用長鏡頭和跟鏡頭再現“妻子送郎上戰場”。“它所采取的題材是描寫農民的,而且從它的導演手法上看也確然可以看得出是為了供給文化水準低落的農民大眾所觀看的。導演史東山先生在制作這部影片時的苦心,在整個畫面上有著最好的說明。中國的農民大眾,他們的文化水準一般地低下,對于電影這種新興藝術的欣賞能力是不夠的”[6]。陪都電影創作者們在電影技法的使用上突破了自我想象,力圖以農民的心境促成農民的醒悟,以達成對陪都重慶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但戰時體制下陪都電影中的女性敘事在視點聚焦與鄉土認同之維的效用,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能是男性的一種革命想象。
三
20世紀20—30年代的革命文學因缺乏性別敘事的范本與經驗,往往束手無策選擇將女性“去女性化”,使女性淪為革命敘事的單純媒介工具、無實質性內涵的“空洞的能指”。而實際上,“能指”本身并不“空洞”,它通常在“具體的、歷史的語義結構關系中展開意指過程”[7]。陪都電影以女性敘事的視角,通過性別與政治語境的關系互動完成了女性生物屬性向男性社會屬性的位移,從而實現了女性性別身份的自我認同。然而女性這一能指的“所指”在陪都電影中被系縛于抗戰救國的主旨,女性的這種自我認同實際上只是男性指涉的自我認同。在陪都電影中,女性面臨著男性視閾與社會視閾的雙重“鏡像”:“一是男性視閾所要求的客體——一個被欲望對象的本質化“女人形象”,二是社會視域所要求的客體——和男人一樣在公共空間闖蕩的中性化的主體,甚至說一個類男人的準主體。”[8]雙重“鏡像”下的女性實質上是陪都戰時體制下男性的革命想象,而女性敘事的社會效用歸根到底也是依托男性的革命想象而達成的。陪都電影中的女性愛情與革命、女性成長與革命所分別呈現出的“革命的羅曼蒂克”和“娜拉出走”傾向顯然是男性想象下的影像寓言,也是對“革命+戀愛”創作模式的覆前戒后。
“革命和愛情是描述中國現代特征的兩個非常有力的話語。愛情至少包含個人的身體經驗與性別認同,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的一種自我實現;革命指稱的是進步、自由、平等和解放的軌跡。”[9]“革命+戀愛”模式曾流行于左翼文學與革命文學中,創作者們在作品中充滿浪漫激情的論證“革命”的合法性,力圖說服民眾參與革命并為之付出代價。雖然這種模式使革命文學“用‘想象的邏輯’‘光明的尾巴’使它們介入現實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是鏡中之行”[10]328,但卻使文學的“武器”功用得以凸顯。有鑒于此,陪都電影在“革命的羅曼蒂克”的女性敘事中完成了性別與政治的互喻,使女性成為男性視閾下身體欲望的對象。在《長空萬里》中,幾名男性對女主人公白嵐暗生愛慕之情。當被問及是否有心上人時,白嵐的回答出人意料:心上人有兩個,一個是長白山的風,另一個是中國空軍。在面臨愛情與革命的抉擇時,她又用歌聲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愿自己永遠是風,吹醒癡男怨女的甜夢;吹破亂臣賊子的鼠膽;每天浮載著凌空的鐵翼,吹吻著空軍健兒褐色的臉面;當侵略者前來吞噬我們時,暴風起來,卷起抵抗巨潮,吹送著空軍健兒為民族的存亡,為世界的自由平等而抗戰……”與以往影片不同的是,作為男性欲望對象的女性首次被賦予了愛情的主動權,而卻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決然放棄。《塞上風云》也上演了一出“革命的羅曼蒂克”。美麗善良的蒙古族少女金花對丁世雄一見鐘情,并展開了熱烈追求,而蒙古族青年迪魯瓦卻熱戀著金花。因為金花,迪魯瓦與丁世雄產生了矛盾。一方面,迪魯瓦以其直率、粗獷的方式追求著金花,劇本中寫道“迪魯瓦愣了一下,催馬追過去,在金花快進入羊群時,他追上她,側身哈腰,伸出有力的臂膀,竟將金花提抱到馬上。”而另一方面,金花又大膽向丁世雄示愛。若三人感情任由發展,很可能會造成蒙漢裂隙。為迎合陪都重慶的主流意識形態,劇作者安排代表男性欲望的金花犧牲。“欲望”消失后不久,迪魯瓦便與丁世雄和解,共同走向抗日的征途。社會視閾下的女性在陪都電影中往往與男性“統一性別”,體現出了女性革命敘事的“娜拉出走”傾向。影片中的每一個“娜拉”或直面抗戰的艱難,或經受苦難生活的經驗,或察覺自身的重擔,而后從思想和行動上“出走”,構筑了一個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的影像寓言。《好丈夫》中的二嫂開始對丈夫服兵役有怨言,因縣長對“誤會”的處理而轉向鼓勵丈夫奮勇殺敵。《白云故鄉》中的陳靜芬因未婚夫白侃如抗日工作繁忙轉而將愛情幻想投向賦閑在家的林懷冰,而林懷冰卻被交際花間諜金露絲所誘惑。面對林懷冰對愛情和抗戰的雙重背叛,靜芬幡然醒悟,心中的“娜拉”出走,轉入抗戰工作。成長之于二嫂、靜芬,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主體性的缺失。無論是自我覺醒還是迫于無奈,她們都通過“娜拉出走”在思想與行動上完成了角色身份由“本然”向“應然”的轉變。
在陪都電影中,女性往往在抗戰救國的感召下,從束囿自己的家庭中出走,憤然走上革命的征途。實際上,女性的成長在更大程度上應體現為對個性解放的追求。但在陪都戰時體制下,其愛情與成長被程式化地讓位于抗戰的需要,并被創作者賦予了超文本的意蘊和內涵。正如詹明信所說:“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11] 523陪都電影中的女性不再是單純的性別身份,而是社會價值系統中的關鍵一環。女性在雙重“鏡像”下成為空洞的能指,成為身份認同的癥結。對男性革命者而言,女性成為抗戰背景下的“一種無助心理下的悲情想象”[12],為革命而棄愛的“木蘭”和出走的“娜拉”,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驅使與想象下的“寓言故事”。女性承擔的角色及陪都電影女性敘事的效用都是一種預設的男性想象。
陪都電影中的女性敘事所采用的“革命的浪漫蒂克”和“娜拉出走”模式,既是對二十世紀左翼文學與革命文學經驗的揚棄,又是對戰時重慶性別與革命關系的潛心考察。女性敘事在陪都電影創作者們手中通過視點聚焦、鄉土認同與男性想象三個維度,被嫻熟地用于對女性之于革命效用的發掘和陪都重慶主流意識形態的宣揚,形成了新的革命敘事話語規范。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既是對電影敘事學價值與視野的開拓,也是對陪都電影史廣度與內涵的襯映。遺憾的是,無論從視點聚焦、鄉土認同還是男性想象任一維度看,陪都電影及其創作者們顯然將女性敘事的效用聚焦于政治革命。“木蘭”與“娜拉”意味著女性性別話語的架空,女性性別通過革命敘事進行重建的理想化為泡影。在陪都電影中,女性往往成為戰時重慶主流意識形態宣傳的媒介符號和男性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實這都是創作者們出于男性與革命視角的一種考量。實際上,陪都電影并沒有脫離革命敘事的樊籠,其女性敘事的模式傾向與維度顯現在本質上仍是革命敘事的“同質異構”。
[1] 逄增玉.志怪、傳奇傳統與中國現代文學[J].齊魯學刊,2002,(5).
[2] 全國婦聯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G].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3] 楊聯芬.女性與革命——以1927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J].貴州社會科學,2009,(2).
[4] 陳曉明.鄉土敘事的終結和開啟—賈平凹的《秦腔》預示的新世紀的美學意義[J].文藝爭鳴,2005,(6).
[5] 傅異星.知識的神話:啟蒙話語的敘事遮蔽[J].中國文學研究,2008,(3).
[6] 葛一虹.從《華北是我們的》與《好丈夫》說到我們抗戰電影制作的路向[N].新華日報,1940-2-22.
[7] 賀桂梅.“可見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為中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3).
[8] 孫桂榮.在社會視閾與男性視閾的雙重“鏡像”下——對當代文學中“性別與事業”沖突主題的文化解讀[J].南方文壇,2006,(2).
[9] 劉劍梅,郭冰茹.革命加戀愛:政治與性別身份的互動[J].當代作家評論,2007,(5).
[10] 周曉明,王又平主編.現代中國文學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1] 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闡釋[M].張京媛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
[12] 王家康.孤島時期阿英及其他作家歷史劇中的女性敘事[J].文學評論,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