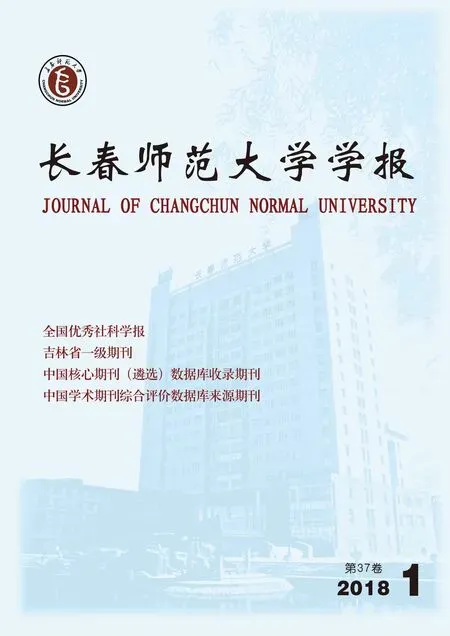略論蘇紳入仕后的政治作為
張奚銘
(長春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032)
蘇紳,字儀甫,初名慶民,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唐末自祖益來到福建,出任漳州刺史,卜居泉州。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中進士,歷任宜州、復州、安州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在此期間,其母謝世,丁憂期間因文采斐然而名聲大震,隨后舉賢良方正科,升任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不久調回京師,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學士,后又遷尚書禮部郎中。因其舉薦的官員馬端告發生母一事而受牽連,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尋恢復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復因上言王德用“貌類藝祖,宅枕干岡”,引起皇帝不悅,不久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未履任而病卒,卒年四十八歲。
一、上疏安化與西北戰事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安化地區少數民族暴亂,寇宜、融等州亂民屠殺當地官吏,“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皆死”[1]宋紀四十一。蘇紳上疏指出解決這次暴亂的迫切性,并提出了具體方案。
首先,認為安化地區地廣人稀且經濟落后,暴亂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家把主要精力用在北方邊防,對南方的留意不夠。“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2]列傳五十三。此外,前任主管官吏嫉賢妒能,錯失解決該地區少數民族問題的最佳時機。“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殺所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2]列傳五十三安化地區的地理特點決定了大規模兵力迅速肅清暴亂存在很大難度。“所恃者地形險厄,居高臨下,大軍難以并進”[2]列傳五十三。
其次,提出解決該地區暴亂的最有效手段。安化地區地形險要、易守難攻,但當地資源匱乏,“壤土磽確,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糇糧”。蘇紳提出用“緩圖”代替“速取”的戰略:“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具體戰術上,蘇紳認為應當調集習慣在類似地區作戰、熟悉暴亂者所用兵器的部隊和將領至安化地區參戰,替換當地原有的不熟悉對少數民族作戰的部隊。“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誼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準備足夠參戰部隊食用數年的糧食,然后堅壁清野,封鎖暴亂者的出路,并且在適當的時候出兵破壞暴亂者的物資。為了達到徹底孤立暴亂者的目的,還應當對周圍地區的其他少數民族有所行動,“諭以朝廷討叛之意”,要求他們“毋得相為聲援”,且“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只要以上條件都滿足,不僅安化地區的暴亂可以在一年以內平叛,整個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騷亂都可以得到有效的震懾,“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2]列傳五十三。
蘇紳對這次“安化蠻叛”事件所提出的解決策略,不只是軍事打擊,還包括對該地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孤立,獲得了很好的效果,這得益于蘇紳對安化地區情況的了解。宋真宗基本按照蘇紳上疏進行了平叛,“明年正月辛亥,廣西鈐轄司奏安化州蠻平”[1]卷一百二十三。但是,蘇紳上疏之中所言“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則有些夸大,不久之后宜州地區再次出現叛亂證明了這一點。
關于西北地區對西夏的用兵問題,蘇紳也有上疏表達自己的觀點。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北宋西北地區的西夏政權反叛。蘇紳上疏《論西北兵事疏》,提出了守不如攻的建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于十年矣”。同時,針對西北地區北宋對西夏的軍事部署,蘇紳認為存在著嚴重的不合理之處,并提出整改措施:“今邊兵止備陜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鄜、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沖,而屯兵眾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陜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于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藉”[1]宋紀四十二。
就當時西北的形勢來看,蘇紳上疏所強調的守不如攻的戰略是錯誤的。北宋軍隊以步兵為主,而西夏軍隊的主要構成是騎兵,并且控制了天然屏障——河西走廊。在冷兵器時代,步兵在不占據地形優勢的前提下與騎兵對戰處于明顯的劣勢。兵法上雖有“以攻為守”一說,但需要結合實際情況而定。結合之后西夏進攻的現實情況來看,蘇紳指出的西北地區軍事布防存在的問題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北宋一朝對少數民族作戰失利的原因眾多,并非單靠軍事部署的完善就能解決,對西夏作戰也是一樣。蘇紳在上疏中提出多增加弓箭手,在隨后的軍事部署中得到落實,但于大局無補。蘇紳從文臣的角度構思具體戰略戰術,再加上其對西北情況不了解,可行性大打折扣。
二、對政府存在問題的建議
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蘇紳向宋仁宗上疏《陳便宜八事》,提出八點意見:一曰重爵賞,二曰慎選擇,三曰明薦舉,四曰異服章,五曰適才宜,六曰擇將帥,七曰辨忠邪,八曰修預備。
重爵賞,即用爵位和賞賜來獎勵對國家有功、有德的人,沒有功勞和品德的人就不應該食厚祿、享美名。官爵和賞賜不能隨便給予,賞罰不合理甚至會導致災禍出現。“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3]卷六十六。
慎選擇,針對的是北宋時期一個嚴重的問題——冗官。大量無用官員的存在使政府機構過度膨脹,且官員升遷門檻太低,對官員的激勵作用大打折扣。“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并甄祿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3]卷六十六。
明薦舉,針對兩個問題:第一,薦舉上來的人主要得益于關系和勢力,而非才能;第二,現行的選任制度過于苛刻,可以薦舉為官的難度越來越大,造成通過關系勢力被薦舉的人沒有自勵,更多的有識之士被滯留在底層。“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歡也”。
異服章,即朝班中有技術的人應當和普通官員在服章上有所區別。這體現出對賢才的特殊禮遇,也是對朝堂儀式的一種完善。“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
適才宜,即用人應當不拘一格、靈活變通,保證一些有特殊才能的能人能得到重用。“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非才實者并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
擇將帥,即選擇將帥不應當以官員是否為武將為標準。歷史上很多有名的將領出身于文官,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武舉能夠提供的人才是有限的,讓一個人同時擅長武藝和韜略并不現實。因此,“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必人才弓馬兼書算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為用也”。
辨忠邪,即奸臣當政,必然會陷害忠良,進而破壞朝廷和國家;如果能夠去惡,就能過保證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而對朝臣忠邪的判斷,只能靠皇帝的辨察。“夫忠賢之嫉奸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奸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愿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
修預備,即在饑荒、瘟疫所帶來的流亡問題比較嚴重的情況下,禁止土地兼并,寬徭薄賦,提倡節儉,減少冗官,務實為主。“欲民之利,則為之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凋偽之原,則國食足矣”[3]卷六十六。
以上八點建議都與官員選拔有關,說明蘇紳上疏的核心思想就是完善選官制度、革新選官思想。蘇紳這份上疏的時間是在西夏反叛后的第一年,此時的北宋北方邊防告急,而且政府中出現了“冗官”現象,造成了人才的浪費和巨大的財政負擔。蘇紳強調,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糾正目前政府運作中的錯誤,從選拔官員制度入手,任用賢才,分辨忠奸,尤其是選拔人才時不能墨守成規。
宋仁宗在位初期,出現了一些比較反常的自然現象:流星,并州、代州地震,入春即響雷等。蘇紳以此為契機,向仁宗上疏《以災異言政事疏》,勸其改變朝中部分官員過分左右朝政,甚至架空皇帝決策權的狀況。
蘇紳把流星的出現看作星星對“天”的背叛,同時用這二者的關系比喻皇上與臣子的關系,進而得出這一自然現象實際上是皇上與臣子關系發生波動的一種反映,希望皇上引以為戒,留心觀察。“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惑,先示其象。陛下既袛畏天誡,則宜推原其本,而預修其備……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
蘇紳以陽比天、以陰比地,認為如果以陰犯陽,就會出現地震。這種“以陰犯陽”暗示臣子之中有超越權限行事的人,甚至存在隱瞞皇上的行為,這是必須要糾正和制止的。“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有越陰之分,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無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兇于而國,是也……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改。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于上,而請托異已行于下矣……此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于下也”。
至于入春即響雷,蘇紳認為這是上天對皇帝的一種警示。雷響意味著雨至,皇帝應當盡早發出強有力的號令,采取有效的措施,解決朝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又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邪除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于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1]宋紀四十一。
蘇紳在上疏中運用傳統的“天人感應理論”將流星、地震、春雷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相聯系,并非牽強附會,而是一種利用適當時機對當朝皇帝進行規勸的策略。“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
“萬物一體”是北宋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先秦儒家哲學中“天人合一”的延續。“萬物一體”的哲學命題分為天道觀和人道觀兩部分。天道觀強調人對周邊世界進行不斷的觀察、了解,提倡積極進取的心態。人道觀以天道觀為基礎,強調自身的修養和完善。從整體來看,“萬物一體”強調人提高自身修養,把自己與整個世界聯系起來。蘇紳借用自然現象向皇帝提出整改朝政的方式,正是受當時主要哲學思想影響的結果。
三、從黨爭的角度看蘇紳與諫官
蘇紳的上疏有對朝廷諫官的批判之辭,這是由北宋特殊的體制決定的。北宋設御史臺為監察機構,御史大夫為最高長官。元豐改制后不再設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便成為御史臺最高長官。北宋時期御史的職責是 “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可以對懷疑的官員提出“廷辨”,也可以直接“彈奏”。
諫官一職在北宋之前即已存在,且基本形成體制。北宋初年設置了獨立的諫官機構——諫院,但此時的諫院形同虛設,諫官主要集中在中書省、門下省。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以后,諫院成為常設辦事機構,隸屬于門下省。諫院諫官與兩省諫官逐漸拉開差距,諫院諫官成為主體,但人數一直不多,多則四人,少則兩人。諫官最初的職責是規勸皇帝;天禧元年以后,諫官與御史并重,合稱“臺諫”,實際上把諫官的監督權限擴大到了監察系統,不僅能議論時政、彈劾百官,甚至有了“風聞言事”的特權。
在這一背景下,以王素、歐陽修為首的諫官成為蘇紳的抨擊對象。借京師地區出現干旱天氣之機,蘇紳上《久旱言政事疏》,對諫官越職行為進行了指責。他援引《尚書》中的《洪范》篇,強調國家的大政方針應當出自皇帝,而不是某些臣子,皇帝需要睿智并善于洞察。“《洪范》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旸。蓋言國之號令,不專于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嘩憤亂,故其咎僭”[2]列傳五十三。當朝廷出現“移權于下”的情況時,就會出現異常的天氣,這是上天對皇帝的警示。“今朝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逾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于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袛,殆非天意”。蘇紳并未直接提及諫官過錯,但其指向已非常明顯。這遭到歐陽修等主要諫官的忌恨,成為后來歐陽修等人上言攻擊蘇紳的導因之一。
歐陽修上言攻擊蘇紳的緣由是一個由蘇紳推薦的名叫馬端的官員勸其母親將私藏的銅器上交,馬母不肯,馬端最終舉報了自己的母親。此事證實以后,馬端的母親遭受了杖脊之刑。歐陽修借攻擊馬端“不孝”的機會,一并攻擊蘇紳舉薦非人之過。歐陽修上言:“端性險巧,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于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奸邪,天下共惡,視端人正士如仇讎,唯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丑惡,人孰不知!而紳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爾。此一事尚敢欺惑人主,其余讒毀忠良,以是為非,又安可信!伏乞寢端成命,黜紳外任,不可更為令人主侍從。紳由是黜。”[1]卷一百四十二
馬端告發其母親是因為其母私藏銅器,這本身是維護法律的行為。然就孝道而言,馬端告發生母又是不孝的行為,因此被歐陽修抓住了話柄。這一事件存在著忠孝之間的矛盾沖突,并非歐陽修所說“端性險巧”這樣簡單。蘇紳并未參與此事,但因其是馬端的舉薦人而受牽連。筆者認為,這一事件與蘇紳之前攻擊諫官干政是有關聯的。歐陽修等諫官抓住話柄彈劾蘇紳,是諫官與御史沖突的一個縮影,也是北宋黨爭的具體表現。
四、結語
蘇紳是北宋時期真宗、仁宗兩朝的主要文官之一,其政治活動的主要形式為上疏陳事。蘇紳入仕期間對政府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敢于直言,其主要上疏既有對弊政的揭露和反對,也有對突發性政治事件的建議。他對處理安化地區少數民族叛亂的建議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而對西北地區西夏反叛事件的建議不免有“紙上談兵”之嫌。對《陳便宜八事》《以災異言政事疏》《久旱言政事疏》這三份上疏,則有必要根據北宋時期的具體情況來理解。北宋太祖、太宗對朝內文官的黨爭問題采用默許和支持的態度,至真宗、仁宗時黨爭逐漸嚴重。在御史與諫官勢如水火的情況下,蘇紳未能獨善其身,在三份上疏中頗有對諫官嚴厲指責的話語。
[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2]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3]黃仲昭.八閩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