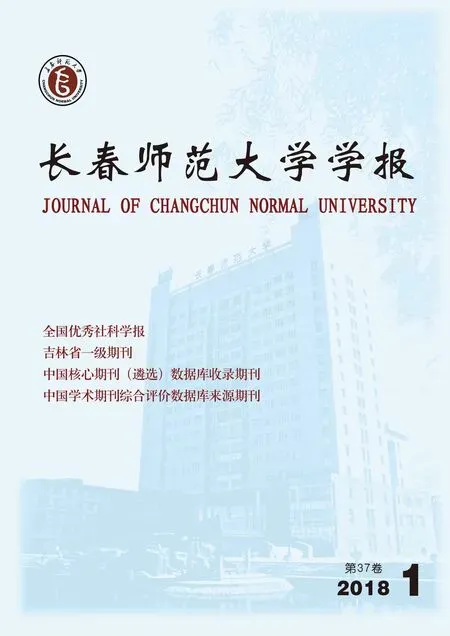時運不濟:民國時期臨時參議會的重新解讀
郭常順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9)
議會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歐美諸國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民意管道作用。近代中國雖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議會制,但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出于發揚民意、支持抗戰的考慮,在中央設立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在地方成立臨時參議會(簡稱臨參會)。本文擬以湖北省臨參會為個案,對臨參會的性質、特點及議案執行情況作一重新解讀。
一、臨參會之源起與議案執行規定
民初以降,國會與省議會相繼成立。國會因二次革命失敗于1914年初被解散,1916年8月復開,一直朝不保夕、存廢無期,直到1924年11月被撤銷。有人揶揄其“僅襲取歐美議會的形體,缺乏獨立精神與公正態度,且悉為軍閥野心家所御用”,“只能說是官僚的應聲蟲、政治的點綴品,還談代表人民、規謀福利嗎!”[1]相形之下,省議會雖未時斷時續,卻淪為黨爭與政爭之平臺,無暇顧及議案執行。“對國計民生甚少關切,彈劾案多有頭無尾,請愿案無法在會中討論,預算和稅收案無解決辦法”,使其“既遭政府輕視,又為人民所詬病。”[2]
抗戰爆發后,為發揚民意、支持抗戰,國民政府在中央設立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在各地設立臨參會,并規定臨參會有權監督議案執行。這樣,臨參會議案執行監督規定被國民政府確認。
臨參會與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一樣,都是國民政府民意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防參議會與國民參政會在中央,前者有15至20余人,由蔣介石聘任;后者擴至150~200人,由各省市推選,報中執委批準[3];臨參會在地方,通常由轄區內有威望、諳民情的人士組成,報行政院轉國防最高會議決定。[4]在議員產生方式這點上,地方與中央確有幾分相似之處。
然而,臨參會因其獨有的議案執行監督職能,在某種程度上又不同于國防參議會與國民參政會。國防參議會“決議提案轉達政府之后,國防最高會議是否采用,采用后實行的狀況如何,也沒有規定應有怎樣向該會報告的手續,只是由代理主席汪精衛把大家的意見口頭轉達政府當局,有時也把政府當局的意見口頭轉達給該會同人,如此而已”;國民參政會雖設駐會委員會,但僅以“聽取政府各項報告及決議案之實施經過為限。”[3]相較而言,臨參會宗旨中有“加強完成地方自治條件”[5]一條,其議案執行監督職能由國民政府明文規定,設駐會委員會監督,開會時還有議案審查委員會審查省政府提交的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因此,臨參會的議案執行監督職能已有某種機制性,接近西方議會制中的復議制度。誠如后人評說,“將完全由國防最高會議復核甚至決定國民政府對內對外方針改為由參議會復議省的重要方針,應該說是一個進步,頗似美國參議會的復議權。”[6]
近年來,學界對臨參會已有部分研究,總括性史實論述居多,由此看來仍有可深入探討的余地。楊天宏教授認為僅強調“代表性不足”及“作用仍然有限”,似未能將最為關鍵的問題道出,不無遺憾。[7]這說明,必須跳出就臨參會論臨參會的怪圈,從其它視角重新審視這一機構。就此而言,我們更應關注其議案執行情形,這才是檢驗臨參會存在價值的試金石,也是衡量其作用大小的準繩。只有更多地關注這一問題,我們才能對臨參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基于這一理由,本文以湖北省臨參會二屆六次大會為例,對臨參會議案執行情形作一詳細考察與分析。
二、湖北省臨參會二屆六次大會提案情形及部分議案執行情況
抗戰勝利后,湖北省臨參會二屆六次大會于1946年春在武昌舉行。此次大會在聽取省政府及各廳處施政報告的基礎上,討論交議案23件、提案83件、臨時動議18件,共124件。經保留與合并,共為90件,其中交議案19件、一般性質10件、民政保安20件、財政建設28件、文化教育13件。
臨參會議案執行報告形式,其基本程式分案由、說明、決議、執行情形四項。先擺明提案理由,然后詳述立案原因或解決辦法,末列省政府態度或對策。
臨參會議案執行監督效力是不完全的,因此一些不合政府規劃或涉外的議案往往被婉拒或“通過”后無具體對策。如:(1)擬請省府開鑿清江以利鄂西交通案,決議:送請省府酌辦,執行情形:此項工程當俟財力物力充裕時再行籌辦;(2)擬以大會名義電請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立即交涉東北蘇軍完全撤退以保領土完整、主權獨立案,決議:通過,執行情形:不詳。
頗需指出的是,臨參會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并不能完全反映其執行情形,必須結合相關檔案及報紙等加以詳察。就此而言,我們試就“水利交通恢復”這一類型略作分析。
湖北位居中國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美譽,水利與交通是制約工廠復工與農村復耕的瓶頸,許多議員基于此點,紛紛提案。省政府除將刨毀天祜垸和開鑿清江緩辦外,其余均按以工代賑辦理。[8]
水利方面,早在1945年春,省主席王東原與救濟總署多次接洽修筑江漢干堤,最終由行政院發25億元,湖北分署撥面粉1.86萬噸,共計80億余元。次年1月,15萬民夫分198處地點先后開工,除少數險工外,多為加高培厚。根據“江漢干堤由江漢工程局負責搶修”“民堤由政府補助款項督令各縣發動人民搶修”的方針,經省府督促與民夫努力,到6月中旬共完工130處。[9]與此同時,從5月至10月還勘查大型水利工程53處、小型55處。省府決定,“小型由水利工程處厘定辦法后交地方自行辦理、水利勘測隊就近督導,大型則擇其經濟價值較大者先行施測設計”。但最終除漢陽世成垸外,其余皆因缺款或戰事而停辦。[10]
交通方面,1945年9月,長江航運復員管委會完成渝漢通航。長江區航政局于次年2月實行區間水運,組織小輪、駁船行駛寧漢兩地。同時,湖北省航業局相繼打通省內上下江線與內河各班線,武漢輪渡第一、二、三航線陸續恢復,全省航運基本恢復正常。除航運外,湖北省公路工程隊于1945年11月搶通漢宜、襄東、襄花三線與鄂東、鄂南公路,到次年10月共計搶通2644公里。[10]省政府為恢復鄂西各線,特派三支測量隊前往趕測,但除緣宜測量隊積極準備相應手續,第一測量隊于10月到達恩施開始測量外,第二測量隊到襄陽后滯留不前[10],工作無形告吹。
水利與交通見效容易,但糧款需求甚巨,極易因糧款缺乏而停滯。例如公路擬修復干支線共3918公里,連購買器材、工具共需810余億元[11],但因缺款,“只能先行恢復戰前原有漢宜、襄花、襄沙、襄老、老白、武陽、武長、漢黃等各干線,其余支線則責令各縣量力修筑”[12]。據估計,上述干線路段約需款140余億元,而國民政府僅能撥款11.8億元,無濟于事,省政府只能“或囑摘要補修,或囑就款辦理”[10]。此后省政府又嘗試通過救濟分署撥發面粉來推行以工代賑,最終僅領到1.68萬噸(干堤)、2萬噸(民堤)、1.2萬噸(公路)[13],僅漢宜及漢黃宣兩線于1946年10月獲準動工,各得面粉1247噸、597噸。[10]可見,糧款缺乏是水利與交通恢復的最大障礙。
由上可知,臨參會議案執行還是取得部分成效的,盡管未能完全實現,但仍不失其價值。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議員們對議案執行有不同程度的要求,省政府態度也不錯,卻不能保證其最終實現。這反映出臨參會職權的有限性——僅有決議權、建議權、聽取報告權、詢問權與選舉權[14]。省政府限于臨參會組織條例,須對議案亮明態度。二者互有制約,議員們抱怨臨參會“并無審議預決算之權,至于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也還要等待將來政治制度的推演,因此我們祗能有說說而已的消極表現”[8]。此即向中銀所說的“代表性不足”及“作用仍然有限”[15],正合楊天宏的論斷:“在國民黨不愿意放棄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國府和地方各級參議會的關系只能是上下級的關系。”[7]
雖說如此,臨參會議案執行仍是議員們關注的焦點,這才是該機構價值的真正體現。在討論階段,議案是民意機構職能和民意的真實反映,具有某種理想性和主觀性;而到執行階段,難免受客觀現實掣肘而裹足不前。與會者認為,“如何救濟農村,如何復興城市,使人民得安生業,為社會培植元氣,這是目前最根本、最迫切的問題”[8]。次年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也提議,“財政問題之解決當從增加生產、充裕國民經濟著手,方為有效”[16]。所以,在議案類型中“財政建設”類最多,在“切實辦理”“查照辦理”中建設類占多數,它們又均屬省府“飭令轉辦”“著手辦理”范圍。總括來看,雖有成績,卻差強人意。這些所謂“飭令轉辦”“著手辦理”者尚如此,余案執行概況隱然可見;戰后和平時期尚如此,要在戰時,議案執行情形更不堪想象。
三、臨參會議案執行監督的意義與局限
臨參會是民國年間繼北洋時期省議會之后中國地方民意機構的又一進步,它上承北洋省議會之端緒,下啟省參議會之先河,在中國議會制歷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過渡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首先,臨參會步入規范化、程序化軌道。在開會方式上,臨參會開會日期由行政院決定,按規定半年一次。《省臨時參議會議事規則》規定其開會程序為:首先由議長致開幕詞,然后由到會的黨政軍領導及其它各機關、社團與部分議員致詞,末由一議員致答詞。接著,議員們聽取省政府、各廳處、保安司令部及有關局署施政報告,隨時提出咨詢建議,由其即席解答或書面報告。末由議員們討論所提議案,經保留或合并后予以表決,通過者送請省政府執行。[14]
其次,臨參會議案在執行方面有了部分制度保障。臨參會通過的議案,本質上處于國民政府決策形成機制中的咨詢建議階段,有別于省府行政會議所作的決議,也就是說它本不在省府執行范圍內,必須送請省府并得到同意后才算進入正式執行階段。行政院明確規定,“送經省臨時參議會議決之事項,省政府立即受其拘束,除請求復議及呈經本院準免執行者外,應予執行,無復自由斟酌余地”[17],因此省府不能置之不理。作為交換,議員們也必須做到“一切無證不信的話我們不愿說,舉凡政府力所不能辦到的事我們不建議,庶免議而不決,決而不議,以失信于人”[8]。可見,當時府會權責還是比較明晰的。然而,實際情形并非完全如此,一些涉及綜合性、長期性問題的議案在短期內不能一蹴而就,就會移交下次大會重新提案,繼續提醒省府注意。如“請嚴厲制止各鄉鎮保長浮濫收支、擅自拘捕人民案”,其執行情形為:查本案迭經通飭遵辦,茲以再飭遵辦。[18]
臨參會議案并非僅供省政府參考。按規定,“抗戰期間,省政府重要施政方針實施前應提交參議會議決,參議會休會期間遇有緊急處置時,應呈行政院批準,于參議會次期集會時報告”。省政府若覺議案不能執行時,“至遲應于省臨參會次期集會時提交復議,復議時如經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贊同原案或對原案予以修正時,省政府對于省臨參會復議之決議,除呈經行政院核準免于執行者外,應予執行”[4],此規定延至戰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具有部分強制性的規定使得臨參會議案有別于國防參議會與國民參政會者,從而具有某種權威性。
再次,臨參會議案基本擺脫了政府內部粉飾太平、諱疾忌醫的陋習。“省臨時參議會對于省政之興革,得向省政府提出建議案”[14]。每次臨參會開會前還要召集議員座談,輔以駐會委員在開會前外出視察歸來所提交的視察報告。雙方相互交流以為參考,藉此集思廣益,公正提案。這表明,臨參會議案有別于省政府及各廳處決議,程序詳贍,環環相扣,更可祛除后者報喜不報憂之弊。
臨參會通過不充分的議案執行監督職能來監督議案執行,意味著地方民意機構開始發生些許新變化。循此以往,就可能走向真正的地方自治,議案無力執行的狀況將會得到較大改觀,這或許是省臨時參議會過渡到省參議會所包含的積極意義。但省參議會成立后,其執行監督機制卻出現倒退。“行政院如認為省參議會決議違反三民主義國策,可呈請國民政府解散省議會,依法重選”[2]。這是臨參會所未曾遇到的,證實了楊天宏的判斷:“即便臨時參議會有類過渡到真正民意機關的一種形式或一個階段,它也只是應對戰時特殊環境需要的產物,不能當作政治常態來看待。”[7]
顯然,臨參會的命運與時局有著千絲萬縷的必然聯系,系當時社會環境的縮影和寫照。這種不利的社會環境,尤其是財政、吏治方面的缺失,最終導致議案執行的有頭無尾。
盡管規定很明確、程序較完備,但臨參會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太不盡人意,這成為其議案執行時不可逾越的鴻溝。
首先是財政不敷,捉襟見肘。與全國其他省份不同,戰時湖北曾分屬四個戰區,有80萬國軍云集此地,慘烈的戰事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這在全國絕無僅有,遂造成全省經濟元氣大傷,一時難見起色。戰后財力不足以使各項事業全面鋪開,省政府只好盡量向中央請款,這真是一種既想放手大干但又步履蹣跚、望洋興嘆的兩難窘境。“財政為庶政之母,現制省無財政,故事業部分計劃內每一項目多需專案向中央請款,自大體言之,在皆應舉辦。而自經費言之,非經中央核準撥款,幾無一事可辦。”[8]1945年底,蔣介石派往湘鄂贛區的宣慰使劉文島面對湖北省臨參會與省政府的撥款訴求,慨嘆道:“聽各位的報告只是一句話,就是要錢、要錢、要錢,這在中央方面也曾以一句話答復,那就是沒有、沒有、沒有。”此后,湖北省主席王東原為減輕本省軍糧、俘糧負擔,曾急電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迅速遣返日俘;臨參會議長沈肇年與省政府田糧處長尹靜夫也赴渝請愿,但收效甚微,于事無補。[19]1945-1946年度湖北仍配購軍糧9056萬斤,實征8000萬斤,雖不夠定額,卻達全國總額的20%,穩居全國首位。[20]
因請款無望、減負無助,經濟恢復又難立竿見影,休養生息之際“不惟苛捐雜稅應予革除,即合法稅捐亦應暫行減免”[8],但各縣要辦事項眾多、補征等事難免,監利縣議長遂建議省主席萬耀煌“將田畝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繳1000元,中等800元,下等500元,如此全縣可實收5億多元,加上其他稅收有1億多,縣府收支可以平衡了”[2]。揆諸實情,似較合理,卻不免加重民眾負擔,所以當“巴東呈請舉辦捐獻收入4800萬元,漢川呈請捐獻警察經費1.7億元,鄖縣呈請捐獻1000萬元,均縣、英山、來鳳呈擬舉辦捐獻或對物捐獻”時,省政府“均經駁飭不準”[22],也是進退維谷、左右為難。1946年7月國民政府財政改制后,中央前后對鄂“補助69個億之多”,但仍“常感迂緩”[23],各縣虧空多則20余億元,少亦五六億元[24],全省下半年“不敷達400億之巨”[23]。1947年4月,張群就任行政院長,竟將萬耀煌給他的“捐獻”提議推廣到全國[21],可見當時國民政府的財政緊迫到何種程度。中央撥款不足與地方財力有限,給臨參會議案執行造成的困境可見一斑。
其次是貪腐橫行,懶政日熾。省主席王東原因“壅蔽中央德意、縱容僚屬貪污、濫支移存款項、破壞人事制度、妨害言論自由”[8]被揭發,牽出大批官員。這一窩案令社會輿論嘩然,然而王僅調職湖南,未曾受罰。國民政府于1946年初頒布《懲治貪污條例》,但鄂省鄒平凡、徐怨宇、袁雍、謝士炎、唐新等要員的貪腐案卻基本草草收場。這些匪夷所思的事件,既挫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期望,又難遏政治生態之惡化。政府威信是與其清廉程度成正比的,貪腐日盛、民心漸失,便不易產生官民齊心的積極效應。
值此百廢待興之際,行政效率也對議案執行造成一定影響。在一個以行政力量為主導的格局中,起決定作用的往往不僅是財力,更在于官場風氣,即各級官員的努力程度。當時因循、敷衍、推諉、欺騙的官僚作風充斥政界,非常突出,誠如時評所言:“過去一般人對于政府有一個總批評,就是機關多于經費,經費多于人才,……機關一膨脹,人才的供應就不易。為了要湊數,不得不降格以求,結果三四流的人才居頭二等的位置,有時不入流之輩也能受國家的委任。”[25]因此,盡管王東原號召“主官集中辦公、實施分層負責、簡化公文手續、厲行公文稽催”以提高行政效率[26],但不久其本人及親信就深陷貪腐漩渦,令人瞠目結舌。
繼任省主席萬耀煌也發現,當時官僚主義已蔚然成風,效率普遍低下。有些人“表面上敷衍得很好,應付也非常圓滿,實際上卻一事不作,遇事推諉、延宕、偷懶、取巧,一天到晚油腔滑調,揶揄人家”;還有人“不遲到、不早退,做事也很負責,可是對于所做的事從不用心思考,所辦公文字句雖極流麗,找不出錯來,但是合不合實際,作不作得通,他卻不問”[27]。他們常以積壓公文、拖延時間來推卸責任,以致這些公文“呈閱時多已事過境遷。”[28]此輩官員若主持政務,必然導致懶政日熾,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一個最初充滿生氣的革命黨,如今已老態龍鐘,勉強維持著門面,再也看不到樂觀地奔向未來的那種青春朝氣。”[29]
不得不承認,臨參會議案形成并通過后,雖被省政府采納,卻難實現。日益惡化的社會環境帶給省政府莫大的困惑與阻撓,其簡單回應和部分執行就不足為奇。臨參會之所以難以正常發揮作用,除了自身原因外,財政不敷、捉襟見肘和貪腐橫行、懶政日熾恐怕才是真正不容忽視的原因。
[1]陳鵬.鄂省議會前途展望[N].華中日報,1946-04-26(03).
[2]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北省志(政權)[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110.
[3]孟廣涵.國民參政會紀實[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5:41,46-49.
[4]湖北政法史志編纂委員會.武漢抗戰法治文獻選編[M].武漢:農村讀物出版社,1987:108.
[5]林代昭,陳有和,王漢昌.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468.
[6]袁繼成,李進修,吳德華.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522-523.
[7]楊天宏.中國議會政治的畸變——評向中銀教授著《重慶市臨時參議會研究》[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108-112.
[8]湖北省臨時參議會第二屆第六次大會記錄[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555-002.
[9]江漢干堤一部修復[N].華中日報,1946-05029(03);江漢堤防工程六月底可完成[N].華中日報,1946-06-12(03).
[10]湖北省政府施政報告稿[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564-005.
[11]省府擴大紀念周,王主席講本省緊急措施與復員準備[N].新湖北日報,1945-09-03(03).
[12]萬武樵先生訪問記[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622-009.
[13]周蒼柏昨飛滬,請示工糧農貸問題[N].華中日報,1946-03-08(03).
[14]孔慶泰.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629.
[15]向中銀.重慶市臨時參議會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9.
[16]三中全會通過經濟改革方案[N].國民日報,1947-03-26(01).
[17]陳之邁.中國政府(3)[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161.
[18]湖北省政府關于執行省臨時參議會第二節第六次大會建議、交議各案情形的報告表[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556-003.
[19]劉特使出席省府座談[N].新湖北日報,1945-12-22(03).
[20]田子渝,黃華文.湖北通史·民國卷[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621.
[21]萬耀煌口述,賈廷詩等記錄.萬耀煌口述自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304-305.
[22]省府充實地方財源[N].華中日報,1946-04-29(03).
[23]湖北省參議會第二次大會施政報告[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564-002.
[24]湖北省政府主席萬耀煌第七區1947年度行政會議講評[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547-002.
[25]社論:以緊縮提高效率[N].新湖北日報,1945-12-14(02).
[26]提高行政效率幾個具體實施辦法[N].新湖北日報,1945-12-05(02).
[27]萬主席在35年12月23日在本府國父紀念周講話[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622-006.
[28]萬耀煌巡視四方兩區觀感[Z].(民國)湖北省政府檔案,LS1-2-0622-005.
[29]易勞逸.革命運動猛烈批判國民黨[A].啟躍.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