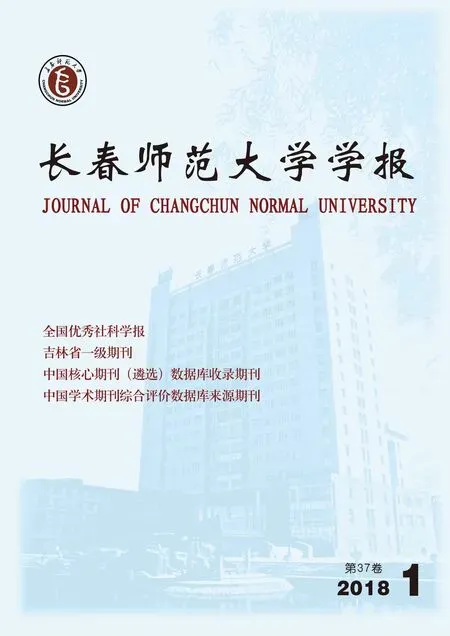維多利亞時代的現(xiàn)代女性薩拉
——《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女性主義解讀
邵 林
(大連外國語大學,遼寧 大連 116044)
英國作家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被譽為后現(xiàn)代小說的經典。它講述了英國貴族青年查爾斯·史密斯和“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伍德拉夫之間的愛情故事。福爾斯將故事設定在1867年,即維多利亞時代,卻選擇了一個生活在20世紀的現(xiàn)代人作為小說的主要敘述者。這種巧妙的安排使得福爾斯站在現(xiàn)代文明的高度對維多利亞時代進行深刻細致的剖析和批判,同時成功塑造了一位頗具現(xiàn)代意識的女主人公薩拉。她獨立、反叛的性格和追求自由與解放的精神徹底顛覆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tǒng)女性形象。
一、薩拉對階級權威的反抗
薩拉的女主人波爾坦尼太太代表了維多利亞社會較高的階層,也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虛偽的道德觀。小說敘述者評論道:“她稱得上是上升時期的大英帝國各種極為狂傲的特征的縮影。她對正義的唯一理解是:她永遠是對的。她對治理的唯一詮釋是:對刁民進行狂暴鎮(zhèn)壓。”[1]14波爾坦尼太太對下人嚴酷無情,在外面卻擺出一副慈善家面孔。她做善事只出于一個原因——“她相信有地獄”[1]15,而她極度渴望死后能進入天堂。可見,波爾坦尼太太是偽善的。薩拉也正因為此才被波爾坦尼太太收留。
薩拉具備一種“天生的深刻洞察力”和“理解他人的能力”,“她能看出別人的本來面目,不會只停留在他們力圖呈現(xiàn)給外界的表面現(xiàn)象上”[1]38。因此,她對波爾坦尼太太的為人和性情了然于胸,于是她在女主人面前刻意表現(xiàn)出軟弱和順從。當波爾坦尼太太與她談話時,她總是帶著一副悲傷的神情,表現(xiàn)出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這讓她的女主人覺得她正在為自己所犯下的罪過而后悔。事實上,薩拉是堅強的,而且極具反叛精神。盡管波爾坦尼太太明確要求她不得去某些特定的地點,但薩拉不僅會繼續(xù)去她想去的地方,還會故意把自己的行蹤暴露給波爾坦尼太太家的總管費爾利太太。薩拉的行動顯然是在挑戰(zhàn)權威。
薩拉的反叛精神在她離開波爾坦尼太太家的那一幕表現(xiàn)得更加淋漓盡致。當女主人要她把一個月的工錢帶走時,薩拉回應道:“你留著吧。如果這一小筆錢足夠的話,我建議你不如拿去買件刑具,將來還會有一些可憐人落在你手里,我相信費爾利太太一定會幫助你對她們動刑的”[1]175。這一席話尖銳地揭穿了波爾坦尼太太的偽善和殘酷本性。當波爾坦尼太太無力地說出“你……說……這話……是要……負責任的”時,薩拉回應道:“是在上帝面前嗎?你那么肯定到了來世上帝還能聽見你說話嗎?”[1]175這無疑戳到了費盡心機要去天堂的波爾坦尼太太的痛處。而后,薩拉首次露出了微笑,向代表著虛偽的“大社會”的女主人表達了自己的蔑視,走出了那座代表著“狹隘的教條”的房子[2]173。
二、薩拉對傳統(tǒng)性觀念和性別角色的挑戰(zhàn)
維多利亞時代對待性的態(tài)度與現(xiàn)代社會截然不同。“我們輕松地談論的事情,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當時是選擇嚴肅態(tài)度來對待的。他們表達嚴肅態(tài)度的方式是不公開談論性問題”[1]192。這意味著維多利亞時代是性壓抑的時代。查爾斯的未婚妻歐內絲蒂娜便是受壓抑女性的代表。雖然她已經注意到女性身體的美,也會時而閃現(xiàn)出性的念頭,但“她在私下里給自己定了一條戒律。每當涉及女人肉體方面的內容,諸如性、月經、分娩等方面的東西,試圖強行進入她的意識時,她都會用無聲的語言告誡自己:‘我不可那樣做。’”[1]21歐內絲蒂娜這種矛盾的心理表明她的思想和行為深受傳統(tǒng)觀念和社會習俗的制約。與之相反,薩拉不愿向所謂的道德風尚低頭,她絲毫沒有性的罪惡感和壓抑感。“她對肉欲并不恐懼。她知道,起碼是猜測,做愛一定能帶來肉體上的快樂”[1]113。不僅如此,她選擇主動談論、感受這一禁忌話題。在她首次對查爾斯“坦白”她把自己給了法國中尉瓦蓋訥之后,“她伸起手,摸到山楂樹枝……好像故意用手在樹枝上使勁捏了一下。手指上立即冒出一滴殷紅的鮮血。”[1]130薩拉這一連串動作可以被解讀為她在感受女性失去貞操的過程,是對女性自我存在展開的思索與探尋。
在穿著打扮和行為舉止方面,薩拉也與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不同。查爾斯第一次見到她時,薩拉身穿一件黑色上衣。對此,小說敘述者評論道:“她的上衣頗怪,更像男士騎馬時穿的外衣,不像四十年來流行過的任何一款女士上衣”[1]6。不僅她的外表,連她平日里的舉手投足也缺乏女性氣質。直到小說第36章,讀者才第一次見到薩拉“做出一個真正的女性動作”[1]199。而在與查爾斯的關系中,薩拉始終引導著查爾斯,一步步激起查爾斯對自己的欲望,操縱著事情發(fā)展的走向,也帶領著查爾斯逐漸認識自我。這樣的關系“顛覆了維多利亞父權社會所規(guī)定的男性是欲望主體,女性是欲望客體,男性是拯救者,女性是等待救贖的對象的二元對立”[3]78。與此同時,薩拉與波爾坦尼太太的女仆米利之間的關系也會令讀者懷疑薩拉的性別傾向。米利常與薩拉睡在一張床上,“這一親密的關系幾乎是無言的……她們知道,真正有意義的是她們能在黑暗中溫暖無言地待在一起。她們的感情中一定會有性的成分嗎?也許有,但是她們從未超出姐妹的界限”[1]114。敘述者刻意加上最后一句話,以避免碰觸女同性戀這一話題。然而,文學評論家大衛(wèi)·蘭德隆卻直接把兩人的關系視作女同性戀關系,他認為產生這種關系的根源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父權思想。父權思想長期控制、壓迫著女性,并強迫她們扮演特定的角色,因此為了擺脫男性的支配,追求自身的獨立發(fā)展,“用女同性戀關系作為對策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選擇”[4]64。即便在查爾斯的眼里,薩拉也完全具備與女性建立這樣一種關系的潛質。在小說第60章描述的團圓式結局里,薩拉告訴查爾斯:“這屋里有一位女士認識我,她比世界上任何人更了解我……她能把我的真實天性……解釋得比我自己更清楚”[1]328。她所指的其實是她與查爾斯的孩子拉萊格,而查爾斯當即猜到的卻是莎拉雇主的姐妹——女詩人克里斯蒂娜·羅塞蒂小姐。這從側面反映出薩拉的確不同于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tǒng)女性形象,她充滿獨立的意識和自由的思想,她的言談舉止并不受道德觀念的束縛。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屬理論認為,“性屬是文化建構而成的”[5]6。在維多利亞時代,女人在男人的引導下行動,她們按照男人指派給她們的角色去操演,建構她們的主體。因此,在一個男性為中心的世界中,女性順從男性的欲望,成為由男性控制和擺布的客體,處于從屬地位。薩拉對傳統(tǒng)性別角色的挑戰(zhàn),實質上是其對父權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挑戰(zhàn),她身上所具備的現(xiàn)代女性意識沖擊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準則和道德規(guī)范。
三、薩拉對自由的追求
薩拉尋求自由的過程是異乎尋常、復雜而奇特的——她利用恥辱來獲取自由。薩拉曾是一位家庭教師,這對于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來說是一份相當體面的工作,但事實遠不及表象那般美好。曾當過家庭教師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自身的感受是,“一個私人家庭女教師根本沒有個人的存在,不被當作活人、一個有理性的人看”[6]29。為了辭掉這份毫無自由可言的工作,讓社會直視她的存在,薩拉選擇公開她與法國中尉瓦蓋訥的關系。薩拉后來坦言她其實并未同瓦蓋訥發(fā)生性關系,因為她在發(fā)現(xiàn)他已經結婚了之后便離開了,但她并沒有向任何人解釋真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薩拉希望自己被視為一個“墮落的女人”,從而使自己不同于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tǒng)女性。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那樣做是為了把自己永遠變成另一個人”;“讓我堅持下來的恰恰是我的恥辱,是我知道自己確實和別的女人不同”[1]126。對此,評論家艾琳·沃伯頓解釋道:“她攀附著殘花敗柳這一虛構的偽裝人格,是因為它強化了她至關重要的獨立性和獨特性的感覺”[2]172。的確,薩拉自稱是“一個被拋棄的人”[1]129,是“法國中尉的妓女”[1]126,小鎮(zhèn)居民也如此看待她。通過這種方式,薩拉至少讓維多利亞社會認真地審視她,她將永遠不會像其他在父權社會里受到壓迫的女性那樣被忽略。沃伯頓對此進一步解釋道:“這種身份強迫一個受到震驚的社會容忍薩拉至少以一個負面的狀態(tài)存在。他們把她當成危險,至少認識到她是某種力量,她與維多利亞時代所規(guī)定的女性的觀念有所不同”[2]172-173。在這樣一個壓制性的社會里,薩拉選擇去做一個可恥的、臭名昭著的人,以便讓眾人正視自己的存在。而她所受到的侮辱和責難都是基于她自己創(chuàng)造的一個虛擬故事,因此,這不僅使薩拉在實質上免于他人的評判,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讓她控制著他人的思想。難怪她會說:“有時候我?guī)缀蹩蓱z她們。我認為自己享有一種她們無法理解的自由。什么侮辱,什么責難,都觸動不了我”[1]126。可見,利用她創(chuàng)造出來的恥辱,薩拉把自己置身于當時社會所不容的境地,從而達到了一種獨特的自由狀態(tài)。
然而,遺憾的是薩拉對自由的追求并未堅持到底。首先,她并沒有徹底離開查爾斯,因為她在最后生下了她與查爾斯的孩子,這意味著薩拉在某種程度上愿意接受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傳統(tǒng)角色。另外,她仍然依附于父權力量,因為在離開查爾斯之后她做了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羅塞蒂的模特。評論家查爾斯·斯克魯格斯認為這是“一種適應的形式,而不是反抗的行為,因而這樣的她是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人”[7]110;艾倫·希爾茲認為,“成為羅塞蒂的模型,薩拉讓自己從主體/藝術家降級為客體/模特”[8]104;陳榕更是認為薩拉與羅塞蒂之間的關系建構起了“女性無助者、模特、追隨者與男性救贖者、藝術家、導師的傳統(tǒng)二元對立”[3]83。的確,薩拉在經濟上依附于羅塞蒂,而女模特又難免被男性藝術家欲望化、客體化。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薩拉一直在努力尋求一種嶄新的生活狀態(tài)和秩序,但最終還是不幸落入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約定俗成。
四、結語
《法國中尉的女人》問世的1969年正是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興起之時,而當時的歐美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性別歧視和男性霸權[9]241-243。很明顯,福爾斯受到了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向讀者講述了地位卑微的薩拉在一個對女性毫無自由可言的維多利亞時代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歷程。在小說結束之際,福爾斯似乎專注于提供一個更“合理”的結局,反而忽略了薩拉這個人物本身的現(xiàn)代意識。因此,小說的最后兩個結局——不論是團圓式結局還是自由式結局——在本質上依然是傳統(tǒng)的結局。莎拉為什么突然停止了對維多利亞傳統(tǒng)觀念的反抗,我們不得而知。畢竟,薩拉雖然可以很好地解讀他人的行為,卻一直不能解釋自己的行為。用她自己的話講,“你別要求我解釋我做過的一切。我不能解釋,也是無法解釋的”[1]255。而為了保持薩拉這一人物的神秘性,福爾斯在小說中也從未探尋她的內心思想,因此沒能很好地幫助讀者了解薩拉的真實想法。
[1]約翰·福爾斯.法國中尉的女人[M].陳安全,譯.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
[2]Warburton, Eileen. Ashes, Ashes, We All Fall Down: Ourika, Cinderella, and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J].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996(1):165-86.
[3]陳榕.薩拉是自由的嗎?[J].外國文學評論,2006(3):77-85.
[4]Landrum,David W. Sarah and Sappho: Lesbian Reference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J].Mosaic, 2000(1):59-76.
[5]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 York: Routledge,1990.
[6]夏洛蒂·勃朗特書信[M].楊靜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7]Charles Scruggs. The Two Endings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J].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85(1):95-113.
[8]Shields Ellen F. Hysteria, Sexual Assault, and the Military: The Trial of Emile de La Ronciere and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J].Mosaic,1995(3):83-108.
[9]蘇紅軍,柏棣.西方后學語境中的女權主義[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