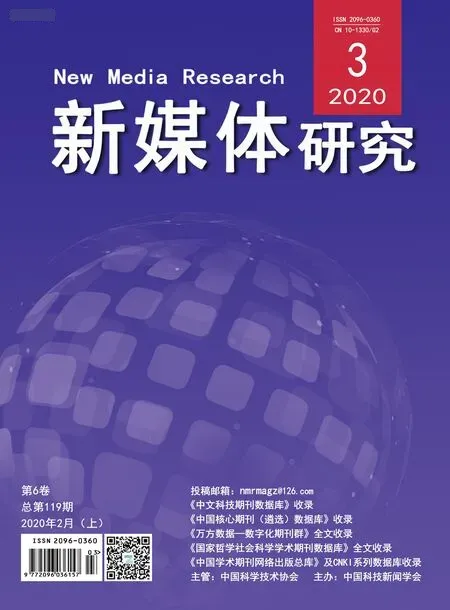全媒體時(shí)代媒體協(xié)同機(jī)制研究
張愛坤
摘 要 全媒體時(shí)代的到來(lái)已成為不爭(zhēng)事實(shí),所謂“全媒體”,指的是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媒介生態(tài)的轉(zhuǎn)變而產(chǎn)生的一種以傳統(tǒng)媒體、新媒體和自媒體為媒介行為主體的多主體性媒介文化生產(chǎn)機(jī)制。協(xié)同學(xué)誕生于20世紀(jì)70年代,主要針對(du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ì)的復(fù)雜系統(tǒng),協(xié)同學(xué)發(fā)展至今,已然具備了哲學(xué)和方法論意義。“全媒體時(shí)代”的媒介文化生產(chǎn)符合協(xié)同學(xué)視域下的復(fù)雜系統(tǒng)特征,以協(xié)同理論為方法論關(guān)照當(dāng)下媒介文化生產(chǎn)機(jī)制,并以此解決全媒體時(shí)代媒介文化生產(chǎn)體系的困境,具有十足的可行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關(guān)鍵詞 全媒體時(shí)代;協(xié)同理論;媒體協(xié)同機(jī)制
中圖分類號(hào) G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2096-0360(2018)03-0074-04
1 “全媒體”的命名
從字面含義理解,所謂“全媒體時(shí)代”,即媒介發(fā)展中包含了所有媒體形態(tài)的一個(gè)全新階段。這里的“全媒體”,既包括以書籍、雜志、報(bào)刊等為代表的傳統(tǒng)媒體,還包括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發(fā)展而誕生的各類新媒體,如網(wǎng)絡(luò)媒體、手機(jī)媒體和數(shù)字電視等媒體形態(tài)。全媒體時(shí)代的出現(xiàn)得益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意味著媒介之間相互融合的不斷加深,也是人類傳播史上一個(gè)全新時(shí)代的開啟。
“全媒體”在媒體應(yīng)用層面的推廣遠(yuǎn)遠(yuǎn)優(yōu)先于理論界的界定,早在2006年,英國(guó)的《每日電訊報(bào)》就開啟了全媒體的改革,隨后,國(guó)外一些傳媒機(jī)構(gòu)開始產(chǎn)業(yè)鏈重構(gòu),并以此開始了全媒體實(shí)踐。所以,“全媒體”作為業(yè)界實(shí)踐誕生于西方,但西方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這個(gè)概念并沒(méi)有做出明確界定。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關(guān)注到這個(gè)概念緣起于傳媒行業(yè)的轉(zhuǎn)型,特別是全媒體發(fā)展的業(yè)界形態(tài)由報(bào)業(yè)向廣播電視界轉(zhuǎn)移之后:2007年,《廣州日?qǐng)?bào)》率先開啟了全媒體轉(zhuǎn)型,通過(guò)報(bào)紙、手機(jī)、網(wǎng)站的聯(lián)動(dòng)發(fā)稿踐行了全媒體的應(yīng)用內(nèi)涵。隨后,寧波日?qǐng)?bào)報(bào)業(yè)集團(tuán)、南方報(bào)業(yè)集團(tuán)等國(guó)內(nèi)傳媒機(jī)構(gòu)紛紛提出全媒體運(yùn)營(yíng)理念。通觀中外,“全媒體”的概念界定和理論建構(gòu)來(lái)自于媒體形態(tài)的演化、轉(zhuǎn)變和融合趨勢(shì)不斷增強(qiáng),傳播內(nèi)容、傳播渠道和媒介功能的日益轉(zhuǎn)變,從根本上講,是人們?cè)诿鎸?duì)和使用媒體的概念時(shí)需要一個(gè)指涉范疇更為廣泛、涵蓋內(nèi)容更為豐富的全新概念來(lái)界定傳媒行業(yè)的全新樣貌,由此,“全媒體”的概念應(yīng)運(yùn)而生。
關(guān)于“全媒體”的具體內(nèi)涵,華中科技大學(xué)石長(zhǎng)順教授在《全媒體的概念建構(gòu)與歷史演進(jìn)》①一文中做了比較清晰的梳理:從概念上,“全媒體”的界說(shuō)主要包括:“報(bào)道體系說(shuō)”——從新聞報(bào)道的業(yè)務(wù)本體出發(fā),落腳點(diǎn)在“報(bào)道體系”上;“傳播形態(tài)說(shuō)”——主要強(qiáng)調(diào)“全媒體”時(shí)代媒介融合形成的信息傳播的立體形態(tài);“整合運(yùn)用說(shuō)”——突出了“全媒體”更具有宏觀意義的“整合應(yīng)用”。基于以上梳理,石長(zhǎng)順教授指出了認(rèn)知和理解“全媒體”概念的幾個(gè)要點(diǎn):1)主體是傳統(tǒng)媒體,“全媒體”是傳統(tǒng)媒體應(yīng)對(duì)新媒體崛起的生存必由之路;2)“全媒體”的關(guān)鍵在于媒介形態(tài)之間的“統(tǒng)合協(xié)同”;3)從傳播學(xué)角度看,“全媒體”面臨的是“分流傳播”——依據(jù)媒體的不同分流來(lái)完成媒介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4)從運(yùn)行模式上講,“全媒體”意味著一種迥異于傳統(tǒng)媒體的全新運(yùn)行模式[1]。
通過(guò)梳理,我們得以比較清晰的認(rèn)知“全媒體”的幾個(gè)要點(diǎn),但總體來(lái)看,本文認(rèn)為,石長(zhǎng)順教授的觀點(diǎn)有兩個(gè)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全媒體”概念誕生之初的媒介行為主體確實(shí)是傳統(tǒng)媒體,彼時(shí)的傳統(tǒng)媒體在面臨新媒體競(jìng)爭(zhēng)時(shí),必須調(diào)整姿態(tài),應(yīng)對(duì)全新的媒介格局,這一點(diǎn)毋庸置疑,但是隨著媒介形態(tài)的演化,特別是媒介融合的趨勢(shì)在最近幾年的不斷加強(qiáng),“新聞傳播的主體也不僅僅是新聞機(jī)構(gòu)、政府部門或社會(huì)組織,越來(lái)越多的個(gè)人參與到新聞信息的生產(chǎn)、發(fā)布和傳播中來(lái)”[2]。也就是說(shuō),我們今天討論“全媒體”這一概念時(shí),它的內(nèi)涵已經(jīng)獲得了進(jìn)一步的豐富,在此前提下,本文姑且將“全媒體”的界定回歸到漢語(yǔ)的字面意義,即“全媒體”的“全”字不僅包括傳統(tǒng)媒體,還包括新媒體甚至自媒體。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就是面對(duì)“全媒體時(shí)代”的媒介行為主體既可能是傳統(tǒng)媒體,還可能是新媒體,甚至可能是自媒體。其次,就“全媒體”形成的傳播形態(tài)來(lái)說(shuō),媒介融合使得新聞傳播“從原來(lái)單一的大眾傳播模式逐漸轉(zhuǎn)化為融大眾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和人際傳播于一體的多模態(tài)全媒體傳播模式。”[2]由此,與“全媒體”想對(duì)應(yīng)的傳播形態(tài)不應(yīng)該僅僅是單純的“分流傳播”,而是基于媒介協(xié)同的“協(xié)同傳播”。本文認(rèn)為:所謂“協(xié)同傳播”,即傳統(tǒng)媒體、新媒體和自媒體在信息傳播的過(guò)程之中基于媒介融合的協(xié)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種迥異于傳統(tǒng)信息傳播方式的,融大眾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和人際傳播于一體的,多層面、全方位、即時(shí)性傳播模式。它打破了過(guò)去線性傳播和網(wǎng)狀傳播的格局,呈現(xiàn)為一種多維的立體傳播形態(tài)。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嘗試性地對(duì)“全媒體”進(jìn)行界定:本文所說(shuō)的“全媒體”,指的是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媒介生態(tài)的轉(zhuǎn)變而產(chǎn)生的一種以傳統(tǒng)媒體、新媒體和自媒體為媒介行為主體的多主體性媒介文化生產(chǎn)機(jī)制,所謂“全媒體時(shí)代”則是以媒介融合為特征,以媒介協(xié)同為發(fā)展動(dòng)力,并以多層次、全方位、即時(shí)性的立體傳播為傳播形態(tài)的媒介發(fā)展新階段。
2 協(xié)同理論與全媒體時(shí)代的信息傳播
上文闡述了“全媒體”這一概念的內(nèi)涵和發(fā)展,并對(duì)其進(jìn)行了界定。在厘清了基本概念之后,接下來(lái)我們面臨的問(wèn)題就是如何在理論和實(shí)踐兩個(gè)層面來(lái)對(duì)這一概念予以豐富。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各個(gè)學(xué)科之間的邊界越發(fā)清晰和細(xì)化,但與此同時(shí),學(xué)科與學(xué)科之間相互滲透的現(xiàn)象也愈發(fā)明顯,在這樣的總體環(huán)境下,傳統(tǒng)意義上處于邊緣地位的“三論(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幾乎同步走到了歷史舞臺(tái)的中心。按照系統(tǒng)論奠基人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統(tǒng)論”,“系統(tǒng)可以定義為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若干要素的復(fù)合體。”[3]“社會(huì)的所有元素和成分之間存在一種相互關(guān)系,公共問(wèn)題、爭(zhēng)議、政策和計(jì)劃中的基本要素通常應(yīng)作為整個(gè)系統(tǒng)中相互依存的部分來(lái)考慮和估價(jià)。”[4]總起來(lái)講,系統(tǒng)思想是對(du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ì)一般系統(tǒng)規(guī)律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它誕生于生物學(xué)領(lǐng)域,但具有哲學(xué)和方法論意義。
由是觀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ì)同樣屬于“系統(tǒng)”,而這兩大系統(tǒng)同樣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子系統(tǒng),系統(tǒng)與子系統(tǒng)的類型多種多樣,它們?cè)诮Y(jié)構(gòu)、特征和行為表現(xiàn)上體現(xiàn)出千差萬(wàn)別的樣貌,但有一點(diǎn)毋庸置疑,那就是這些子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特征和行為表現(xiàn)的簡(jiǎn)單相加并不能替代上一級(jí)系統(tǒng)的功能,也即是說(shuō),子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帶有明確的目的性和調(diào)節(jié)性,它們統(tǒng)一服從于上一級(jí)系統(tǒng)的總體功能,子系統(tǒng)間這種“1+1>2”的相互作用就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ì)系統(tǒng)中廣泛存在的“協(xié)同現(xiàn)象”。
20世紀(jì)70年代,在諸多學(xué)科研究的基礎(chǔ)上,一門專門研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ì)協(xié)同現(xiàn)象的新生學(xué)科誕生——斯圖加特大學(xué)哈肯教授發(fā)表了《協(xié)同學(xué):一門協(xié)作的科學(xué)》(1971),標(biāo)志著協(xié)同學(xué)和協(xié)同理論的誕生。“在協(xié)同學(xué)意義上,會(huì)從很多個(gè)別事實(shí)中——像圖畫拼版玩具那樣——得出一個(gè)嶄新的圖景來(lái)。”[5]協(xié)同理論強(qiáng)調(diào)“事物或系統(tǒng)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其內(nèi)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統(tǒng)之間保持合作性、集體性的狀態(tài)和趨勢(shì),它強(qiáng)調(diào)整合、協(xié)作的一致性或和諧性,以及在某種模式的支配下事物或系統(tǒng)產(chǎn)生不同于原來(lái)狀態(tài)的質(zhì)變過(guò)程。”[6]協(xié)同學(xué)同樣屬于系統(tǒng)理論科學(xué),它接受了系統(tǒng)論的基本邏輯,主要針對(duì)兩個(gè)層面的內(nèi)容:其一是復(fù)雜系統(tǒng)內(nèi)部各個(gè)子系統(tǒng)之間非線性的相互作用機(jī)制——在面臨外界控制參量閾值的轉(zhuǎn)變時(shí),如何以子系統(tǒng)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合作替代獨(dú)立、競(jìng)爭(zhēng),從而增強(qiáng)整體效應(yīng),推進(jìn)系統(tǒng)由無(wú)序狀態(tài)向有序狀態(tài)的轉(zhuǎn)化;其二是系統(tǒng)的自組織性,通過(guò)系統(tǒng)的內(nèi)在動(dòng)力轉(zhuǎn)化,實(shí)現(xiàn)復(fù)雜系統(tǒng)的協(xié)同效應(yīng)。
現(xiàn)代傳媒作為一個(gè)宏大的文化體系,具備復(fù)雜系統(tǒng)的一般特征,針對(duì)復(fù)雜系統(tǒng)的協(xié)同理論對(duì)現(xiàn)代傳媒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à)值。“全媒體”的內(nèi)涵要求媒介機(jī)構(gòu)必須主動(dòng)轉(zhuǎn)變傳統(tǒng)運(yùn)營(yíng)模式,并積極面對(duì)新媒體的崛起和自媒體時(shí)代的到來(lái)。無(wú)論媒介圖景怎樣,信息傳播的終點(diǎn)依舊是受眾,因此,如何讓信息更好的被受眾接受一直都是傳播學(xué)研究的核心話題之一。只是如今“全媒體時(shí)代”,媒介生態(tài)的轉(zhuǎn)變使得這個(gè)問(wèn)題更加復(fù)雜:首先,從傳播者角度來(lái)看,全媒體時(shí)代的傳播者十分多元,除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新聞機(jī)構(gòu)之外,新媒體也扮演著重要的傳播者角色,甚至在輿論導(dǎo)向上,新媒體(特別是網(wǎng)絡(luò)媒體)的作用已然超越了傳統(tǒng)媒體。除此之外,自媒體時(shí)代的到來(lái)使得傳播者的個(gè)人性特質(zhì)提高到無(wú)以復(fù)加的地步,朋友圈、微博、貼吧、QQ等自媒體空間使得信息傳播者的身份匿名化、模糊化,同時(shí)弱化了信源的真實(shí)價(jià)值,挑戰(zhàn)甚至破壞了把關(guān)人的社會(huì)功能,在一些特殊性社會(huì)事件的信息傳播中(如公共安全等),傳統(tǒng)媒體的輿論導(dǎo)向性與自媒體的感性化、主觀化渲染相悖,導(dǎo)致情感壓過(guò)理性,社會(huì)大眾被謠言誤導(dǎo),甚至引發(fā)激化事件。其次,從傳播媒介來(lái)看,全媒體時(shí)代的信息傳播渠道也極為多元,同時(shí)增加的還包括信息的總量,與信息總量增加、傳播渠道多元相伴生的,則是“噪音”的負(fù)面影響愈發(fā)嚴(yán)重,因?yàn)椤靶诺廊萘亢腿哂喙餐萍s信息傳遞的精確度。高效的信息傳遞需要最大限度的解碼率,但又不能超過(guò)信道的容量。它還意味著使用適量的過(guò)剩信息代碼,以此來(lái)抵消信道內(nèi)存在的噪音的負(fù)面影響。”[7]最后,從受眾來(lái)看,受眾在選擇媒介和信息時(shí)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一般來(lái)說(shuō),受眾對(duì)信息的心理選擇過(guò)程包括三個(gè)環(huán)節(jié):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這三個(gè)環(huán)節(jié)相當(dāng)于受眾心理的三道防線,層級(jí)由淺至深,遵從接觸到理解再到被記憶的邏輯規(guī)律,只有到了第三個(gè)階段,我們才能說(shuō)信息傳播的目的達(dá)到了。站在信息本位上看,如何讓受眾獲取信息在今天似乎不是問(wèn)題——今天的受眾獲取信息的方式極其多元化,問(wèn)題在于如何實(shí)現(xiàn)受眾在信息上面的“停留”。海量信息的出現(xiàn)造成的一個(gè)嚴(yán)重后果就是信息更迭太過(guò)迅速,信息的深度被忽視,甚至信息本身也變?yōu)樽钊菀走z忘的東西,人們對(duì)信息的需求淺層化——獲知即可,閱后即忘。媒介,作為“人體的延伸”,其本質(zhì)是人造之物,所以,無(wú)論哪個(gè)時(shí)代,媒介的運(yùn)作都是為了給人類提供需知和未知信息,可是今天“短、平、快”的媒介圖景卻隱含著巨大的信息危機(jī),這似乎是一個(gè)悖論,然而也是一個(gè)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信息過(guò)剩的年代,受眾卻面臨信息的危機(jī)。
由此,我們得以在傳播學(xué)和協(xié)同學(xué)之間找到理論的連接點(diǎn):協(xié)同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ì)的復(fù)雜系統(tǒng),而全媒體時(shí)代的媒介運(yùn)營(yíng)、信息生產(chǎn)和信息傳播活動(dòng)恰恰構(gòu)成了一個(gè)符合著復(fù)雜系統(tǒng)特征的存在,它面臨著如何“協(xié)同”的基本問(wèn)題。所以,將信息傳播活動(dòng)置于協(xié)同學(xué)的理論模式中探討具有十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3 全媒體時(shí)代的媒體協(xié)同機(jī)制
考量協(xié)同學(xué)視域下的媒介協(xié)同就是將協(xié)同學(xué)作為方法論,以傳播學(xué)的知識(shí)解決今天信息傳播活動(dòng)面臨的最主要問(wèn)題。在協(xié)同學(xué)視域下,全媒體首先表現(xiàn)為一個(gè)復(fù)雜系統(tǒng),其概念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因此,對(duì)全媒體時(shí)代媒介協(xié)同的操作也具備了業(yè)務(wù)模式、運(yùn)營(yíng)模式、人才模式等多個(gè)層面的內(nèi)涵。
全媒體是媒介業(yè)務(wù)模式的一次重塑。一般意義上理解,媒介業(yè)務(wù)主要針對(duì)媒介工作者,它包括采訪、寫作、編輯、攝影、發(fā)行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以往的采編模式總是受到傳播介質(zhì)的限定,如報(bào)紙的記者更注重文字和靜態(tài)圖片信息,面對(duì)廣播電視的競(jìng)爭(zhēng)時(shí),報(bào)紙必須在報(bào)道的“深度”上下足功夫。廣播報(bào)道只有聲音符號(hào)的介質(zhì),在采編報(bào)道中只能秉承“以聲奪人”的策略。很顯然,這種單兵作戰(zhàn)的模式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滯后于當(dāng)下的全媒體環(huán)境,全媒體的“全”字,首先可以理解為一種“全介質(zhì)”傳播的形態(tài)。事實(shí)上,今天的媒體轉(zhuǎn)型最主要的也是在這個(gè)“全”字上下功夫,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從“傳媒集團(tuán)”的命名上即可見一斑,如鳳凰傳媒集團(tuán)即是整合了鳳凰旗下的鳳凰衛(wèi)視、鳳凰網(wǎng)已經(jīng)鳳凰新聞客戶端等不同媒介終端,通過(guò)傳播介質(zhì)的聚集來(lái)實(shí)現(xiàn)全渠道、多層面和全方位的信息覆蓋。除此之外,“全媒體”還體現(xiàn)在跨媒介的信息資源共享上,這一點(diǎn)特質(zhì)是從全介質(zhì)傳播這一要點(diǎn)上面衍生出來(lái)的,“全介質(zhì)傳播”體現(xiàn)在電視媒介、紙質(zhì)媒介、網(wǎng)絡(luò)媒介等媒介形式的協(xié)作,“尤其側(cè)重于‘各種類型媒體信息之間的全體實(shí)時(shí)的交互。”[8]按照議程設(shè)置理論,媒介可以為公眾設(shè)置“議事日程”——通過(guò)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某類新聞報(bào)道來(lái)強(qiáng)化這一話題在公眾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也就是說(shuō),如果在一個(gè)時(shí)間段內(nèi)媒介關(guān)注某一話題,那么這一話題在受眾心目中的地位也會(huì)隨之上升。在全媒體時(shí)代,媒介機(jī)構(gòu)對(duì)于受眾議程的把握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加強(qiáng),通過(guò)信息的跨媒介運(yùn)作,實(shí)現(xiàn)受眾關(guān)注焦點(diǎn)的聚集。凡此種種,都預(yù)示著全媒體時(shí)代媒介業(yè)務(wù)模式所面臨的質(zhì)變,它不僅僅是跨媒介的單純結(jié)合,而是包括了傳播理念、傳播技術(shù)、傳播平臺(tái)、傳播介質(zhì)和傳播過(guò)程的一次深度協(xié)同。
從運(yùn)營(yíng)模式上來(lái)講,全媒體時(shí)代的到來(lái)要求媒介運(yùn)營(yíng)者必須適應(yīng)新的時(shí)代特色,拋去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運(yùn)營(yíng)理念。全媒體的全介質(zhì)傳播和跨媒介融合特征決定了運(yùn)營(yíng)者必須站在更高的歷史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媒介資源的全方位共享。實(shí)際上,這也是當(dāng)下媒介運(yùn)營(yíng)面臨的巨大困難。媒介轉(zhuǎn)型并不是一個(gè)新話題,但是時(shí)至今日,媒介轉(zhuǎn)型的效果卻并不理想。全媒體時(shí)代意味著媒介之間的深度融合,按照美國(guó)學(xué)者高登的說(shuō)法,媒介融合包含五個(gè)層面的內(nèi)涵:“所有權(quán)融合(實(shí)現(xiàn)媒介集團(tuán)之間的資源共享)、策略性融合(所有權(quán)不同的媒介之間實(shí)現(xiàn)內(nèi)容上的共享)、結(jié)構(gòu)性融合(重整新聞采集和分配方式)、信息采集融合(新聞從業(yè)者以媒介融合的新聞技能完成信息采集)、新聞表達(dá)融合(記者和編輯綜合運(yùn)用多種媒介工具來(lái)完成事實(shí)的新聞表達(dá))。”[9]從國(guó)外學(xué)者的論述我們看到,媒介融合實(shí)際上包含著媒介形態(tài)、媒介功能、傳播手段、資本所有權(quán)和組織結(jié)構(gòu)等多方面要素的融合,它絕不僅僅是一個(gè)抽象的概念,相反,這是一項(xiàng)有關(guān)媒介全局的巨大工程,它與每一種媒介形態(tài)、每一個(gè)媒介機(jī)構(gòu)甚至每一位媒介從業(yè)人員都有巨大關(guān)聯(lián)。因此,我們要推動(dòng)的媒介融合面臨著重重艱難:首先是政策壁壘,時(shí)至今日,在傳媒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上,政府管制并未真正放開,地區(qū)性政策存在一定的隔膜,這勢(shì)必造成國(guó)內(nèi)媒介融合推進(jìn)的受阻。從國(guó)際上來(lái)講,各個(gè)國(guó)家的傳媒政策不盡相同,全球性的媒介融合進(jìn)程尚需要一系列國(guó)際通用法規(guī)的支持。其次,體現(xiàn)在媒介管理經(jīng)驗(yàn)的不足,特別是國(guó)內(nèi)的傳媒機(jī)構(gòu),這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相關(guān)部門對(duì)于如何面對(duì)媒介融合態(tài)勢(shì)的決策,如報(bào)網(wǎng)融合的推進(jìn),實(shí)際上,今天的網(wǎng)絡(luò)媒介仍然過(guò)分依賴于報(bào)紙媒介,無(wú)論是信息采集、信息處理甚至廣告盈利等方面還遠(yuǎn)遠(yuǎn)未充分發(fā)揮出網(wǎng)絡(luò)媒介自身的獨(dú)特優(yōu)勢(shì)。最后,體現(xiàn)在媒介從業(yè)者基本素質(zhì)和技能的缺乏上,媒介融合意味著未來(lái)的新聞編輯部很可能成為一個(gè)只針對(duì)信息本身的信息匯總地,媒體從業(yè)者要面臨的可能是多種媒介形態(tài)的信息處理與加工,編輯部只針對(duì)信息本身與傳播介質(zhì)的適應(yīng)性,徹底打破如今的報(bào)紙、廣播、電視、網(wǎng)絡(luò)等媒介壁壘,唯有如此,才能充分發(fā)揮各個(gè)傳播介質(zhì)的優(yōu)越性。對(duì)于從業(yè)者來(lái)講,這要求其能夠掌握?qǐng)?bào)紙、電視、廣播、網(wǎng)絡(luò)等各種媒介的采編能力,這項(xiàng)目標(biāo)對(duì)職業(yè)技能和素養(yǎng)的要求很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搭建起與媒介融合態(tài)勢(shì)相匹配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既包括學(xué)校教育中針對(duì)學(xué)生的課程設(shè)置和能力培養(yǎng),還包括針對(duì)從業(yè)者在從業(yè)之后的技能培訓(xùn)和業(yè)務(wù)進(jìn)修等方面。
總之,“全媒體時(shí)代”的到來(lái)已經(jīng)成為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它意味著傳播者、傳播媒介甚至受眾必須以全方位的理念轉(zhuǎn)變來(lái)予以迎接。在這個(gè)意義上,媒介融合、全介質(zhì)傳播和跨媒介合作的趨勢(shì)不僅僅是傳媒行業(yè)內(nèi)部的問(wèn)題,相反,它牽涉著社會(huì)的方方面面,昭示著一個(gè)全新時(shí)代的到來(lái),預(yù)言著一個(gè)“全媒體社會(huì)”的深刻社會(huì)轉(zhuǎn)型,甚至關(guān)涉著處于社會(huì)和文化系統(tǒng)當(dāng)中的每一個(gè)個(gè)體。而我們對(duì)于全媒體的認(rèn)知和探討,不過(guò)剛剛起步。
注釋
①編輯之友,2013-05:51-54。
參考文獻(xiàn)
[1]石長(zhǎng)順,景義新.全媒體的概念建構(gòu)與歷史演進(jìn)[J].編輯之友,2013(5):51-52.
[2]邵培仁.媒介理論前瞻[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2:2.
[3]費(fèi)軍,余麗華.泛系理論與一般系統(tǒng)論比較研究[J].系統(tǒng)辯證學(xué)學(xué)報(bào),1997(10):71.
[4]貝塔朗菲.一般系統(tǒng)論:基礎(chǔ)·發(fā)展·應(yīng)用[M].秋同,袁嘉新,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87:2.
[5]哈肯.協(xié)同學(xué)——大自然成功的奧秘[M].上海:上海科學(xué)普及出版社,1988:9.
[6]潘開靈,白烈湖.管理協(xié)同理論及其應(yīng)用[M].北京:經(jīng)濟(jì)管理出版社,2006:58.
[7]董璐.傳播學(xué)核心理論與概念[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66.
[8]嵇美云,查冠琳,支庭榮.全媒體社會(huì)即將來(lái)臨——基于對(duì)“全媒體”概念的梳理和剖析[J].新媒體前沿,2013-0(8):38.
[9]邵培仁.媒介理論前沿[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9: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