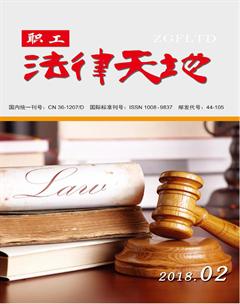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之探析
溫雯

摘要:《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彌補(bǔ)了國(guó)家工作人員打法律擦邊球的行為。但立法上的規(guī)定模糊了它與共同受賄的界限。為了與《刑法》正義和效率的價(jià)值相統(tǒng)一,通過(guò)囚徒困境的分析,本文認(rèn)為《刑法》沒(méi)有必要單獨(dú)規(guī)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可以通過(guò)刑法擬制的規(guī)定,將該行為擬制為受賄罪,一方面可以與《刑法》的對(duì)象體系相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明晰它與共同受賄之間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特定關(guān)系人;共同受賄;囚徒困境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了《關(guān)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意見(jiàn)》(以下簡(jiǎn)稱《意見(jiàn)》)。《意見(jiàn)》就關(guān)于特定關(guān)系人收受賄賂問(wèn)題作出了規(guī)定,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shí)施受賄行為的,對(duì)特定關(guān)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但《意見(jiàn)》沒(méi)有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作出規(guī)定。該行為是指特定關(guān)系人利用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行為或者利用國(guó)家工作人員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qǐng)托人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qǐng)托人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jié)的行為。根據(jù)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沒(méi)有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彌補(bǔ)了立法上的空白,即將特定關(guān)系人擴(kuò)大到貪污賄賂罪類罪名的主體范圍之內(nèi)。盡管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國(guó)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guān)系人是否存在共謀,如果存在共謀則認(rèn)定為受賄罪的共犯。但是,在司法實(shí)踐中,二者的界限并非像立法或者司法解釋那樣明晰,這就需要對(duì)二者的關(guān)系進(jìn)行進(jìn)一步探析。
一、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關(guān)系
(一)特定關(guān)系人的定性
特定關(guān)系人即密切關(guān)系人。特定關(guān)系人是指與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存在血緣關(guān)系、情誼關(guān)系或者利益關(guān)系等社會(huì)關(guān)系較為親密的人。學(xué)者們關(guān)于特定關(guān)系人的理解多采用列舉法,如認(rèn)為其包含親戚關(guān)系、情人關(guān)系、情感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利益關(guān)系、朋友關(guān)系、同事關(guān)系、同學(xué)關(guān)系、老鄉(xiāng)關(guān)系等。這種定義的好處在于方便民眾的理解,缺陷在于容易“掛一漏萬(wàn)”。且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對(duì)各種各樣關(guān)系的列舉,仍然需要“等”來(lái)兜底,而且所列舉的上述關(guān)系也并不必然就是“密切關(guān)系”,只是表明密切關(guān)系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說(shuō)較大的可能性,而不能表明必然存在密切關(guān)系。一方面,不管采用何種方式定義或者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特定關(guān)系人的意志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意志具有重合性,讓第三人無(wú)法識(shí)別他們之間意思表示的真實(shí)界限,這種模糊性也為第三人向特定關(guān)系人行賄提供了腐敗的溫床。另一方面,我國(guó)是人情社會(huì),個(gè)體間的利益彼此交織在一起,牽一發(fā)而動(dòng)全身。第三人之所以向特定關(guān)系人行賄,其原因在于第三人很清楚他們二者的關(guān)系,并且內(nèi)心也希望國(guó)家工作人員知曉這件事。事實(shí)上,國(guó)家工作人員知曉特定關(guān)系人受賄的概率很大。這就更進(jìn)一步加深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共犯之間界限的模糊性。
我國(guó)的立法也試圖厘清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之間犯罪行為的界限,并為此做出了努力,如: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關(guān)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意見(jiàn)》,對(duì)于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關(guān)系做了進(jìn)一步的劃分,根據(jù)不同的情形可能構(gòu)成不同的定性。
第一種情形,國(guó)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為請(qǐng)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qǐng)托人將有關(guān)財(cái)物給予特定關(guān)系人的,以受賄論處。對(duì)于此行為,《意見(jiàn)》僅僅是強(qiáng)調(diào)國(guó)家工作人員應(yīng)認(rèn)定為受賄罪,特定關(guān)系人應(yīng)認(rèn)定為什么罪呢?法律沒(méi)有作出明確的說(shuō)明,本文認(rèn)為其應(yīng)定性為受賄罪的共犯。其理由為:首先,特定關(guān)系人為幫助犯,為國(guó)家工作人員受賄的實(shí)行行為提供了隱秘的便利,促使其完成犯罪行為。其次,特定關(guān)系人是在犯罪過(guò)程中提供的幫助,而非事后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因此參與了共同犯罪行為。再次,盡管國(guó)家工作人員將特定關(guān)系人當(dāng)做了工具利用,但是特定關(guān)系人是知情的且是自愿的,二者存在共同的犯意。這就意味著國(guó)家工作人員不是間接共犯,而是與特定關(guān)系人構(gòu)成普通的共同犯罪。
第二種情形,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shí)施受賄行為的,對(duì)特定關(guān)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大陸法系各國(guó)刑法,則區(qū)分正犯與共犯。共犯是相對(duì)于正犯而言的,正犯一般指實(shí)行犯,共犯一般指從犯或者教唆犯。具體表現(xiàn)為,在共同受賄犯罪中,國(guó)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起主要的作用,認(rèn)定為主犯;而特定關(guān)系人起到教唆沒(méi)有犯意的國(guó)家工作人員產(chǎn)生犯意或者雖有犯意,但犯意不強(qiáng),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在共同犯罪過(guò)程中,特定行為人只起到出謀劃策、提供便利條件等輔助作用。
事實(shí)上,《意見(jiàn)》的這兩條法律規(guī)則,表達(dá)的是同一個(gè)意思,都表明特定關(guān)系人在存在共謀的情況下,是可能存在共同受賄行為的。
(二)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意思表示類型
意思表示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表現(xiàn)形式:
首先,明示的意思表示。也就意味著國(guó)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guān)系人對(duì)收受或者索取請(qǐng)托人財(cái)物的行為存在著書(shū)面或者口頭一致的犯意,二者存在著共謀。
其次,默示的意思表示。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明文規(guī)定時(shí),才可以推定行為人作出了內(nèi)心真實(shí)的表示行為,即國(guó)家工作人員對(duì)特定關(guān)系人利用其職權(quán)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收受或者索取他人財(cái)物的行為知情,雖然沒(méi)有作出任何行為,也沒(méi)有作出明確的意思表示,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默許或者放任了不法行為的發(fā)生,根據(jù)我國(guó)“親親得相首匿”的倫理道德,國(guó)家工作人員沒(méi)有義務(wù)去檢舉或者阻止此不法行為的繼續(xù)發(fā)生。因此,不能就此認(rèn)定國(guó)家工作人員具有間接故意。
再次,行為的意思表示。如果國(guó)家工作人員沒(méi)有作出積極的明示的意思表示,但是其知情,并以行為幫助了特定行為人,則可認(rèn)定二者為共同犯罪,但對(duì)特定關(guān)系人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對(duì)國(guó)家工作人員定受賄罪。理由為:二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犯,國(guó)家工作人員為片面共犯。片面共犯,是指參與同一犯罪的人中,一方認(rèn)識(shí)到自己是在和他人共同犯罪,而另一方?jīng)]有認(rèn)識(shí)到有他人和自己共同犯罪。對(duì)于片面共犯,僅對(duì)知情的一方適用共犯的處罰原則,對(duì)不知情的一方不適用共犯的處罰原則。在特定關(guān)系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國(guó)家工作人員暗中幫助特定關(guān)系人的行為與片面共犯的情形比較類似,但是由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受賄罪都是身份犯。對(duì)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刑法》作了特別的規(guī)定,所以國(guó)家工作人員不應(yīng)定性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共犯,而應(yīng)該作為受賄罪定罪,但在量刑上應(yīng)該按照共犯的原理,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加重或者減輕處罰。
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的區(qū)別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二者在主體方面的區(qū)別是顯而易見(jiàn)的,二者都是身份犯。一般情況下,受賄罪共犯的主體要求為國(guó)家工作人員,但是在法律擬制的情況下,即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共謀時(shí),也將特定關(guān)系人作為受賄罪的共犯。法律擬制主要是受國(guó)家打擊犯罪的政策影響,因此應(yīng)該受到嚴(yán)格限制,否則有礙刑法對(duì)象犯體系的統(tǒng)一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要求為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與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關(guān)系密切的人以及離職的國(guó)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guān)系密切的人,即為特定關(guān)系人。當(dāng)出現(xiàn)法律擬制時(shí),就意味著二者都存在有非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情形,這造成了二者罪名界限的模糊性。
二者在客體上的區(qū)別,則存在爭(zhēng)議。犯罪客體是指我國(guó)《刑法》所保護(hù)的,而被犯罪行為所侵害或者威脅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所侵害的客體,學(xué)界有不同的觀點(diǎn)。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客體是公職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mǎi)性,對(duì)于索取他人財(cái)物的受賄罪而言,犯罪的客體還包括被迫交付財(cái)物的人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另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侵犯的客體為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tuán)體正常的工作秩序。其理由為: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其行為雖然與公共權(quán)力或者公務(wù)活動(dòng)有關(guān)聯(lián),但這種關(guān)聯(lián)是間接的,具有影響力的人只是借助了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力量,而其本人并不是國(guó)家工作人員,不可能也沒(méi)有能力和義務(wù)保證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行為的廉潔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所要禁止的是通過(guò)買(mǎi)賣影響力而施加影響于公務(wù)人員,破壞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及其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tuán)體正常的工作秩序的行為。而共同受賄是受賄罪的共犯,通說(shuō)認(rèn)為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guó)家職務(wù)行為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mǎi)性。如果按照第一種觀點(diǎn)的理解,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侵犯的法益是相同的,如果按照第二種觀點(diǎn)的理解,二者的客體是不同的,分別為破壞工作秩序與職務(wù)廉潔性。我認(rèn)為第一種觀點(diǎn)比較合理,實(shí)際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就是受賄罪的一個(gè)衍生罪名,二者是同源的,兩個(gè)罪名都是因利用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身份或者地位而產(chǎn)生犯罪行為。因此侵犯的客體或或者法益也應(yīng)該是相同的,沒(méi)有必要為了區(qū)分兩個(gè)罪名而刻意地作出區(qū)分。
在客觀方面,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要求的是為他人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而對(duì)于受賄罪共犯而言,不管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dāng),都不影響其定性。如果國(guó)家工作人員收受或者索取財(cái)物,為他人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的同時(shí),又有特定關(guān)系人參與時(shí),則可能出現(xiàn)二者罪名的模糊現(xiàn)象。
但這些區(qū)別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區(qū)別還要看主觀上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是否存在著共謀。有無(wú)共同犯意,是區(qū)分二者的關(guān)鍵。如果存在共謀,則特定關(guān)系人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為受賄罪的共犯。反之,則對(duì)特定關(guān)系人定性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但其主觀上是否存在共謀,在舉證上存在難度,尤其是如何認(rèn)定國(guó)家工作人員是否知情,是從行賄人的角度,受賄人的角度,還是社會(huì)一般人的角度來(lái)認(rèn)定,學(xué)者的認(rèn)識(shí)不統(tǒng)一。本文認(rèn)為主觀上的心態(tài)一般是通過(guò)客觀的行為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因此為了避免主觀歸罪,在司法實(shí)踐中,可以通過(guò)將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行為與特定關(guān)系人的行為進(jìn)行對(duì)比,從社會(huì)一般人的角度理解,看二者的行為是否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如果行為契合程度蓋然性高,則表明國(guó)家工作人員知情,且與特定關(guān)系人存在著共謀。
三、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混淆之成因及法律完善建議
(一)原因分析
本文認(rèn)為,《刑法》單獨(dú)設(shè)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導(dǎo)致兩個(gè)罪名界限模糊的根源。立法設(shè)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初衷,是為了避免國(guó)家工作人員利用特定關(guān)系人收受或者索取他人財(cái)物,而打法律擦邊球的現(xiàn)象,同時(shí)也是與《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的“影響力交易罪”的精神相統(tǒng)一,擴(kuò)大打擊破壞職務(wù)廉潔性的范圍。這符合了《刑法》的正義價(jià)值,讓違法行為受到應(yīng)有的法律制裁。但是它與《刑法》的效率價(jià)值以及立法的精神不符。造成二者罪名混淆的具體原因表現(xiàn)為:
1.《刑法》的效率價(jià)值沒(méi)有得以體現(xiàn)
單獨(dú)設(shè)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沒(méi)有體現(xiàn)《刑法》的效率價(jià)值。一方面立法是有成本的,法律能否實(shí)現(xiàn)預(yù)期的效率,這是立法所必須考慮的問(wèn)題。同時(shí)由于人的趨利避害性,在存在共同受賄的情形下,面臨刑罰制裁的博弈過(guò)程中,特定關(guān)系人和國(guó)家工作人員都明白他們彼此的行為,如何作出最優(yōu)戰(zhàn)略的組合,這就涉及到利益的衡量,這就是囚徒困境。
當(dāng)國(guó)家工作人員和特定關(guān)系人都對(duì)彼此存在共謀的事實(shí)沉默,而司法機(jī)關(guān)又無(wú)相關(guān)證據(jù)證明時(shí),則國(guó)家工作人員不認(rèn)為是犯罪(0),特定關(guān)系人則認(rèn)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1),輕則處以拘役,重則處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當(dāng)國(guó)家工作人員和特定關(guān)系人都彼此坦白存在共謀的事實(shí)時(shí),則認(rèn)定為受賄罪的共犯,根據(jù)主、從犯等犯罪情節(jié),輕則處以行政處罰,重則處以死刑。一般情況下,國(guó)家工作人員為主犯,從重;特定關(guān)系人為從犯,從輕;但是不排除特定關(guān)系人為主犯的情形,如特定關(guān)系人脅迫國(guó)家工作人員受賄,情節(jié)惡劣的,特定關(guān)系人也可能成為主犯。由于坦白是法定從寬情節(jié),所以對(duì)二者應(yīng)從寬處理(-2;-2)。而對(duì)于一方沉默,另一方坦白的情形,則在認(rèn)定受賄罪共犯的情況下,對(duì)坦白的一方從寬(-2)。通過(guò)比較,如果雙方在受到訊問(wèn)時(shí)都對(duì)共謀的事實(shí)選擇沉默,這對(duì)于雙方都最有利(0;-1),尤其是國(guó)家工作人員在不被懲罰的情況下,意味著獲取利益的源泉沒(méi)有倒下,是更有利于特定關(guān)系人以后長(zhǎng)期的不法行為發(fā)展,攫取更多的不法利益。由于該刑罰威懾力程度低,不能對(duì)一般公民發(fā)揮《刑法》的一般預(yù)防功能,也不能使犯罪人內(nèi)心起到悔改作用的特殊預(yù)防功能。
2.立法的原則、技術(shù)沒(méi)有嚴(yán)格地貫徹
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罪名與立法的良法精神不符。立法是社會(huì)利益階層之間的博弈的結(jié)果。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在立法過(guò)程中,沒(méi)有做到科學(xué)立法、民主立法。在《刑法修正案(七)》增設(sh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過(guò)程中,沒(méi)有充分考慮各方利益主體的法律需求。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提出“已經(jīng)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以及“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yīng)該本身是制訂的良法的法律”。因此,良法應(yīng)該得到普遍公眾的參與,而事實(shí)上在制定《刑法修正案(七)》時(shí)幾乎沒(méi)有公眾的參與,也缺少普法的過(guò)程,目前正在進(jìn)行中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雖然在社會(huì)上公布,但是在社會(huì)上的反響不大。如果缺少民眾參與的立法,我們很難說(shuō)它是一部在最大程度上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良法。良法能使壞人從善,而惡法能使好人變惡。特別是對(duì)于像《刑法》這樣生殺予奪的法律更應(yīng)該有公民的充分參與。由于缺乏民主的討論,導(dǎo)致《刑法》罪名的邏輯性問(wèn)題沒(méi)有得以及時(shí)糾正。
在立法技術(shù)上,沒(méi)有處理好對(duì)象犯體系也是導(dǎo)致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界限模糊的原因。有受賄行為必有行賄行為,在我國(guó)刑法典中規(guī)定了受賄罪和行賄罪。行賄罪是一般公民向國(guó)家工作人員送取財(cái)物,受賄罪是身份犯,特定關(guān)系人不具有國(guó)家工作人員身份,因此行賄罪是與受賄罪相對(duì)應(yīng)的。非國(guó)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是與向非國(guó)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相對(duì)應(yīng)的,其主體為公司、企業(yè)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因此沒(méi)有一個(gè)罪名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相對(duì)應(yīng),這也造成了認(rèn)定兩個(gè)罪名的混淆性,這與科學(xué)立法的原則與技術(shù)不符。
(二)法律完善建議
《刑法》的價(jià)值理念已經(jīng)不再是德國(guó)古典刑法學(xué)派費(fèi)爾巴哈所主張的形式意義上的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法定的內(nèi)容應(yīng)隨著時(shí)代的變化而有所發(fā)展。現(xiàn)代社會(huì)更強(qiáng)調(diào)實(shí)質(zhì)正義,因此有必要突破傳統(tǒng)的刑法理念,實(shí)現(xiàn)實(shí)質(zhì)意義上的罪刑法定主義,其具體表現(xiàn)為對(duì)法律規(guī)則應(yīng)做適當(dāng)?shù)臄U(kuò)大解釋,即使是合理的法律擬制行為也是要符合罪刑法定的價(jià)值追求。因此可以通過(guò)立法直接將利用影響力受賄的客觀表現(xiàn)形式擬制為受賄罪。
同時(shí),立法的制定還要考慮刑罰的邊際威懾。所謂刑罰邊際威懾是指在設(shè)置刑罰的嚴(yán)厲性程度每增加一個(gè)單位,所產(chǎn)生的成本刺激犯罪分子不再實(shí)施較為嚴(yán)重的另—個(gè)犯罪的效果。當(dāng)前我國(guó)受賄類犯罪的威懾力較低,且太過(guò)于死板,這種單行刑法色彩的立法已經(jīng)不能適應(yīng)社會(huì)的發(fā)展了,因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受賄的數(shù)額上改變了現(xiàn)行《刑法》以固定數(shù)額作為犯罪情節(jié)的方法,而改用“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這有利于法院結(jié)合當(dāng)?shù)氐慕?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合理的判案,防止了過(guò)去不考慮各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差異,而一刀切的做法。
四、結(jié)語(yǔ)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共同受賄具有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造成二者認(rèn)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刑法修正案(七)》單獨(dú)設(shè)立利用影響力罪造成的,為了實(shí)現(xiàn)與共同受賄行為的統(tǒng)一,可以在立法上將利用影響力受賄的行為擬制為受賄罪,減少二者之間認(rèn)定的矛盾。同時(shí)我國(guó)當(dāng)前受賄類犯罪的《刑法》威懾力度過(guò)低,因此應(yīng)提高犯罪成本,達(dá)到《刑法》一般預(yù)防與共同預(yù)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