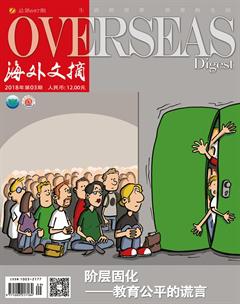罐子里的世界
利伯蒂·田納西 肖穎
桑多爾·卡茨的廚房就像是煉金術(shù)士的實(shí)驗(yàn)室。天花板高的架子上整齊地碼放著一排玻璃罐,罐里裝著各種谷粒和香料,常見的和不常見的都有。比如,去殼燕麥粒和稻米,小米和干西米,糖和甘草,紅藻和鼠李皮。罐子下面擺著一些大玻璃瓶,裝滿了自制的蜂蜜酒、果酒和梨子酒。廚房中間有張大桌子,上面放著一些玻璃罐和陶瓷壇子,里面裝著這位“煉金術(shù)士”的好幫手——數(shù)以萬(wàn)億的菌類。正是有了它們,少許葛縷子、紫甘藍(lán)就能變成爽脆的酸菜;正是因?yàn)樗鼈儯募旧罹G色的黃瓜搖身一變,就成了橄欖綠色的腌黃瓜,酸爽可口;也正是它們的存在,使得胡蘿卜和綠卷心菜變成清爽的中國(guó)泡菜,一片片白蘿卜變成美味的韓式泡菜。卡茨先生一打開壇蓋,一股濃烈的酸臭味馬上在屋內(nèi)彌漫開來(lái)。

發(fā)酵工藝在時(shí)間和空間兩個(gè)維度對(duì)微生物菌落作了延伸。
發(fā)酵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儲(chǔ)存食物的方法。它的產(chǎn)生是源于實(shí)用性。卷心菜和谷物可以邊收邊種,但你不可能一下子把你收獲的東西全都吃掉。這時(shí),如果你把卷心菜切成條,撒上鹽,再裝進(jìn)罐子里,那么它們幾乎就能無(wú)限期地保存起來(lái)了,而且在存放過(guò)程中還會(huì)變得更加美味。
人們一般認(rèn)為發(fā)酵的食物腌漬的味道很重,而且很酸,比如泡菜。但實(shí)際上,面包、奶酪、酸奶、巧克力和茶都是經(jīng)過(guò)某種發(fā)酵后的產(chǎn)物。面包的制作要依靠發(fā)酵才能讓面團(tuán)膨脹起來(lái)。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酵母菌——自然界存在的也好,實(shí)驗(yàn)室培養(yǎng)的也好——會(huì)將面粉里的單糖分解掉。不過(guò),跟制作巧克力一樣,在面包的制作過(guò)程中,微生物在分解單糖的階段就已經(jīng)失去了活性。而另一方面,未經(jīng)巴氏滅菌的泡菜、腌菜和康普茶則富含活性酵母菌。
對(duì)生物學(xué)家而言,發(fā)酵即是糖的厭氧代謝過(guò)程。這是用來(lái)制作面包、啤酒和葡萄酒的酵母所發(fā)揮的作用。在無(wú)氧條件下,它會(huì)把碳水化合物轉(zhuǎn)化為酒精和二氧化碳。但在卡茨先生的廚房?jī)?nèi),并不是所有的發(fā)酵過(guò)程都是無(wú)氧的。天貝是一種爪哇食物,它是由大豆接種根霉菌(一種寄生真菌)的孢子后制成的。制作過(guò)程中,若要使霉菌圍繞大豆形成固體塊狀,則需要流通的空氣。在卡茨先生所著的《發(fā)酵的藝術(shù)》一書中,他傾向于對(duì)“發(fā)酵”給出一種更為寬泛的定義:在各類細(xì)菌、真菌以及它們所產(chǎn)生的酶的作用下,食物發(fā)生轉(zhuǎn)變的過(guò)程。

面包、奶酪、酸奶、巧克力和茶都是經(jīng)過(guò)某種發(fā)酵后的產(chǎn)物。面包的制作要依靠發(fā)酵才能讓面團(tuán)膨脹起來(lái)。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酵母菌——自然界存在的也好,實(shí)驗(yàn)室培養(yǎng)的也好——會(huì)將面粉里的單糖分解掉。
由微生物引發(fā)的食物變性并非全都為人所喜愛。把一棵卷心菜放在鹽水中,一周或一個(gè)月后,就可以吃到可口的泡菜(在網(wǎng)上可以看到我們的節(jié)日食譜)。假如這顆卷心菜是放在灶臺(tái)上,一個(gè)月后,它會(huì)變成一團(tuán)黏糊糊的臟東西。然而,“發(fā)酵”與“腐爛”之間的界限并不總是十分鮮明。就像美是個(gè)人的主觀感受一樣,“發(fā)酵”還是“腐爛”有時(shí)也是一種個(gè)人判斷。除了部分北歐人以外,西方人總是對(duì)難聞的發(fā)酵魚肉感到很惡心,但他們會(huì)欣然接受難聞的發(fā)酵牛奶,比如,戈?duì)栘曌衾衫一蛩沟贍栴D奶酪。在許多東亞和東南亞國(guó)家,人們常常食用魚露,可是對(duì)于奶酪,他們卻避之不及。
不過(guò),現(xiàn)在人們的口味似乎越來(lái)越多樣化了。卡茨先生在世界各地給素不相識(shí)的人們傳授發(fā)酵方法。他們聚在一起腌制和壓制根塊蔬菜,交易“斯考比”(SCOBY,這是一種由細(xì)菌和酵母共生而形成的結(jié)合體,它是一種肥厚粘稠的盤狀物,在它的作用下,茶和糖就變成了康普茶)。發(fā)酵達(dá)人們還會(huì)相互交易酸酵頭和開菲爾粒(BBC長(zhǎng)篇廣播連續(xù)劇《阿切爾一家》的故事發(fā)生在安布里奇的布里奇農(nóng)場(chǎng),那里的人們幾乎不談發(fā)酵以外的事情)。過(guò)去的10年曾一度流行“分子美食學(xué)”,它是指人為地運(yùn)用化學(xué)方法改變食物的味道和口感。當(dāng)今,發(fā)酵食品廣受歡迎,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對(duì)“分子美食學(xué)”的一種抗拒,與其他倡導(dǎo)回歸自然的理念——例如,提倡在野外覓食和在火堆上做飯——是一致的。
微生物美食學(xué)
發(fā)酵能產(chǎn)生美味的食物。不僅如此,發(fā)酵還將人類和看不見的生命歷程聯(lián)系在一起,即和微生物聯(lián)系在一起。這些微生物在人類誕生以前就已經(jīng)在這里生存了數(shù)十億年,即便是在人類滅絕后,它們依舊會(huì)繼續(xù)存活數(shù)十億年。發(fā)酵需要微生物的參與,需要依照它們的作用時(shí)間來(lái)進(jìn)行。發(fā)酵的成敗取決于這些微生物要求的條件和自然規(guī)律。
這種結(jié)合的含義比上述的更加深遠(yuǎn)。佛教術(shù)語(yǔ)“阿那托(anatta)”,也稱“無(wú)我”,從生物學(xué)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是事實(shí)。人類并不是一種單一的生命體,他們是由寄居在身體表面和內(nèi)部的“微生物”組成的小世界。人的口腔內(nèi)一般有超過(guò)700種微生物。腸道內(nèi)則充滿了數(shù)以萬(wàn)億計(jì)的細(xì)菌,它們幫助我們消化,參與決定我們的健康、體重,甚至是心情。不同的人制作同一種發(fā)酵物可能會(huì)有不一樣的變化,因?yàn)槊總€(gè)人手上攜帶的微生物不盡相同。還有一些人突發(fā)奇想,嘗試著用腋窩和肚臍里的菌群制作奶酪。
發(fā)酵工藝在時(shí)間和空間兩個(gè)維度對(duì)微生物菌落作了延伸,使其中的微生物在接觸口唇之前就開始分解食物。因此,發(fā)酵過(guò)程中啟用的微生物也許是經(jīng)過(guò)仔細(xì)篩選,再一代代傳下來(lái)的。它們可能只是通過(guò)一種“轉(zhuǎn)酵”技術(shù)引入的。這種技術(shù)是從之前發(fā)酵好的原料上取下少許,重新接種到下一批原料中再次發(fā)酵。再或者,這些微生物的存活可能全憑運(yùn)氣。比如,蘭比克啤酒和一些酸酵頭是利用空氣中或者有機(jī)物上附著的野生酵母菌制成的。不過(guò),這有一定的風(fēng)險(xiǎn),發(fā)酵成功的酸酵頭氣味會(huì)有些發(fā)酸,還帶有好聞的酵母味。可一旦不適宜的微生物占了上風(fēng),酸酵頭就會(huì)散發(fā)出嘔吐物或者腐爛物一樣的味道。
地球上的每個(gè)人幾乎都會(huì)經(jīng)常食用某種形式的發(fā)酵食品,世界上大多數(shù)地區(qū)都是這樣。當(dāng)下,西方世界重新興起的發(fā)酵熱潮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回歸常態(tài)。在20世紀(jì),大部分歐洲和美洲地區(qū)的人們都沒有真正了解發(fā)酵食品。
在西方,發(fā)酵技術(shù)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農(nóng)業(yè)的集約化。在1870年,從事農(nóng)業(yè)的人幾乎占到了美國(guó)勞動(dòng)力的一半,每位農(nóng)場(chǎng)工人生產(chǎn)的糧食還可以養(yǎng)活另外5個(gè)人。那時(shí),人們對(duì)如何儲(chǔ)存和烹制食物十分精通。如今,美國(guó)勞動(dòng)力中僅有1.4%的人在農(nóng)場(chǎng)工作。這樣,人們就無(wú)需花費(fèi)數(shù)小時(shí),將他們從奶牛身上擠出的奶攪拌成黃油。也無(wú)需把好幾片菜地里的卷心菜和蘿卜手工切成絲,再撒上鹽以便冬季儲(chǔ)藏。這也使廉價(jià)的食物隨處可得,讓工人們轉(zhuǎn)而從事有更好經(jīng)濟(jì)效益的工作。但就像卡茨先生所說(shuō)的,正是這場(chǎng)從農(nóng)戶的門廊和地窖到工廠的轉(zhuǎn)變使昔日平淡無(wú)奇的發(fā)酵過(guò)程變得神秘起來(lái)。

把一棵卷心菜放在鹽水中,一周或一個(gè)月后,就可以吃到可口的泡菜。
農(nóng)業(yè)的集約化還使食物更易為人所掌控,使批量生產(chǎn)變得更容易。商業(yè)用途的酵母菌能迅速發(fā)酵,效果絕佳。手工制作酸酵頭則需要把面粉和水和成面團(tuán),以適宜酵母菌和乳酸菌的繁殖。好幾天之后,酸酵頭就做好了,而且地點(diǎn)不同,酸酵頭的味道也會(huì)不同。酸酵頭發(fā)出來(lái)的面包與雜貨鋪架子上包裹著塑料膜的潮濕皮軟的面包相比,味道要好得多。但是,超市銷售的品牌面包要求口味保持一致。而且,無(wú)論何時(shí),每當(dāng)人們想吃烤面包的時(shí)候,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親手烤制(或者購(gòu)買)一條手工面包的,無(wú)論它有多么美味。
巴氏殺菌法也促成了發(fā)酵工藝在西方的沒落。并不是所有的菌種都是有益菌,而路易·巴斯德發(fā)明了通過(guò)把牛奶和其他食物加熱到一定溫度來(lái)殺菌的方法,這無(wú)疑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與此同時(shí),這給人們?cè)斐闪艘环N印象,那就是所有的細(xì)菌都會(huì)致病,應(yīng)當(dāng)全部殺滅,而不是把它們當(dāng)成一種可以利用的資源,或是人類應(yīng)當(dāng)積極爭(zhēng)取的伙伴。
羅布·奈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圣地亞哥分校“美國(guó)人腸道微生物計(jì)劃”的項(xiàng)目負(fù)責(zé)人,他研究的是微生物與人體總體健康狀況的關(guān)聯(lián)。他表示,乳酸菌在泡菜壇和酸奶罐中的作用原理和在我們腸道中的作用原理是一樣的:它們會(huì)把周圍的環(huán)境變得不利于有害菌的生長(zhǎng),從而抑制它們的繁殖。奈特先生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常吃發(fā)酵食品的人體內(nèi)往往有多樣的腸道菌群。這相應(yīng)地與優(yōu)良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所關(guān)聯(lián),盡管人們尚不清楚腸道內(nèi)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究竟是良好健康狀況的原因還是結(jié)果。
食物中無(wú)論是否含有乙酸,只要是經(jīng)過(guò)巴氏消毒的,確實(shí)能夠保存得更久。有時(shí)候,發(fā)酵而未經(jīng)巴氏消毒的食物是不安全的。但是,以巴氏消毒法儲(chǔ)存的發(fā)酵食物與那些依靠酵母菌儲(chǔ)存的發(fā)酵食物相比,味道會(huì)更苦澀,口感也不如后者微妙,而且也喪失了其生物多樣性。
當(dāng)發(fā)酵依賴于周圍環(huán)境的微生物時(shí),這樣的發(fā)酵會(huì)非常具有地域性。但是,就像對(duì)當(dāng)今所有事物的熱情一樣,對(duì)發(fā)酵食物重新激起的熱情,自然要以貫通世界的互聯(lián)網(wǎng)為歸宿。在社交平臺(tái)“臉書”(Facebook)的群組內(nèi),烘焙愛好者可以上傳照片,展示自己制作的發(fā)酵面包,然后收集大家的建議(例如“開始不要加酵頭或者鹽,用冷水和團(tuán),這樣面會(huì)更筋道”)和稱贊。康普茶的制作者們可以把自己的“發(fā)酵基”與想要的人分享(“如果兩天內(nèi)沒人要的話,它就變成肥料了”)。而啤酒釀造者們可以討論酒香酵母(一種野生酵母)的妙處,用高粱發(fā)酵產(chǎn)生的成果,以及讓酒桶保持良好狀況的最佳方法。
易集網(wǎng)(Etsy)是手工藝品的電子交易平臺(tái)。在那里,面包師們可以買到有來(lái)頭的酸酵頭。其中,肯·格林魯銷售的一款酸酵頭有個(gè)讓人大倒胃口的名字——“巴伐利亞黑死病”。他賣的這款酸酵頭據(jù)稱是源于1633年德國(guó)巴伐利亞南部的上阿默高小鎮(zhèn)。還有一款酸酵頭源自于埃及,號(hào)稱“和金字塔一般古老”。它們是否經(jīng)過(guò)考證,追溯到它們聲稱的源頭了呢?并非如此,“也不必完全當(dāng)真。”格林魯先生說(shuō)(當(dāng)然,他指的是關(guān)于酸酵頭來(lái)歷的說(shuō)法,并不是指酸酵頭本身)。
拋開故事不談,大多數(shù)酸酵頭都出于無(wú)名者之手。這股由互聯(lián)網(wǎng)掀起的發(fā)酵熱潮意味著任何品質(zhì)的酸酵頭都不會(huì)甘于默默無(wú)聞;人們培養(yǎng)出來(lái)的任何前景可觀的有益微生物都不會(huì)消失。埃里克·魯施在網(wǎng)上出售自制的酸酵頭已經(jīng)有12年了。“如果我的酸酵頭出了什么問題,”他說(shuō)道,語(yǔ)氣無(wú)異于一位驕傲的父親,“我會(huì)給3萬(wàn)人發(fā)電子郵件,然后召回酸酵頭。想到各地的人們都在用從這里誕生的,我親手制作的酸酵頭做面包,我就很開心。”發(fā)酵物能創(chuàng)造一個(gè)個(gè)新的世界,而這些新世界不只限于微生物的領(lǐng)域。
[譯自英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