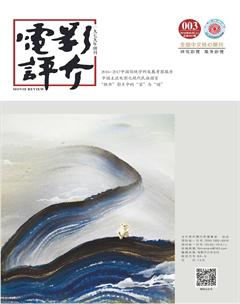“聯華”影片中的“家”與“國”
李璠玎
1929年12月,聯華影業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故都春夢》在北平開機。該片為吸引觀眾而打出的廣告語“復興國片之革命軍,對抗舶來影片之先鋒隊,北京軍閥時代之燃犀錄,我國家庭之照妖鏡”,揭示出其以“家庭倫理”為外顯、“時代批判”為內蘊的創作路徑。影片公映后,因“暴露了北洋軍閥統治下官場的黑暗,從一個側面相當深刻地展示了當時社會的一部分現實”[1],獲得了國產電影前所未有的認可。影片采納具備相當觀眾基礎、在20世紀20年代的“國產電影運動”時期就已被打造成形的類型樣式――家庭倫理片。此類影片立足中國的家庭倫理,以家庭的聚散離合為主要敘事線索,著力表現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但在展示其相互矛盾、對比其品性、體現其觀念沖突的過程中,又有許多超越“家庭倫理”本體的深層內容被填充,《故都春夢》同樣如此。
自古以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傳統社會所認同的“家國一體”思想的實踐路徑,也是士大夫們畢生追求的人生理想,但《故都春夢》里的朱家杰是“宦念一生”“惑于名利”,即道德有所失范后,借妓女燕燕的引見當上稅務局長,走上了“從仕”這一傳統社會公認的“治國、平天下”的道路;此后原配妻子蕙蘭雖各種隱忍,卻仍然無法與燕燕居于同一屋檐下,長女瑩姑則受燕燕影響而墮落,惠蘭只得攜幼女返鄉,朱家杰的家庭儼然已經破碎,他最終在靠山倒臺、鋃鐺入獄后重新回歸家庭。于是,影片中的“家”與“國”被放置到兩個對立的方向:傳統認知中與國相聯的“為官”成了破壞家庭的原初動力。然而,儒家思想“從人生哲學(心正、意誠)出發,推及道德哲學(修身、齊家)與政治哲學(治國、平天下)”[2],朱家杰心術不正,借妓女之力換取官位,導致“家不齊”,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雖然短時間內獲得“優差”,但迅速跌落,無法實現真正的“治國、平天下”夢想,該片的劇情演繹其實從反向契合了儒家的思想文化邏輯。聯華影業公司的這部開山之作,以表層的“家國對立”論證了實質上的“家國一體”,在對官場黑暗的隱射、對士大夫終極人生目標的背棄的同時,傳統儒家的倫理思想、文化邏輯仍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故都春夢》作為一部經典樣本,開啟了“聯華”影片中“家”與“國”糾纏往復,既統一又分離的文化意象呈現之旅,而生發該種現象的動機與背后的力量,更是耐人尋味。
一、“家國一體”:維護現行統治與喚醒民族意識
溯源于西周時期的“家國一體”思想,經孔子及其門人的系統闡釋,逐漸成為儒家學派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之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領域占據了統治地位,其中的“家國一體”思想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一種基本理念。[3]而在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的主導話語也基本依托儒家倫理生成:作為國民黨政治意識形態元話語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認為“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和平。”①孫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又將三民主義進行儒化闡釋,宣稱“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思想”,“是中國固有之倫理哲學的和政治哲學的思想為基礎”[4],認為“民族主義的基礎,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權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信義的道德,民生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5]
聯華公司的經營者與創作者,很多都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里,對‘國的概念主要理解為兩點:一是‘疆土,二是‘君主。”[6]辛亥革命以后,“君主”被政府替代。對那些從小接受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傳統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來說,國與政府等同,而政府提倡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又與他們產生了源于知識層面的深度契合,因此,在作品中呼應政府話語、提倡儒家倫理,屬于理所當然的事情。另一方面,“儒家歷來主張以己推人,由近及遠,將處理血緣關系的原則推廣到社會關系之中……按這種由近及遠的思想邏輯,儒家認為:家是縮小的國,國則是放大的家。”[7]再加上從早期國產電影伊始,“家”就一直是一個被濃墨重彩書寫的文化意象,家庭倫理片則是一種極富本土特色的國產電影類型。鑒于此,以家庭為敘事載體,在書寫的過程中進行“國”的指代,是許多“聯華”影片順理成章的選擇,并以此造成主觀或客觀上維護政府現行統治的功能效果。根據不同的生產動機與創作側重點,這類影片可被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
第一類影片立足于國民政府的主導話語,自身負載的宣教功能十分明顯,《國風》和《小天使》為其典型。《國風》是響應國民政府在1934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而攝制的“命題作業”,“新生活運動”在實質上是儒家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結合,其準則是重新闡釋過的“禮義廉恥”:“禮”即“理”,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它包括自然定律、社會規律、國家紀律等,要求國民以“禮”生活,即對定律、規律、紀律等要有規規矩矩的態度[8],是“禮義廉恥”的核心。《國風》以張家兩個性情迥異的姐妹來映射國家,通過對妹妹張桃為代表的“不守規矩”的群體的批判,將“新生活運動”這一官方主導話語強行嵌入,使影片淪為一部標準的政府運動宣傳片。相比之下,同樣有著政府主導話語介入的《小天使》則顯得含蘊圓潤一些。該片也采用了對比模式進行觀念傳遞,表現對象是一貧一富比鄰而居的兩個家庭。通過窮困的黃家傳達了政府想要教化人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思想,以及“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的中國傳統家庭倫理道德。其中不乏在價值取向上明顯維護現行統治、呼應政府主導話語的段落:黃敏與楊達為堆雪人打架,爺爺見狀后,對黃敏的自衛行為表示了贊同,并教育他說:“我們不應該私斗,應該為國家服務,像你父親一樣。”對內避免暴力斗爭、維護現行統治,是國民政府隱藏在提倡傳統倫理道德之下的實質核心,而斗爭的合法性是唯一的,那就是為國而戰,換句話說,只有為國民政府的斗爭才具有合法性,就像黃家缺失的父親一樣。
第二類影片立足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倫理道德的展示與提倡,內嵌的文化價值取向由此與國民政府的主導話語產生契合。該類影片的創作動機并非全然是為政府官方意識形態搖旗吶喊,更多地是由創作者本身的文化積淀促成,最為突出的代表是由卜萬蒼導演的《人道》與費穆導演的《天倫》。
《人道》用典型的家庭倫理片形態來講述了一個陳世美式的故事,并通過導演卜萬蒼細膩精湛的表現手法,將中國觀眾一向追捧的“苦情”渲染得淋漓盡致。雖然該片被左翼影評認為是“客觀上是明顯的盡了資產階級的奸細作用”,“是舊意識的發酵”,“拿家庭放在社會的前面”[9],但仔細分析將會發現,這部影片的真正關注點是家庭倫理。中國古代哲學的“義理之學”包括關于“道體”(天道)、“人道”(人倫道德)以及“為學之方”(治學方法)的學說,其中關于人道(人倫道德)的學說可專稱為倫理學[10]。倫理與道德相聯,“家庭倫理”由此可看作是一種家庭倫理關系中的道德體系。影片通過趙民杰的家庭悲劇,向觀眾展示了在家庭中無論是為人子亦或為人夫,都有應盡的責任義務、應恪守的道德準則,其價值取向雖與政府話語有重合之處,但更多地體現出的是超越政治意識的普適意義。
為響應“新生活運動”而攝制的《天倫》,則描繪了一個“圣人”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的過程,刻畫出一幅儒家傳統的道德圖景。這種對“大日博愛,共享天倫”的“人類愛”的推崇[11],與“新生活運動”提倡的“禮義廉恥”關系不大,流露出的似乎是編劇鐘石根與導演費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一種信念:“儒家知識分子是行動主義者,講求實效的考慮使其正視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世界,并且從內部著手改變它。他相信,通過自我努力,人性可得以完善,固有的美德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天人有可能合一,使能夠對握有權力、擁有影響的人保持批評態度。”[12]而《天倫》正是這種理念的影像化表述:最終,父親的宿愿得以達成,不僅孫子繼承了他開辦孤兒院、照顧老人的事業,還感化了離家多年的兒子媳婦,家庭得以團圓。
在“聯華”的出品中,無論是奉官方意識形態為圭臬、采納“家庭”作為敘事載體的影片,還是以遵循傳統家庭倫理道德為價值取向,由此與政府的主導話語同謀媾和的作品,都源于對儒家文化的依托,創作者在“家國一體”思想的支配下有意或無意地傳遞出對現行統治的維護。“而儒學自西漢武帝之后所以被歷代封建王朝奉為顯學或官學,除了它確實投合歷代王朝以圖宗族統治的長治久安這一政治需要之外,還在于儒學對于中華民族的生存凝聚承擔過某種精神內核的作用。”[13]因此,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與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后,“聯華”影片為呼應“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呈現出另外一種文化景象:不僅負載著傳統儒家“家國一體”的理念,而且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更為強調“家”與“國”的“共同體”命運。
為響應時局,聯華公司攝制了大量著力喚醒民族意識的故事片,最先進入觀眾眼簾的是《共赴國難》。受“家國一體”思想的影響,“傳統社會的家庭(族),都將儒家思想作為家規族訓的指導思想,將撫育兒女、凝聚社會和盡忠報國作為其存在的價值所在”[14],而“家族群體是形成中華大一統局面的基礎性力量,家族文化則是中華大一統的思想基礎”[15],《共赴國難》正是用影像表述了該種傳統家庭的價值理念與文化功用,將“家”與“國”放到了同一位置――保家必先救國。片中父親華翁“蒿目時艱,因恒以愛國宏論,激發后輩”[16],把“愛國”這一主導文化澆鑄成為家庭文化,并被長子所承續,這樣的人物安排也符合傳統的家庭倫理秩序,最終,戰爭的爆發使全家人團結起來共御外侮,“國”成為擴大版的家。
如果說《共赴國難》演繹了“受到強大外力壓迫更容易出現弱勢群體的團結、凝聚并在一定程度上摒棄內部異議”的整個過程[17],從而將“家”與“國”融為一體;那么《小玩意》則是將受到強大外力壓迫(軍閥混戰與日本入侵)后家的分崩離析展示給觀眾,來喚醒國人,號召他們集聚力量、抵御外侮。片中美麗善良、心靈手巧的葉大娘是“強調個人對家庭的責任,特別是強調個人對國家的責任”[18]的“家國一體”理念的化身:她既擔當起了對家庭的責任――縱然被左鄰右舍稱為“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面對大學生袁璞的示愛,她仍不愿拋棄家庭;又負載著對國家的責任――她鼓勵袁璞參與到“工業救國”當中,最后即使發了瘋,面對人群喊出的仍是警世之言:“敵人殺來了!……快出去打呀!……大家一齊打呀!”導致葉大娘最終發瘋的兩次家庭破碎均源于戰爭,一次是內戰,一次是外敵入侵,劇情用淺顯易懂的邏輯證明:當“國”遭遇重創時,“家”亦隨之經受浩劫,只有消泯內部戰爭、共同抵御外侮,家才能得以長存。該種敘事策略將“家”與“國”作為一個共同體來書寫,能夠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滋生出角色代入感,以強烈的民族、國家認同來應和儒家提倡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二、 舍棄、批判與回望:“家”與“國”的糾纏往復
作為一種國家建構的形態,“家國一體”持續到了近代。晚清以后,面對內憂外患的困境,思想界積極展開對國家觀念的討論并形成一個共識——“去家化”,直接將國家與人民聯系起來,對“家”的批判由此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五四”帶來的啟蒙敘事,在凸顯反封建、反傳統的內涵的同時,追求把個體從大家族中解放出來,以獲得自由、平等、獨立的地位。以此為背景,聯華公司出品了一系列以“報效國家”為立足點來舍棄“家”的影片,典型代表即是《野玫瑰》。
《野玫瑰》繼承了源起于20世紀20年代的戀愛婚姻自由的啟蒙話題,并十分敞亮地呈現著對“國”的表達。特別是影片的結尾部分,苦苦思念小鳳的江波推開家里的窗戶,看到了招募義勇軍的隊伍中他的窮朋友們,于是他跳了下去,在人群里,見到了日思夜想的小鳳。江波投向義勇軍隊伍的行為,暗示著他對家的離棄。“舍家投國”的行為無疑是對“去家化”的新國家觀念的影像化表述,而人群中的小鳳正是愛情所在。因此,啟蒙話語中有關戀愛婚姻自由的命題,與“國”處在了同一位置,無視國難當頭、依然安于享樂的江家則不僅成為自由戀愛的絆腳石,同樣也成為國家的對立面,呼應了“自晚清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不得不矮化以父權與夫權的支配、吃人的禮教等建構的‘家,以解放任何形式出現的‘家對個人的占用,而將之收歸于‘國”的現代國家理念。[19]
從表面上看,與《野玫瑰》同樣采用決絕的態度舍棄家庭的,還有一部十分特殊的戲曲片《斬經堂》。該片取自徽班名劇,講述了潼關守將吳漢舍棄自己與王莽之女王蘭英的家庭,出關投奔劉秀的故事,“家國一體”思想是促成片中吳漢“舍家投國”行為的主要支配力量。片中吳母逼迫吳漢殺死妻子的情節,違背了人性情理,頗為殘忍,遵循的顯然是由“家國一體”所生發的倫理關系:吳母代吳漢被王莽所殺的父親行使權威,而王蘭英的自殺,則是對夫權的遵從。這一系列行為源于:“家國一體,政權與族權結合,使得人們的一切活動都被納入到封建綱常倫理關系之中……在綱常倫理關系中,人們之間的關系通過‘忠‘孝等所具有的確定不移的政治含義,使君臣、父子、夫妻、上下級之間的權力與義務關系秩序化了。前者對后者有絕對的權威,而后者只是對前者有遵從的義務。”[20]勿庸置疑,《斬經堂》在“舍家投國”的徹底性上仿佛與《野玫瑰》相似,但背后的文化力量卻是南轅背轍,它傳遞出的不是在中國社會被呼喚傳播多年的啟蒙思想,而是被其視為應打倒的對象――傳統倫理(涵蓋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兩個層面)。雖然該片在戲曲片探索上、在號召民眾抵御外敵層面具備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內嵌的文化意識與隱喻邏輯卻是典型的反現代反啟蒙立場。
仔細巡檢“聯華”影片將會發現,把“家”與“國”分離開來所采用的顯要策略不僅是在批判的視野中舍棄家庭,同時還對其懸置疏離,讓人物失去家的牽絆,以獨立的個體姿態投向國家。《春到人間》中的玉哥、《大路》里以金哥為首的筑路工人等,都是一群無家之人。這樣的文本表現呼應了現代中國啟蒙思想的要義,即“將個人從傳統的身-家-國-天下的四重結構,蛻變為無所倚傍的個體,而后才能成為國家秩序締造的真正原子化單位,也即為現代國家的建構生產相應的主體”[21]。但對現代國家的追尋與建構,還需要建立在對舊有政權的批判的基礎之上。以清王朝為代表的封建皇權統治、造成幾十年持續混亂的割據軍閥政權,作為“非現代民族國家”的過去的國家形態,都應是被批判的對象,吊詭的是,在“聯華”的影片中,對他們的批判卻又被定性于“破壞家庭的元兇”這一位置,從而生成“家”――“過去的國”二元對立模式。
1931年誕生的《自由魂》(又名《碧血黃花》)延續了《故都春夢》對歷史政權的批判之路。片中主人公羅超的家庭毀于清朝貝勒德祥之手,這無疑是他愿意加入革命黨、推翻清政權的重要原因,而1911年“辛亥廣州起義”的事件背景,與羅超的個人恩怨編織在一起,成功構建了對清王朝的“國仇家恨”這一行為動機。與此類似的還有《天明》,黑暗腐朽的軍閥政權不僅使菱菱等人與故土離散,還扭曲了他們在城市中的家族依靠:菱菱在上海唯一的親人――堂姐被小廠主所逼,幫助他使菱菱受到凌辱,而這家紗廠正是由軍閥開設。這樣的劇情編織使軍閥政權不僅成為菱菱離家的根源,也成為她被家所(堂姐所象征)出賣的元兇,還讓她與戀人張進向往的“結婚成家”變為泡影。此種將軍閥政權設置為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的表現策略,在《孤城烈女》中同樣被使用。影片在劇情中巧妙的將張克農“從家庭中出走”這一行為歸因于軍閥的迫害欺壓,一方面借助家庭的破碎來批判舊有政權,另一方面又通過投靠革命軍來彰顯對新的民族國家的向往。上述文本象征策略在呼應現代國家觀念意識的同時,流露出對家庭的眷戀,以及對其背后的傳統中國的回望。這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真正的傳統是已經積淀在人們的行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態度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儒家孔學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僅僅是一種學說、理論、思想,而是融化浸透在人們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這一民族心理國民性格的重要因素。”[22]
縱使“聯華”影片主觀上希望能夠呼應思想界顛覆“家國一體”思想、破壞“家”在國與個體中的橋梁地位的意圖,但在批判舊政權、呼喚新民族國家的時候,又無意識地轉回到“家”的領域中去尋求與觀眾達成一致的認同基礎。此種列文森所說的“理知上面向未來(西方),情感上回顧傳統(中國)”的行為模式甚至在更為激進的突顯階級斗爭、尋求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救中國的文本《母性之光》中都有體現。該片以家庭作為主要敘事范疇,“對人物感情的處理(如父女相認、夫妻團圓)也很成功,很能打動人,故在當時被稱作‘倫理片。”[23]人物設計方面,革命志士家瑚被安排為小梅的生父,養父林寄梅則代表被批判的資產階級,故事最終的結局是小梅與母親、生父一家團圓,傳統“家國一體”思想所依托的血緣紐帶在此得到高揚。而革命者家瑚作為新的、尚未誕生的國家象征,憑借“親生父親”這一身份在家庭倫理體系中獲得認可,根據“家國一體”的思想內涵,國是家的放大,他所代表的那個未被明確顯影的無產階級國度,則依此邏輯占據了象征意義上的政權合法性。影片最后,小梅與金礦主之子黃書麟所生的女兒不治離世,一方面體現了失去孩子的小梅投身于孤兒養育事業的“母性之光”,另一方面則是斬斷了小梅一家與資產階級的所有關聯――女兒蓮絳與黃書麟有著無法消泯的血緣關系,只有她的消失,才能徹底抹去小梅曾歸屬于資產階級家庭的所有痕跡。顯而易見,作為一部家庭倫理片,《母性之光》中文化象征的演繹邏輯仍然是傳統中國的“家國一體”思想,因為“血緣是家國同構關系的基本依托點,肯定家和血緣的重要性是倫理政治的客觀需要”[23],影片正是以此為工具,來映射批判現行政權,隱晦地顛覆當前的國家體系。
無論“聯華”影片對“家”的批判,還是對過去或當前政權所代表的“國”的批判,均是將兩者分放在對立的位置來進行,但其中還有一類影片“以家寓國”,通過對“家”的批判衍生至對“國”的批判,雖然沿襲的仍然是 “將國當作放大的家”這一儒家思想邏輯,傳遞出的卻是對舊式倫理的顛覆,對傳統中國的背棄。以“溫和現實主義”為標識的朱石麟,在“聯華”中創作了大量張揚儒家傳統思想的影片,但他在1937年卻推出了一部揭示國民劣根性、將矛頭對準傳統中國黑暗面的作品《新舊時代》。影片以董家為主要敘事空間,父親董懷及其四個兒女是主要表現對象,通過劇情批判了封建迷信、賭博、輕視女性、好面子等中國傳統風俗與觀念中的糟粕,并宣揚了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提升婦女地位、使其接受教育自食其力的觀點,以及婚姻自主等啟蒙命題。與傳統男權思想背道而施的是,片中的正面角色均為女性。與姑媽一起辦學的四女兒,不僅沖破了舊式家庭的思想桎梏,還感染影響到父親董懷,促成了他的轉變。傳統家庭倫理體系中極為重要的長子,則成為一個被父親斥為“引狼入室,出賣同胞,天良何在”的角色,而對時勢的影射也在這句臺詞中昭然若揭。片尾,當老大與前來鬧事的杜二正起爭執時,董家的房子垮了――這無疑是對此時千瘡百孔的國家現狀的隱喻,但因為父親董懷的轉變,似乎又有一種“棄舊迎新”的隱隱綽綽的希望所在,這幢房子,如同之前仆人所說“外頭好,木頭里面爛了”,徹底的坍塌反而能給予其重建的機會。
此類“以家寓國”、通過暴露家的缺陷來暗示國的危機的作品,還有集錦片《聯華交響曲》中的《陌生人》——老梅貪圖錢財,放走了殺害兒子的陌生人,兒媳也因此自殺――家無疑毀于父親老梅的目光短淺;《小五義》里,糊涂的父親老李因為老何的假意示好而相信了他,不僅導致家被霸占,連小女兒都被他偷走。這兩部短片中的父親都成為家的缺陷,是導致家庭破碎的主要原因。父權制是傳統中國社會家庭存在的基礎,立足于此的父子關系從而被儒家倫理視為家庭血緣關系之首,并衍生出“忠孝一體”這一“家國一體”思想在倫理層面的結合。“聯華”影片中這些不太光鮮的父親形象的出臺,一方面暗示了導致國家風雨飄搖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則破壞了“家國一體”的思想根基——“家國一體”的實質是“忠孝一體”,兩者結合來共同維護封建專制主義,但當“孝”的實施對象“父”從神壇上跌落以后,“忠”的實施對象“國”也理所當然可以被放置到被批判的角度。此種文化象征邏輯的變遷,彰顯了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即,時局的不堪與影響漸深的啟蒙敘事相結合,共同消泯了“聯華”影片的國家敘事中對傳統儒家文化邏輯的依賴,從而建構了一種全新的家國關系意象。
結語
林語堂曾說:“家是中國人文主義的象征。”[25]從表現包辦婚姻的第一部故事片《難夫難妻》開始,中國電影對“家”投以的目光就從未轉移。聯華公司生逢20世紀30年代,作為一家頗具實力與民族責任感的現代電影企業,動蕩的時局與孱弱的國力生發了其出品的影片對國家話題的關注,而“家國關系具有廣泛而深刻的集體記憶與經驗,提供了小與大、具體與抽象、情感與理智等眾多具有張力的敘事空間”[26]。在傳統與現實的共同作用下,“聯華”影片以當時紛繁復雜的時代文化語境為基礎,探索呈現出了一幅又一幅意蘊深長的家國關系文化圖景。
參考文獻:
[1]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150.
[2][26]陳林俠.家國模式與中國電影建構國家形象的話語修辭[J].中州學刊,2014(11):17,14.
[3][6]劉紫春,汪紅亮.家國情懷的傳承與重構[J].江西社會科學,2015(7):43,45.
[4][5]季甄馥.中國近代哲學史資料選編(第4卷)[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513,514.
[7][24]舒敏華.“家國同構”觀念的形成、實質及其影響[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
[8]張其昀.蔣總統集(第2冊)[M].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8:2099.
[9]塵無.《人道》的意義[N].時報·電影時報,1932-07-23.
[10]張岱年.中國倫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
[11][16]鄭培為,劉桂清.天倫歌[M]//中國無聲電影劇本.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3038,2242.
[12]杜維明.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的結構與功能[M]//許紀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3][18]童鷹.論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的二律背反——兼論新世紀中國儒學的走向[M].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1):38.
[14]劉紫春,汪紅亮.家國情懷的傳承與重構[J].江西社會科學,2015(7):44.
[15]馮爾康.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當代意義[J].江海學刊,2003(6).
[17]房默.民國早期上海電影業的民族國家意識及其歷史作用[J].文藝爭鳴,2015(4):190.
[19][21]陳赟.“去家化”與“再家化”——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內在張力[J].探索與爭鳴,2015(1).
[20]李彥.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特點及其形成的社會基礎[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6):68.
[22]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37.
[23]酈蘇元,胡菊彬.中國無聲電影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319.
[25]林語堂.中國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