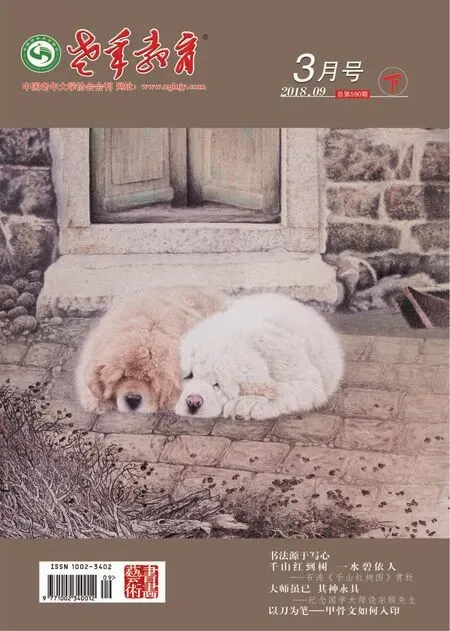和介堪老人的最后一面
□劉一聞

《一年一度秋風勁》 方介堪
1986年,我到溫州探訪了闊別已久的方介堪先生。
方介堪,原名文榘,是我國素負盛名的金石書畫家,尤以其篆刻,猶如繪畫界的張大千,堪稱一代大師。早在20世紀20年代,介老便入滬于趙叔孺先生門下,之后,在這塊藝術奠基地上,他辛勤耕耘了幾十個春秋。在長達70年的藝術生涯中,介老建樹廓綽,蜚聲海內外。
在馬亦釗的陪同下,我們來到了介堪先生的住所。這是一座新型的單元套房,老人居住的是一間南向的并不算太大的工作室兼作臥室的屋子。只見壁間張掛著他的老友張大千、臺靜農為祝介老八十華誕的人物肖像和寫梅圖,兩張碩大的鈐滿了印章的鏡框,似乎表明主人那特有的身份。整個陳設,一如介老所崇尚的藝術風格,典雅而安詳。
此刻,值午憩以后,老人正看報。一眼望去,他的身體遠比我想象中好得多,只是由于長期病臥床褥,臉色略帶蒼白。看到我們的到來,介老格外興奮,竟然幾次都想折身起臥。老人的身體,是在那昏天黑地的年月里被搞壞的。當時,為了保護溫州文物館倉庫,他冒著生命危險,受著大屈大辱屢遭折磨,致使腰椎傷殘,隨著年事益高,逐漸衍及體內其它器官。這對一位年屆86歲高齡的耄耋長者來說,思想和肉體上的苦痛是可想而知的。盡管如此,介老仍以驚人的毅力與病魔作斗爭。也許是因為“精神制勝”的作用吧,老人至今居然眼不花,耳不背,且思路敏銳異常!他天天展讀報紙雜志和各地書信,收聽新聞廣播,時時關心國內外大事。他指著導尿管詼諧地對我說:“要不是這番‘牽連’,我一直打算去上海會會老朋友呢!”說罷,又十分詳細地詢問了他的老友謝稚柳、唐云等諸老的情況。
看到他的精神這般之好,我們從內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此趟過溫州,我原先打算一來是看望介老,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能和老人留一張合影,哪怕就在床頭,也算是一種奢望和不虛此行了。誰料介老在得知我的想法后,很表贊成,并于次日上午,特意請了理發師整理一番。他說:“你們特地來,我非常高興,我不但要拍照,還要寫字給你哩。”我語塞了,一時竟尋不出一句像樣的話來應答。不難想象,要完成這套“節目”,殊不容易。整整一個半小時,俟老人一筆不茍地題寫完我的齋名,就要回到床上時,那情形,即使用“艱難”來描說,也毫不為過。臨行時,介老把我拉到床邊,對我用一種近似征詢的口吻說:“解放后,我總共收了三個學生,兩個在溫州,一個在上海(即溫州博物館副館長林劍丹、溫州大學馬亦釗和上海畫院韓天衡),我打算把你作為我的最后一個學生,你看可妥當?若允,我將把丙寅重陽后第九天這一內容寫進我的《年譜》。”神甫未定的我,此刻可真是倥傯萬分了。我,一個淺薄的區區后學之輩,居然也能列名于方介堪的巨麾之下么?這無疑是一份殊榮。我深深地懂得,其中的意義,是絕不僅僅停留在它的外部表現形式上的。
正想待到春暖花開時,又能與方老在上海歡聚,竟傳來噩耗。沒想到這次探訪,竟成為我和介堪老人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