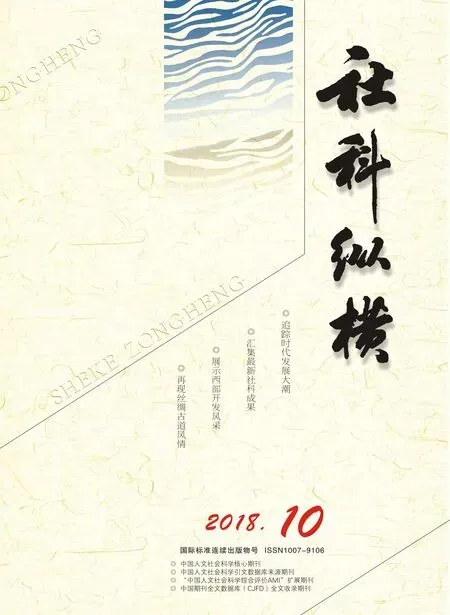隴東南紅色歌謠整理研究新思路探索
李天英 李利軍
(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 甘肅 天水 741001)
一、國內紅色歌謠整理研究現狀
國內紅色歌謠的整理研究工作自建國以來即廣泛開展,尤其以50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最為集中,其中又以收集整理為主。從收錄的內容和范圍來看,這些整理研究成果大體可分為三大類型。
第一類,以省為單位的整理研究。除崔峰主編的陜西省的《紅色歌謠》(196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主編的《河南紅色歌謠》(1960年)之外,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西省的紅色歌謠的整理,既全面又有特色。中國作家協會江西分會主編的《紅色歌謠》(上下冊,1959年)共收集478首紅色歌謠,并將其分為“紅軍謠”、“送郎當紅軍”、“井岡山上紅旗飄”、“漫漫長夜會天光”、“蘇區婦女謠”、“紅色童謠”、“蘇區好”7大類,概括全面,主題清晰;《江西文藝》編輯部編著的《紅色歌謠》(1978年)搜集紅色歌謠 157 首,分為“救星歌”、“紅區好”、“紅軍謠”、“當紅軍”、“燎原火”、“軍民情”、“盼紅軍”、“工農歌”、“斥白匪”9大類,收錄標準較為嚴格,內容上更突出革命色彩;徐臘梅編著的《紅色歌謠》(2007年)與《紅色英烈》、《紅色景觀》、《紅色文物》構成有特色的根據地周年獻禮,被收錄的72首作品兼具紅色主題和藝術表現力。
第二類,以具體的革命根據地為單位的搜集整理。江流采輯的《大別山區紅色歌謠選集》(1958年)、謝善廣編著的《巍巍井崗》(1987年)、福建省龍巖地區文化局編著的《閩西革命歌謠》(1980年)分別整理匯集大別山、井岡山、閩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色歌謠,分類的主題鮮明,別具地方特色。田海燕、高魯主編的《紅色歌謠集》(1959年)從頌歌、歌唱紅軍勝利、工農革命三個角度詳細地整理了“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川陜蘇區”、海陸豐農民起義和紅軍長征的紅色歌謠,從而讓人了解真正的勞動人民的歷史。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研究會主編《川陜蘇區紅色歌謠選》通過不同省份同一根據地的歌謠來反映當面對壓迫時,人們渴求解放的共同愿望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謝濟堂主編的《中央蘇區革命歌謠選集》(1990年)將紅色歌謠分成十五個不同主題,形象、生動、全面地展現閩西蘇區人民群眾的生活轉變。
第三類,作為民歌總集或選集的組成部分的整理。這類整理方法占據大多數,比如《陜西歌謠》(1960年)、《甘肅歌謠》(1960年)、《紅色采風錄》(2008年)、《中國歌謠集成》、《廣東民歌選》(1958年)、《革命民歌集》(1959年)等。選錄到這類民歌集中的紅色歌謠數量雖少,但往往既有譜曲,又有和其他民歌類型的比較,該類整理往往能夠體現出較為集中的思想傾向和主題,突出歌謠的文化藝術價值。
國內關于紅色歌謠的研究成果體現為三類。第一類,整理研究。一方面,作品集的序言部分會對特定地域的歌謠或紅色歌謠的生成演化過程和藝術特征作以簡單介紹。另一方面,作品集中歌謠的不同的分類方法也體現著整理者對歌謠的理解和認識。第二類,綜合研究,以期刊論文為主。從1981年至今,共有113篇相關論文,視角各不相同。徐德培、彭西西、劉小蘭、賀新春等從交叉學科的角度研究紅色歌謠對音樂、人際關系、旅游、語言、教育的啟發意義;吳小川等從文化的角度探討紅色資源的當下意義;張珊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強調紅色歌謠的口傳史料價值;姚麗萍從女性研究出發研究紅色歌謠的婦女形象;此外,不乏紅色歌謠本體論的研究,如彭玉蘭、姚麗萍、陳婷婷、陳麗、楊莉等對紅色歌謠的藝術特征、思想內涵以及淵源和傳承進行研究。第三類,專題研究。王焰安編著的《紅色記憶叢書 紅色歌謠》(2011年)是目前國內紅色歌謠研究的不多見的專著之一。該專著描述了紅色歌謠的流傳方式及其宣傳性、紀實性、歌頌性和變異性的特征,重點分析講述《紅米飯那個南瓜湯——毛委員好我們在一起》等的紅色歌謠的產生流傳和發展的過程,立意新穎、內容詳實。
顯然,由于紅色歌謠題材的特殊性,難免使研究陷入平均化、平庸化的境地,所以專題性的研究應該繼續加強,這樣才能有望改變整理大于研究的現狀。
二、隴東南紅色歌謠整理研究現狀分析
關于隴東南紅色歌謠的整理,天水、隴南與隴東的情況大不相同。隴東的紅色歌謠的整理已經相對成熟。兩當兵變之前關于表達窮人苦不堪言的生活的歌謠如《長工苦》(寧縣)、《窮人活受罪》(環縣)等現存13首。兵變期間及之后的歌謠則充滿欣喜的情緒,其占據大多數。甘肅省文化局主編的《甘肅歌謠》(1960年)中收集的隴東紅色歌謠《個個等紅軍》(慶陽縣)等共33首;高文編的《隴東革命歌謠》(1982年)中收集《盼救星》(寧縣)等61首隴東紅色歌謠;《中國民歌集成·甘肅卷》中收集隴東紅色歌謠《紅燈照得明》(鎮原縣)等19首。后來搜集工作越發周詳,2011年高文、鞏世峰主編的《隴東紅色歌謠》出版,全面地收集了其中包括了土地革命、抗日革命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紅色歌謠。
隴南和天水紅色歌謠的整理及研究尚十分欠缺,留存數量極少,且非常分散。兩當兵變前天水和隴南的紅色歌謠有《養下娃娃姓蔣的》(甘谷)、《長工訴苦》(天水縣)、《長工愁》(清川)、《跑壯丁》(張川)、《拉壯丁》(兩當)、《點兵》(兩當)、《行兵》(武都、岷縣)、《四季行兵》(天水市)、《十可恨》(天水縣)9首,充滿對現實的自嘲和無奈的情緒;兵變期間紅色歌謠以《紅軍歌謠》(成縣)、《想紅軍》(徽縣)、《盼紅軍》(禮縣)、《紅軍直下徽成縣》(西和縣)、《愛兵比娘親》(天水市)、《秦州大捷》(天水市)為代表,表達變革時的疾風驟雨和兵民魚水情;兵變之后的紅色歌謠則以《盼解放》(徽縣)《點兵》(隴南)、《放哨歌》(隴南)、《盼解放》(徽縣)《天變地變日月變》(岷縣)、《社會旋旋好開了》(武都)、《送夫參軍》(天水縣)、《放哨歌》(兩當)、《打日本》(禮縣)為代表,表達涌動的革命激情。這些歌謠分別散見于《天水民歌集成》(1987年)、《中國歌謠集成》(2000年,甘肅卷)和隴南行署文化處編著《隴南地區民歌集成》(1988年)中,還有沒被收錄,散落在民間的紅色歌謠,尚有待考察其出處和時間。
隴南相關的革命歌謠非常稀少,筆者認為主要出自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從1936年7月中旬到10月底,紅軍部隊第二方面軍為主力轉戰隴南,先后發動成徽兩康等戰役,先后在各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積極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發動群眾斗土豪等,擴大了紅軍的群眾基礎,裝大了紅軍隊伍。但是由于張國燾違背中央命令,強迫紅四方面軍擅自脫離隴東南地區,敵我形勢此消彼長,在國民黨胡宗南部隊追擊和天水王均部隊的堵截下,革命形勢日趨嚴峻,不得不根據中央的指令進行戰略轉移,撤離隴南地區。本就脆弱的蘇維埃政權被卷土重來的國民黨勢力破壞殆盡,造成革命基礎薄弱,沒有更多的空間去進行歌謠的創作與傳播。另一方面,多民族地區革命歌謠因藝術形式的局限性,無法很快融入當地的藝術表現,不能在當地群眾中廣泛地進行傳播。
這也導致隴南地區的關于隴東南紅色歌謠的研究非常匱乏,至今沒有公開出版和發行的研究型論著和論文;就整理而論,地處隴東南范圍的天水、隴南、平涼、慶陽四市的紅色歌謠整理進程參差不齊,天水、隴南尤其滯后。天水、隴南自古以來,命運息息相關。1933年6月,共產黨員柴宗孔在武山、甘谷、禮縣、天水一帶組成“西北人民自衛軍”,柴任總指揮,打擊貪官污吏,保護人民利益;1937年,天水“戰時教師服務團”中部分老師去成縣簡易鄉村師范學校執教,他們組織抗日宣傳,編演抗日文藝等,諸如此類的種種歷史事件都說明,天水、隴南紅色歌謠的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共同的歷史原因。因此,以天水和隴南紅色歌謠的整理為突破口的研究,不論是對拓展隴東南紅色文藝的研究還是促進隴東南文化的交流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總而言之,相比較全國的紅色歌謠的研究,隴東南紅色歌謠的整理及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對于整理相對完善的隴東紅色歌謠,應該推進歌謠的內涵研究,拓寬整理研究的視角,可以是歷時整理視角,也可以通過共時整理方法推進內涵研究;第二,將紅色歌謠的研究做為紅色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加強歌謠的文化意義和地方文化建設的挖掘,避免讓研究失去意義;第三,也是全國紅色歌謠整理研究的缺憾,即加強專題性研究,以點為核心,發散思維,尋找與其相關的歷史記憶、藝術闡釋和當代發展,將紅色歌謠也變成一種具有時代感的文化形式;第四,繼續拓展隴東南紅色歌謠的整理研究視角,使紅色歌謠更能體現時代情懷和當下意義。
三、以隴東為突破口的紅色歌謠整理新視角探索
在隴東地區,流傳著一部分記錄戰士守衛邊區的生活的歌謠創作,其中不但凝結著戰士們的智慧,也凝結著他們對前線革命的默默支持,通過這部分生活氣息濃厚、內容生動的歌謠更加凸顯了革命的意義,戰士們為人民服務、保衛人民的重大意義,凸顯著與傳統意義上的紅色歌謠不一樣的內蘊。
一方面,“守”不但要鞏固革命力量,更要加強革命力量。常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頑固派始終在尋找機會在人民內部制造矛盾,企圖瓦解人民的力量。“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民黨甘肅省政府秉承國民黨五中、六中全會的宗旨,把‘防共’、‘反共’列成施政首要任務,公開在隴東建立‘防共線’,并在陜甘寧邊區制造了大小幾十起摩擦事件”[1](P115),但是也正是留守軍與這些頑固派的斗爭及其勝利,鞏固了革命的力量,極大地鼓舞人性并擴大革命的力量。
隴東作為黨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據地的西南大門,在革命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東接延安、洛川,西連固原、平涼,南近長武、靈臺,北靠定邊、環縣。連接內蒙、寧夏、甘肅和陜西四個省,七七零團留守隴東,駐守著這個革命要地,潑灑著革命戰士對革命的一腔熱血,遵守著毛主席給留守兵團的重要任務:“保衛河防!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留守的戰士大多是文盲,革命是需要在思想上向黨中央看齊,文化運動作為留守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其中包括掃盲、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戰士的思想覺悟,口號、標語和歌謠就成為識字活動和思想教育的文化載體。在部隊中流傳很多留守歌謠,“一棵古樹萬條根,紅軍百姓一家人,紅軍如魚民如水,魚水片刻也難分。”戰士們對其進行改編潤色,使之變得更加有情有義:“隴東紅棗樹根盤根,八路軍和老百姓一家親,子弟兵是魚呀人民是水,魚水深情呦心連心!”這些歌謠背后都是一個個鮮活的革命故事,講述了老百姓在革命中的睿智、雪中送炭和不怕犧牲的精神。
另一方面,“守”更體現了革命的本質和目的。戰士與群眾相處的過程中,他們向當地老百姓學習的場景也充滿生活氣息,展現軍民一家的和諧畫面,展示戰爭年代的理想和情懷。比如留守戰士們都會唱《送糧歌》:“溝娃子咬嘛雞娃子叫,當年的紅軍哥哥呦回呀嘛回來了。”“紅軍哥哥依回來了,塬上溝里嘛人歡笑。老漢們樂呵呵喲送公糧,娃兒們笑嘻喜喲掃街道;媳婦們通宵喲做呀做軍鞋,婆婆們清晨喲送茶又送棗。”“吱……!紅軍哥哥嘛回來了,隴東高原嘛紅旗飄。工農人民嘛當家做主人,‘刮民黨’頑固派嘛夾著尾巴跑。安居樂業嘛齊呀齊增產,抗日救國嘛掀呀掀高潮!”“吱……!紅軍哥哥嘛回來了,咱和紅軍嘛心一條。八路軍老百姓嘛一家親,咱送愛國公糧嘛把心表。”[2](P193)
在戰斗中,群眾與戰士們并肩作戰,在生活中,群眾為戰士們做后勤保障,戰士們為群眾們的生活保駕護航,這份情誼不是一兩句大話能夠概括的,而是由千千萬萬個具體的細節和事件充實起來。并且這些東西又會成為詩句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來,“辦社籌資本,全團爭獻金。為國可捐軀,對黨能掏心。克敵渡難關,建軍何惜銀?涓溪可匯海,眾志能鑄城。國強軍新日,再敘隴東情!”[2](P258)
留守的部隊就像先行的開荒者,不但保衛著后方,并且不斷創造新的生活,開墾荒地、養牲畜自給自足、開設小工廠自己制造產品,以滿足生活物質需要。積極響應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針。《開荒歌曲》無不反應這種斗志昂揚和自信的革命自信:
“你一锨吁,我一锨,比比誰的力量壯?你一鋤呀,我一鋤,開荒好比上戰場。上戰場呀打東洋,咱們生產為誰忙?為的是啊打勝仗。打勝仗,保家鄉。保家鄉啊,要武裝啊,抗日軍民有公糧,勞動英雄有榮光!”[2](P325)
在留守期間戰士們時刻準備著上戰場的堅韌和意志也表達地更加真實和感人,戰士們并沒有因為遠離戰場而忘記前線的緊迫,而是抓緊訓練,時刻準備著。在歌謠《人人爭當‘小炮’》中:“胡基柱,有絕招,投彈賽門‘小鋼炮’五十米大關早闖過,六十米紀錄定來到。學他苦練加巧練,學他出名不驕傲。訓練就是為打仗,家他國恨要記牢。子午嶺上擺戰場,壓風踏雷磨戰刀。全連多出胡基柱,人人爭當‘小鋼炮’”[2](P364)
人民的隊伍像一盞明燈一樣照亮了勞苦大眾暗無天日的生活,前線的革命轟轟烈烈,真槍實彈,但是后方的戰斗也刻不容緩,“可憐可憐真可憐,好比豬膽蒸黃連,地主風車霍霍叫,絞得窮漢淚不干”[3](P27),就是備受壓迫的勞動人民的真實寫照。歸根結底,前方的戰爭都是為了人民從苦難中走出來,過上美好的生活,而這些為人民創造生活的“留守”戰士更是責任重大,他們就是為人民主持公道的救星:“玉蘭花開分兩盞,紅軍來了天開眼,打土豪,分谷田,癩子頭上把刀扳,眾鄉鄰,若不信,山沖外頭走一轉。”[3](P30)毛主席曾在陜甘寧留守兵團成立后的會餐上這樣講:“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揮嘛,可以給前方出點子啊。你們七六九團公陽明山就打了勝仗嘛。都走了,誰給我們中央這些人搞飯吃呀?我對你們肖主任講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團吃飯吶。”[4](P320)
戰爭從來都不是以戰場為目的,其目的都是為了人民安定幸福的生活,后方的建設,根據地堅固的堡壘才能確保在千鈞一發的時候從里到外,從上到下,團結一致,最終取得全面的勝利,而這種基礎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具備的。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解放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在我軍條件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人民的支持是勝利的必備堡壘,《解放大西北》中寫道:“在防御作戰中,陜甘寧邊區人民在遭到胡敵嚴重破壞,兼以天早歉收的困境中,全力支援革命戰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據不完全統計,從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陜甘寧邊區動員擔架民工近30萬人,向后方運送傷員所用牲畜2.8萬余頭;參加運送糧草、彈藥等物資者128.2萬余人次,出牲畜128.4萬余頭次;為軍隊磨面、炒干糧、做軍鞋等項,計用民力65萬余人;還參加了修工事、押送俘虜等戰場勤務。邊區人民堅壁清野,對敵人封鎖消息,給我軍帶路、報告情況,使進入陜北之敵變成了聾子、瞎子,而我軍卻能隨時事握敵人動向,有利于捕捉戰機.及時圍殲敵人。陜北戰場的防御作戰,是一場最廣泛、最生動的人民戰爭。”[5](P8)我軍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始終離不開人民的支持。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對隴東南紅色紅色歌謠的整理研究將不應該拘泥于它的一般概念,即不應該僅僅圍繞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鼓勵和倡導下,流傳于蘇區、各個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歌謠而展開,而是應該將歷時的概念融入共時的歷史和情感,不但強調革命事實和歷史,也應重視表達革命的情感;不但重視歌謠宏觀的內容,也要重視歌謠微觀的細節,而細節往往更加具有活力,更能體現歌謠革命精神的傳承和堅守,這也恰恰體現紅色歌謠整理研究的當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