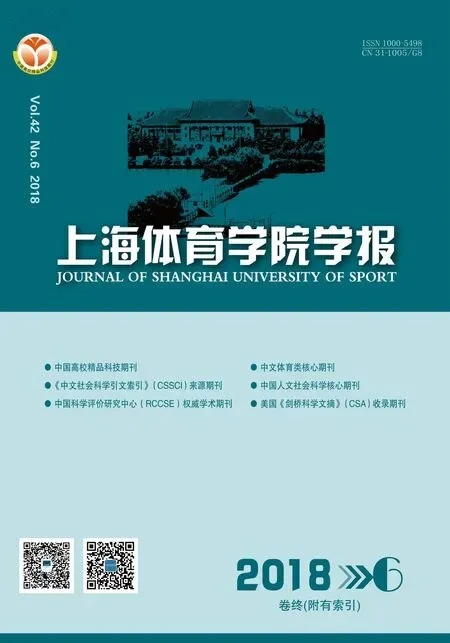“玩拳、說拳、亮拳”對村落文化空間的構建
——基于冀南廣宗縣前魏村梅花拳的田野調查
唐韶軍, 李 洋
(1. 魯東大學 體育學院,山東 煙臺 264025;2. 赤峰學院 體育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關于中國村落社區的研究肇始于19世紀末美國學者明恩溥的《中國鄉村生活》一書。此后,眾多西方學者,如凱恩、狄特摩爾、白克令、葛學溥等,均以西方研究范式對中國村落社會進行了層次各異的研究[1]。這些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國本土學者對中國村落研究的熱情”[2]。在眾多的本土研究中,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開創了通過村落社區審視中國社會的研究范式。至今,這種對村落進行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仍具有廣泛的學術市場,諸多學者分別從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領域對中國村落社區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其間,也偶有武術學者對村落武術的探討,如王明建對河南“陳家溝”、貴州“鮑屯村”和山西“東街村”武術現狀的探討[3]。從整個武術領域看,對村落武術的研究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本文利用文獻資料法,在得出鄉村武術具有“亮拳”“玩拳”“說拳”3種存在形態的假設之后,有針對性地選擇了冀南廣宗縣前魏村進行田野調查,試圖在武術領域驗證“田野工作有了理論的根據才有科學的意義,理論有了事實的基礎才不至于空泛”[4]的人類學研究過程。
1 研究方法
1.1文獻資料法以“梅花拳”“村落”“社區”為關鍵詞,通過中國知網檢索出與“拳民村”研究相關性較高的30篇文獻,對這些文獻進行深入分析。在梳理出村落武術,特別是梅花拳具有“說拳”“玩拳”“亮拳”的文化特性后,結合梅花拳的地域分布狀況,對《廣宗縣志》進行仔細研讀,挖掘其中村落文化與武術活動相融合的記錄,初步形成關于武術活動構建村落文化空間的研究假設,為下一步的田野驗證做好準備。
1.2田野調查法據查閱的文獻資料得知,廣宗縣前魏村是遠近聞名的拳民村,民俗活動豐富多彩,且多與武術相關。故筆者選取前魏村為田野調查點,分別于2015年4月5—6日和2016年2月15—17日2次深入前魏村進行調研,分別參與了當地的“亮拳”和“打醮”活動,并在此期間有針對性地選擇李玉琢等9名對象進行訪談。田野調查結束后對訪談記錄進行分類、歸納與總結,試圖通過田野和史料互證的方法論證本文的假設。
2 “玩拳”:對村落娛樂文化空間的構建
在前魏村,練武術常被稱作“玩拳”,而練武術的人自然被稱之為“玩拳的”。一個“玩”字道出了習武練拳和娛樂休閑之間水乳交融的關系,說明在日常生活中拳民已經把練武當成一種休閑娛樂的方式,真正實現了武術的生活化和娛樂化。
2.1勞作之余的“玩拳” 前魏村位于廣宗縣城以北7.5 km、縣級公路“大牙線”以西的廣闊地域。村里無任何工業,除了少數年輕人外出讀書、打工之外,大多數人都以務農為生。耕地多為沙壤土,較為貧瘠,又均為水澆地,村民往往需要長時間的精心耕作才能維持正常生計。耕作的異常辛苦和生活的單調乏味,促生了村民對娛樂生活的需求。勞作間隙、農閑時節玩上一段梅花拳可以調節心情,緩和勞作的辛苦。前魏村的村民們一直把練拳說成是玩拳,“白天去種地,晚上來玩拳”的娛樂傳統一直流傳至今。在調研中,常聽前魏村的老人們稱梅花拳為“莊稼拳”,這不僅說明了梅花拳的練拳群體大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還說明了練拳的場地大都是在田間地頭、打麥場等與生產勞動密切相關的場所。此外,梅花拳除了槍、刀、棍、劍等常規武器之外,還有許多稀有的兵器,它們主要來源于一輛農用獨輪車:拉車繩是“流星錘”,車輪子拆開就是一對“風火輪”,車攀繩變成了“七節鞭”,車爬頭就是“大梢子”。還有“文棒”“上天梯”“護身披”“群母槍”“小拐”“量天尺”“梅花針”等都是由獨輪車各部件變化而來的,就連修車用的工具小錛也變成了“一錛三槍”等,一輛獨輪車可拆成20多件稀有兵器。如果是性情所致,鐵锨、鋤頭、鐮刀等生產工具也能成為村民手中的兵器。這說明,在前魏村的社區文化空間中,村民已把生產、練拳和娛樂三者有機結合為一體。
2.2民俗節日的“玩拳” 民俗節日是一個村落社區文化空間的重要構成要素,生動地記錄著該村落歷史悠久、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節日就意味著歡樂、喜慶、溫馨和幸福,“娛樂就成為民俗節日永恒的主題”[5]。所以,極具娛樂性的梅花拳表演便成為前魏村民俗節日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承擔起鄉村娛樂空間的建構任務。在前魏村,不管什么節日,武術和鑼鼓這2項活動不能少,少了它們就不能稱其為節日。由于前魏村是一個典型的梅花拳村落,村里人大多會打梅花拳,而梅花拳在“亮拳”時又必須要有鑼鼓伴奏,久而久之,拳民在耳濡目染中也學會了鑼鼓演奏。“節日上的武術表演主要是梅花拳,再早些年的時候還有洪拳,現在我們村洪拳已經基本失傳了,就剩下梅花拳了。但是,敲鑼打鼓的傳統始終沒啥變化”(張俊華)。每逢民俗佳節,梅花拳弟子就會聚集在一處,通常是在村里的廣場、主要路口或集市上,一邊演練武藝,一邊敲鑼打鼓,吸引眾多村民前來觀看。如果觀眾太擁擠,表演者就不得不舞動長器械(槍、棍等)或軟器械(九節鞭、三節棍、繩鏢等)來“開場子”,把觀眾“嚇退”,以便騰出一塊足夠大的地盤進行武術表演。過一會兒,在觀眾推搡、擁擠、爭先恐后地觀看中,場子會越縮越小,此刻就需要再次“開場子”。在每一次“開”與“縮”的互動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唏噓聲、驚叫聲、吶喊聲……聲聲不絕于耳。武術表演的同時,鑼鼓隊員自然不甘示弱,他們挺胸腆肚、左顧右盼、奮力擂鼓,足以把自己內心的喜悅之情通過鑼鼓聲傳遞出來,感染著在場的每一位村民。村民在歡快熱鬧的氛圍中釋放了壓力,緩解了痛苦,增強了生活的信心。“玩拳”已成為前魏村村民調節身心、豐富精神生活的一種娛樂活動。
2.3宗教儀式的“玩拳” 前魏村村民主要靠農業生存,然而該村耕種環境不容樂觀,“春季暴風驟起,沙土橫飛,咫尺莫辨……夏至雨量短少,歷年多患亢旱”[6]105。而且,“全境均旱田,無河流可興溝渠,無井泉可供灌溉”[6]108。在這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村民“靠天吃飯”的觀念較為明顯,加之生活空間相對閉塞,“這就為村落信仰的產生、存在和傳承提供了條件”[7]。人們在自然災害面前無能為力,只能燒香拜佛祈求神靈的庇佑,因此,前魏村的廟宇較多,“解放前共有7座,分別是關帝廟(村東)、南海菩薩廟(村南)、三官廟(村北)、玉皇廟和齊天大圣廟(村西),另外,村東北角還有一座姜太公廟,村主街上還有一座土地廟”(張玉寶)。經過“破四舊”運動后,現在仍保留下來4座,分別是土地廟、玉皇廟、姜太公廟和齊天大圣廟。此外,村民家中均供奉天地、土地、灶王、全神、財神、南海等諸神位。逢年過節、初一、十五村民都要擺供品、燒香、磕頭,以祈求神靈保佑。前魏村的宗教活動異常豐富,在全村影響大的就屬“打醮”和“擺會”活動。“打醮”是道士設壇為人做法事以求福禳災的一種道教活動;“擺會”則是一種以佛爺信仰為代表的佛教活動,通過念誦佛經以祈福納祥。這2種宗教儀式盡管在具體內容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有一項活動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通過“玩拳”娛神娛人,以增加吉祥和諧的喜慶氣氛。炫耀武力、比試武功的意圖已明顯淡化,取而代之的則是同喜同樂、相互祈福、情感交流的互助心理。
村落社區通過“玩拳”構建休閑文化空間的方式有3種類型:一是個體性的,即以娛樂身心、強健體魄、提高修養為目的的“娛己”型玩拳方式;二是交往性的,即在民俗節日走出拳場到公共場合進行的交流表演、渲染節日氛圍的“娛他”型玩拳方式;三是宗教性的,即在宗教儀式中擔當“娛神”重任的玩拳方式。通過這3種方式,村落社區就在文化層面上構建起了一個其樂融融、“人神共娛”的娛樂文化空間。
3 “說拳”:對村落道德倫理文化空間的構建
3.1說古:凈化村落道德秩序的手段說古,就是講歷史故事。前魏村人所講的歷史故事,大都是歷代拳師的傳奇故事。這些故事在口口相傳的過程中,被不斷地“進行一種有意的重構”[8],即格爾茨所謂的“深描”[9],最擅長于演繹那種武術人德藝雙馨、匡扶正義的英雄事跡。在鄉村社會講故事、聽故事是一種靈活便捷、成本低廉的道德教化活動,即使文化水平很低的村民也能聽得懂,并能從中領會到主人公的高尚品德和俠義之舉。前魏村的老人大都能隨口講上3~5個膾炙人口的故事,有的甚至能講到10多個。“老輩拳師的故事多著呢!比如,武探花護駕西域行、三德請師、史聰明皇宮教拳、佛祖梅開授拳、蔡師爺傳道來河北、刀劈飛雞、廟中仙人授藝等等,還有很多,都是我們梅花拳的故事”(李玉琢)。這些故事可歸為2類:一類是真實故事,即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大都是某些武術名人的生活經歷;另一類是民間傳說,這類故事往往帶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一種是神話化了的歷史,即原本是歷史事實,后來卻被附加上了許多神性的東西,故事喪失了其歷史性,轉而成為了一種理想或信念;另一種是歷史化了的神話,故事本來源自于神話,然而在歷代反復地講述中,由于聽眾并不在乎它含有多少真實性成分,最終就信以為真,把它們當成歷史了)。不管是哪類故事,其主人公都代表了忠厚、仁愛、正義、俠勇等傳統美德。可見,武術故事所傳遞的是對后人進行導德齊禮的教化信息。
3.2說招:以和為貴的比武形式長久以來,強調社會的和諧融洽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顯著的特征之一[10]。特別是在鄉村社會,以和為貴的處世方略更是根深蒂固。儒家思想追求的溫、良、恭、儉、讓,既是對個人修養提出的要求,也是檢驗良好社會風尚的標尺。對于村落社區而言,最理想的自治狀態就是村民之間“和睦”而“不爭”。然而,對于武術人而言,常會因為比武而大動干戈,不僅傷了和氣,更有甚者還會擾亂村落正常的生活秩序。為了避免沖突、化解爭斗,前魏村傳承著一種“說招”的比武方式。就是用交談的方式把自己進攻的招式告訴對方,然后聽對方說如何防守,或對方一說出進攻之招,我立刻答出破解之法。如此往復,循環不已,在言語的“你來我往”中比試就完成了。“我們很少動手比武,越是老拳師越喜歡‘說招’,不是因為不能打了,而是怕傷了和氣,無論誰‘花了臉’,都沒面子,是吧?……就那么說說,比劃比劃就算是比武了,而噼里啪啦打起來的比武,在這里不常見了”(李玉普)。一場比武,用“說招”的方式能分出高下,自然會和和氣氣地結束。僅“說招”也不能完全代替動手比試,只是人們在“貴和”“尚和”等傳統思想的影響下,更希望把武力沖突降低到最低,以求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相處,安寧無爭。這樣既能點到為止,又給對手留了顏面。“說招”把武術比試之“做”異化成了“說”,以交談的方式替代實實在在的身體對抗,由“動手”變成了“動嘴”,或變成“只說不做”,契合了“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和諧文明價值取向[11]。
3.3盤道:與陌生人的交流方式武林中向來就有“盤道”的習慣,所謂的“盤道”就是武術人用行話,對陌生人進行“盤問”及陌生人“回答”的過程。“盤道”并不是有意為難陌生人或對陌生人的挑釁,而是一種友善的交流方式,是武術人為確認陌生人的身份,而謹慎采用的一種自保性的語言試探。前魏村拳民“盤道”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問——你從哪里來?答——從東土而來。再問——你到哪里去?再答——去西域拜師學藝。又問——拜誰為師?又答——半云空中一領席,上寫天地君親師。還問——你吃的是誰家的飯?還答——鄒、孟二師家(王立穩)。經過這樣一番問答,如果陌生人對答如流,那么就知道他是“在拳”的“門內人”了,應熱情招待,接下來就是擺輩分、論稱呼了[12]。在前魏村,梅花拳弟子素來強調“天下梅花一家人”,只要是“在拳”的弟子,不管是本村的還是鄰村的,也不論是本省的還是他省的,甚至是國際友人,見面時只要一“盤道”,一說出你在拳派中的輩分,就立刻知道該如何相互稱呼,晚輩還要向前輩行禮問好[13]。梅花拳派的這種“盤道”行為已經深深地扎根于廣大弟子的內心深處,并形成了一種習慣。當然,伴隨著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遷,以上程序雖然有所簡化,但“盤道”的習俗始終以一種慣性的力量在廣大梅花拳弟子中傳承不息。
知識分子可以在黃卷青燈、讀書萬卷中與古人“神交”,而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拳民則只能通過“說拳”與傳統文化“神交”了,并在反復的述說中品味著武林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正是因為“說拳”有了這種文化意義上的內涵,拳民的體味才不會只限于脆弱個體的表面娛樂和現實功利,而是上升為一種超越自我的道德感、責任感和使命感[14]。“說拳”在構建村落道德倫理文化空間的過程中擔當著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不僅是習武練拳者的理性追求,更含有道德教化、倫理關懷、情感潤澤乃至自我實現的內在文化意義。
4 “亮拳”:對村落權力文化空間的構建
前魏村梅花拳亮拳的傳統由來已久,往往“趁商賈墟市之場,約期聚眾,在大庭廣眾之前,公開比賽表演,名曰‘亮拳’”[15]。亮拳活動突出一個“亮”字,即明白地、清楚地、響亮地展示給別人看。據前魏村梅花拳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李玉琢回憶,“以前的亮拳還有比武的內容,但現在基本上沒有了,只有表演了”(李玉琢)。其實,無論是比武還是表演,拳民們都是在“比試”武功,只是方式不同。所以,亮拳的目的性非常明確,就是要炫耀武功、震懾他人。
4.1使武術人獲得“隱權力” 在儒家“貴和”“尚和”等禮法思想的長期浸染下,中國人普遍形成了“賤訟”“息訟”“無訟”的觀念。特別是在廣大鄉村,村民都認為打官司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所以,在遇到矛盾糾紛時,往往習慣找村里的“頭面人物”出面調解而不是到政府部門告狀[16]。這種“頭面人物”雖然不是政府官員,卻能憑借自己在村里的威望行使話語權。借用吳鉤先生提出的概念,這種權力就是“隱權力”[17]。它是一種雖缺乏合法性卻能產生巨大影響力的非正式權力,主要通過個人威望、人情關系、社會影響力等因素累積而成。在前魏村的“頭面人物”中,武術能人占很大比例,而他們的這種“隱權力”就是靠“亮拳”時展示武功而獲得的威望和震懾力。在采訪中,一提起梅花拳,村民就會說:“李玉琢武功最好,最厲害,亮拳的時候,只要他一上場,全場都給他叫好”(王林竹)。所以,在每次推選本村民俗活動的“會首”時,李玉琢都是其中之一。就是因為李玉琢在亮拳活動中,展示了自己的高超武功,足以令人震服。“村里的任何活動,只要他一出現,準能鎮得住場!你想啊,凡是調皮搗蛋的都是會三拳兩腳的,誰的功夫強,他們才聽誰的”(王林竹)。由此可見,武術人在亮拳活動中展現出來的精湛武藝是其獲得“隱權力”的主要來源,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憑借這種權力足以達到化解矛盾、息事寧人的目的。
4.2促進武術人的社會化武術人之所以重視“亮拳”,就是希望通過在公開場合的武藝展示,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替自己揚名,以利于自己將來更好地參與到社會生活中。所以,“亮拳”還是一個把自己推向社會、得到社會認可的社會化過程。在梅花拳的亮拳傳統中,往往是“一村亮拳,多村參與”。前魏村亮拳當天,還不到8:00,梅拳圣地已經人頭攢動、擁擠不堪。雖然大都是附近的梅花拳村民,但也不乏鄰縣、鄰省的梅花拳表演隊。對習武者而言,這是一個提高社會知名度的絕佳機會。武功高強者往往會在一朝一夕之間成為遠近聞名的武術能人或村落精英。“亮拳的時候,不用通名報姓,只要你練得好,人家都會去打聽你是哪個村的,叫什么名字。練得不好,報名字也沒人記得住”(陳志善)。“其他村梅花拳練得好的,我們都是通過亮拳知道的,比如楊家莊的邢銀超、北楊莊的邢玉棟、后馬井的李濟民、趙寨村的王鳳剛、磚窯村的侯永武,都是亮拳中的高手,誰都認得,不認得也聽說過他們的大名!我們村的李玉琢、王孟強,附近十里八鄉的也都認得”(王連深)。然而,提高知名度只是武術人社會化的第一步,更重要的還得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例如,20世紀80—90年代,前魏村的梅花拳弟子在村落事務中都起著帶頭作用,影響了一大批人[18]。如今,在發展鄉村經濟、傳承村落文化等社會實踐中,相對封閉的村落更須依靠武術名人進行溝通與協調。在廣宗縣,很多村都是拳民村,習武練拳者占大多數,他們只知道附近村莊里誰練拳練得好,在村際互動中,這些武術能人能發揮重要作用。
4.3提升武術人的功夫俗話說,“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亮拳時每個弟子為了要在“臺上”展示功夫、炫耀武力,就必須在“臺下”(拳場)做充足的準備,即勤修苦練。因為只有技壓群雄、脫穎而出,才能震懾對方,達到“亮拳”的目的,也才能在鄉人面前更有話語權。在傳統的鄉村社區里,一個人要活得有尊嚴,就必須得有“顏面”。“顏面”必須通過互動和交往活動才能獲得,即“顏面”需要從別人那里才能獲得。武術人在鄉民面前的“亮拳”正好構成了“顏面”的生存空間,成為拳民爭“顏面”的一次人際互動。然而要想得到“顏面”,就必須先做好“自己”。為了做足“顏面”,拳民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在日常的拳場訓練中苦練不輟,只有平時多流汗才能在亮拳時拿出值得炫耀的武功,這就在無形中為習武者提供了拳場苦練的動機,極有利于自身武功的日益精進。“老輩人亮拳,都是以拳場為單位,誰該上誰不該上,誰先上誰后上,都是非常講究的,生怕水平不夠而影響了整個拳場的聲譽。要想在亮拳時大顯身手,就必須在平日里苦練架子,馬虎不得”(張蘭娥)。所以,亮拳時各方拳民都是把精心準備的最好的武功表演給觀眾看。另外,拳民在展示武功的同時,也為他人提供了一個相互學習、交流技藝的機會,使觀眾既可以學到新奇實用的招式,又可以在與他者的對照中尋找不足,為日后自我武功的精進提供訓練標準或努力的方向。無論從表演者的角度,還是從觀賞者的角度而言,亮拳都是一種提升練功效果的手段。
由此可見,爭取“顏面”是村落社區的典型文化特性之一,它不僅僅是人際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更是村民能夠立足的根基。村落社區的“亮拳”活動便是拳民獲得“顏面”的一種主要途徑,它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隱權力,還可以通過各種“功夫”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武功,以至于改善人際關系。最終,村民通過“亮拳—顏面—權力”的運作機制,完成村落權力文化空間的構建,并以此有效促進村落社區的人際和諧及秩序穩定。
5 結束語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首先應是社會文化的建設,對村落社區的文化構建才是農民迫切需要的。而今,鄉土社會的急劇變遷導致農民社會文化生活極度匱乏,甚至出現了一些畸形文化形態,急需給予正確的引導和有力支持,積極建構健康、活潑的社會文化形態。作為村落武術3種存在形態的“說拳”“玩拳” “亮拳”,正是一種村落文化的集體記憶,它完全融入了當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代表了當地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倫理道德、處世原則、生活方式等。“說拳”“玩拳”“亮拳”已成為構建村落社區空間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有效載體。對其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適當利用,不僅有助于滿足農民對村落文化的實際需求,提升農民的幸福指數,還有利于發揮村落社區文化的獨特魅力,最終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