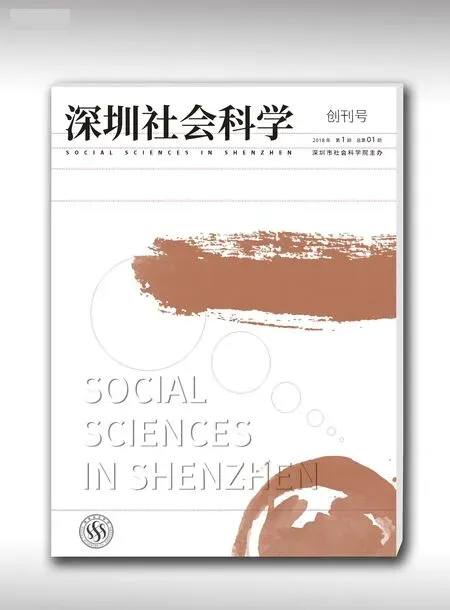“慎獨”“自反”與“目光”*—儒家修身學中的自我反省向度
陳立勝
在《荀子·不茍》《莊子·大宗師》《管子·心術》《文子·精誠》與《禮記》之《中庸》《大學》《禮器》三篇等傳世經典以及出土文獻馬王堆帛書與郭店竹簡《五行》中,都出現了“慎其獨”或“見獨”一類的“獨”文本,這無疑表明“獨”的觀念乃是先秦儒道二家工夫論之共同議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島森哲男就指出,在先秦儒家的慎獨文字之中,“獨”字提出的背景通常是設定了除了自己以外、無他人在看這一場景。為何慎獨的要求通常是在這種場景下提出來呢?這是緣于“對人性的洞察或危懼而來”,因為“人類會因為他者的在或不在而改變態度,尤其他者不在時,人性有容易偏向惡的傾向”,故在慎其獨的文本之中,“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的說法便格外搶眼,這是一種“從外部而來的銳利的視線”,是“鬼神的視線”,慎獨文本之中濃厚的他者的目光這一思想氛圍,“顯示了他者的視線對自己滲透的深度,以及人生活在共同體中彼此有著密切關系。即使對社會歸屬感稀薄的我們,有時也不得不感受到這樣的視線,更何況對于緊密生活在共同體的古代人來說,必定更強烈感受到視線的威力。”①島森哲男:《慎獨思想》,梁濤、斯云龍編:《出土文獻與君子慎獨—慎獨問題討論集》,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14頁。
筆者認為,島森哲男對慎獨文本之中的他者目光的闡述,對于我們理解儒家的省身工夫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實際上,在儒家修身學中,無論在慎獨要求抑或在“三自反”的主張之中,都設定了一種“他者的目光”,這個他者的目光首先表現為“鬼神的目光”與“他人的目光”,而隨著儒家人文主義精神之勃興,他者的目光漸被每個人內在的“心目之光”“良知之光”所替代。在儒家修身工夫的“反省”向度之中,“鬼神的目光”“他者的目光”與“良知之光”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一、“鬼神的目光”
古人很早就觀察到“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之兩面性:在眾目睽睽的“前臺”,自我容易配合觀眾目光的“角色期待”,而表現出循規蹈矩、彬彬有禮之一面,及至退至“后臺”,則容易暴露原形,顯示出私小之面目。《慎子》有句話就生動地描述這種人性的“雙面”:“能辭萬鐘之祿于朝陛,不能不拾一金于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于廟宇,不能不弛一容于獨居之余。蓋人情每狎于所私故也。”因“朝陛”與“無人之地”、“廟宇”與“獨居之余”場景之轉換,人之行為表現出強烈的反差:在權力之大庭與神圣之空間表現光鮮動人,在隱秘與私己之場所則寸利必得、放肆無忌。《慎子》這里所描述的人性現象屬于典型的“人莫不自為”、“每狎于所私”這一人性丑陋的一面,同樣的觀察也見于《大學》:“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如何克服此人性之有限性?一個最直接的方式莫過于讓行動者始終保持活動于“前臺”、活動于“光天化日之下”之感受。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這強烈地暗示出一種通過公共的目光審視自家之“過”的省思模式,就如同在都市行走的今人無時不感受到既高清又無死角的全程監控一樣。于是,老子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說法。是的,今天大陸都市的監控系統就叫天網工程。不過古人的天網工程的主角不是無處不在的攝像頭,而是比攝像頭更加神奇的“鬼神”:《詩·大雅·抑》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神”的臨在不可揣度,曾子所說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亦描述出古人對這種“目光”的敬畏、忌憚之感受。《墨子·天志上》指出,處家、處國雖“共相儆戒”“不可不戒”“不可不慎”,但得罪于家長,猶可逃往鄰家,躲避家長之懲罰;得罪于國君,猶可逃往鄰國,躲避國君之懲罰;而得罪于天,則無所逃避:“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將無所以逃避之者矣。”(《天志下》)因為“鬼神的目光”無處不在(《明鬼下》):“子墨子言曰:雖有深溪、博林、幽澗毋(無)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堇),見有鬼神視之。”②漢代天人感應思想大盛,人之罪行,天必知之、感之而誅伐之。《淮南子·覽冥訓》云:“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閑,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新書·耳痹》亦有類似的說法:“故天之誅伐,不可為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莊子·庚桑楚》也說:“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閑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獨行。”“顯明”處人之目光與“幽閑”處“鬼神的目光”共同交織成為無處、無時不在的“他者的目光”,讓人在行動的每一刻都有被人神共同關注(“明乎人、明乎鬼”)的感受,惟如此方能做到郭象注中所說“幽顯無愧于心,則獨行而不懼”。顯然,《庚桑楚》的說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庸》的說法,林希逸就說:“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后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①林希逸著、周啟成校注:《莊子口義校注》卷23,中華書局,1997年,第360頁。白居易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后(一作‘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詩中透露出“人的目光”的有限性,理學家張履祥就撰詩駁正曰:“周公自有周公志,王莽終懷王莽情。勿謂隱微人不見,千秋公論日星明。”②張履祥著、陳祖武點校:《題王介甫詩后》,《楊園先生全集》,中華書局,2002年,第9頁。此白居易詩自明代即被誤傳為王安石所作。“他者的目光”成為超越時代的目光,換言之,“隱微”之事縱一世不為人知,卻最終也難逃“千秋公論”這一“歷史目光”的審視。
在這樣一種“他者的目光”的濃厚文化心理氛圍下,《大學》之“慎其獨”的鄭玄之注也就不難理解了:“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小人于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可以肯定的是,鄭玄將“獨”訓為“閑居之所為”,其背后的問題意識看來還是與這種無處不在的“他者的目光”相關。實際上,如果我們瀏覽以下鄭玄前后的思想家對“慎其獨”文本的理解,都可以看到它們都有共同的問題意識,即對“人情之所忽”有高度的警惕:
劉向《說苑·敬慎》:存亡禍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誡,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隠,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第240頁。
《后漢書·楊震列傳》:(王密)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④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第7冊,中華書局,1965,第1760頁。
徐干《中論·法象》: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⑤徐干撰、孫啟治解詁:《中論解詁》,中華書局,2014,第25頁。
“隱微”、“幽微”、“孤獨”之處是常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能夠在此處“敬慎”,方可稱為君子。楊震暮夜卻金故事明確指出,夜晚所發生之事除了當事人知道之外,還有“天知”與“神知”這一無處不在的超越性的“知”之向度。徐干則將君子敬孤獨慎幽微與“鬼神不得見其隙”相提并論,再次展現“他者的目光”之無所不在性。其后,《劉子·慎獨》更是盡暢此鬼神目光之旨趣:“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于明,行悖于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這里的著眼點仍然還是幽暗之處的舉止(“行悖于幽”)。鄭玄著重從閑居之所為訓“獨”良有以也。
能夠在“幽閑”處、“屋漏處”、孤獨幽微處貞定其心志的人格稱為“君子”,《淮南子·說山訓》說:“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這種獨立不改、表里如一的君子人格也正是儒家“慎其獨”工夫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一語早見于《晏子春秋》,及至《文子·精誠》,則將“不慚于影”直接與“君子慎其獨”聯系在一起:“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圣人不慚于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章太炎將儒家的慎獨觀念追溯至晏嬰,不亦宜乎!①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79~980頁。實際上,《論語·鄉黨》對夫子行為之描述,無論在鄉黨抑或在朝廷夫子之行為表現出修己以敬的高度一致性,無疑是慎獨工夫之典范。
《中庸》之中濃墨重彩的“鬼神的目光”實際上可以被視為殷周鬼神文化的遺留。“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昭,見也。文王見于天,且在帝左右,文王顯現于天、與帝同在的畫面無疑折射出的是先民對祖靈與上天的仰視與敬畏之情。“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管四方,求民之莫”(《詩經·大雅·皇矣》),“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詩經·大雅·大明》),“敬天之怒,無敢豫戲”(《詩經·大雅·板》),由《詩經》中的這些篇章可以管窺先民對一種自上而下的、威懾性的、監視性的鬼神目光之感受。只是這種宗教性的“他者的目光”在文明的軸心期突破的過程之中,經過儒家人文主義的洗禮,而逐漸內化為一種“天命意識”、一種“仁義禮智根于心”的德性生命意識。故儒家“慎其獨”之“獨”在本質上乃是天所賦予的內在的“德性”及其棲息之所(“內心”),用孟子的話說是“天爵”“良貴”。誠如島森哲男所指出的,這種指向內在良心的目光乃是“具有積極意義的‘獨’”,它有別于“他者的目光”這一消極意義上的“獨”,“積極意義上的獨”則表現為“自己本身成為視線的主人,用內省的視線來規律自己。也就是所謂‘毋自欺’(《大學》)、‘自謙’(《大學》)、‘內省不疚,無惡于志’(《中庸》)的立場。”②島森哲男:《慎獨思想》,梁濤、斯云龍編:《出土文獻與君子慎獨—慎獨問題討論集》,第16~17頁。而這種“內省的視線”與孟子反身而誠、求其放心的工夫取向緊密相關,“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基于內在的存養之功所呈現的“恒心”自是一浩然之氣之道德場域,美、大、圣、神則是其華彩流光(“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儒家對“獨處”行為有著嚴格的要求,這種要求在后來的理學修身工夫實踐之中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甚至最隱秘的夫妻生活、床第生活也成了“鬼神的目光”的場所。顏元有“閨門之內,肅若朝廷”之說,李二曲更是稱:“閨門床第之際,莫非上天昭鑒之所,處閨門如處大庭,心思言動,毫不自茍。不愧其妻,斯不愧天地。”③李颙撰、陳俊民點校:《二曲集》卷三十,中華書局,1996年,第420頁。呂妙芬《成圣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一書(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第六章第二節(“廣嗣與寡欲的夫婦生活”)對此有生動描述。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對“獨處”這一嚴格要求僅限于“修己”這一自我關涉面向(用孔子的話說是“躬自厚”),它絕不意味著對他人隱私的干涉,相反《禮記》之中不乏對他人隱私保護之禮儀,如“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禮記·曲禮》中的這一行為準則在今天仍不失其意義。而《韓詩外傳》所記孟子與孟母之對話則表明《禮記·曲禮》的這一規定由來已久: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于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①韓嬰:《韓詩外傳》卷九第十七章,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第322頁。
君子必須對他人獨處之隱私保持足夠的尊重,“箕踞”本是一非常不雅之坐姿(古人上衣下裳,箕踞極易露出私處),孔子老友原壤箕踞以待,就被夫子斥為無禮并以杖擊其小腿(《論語·憲問》)。
二、“他人的目光”
在儒家的省身傳統之中尚有另一種“他者的目光”,這種“他者的目光”乃是在具體的生活處境之中、在人際的互動之中所遭遇到的“他人的目光”。這種“他人的目光”雖然也往往讓我感受到不適、不安,但它有別于“鬼神的目光”,它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監視性的、威懾性的目光,而是與我的目光平行的、向我表達某種不滿的目光,是讓我感到受冷漠、懷疑、蔑視、鄙夷等等的目光。在先秦的政治哲學之中,人們往往把這種“他人的目光”視為君主、為政者獲得清醒的自我認識之不可或缺的借鏡,《墨子·非攻上》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面之容,鏡于人則知吉與兇。”《國語·吳語》亦有“王其盍亦鑒于人,無鑒于水”之說,這些說法的意思不外是在他者的反應(目光、表情、舉止)那里認清自己的“欠缺”與“虧欠”。而在儒家這里,這種日常的“他人的目光”則應成為君子“反身而誠”的一個契機,這是先秦儒家“自反”思想的一個核心內容。
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又說:“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孟子·離婁下》)《荀子·榮辱》也有類似的說法:“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而《荀子·法行》則明確引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顯然孟子的三自反思想出自曾子,實際上,曾子三省工夫(《論語·學而》)未嘗不可視為是一種自反工夫,這是一種事后的自我省思②《大戴禮記》有兩處文字暗示三省的工夫乃是在晚上進行的:《曾子立事》記曾子語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曾子制言中》:“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實際上,如果我們考慮《國語·魯語下》對“士”一天修身內容所做的以下描述:“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后即安”,則可以斷定曾子三省工夫即屬于“夜而計過無憾”一類的士之修身活動。,而三省之對象均牽涉到對待他者的態度。這些看法最終都可以溯源到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以及顏子“犯而不校”這一要求上面。可以說“自反”乃是先秦儒家修身工夫的共法。實際上墨子亦分享儒家這一自反的修身理念,其“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墨子·親士》)即是夫子恭厚薄責之義,而《墨子·修身》更是指出,君子如見不修行、見毀則應“反之身”。“仁義忠信”這些德目所涉及他人的態度最終都是由內在的心性向度發出的,需要省思的是這個“內”之向度是否是由衷的、真誠不妄的,如是,則是“動以天”,用孟子的話就是“誠者天之道”;如否,則是“動以人”,則須反身而誠,此為“思誠者人之道”,《荀子·不茍》中以“誠心守仁”、“誠心行義”來指點“君子養心莫善于誠”之工夫,跟孟子“反身而誠”的工夫也是高度一致的,學界在追溯孟子誠身工夫時往往指出子思的影響,此誠然不錯,但論起源頭當應進一步上溯至曾子之自反的工夫論這里。
人之生存于世,其目光通常是向外的,尋視于周遭世界之人與物:“行路”尋視著遠方與腳下,“生產”尋視著工具與活動所關涉之對象,“交往”則尋視著各色人等,諸如此類。而在交往活動之中,眼神的交流通常或是向對方表達我們的意圖、訴求、情感,或是透過對方的眼神而力抵其內心世界。在我們遭遇到對方不屑、不滿、憤怒的表情、目光之際,或是針鋒相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牙還牙,甚或加倍奉還,或是躲避,惹不起,躲得起。惟在儒家“自反”的要求之中,我們則順著他人向我表達不屑、不滿、憤怒的表情、目光而關注到“自我”,“他人的目光”成為我心靈生活的一面明鏡,他人的眼睛成了我自己心靈生活的窗戶:我藉著這個窗戶看到自家的內心世界。毫無疑問,這種“內視”乃是一種“審視”:我對他者的關愛是否是真誠的?我對他者尊敬是否是自然的?一言以蔽之,我內在的德性世界究竟有無欠缺以及有何欠缺?
孟子的三自反要求本是極高的道德自省要求,但后儒有不若顏子“犯而不校”之高明之疑問(楊時即有此疑問,見朱子《論語或問》卷八),對此馮少墟辯解說:“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詞,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且自反不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昔人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犯而不校,誤矣。”①馮從吾撰:《少墟集》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第89頁。少墟對“犯而不校”與“自反”之關系辨析甚精:“世之犯而必校者無論,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樣: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又以不校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橫逆即曰此妄人也,此禽獸也,何足與之校!如此,若與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又傲妄之尤者也,益失顏子不校之意矣;至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后之說,是又以不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厘千里之異耳,犯而不校談何容易!”同上書,第90頁。不過孟子“比妄人為禽獸”的說法還是遭到后儒的批評,認為“英氣太露”,王陽明說:“孟子三自反后比妄人為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于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者也。”②王陽明撰,吳光、錢明等編校:《新編王陽明全集》,第5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00頁。
當然陽明后學之中也有不認同陽明之批評者,如面對門人對孟子三反之后比妄人為禽獸之如下質疑:“孔子于君子既斷謂之‘無爭’,孟子亦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大率修身為本故,是洙泗相傳之家法也。決無有向人分上校計之理。何三反之后,乃曰:‘如此,則于禽獸奚擇焉?又何難焉?’此其絕人也得無已甚,而自反之道尚為未至耶……”,李見羅以自己的切身經歷給出了以下回應:“經創知懲,遇跌長智。自非身履其境,亦誰識孟子立言之意于自反乃最深切乎?偶記二十載前,曾同從兄迪菴看山。抵山落步,為騾所踶。予時負痛之甚,手自拊摩。迪菴兄亦就摩之。乃直悔其落腳之失支持,而曾不以一語責及于騾也。予因嘻笑曰:‘予乃今知禽獸何難,孟子之非輕絕人也。至于自反而忠而曾莫之省焉,是真猶木石禽蟲之蠢然無知識者矣,而尚可責乎?是正教人以自反之至,到底不以纖毫之意氣涉向人邊也。’”①李材:《教學錄》卷九,《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12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52頁。毫無疑問,圍繞孟子三自反工夫所展開的討論,反映了理學自反工夫日趨細膩與嚴格之趨勢。
三、“良知的目光”
在儒家的反省工夫之中,還有一種“目光現象”值得留意,這是由“三自反”而推衍出一種自我審視的目光,曾子的三省、孟子的三自反實際上有一理論上的預設,即有一反省內視的主體可對其內在的心靈生活加以審視、檢查。羅近溪即揭示了這一現象:
諸友靜坐,寂然無嘩,良久有將欲為問難者。羅子乃止令復坐,徐徐語之曰:“諸君當此靜默之境,能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朗;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在于懷中,卻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待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鏡否?”羅子曰:“此個鏡子,原得于造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后因反己乃知也。”②方祖猷等編校整理:《羅汝芳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92~193頁。在羅近溪的描述之中,讓我們照見自己的鏡子不再是“他人的目光”與“他人的面容”,而是每個人抱于懷中的“明鏡”,這面鏡子“與生俱生”,故是先天本具的;“不待人照而常自照”;故是獨立的、無待的;“人纖毫瞞他不過”(“心目醒然”),故是不可欺的。它所照出的乃是內外一如的自家面目:“心事端莊”則“意態自然精明”,“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而“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后因反己乃知也”表明:“念頭塵俗”、“不忠不仁”,則是自我放縱之結果,用王陽明的話說,不忠、不仁之念起處,“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自反”即是返回到這一“不應放過”的“自知”向度。近溪的“明鏡說”充分顯明,良知乃是內在的、先天本具的、恒常的,完全超越了人己、共處獨處之對待的“光之體”。近溪“良知光照”說可溯源至陽明處,昔南大吉向陽明問學,自述臨政多過,為何陽明無一言及之,陽明答曰:“吾言之矣”。大吉不解。陽明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始恍然有悟“良知自知之”之說。其后,大吉屢屢向陽明坦誠其過,并有“身過可勉,心過奈何?”之請益,王陽明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腳。此正入圣之機也。勉之。”③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臺北學生書局,2006年修訂版,第415~416頁。
而在劉蕺山的靜坐訟過法之中,這種自我審視的“良知的目光”與“鬼神的目光”、“他人的目光”交織在一起,成為一道“內在而超越”的強光,具有照徹心靈整體的透視力: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凈幾,布一蒲團座子于下,方會平旦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間,鑒臨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進而敕之,曰:“爾固儼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獸乃禽,種種墮落,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敕之曰:“莫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頃之,一線清明之氣徐徐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霍間,整身而起,閉合終日。①劉宗周:《人譜》,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2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6頁。
這里,“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凈幾,布一蒲團座子于下”,乃是要營造一種靜謐的宗教氛圍,“平旦”這一時間點的選擇是考慮到孟子“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孟子·告子上》)這一說法,這是最適合省察與涵養的時機。“鑒臨有赫”無疑四字衍自《詩經》“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乃是指是指“鬼神的目光”,而“十目十手”則又系“他人的目光”與指點,顯然這是“鬼神的目光”與“他人的目光”共同交織而成的“良知之光”,其實質是要達到“通身是眼”②“通身是眼”一說出自李颙撰、陳俊民點校《二曲集》卷4,中華書局,1996年,第37頁。之效果,良知之為高懸的明鏡,如洋洋在上的目光,如十目十手之所睽、所指,我全幅的心靈生活完全暴露在良知的強光聚焦之下。在劉蕺山的靜坐訟過儀式之中,儒家的反省的理論結構已經昭然若揭:
(1)“超越于我”的目光之永恒在場(鑒臨有赫、十目十指),在此威懾性氛圍下,“良知的呼聲”乃是類似于審判官的嚴厲的聲音。
(2)“鑒臨有赫”的目光雖超越于有待審判的習染之我(客我),但又不是一完全的“外在之超越”,究其實,它不過是“內在”于我的“獨體”“良知”之光照。質言之,在這一虛擬的審判法庭之中,訴訟者與應訟者是同一個當事人。
(3)在嚴格而逼真的審判氛圍下,意識生活之中各種疾病,特別是積淀、潛伏在無意識深處的“宿疚”成為反省、省察之對象。
(4)反省、省察乃一種道德上的審判、一種心靈的拷問(“若身親三木”),作為“良知呼聲”的被呼喚者成了一位“有罪者”、一位“被審判者”。
(5)反省、省察過程本身既是一“審判過程”又是一當下“執行過程”,是一“治療過程”、一“涵養過程”,朱子那里省察與涵養工夫在此融為即省察即涵養的工夫:一邊省察(“痛汗微星,赤光發頰”),一邊涵養、“葆任”(“一線清明之氣徐徐來”、“一真自若,湛湛澄澄”)。
論者(牟宗三、王汎森等)或將劉蕺山的這種靜坐訟過法追溯至佛教的《法華懺儀》,或認為它跟西方式靈魂審判(the soul on trial)有相近之處③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冊,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31頁。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4頁。Pei-yi Wu,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4.何俊:《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5~346頁。,確實,旨在轉化自我的反省法在世界各大宗教傳統之中本是一“共法”。其實在儒家傳統自孔子提出“內自訟”的要求后,這種自我審判的反省方法就一直是儒者修身一個重要工夫,王陽明“倒巢搜賊”式的省察之功已經為劉蕺山靜坐訟過法的出場做足了鋪墊工作: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①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臺北學生書局,2006年修訂版,第75頁。在這里,良知之光照(“一眼看著,一耳聽著”)被擬為捉賊的捕頭、捕鼠的貓之銳利的目光,而潛藏在意識生活之中的“好色好貨好名等私”則被擬為賊與鼠,于是,自我省察與反省成了一場捕頭捉賊、貓捕老鼠的游戲。在良知“知是知非”的光照下,如賊、鼠一樣潛伏在暗處的私心雜念遂暴露目標(“一念萌動”)而自投羅網(“即與克去”)。
而早在程子那里,心靈生活自我澄澈的工夫就與鬼神的目光、上帝的目光的綰結在一起:
“忠信所以進徳”,“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與后,己與人。②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3頁。
“終日對越在天”“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說明君子進德修身的實踐活動始終是在一“上帝臨在”(“上帝臨女”)的場域之中展開的,而“敬”(“毋不敬”)之工夫最能保持此心靈生活的肅穆、嚴謹與神圣性。毫無疑問,在程子那里,“對越在天”首先是在心靈的自我澄澈之中敞開的,朱子就說“人心茍正,表里洞達,無纖豪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又告誡門人“今且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③《朱子語類》卷八十七,《朱子全書》,第17冊,第2984頁。朱子鬼神觀研究可參吾妻重二:《朱熹的鬼神論和氣的邏輯》,吾妻重二著、付錫洪等譯:《朱子學的新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41~155頁;吳展良:《朱子之鬼神論述義》,《漢學研究》31卷第4期,2013年,第111~144頁。這種重在心地上用功的路徑跟道家中“神明來舍”的觀念是相通的:“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管子·心術》)“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莊子·知北游》)理學家所說的敬的工夫與莊子所謂的“心齋”工夫確實有某種對應性,吳與弼“精白一心,對越神明”④吳與弼:《康齋集》,《四庫全書》,第125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575頁。的說法更是與莊子“虛室生白”、“鬼神將來舍”的說法(《莊子·人間世》)如出一轍。不過在理學家的對越上帝的論述之中,“對越”一詞逐漸具有了“面見”“直面”“面對”的意思⑤翟奎鳳:《“對越上帝”與儒學的宗教性》,《哲學動態》,2017年第10期。,中晚明省過工夫之中“上帝的目光”(天之靈光)與“心靈的目光”(心之靈光)的交織就折射出這一現象,而劉蕺山的靜坐訟過法無疑是其經典案例。牟宗三先生在論程子“對越在天”的觀念時指出,“對越在天”有“原始之超越地對”與“經過孔子之仁與孟子之心性而為內在地對”兩義:
凡《詩》《書》中說及帝、天,皆是超越地對,帝天皆有人格神之意。但經過孔子之仁與孟子之心性,則漸轉成道德的、形而上的實體義,超越的帝天與內在的心性打成一片,無論帝天或心性皆變成能起宇宙生化或道德創造之寂感真幾,就此而言“對越在天”便為內在地對,此即所謂“覿體承當”也。面對既超越而又內在之道德實體而承當下來,以清澈光暢吾人之生命,便是內在地對,此是進德修業之更為內在化與深邃化。①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6冊,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5~26頁。
就劉蕺山靜坐訟過法而看,牟先生的觀察還是很精準的,一方面,“鑒臨有赫”、“十目十指”的說法確實強烈地營造出“鬼神的目光”與“他者的目光”于我個己心靈生活的“超越性”,在此“超越于我”的他者目光注視下,“我”成了一個被審判者,然而另一方面,這一“目光”又出自“我”的“良知獨體”,這并不是一種完全異在的目光。在本質上,這是一種“出于我”(此為“內在”)而又“高于我”(此為“超越”)的目光。這種“出于我”而又“高于我”的結構,倒頗有點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之中對“此在”(Dasein)的良知呼喚現象的描述:“此在”在良知中呼喚自己本身,“此在”既是呼喚者,又是被召喚者,良知的呼聲“出于我而又逾越我”,由于良知所呼喚的乃是“此在”“本己的能在自身”,而這種本己的能在自身在“常人”狀態下被遮蔽、被壓抑已久,故良知的呼聲于此在聽來竟然像是一種“陌生的聲音”,“呼聲不是明確地由我呼出的,倒不如說‘有聲呼喚’”。劉蕺山“鑒臨有赫”“十目十指”的說法也是在營造一種“陌生的”“超越”于我的效果,但這個“逾越”的光照實際上是出于我的良知獨體,所謂“造化鬼神不必事,吾心之鬼神不可不事”②劉蕺山:《答履思二》,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3冊,第310頁。,吾心之鬼神即此“鑒臨有赫”之謂也。在此良知獨體的自我透視下,遮蔽我、扭曲我的“常人”格套被徹底剝落,最終我認出了我的“本己的能在本身”(“本來真面目”)。
不過,在明清之際省過思潮愈演愈烈的局勢下,儒學陣營之中確實不乏將“對越上帝”觀念重新恢復“原始之超越地對”之嘗試。李二曲說:“知鬼神體物不遺,則知無處無鬼神,無時無鬼神。人心甫動,鬼神即覺,存心之功,真無一時一刻而可忽,故必質諸鬼神而無疑,方可言學。”他還批評后儒淡化鬼神的觀念:“夫子贊鬼神之德之盛,分明說體物而不遺;乃后儒動言無鬼神,啟人無忌憚之心,而為不善于幽獨者,必此之言夫。”③李颙撰、陳俊民點校:《二曲集》卷30,第421頁。
結 論
1.“鬼神的目光”是無人之際、獨處之時一種超越的監視目光,“我”是這個目光聚焦下的“行動者”,“我”之舉止與眾人共處之時完全一樣,不欺暗室,因為“暗室”本不暗,“鬼神的目光”在嚴厲地盯著“我”(“舉頭三尺有神明”),故在“鬼神的目光”下,營造出的是“我必須……”(I must)這一當下的行為期待,伴隨這種期待而來的是“我”當下小心翼翼的舉止。
2.“三自反”處境下所遭遇的“他人的目光”是一種責備的目光、令“我”不安的目光,“我”順著這個目光返觀內視,“我”是對某一行為(“橫逆”)的“負責者”,“我”對自己適才對待他人的行動加以省察,它所省察的對象是“我”之內心世界對他人不滿、憤怒一類的負面的目光與表情究竟負何種責任、“我”在哪些方面本應做得更好而未能做好,故在三自反的“內視目光”下,營造出的是“我本應該……”(I should have)這一對適才發生的行動之反省,伴隨這種反省而來的是愧疚感(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3.靜坐訟過之中自我審視的“良知的目光”(“通身是眼”)是一種審判的目光,“我”是這一目光下的“有罪者”“被審判者”,面對這一鑒臨赫然之光,“我”全盤交待出自己心靈之隱情(以往的不當行為、宿疚、各種各樣潛存的私心雜念),“我”是聚光燈下的被審判者,當然“我”又是審判者:“兩造當庭,抵死讎對”,故在自我審視的“良知的目光”下,營造出的是“我認罪……”(I confess)這一對心靈生活負責的懺悔態度,伴隨著這種懺悔而來的是精神生命的重生。
4.這三種自我省思的模式各有側重,“鬼神的目光”讓“我”在獨居、暗室之中的行動與在大庭廣眾下的行動一樣保持一種連續性;藉著“他人的目光”“反觀內視”,則旨在對自己行動背后的情感、態度、動機加以檢討,讓“我”成為一個表里如一的真誠的道德行動者;出于良知的目光的自我審判則是一種專題化的蕩滌心靈染污“心理治療術”。三者之共同的旨趣均是通過省思而培育一德性人格,一無計順境(“得志”“達”)與逆境(“不得志”“窮”)、獨處(“幽閑”)與共處(“顯明”)始終如一、表里如一的獨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