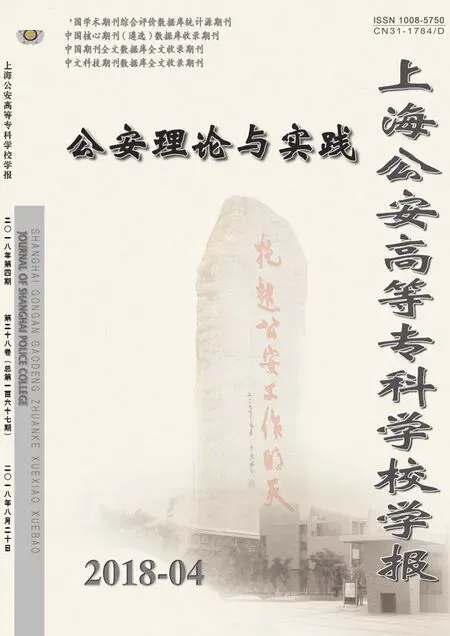非法組織賣血罪既遂標準探究
曹 堅,趙擁軍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上海 200052;上海市徐匯區(qū)人民法院, 上海 200235)
一、問題的緣起
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條規(guī)定的非法組織賣血罪僅以簡單罪狀將其客觀行為方式表述為“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由于司法實務中,該罪一般是由非法組織賣血活動的一系列環(huán)節(jié)組成,如通過網(wǎng)絡或者熟人介紹等途徑發(fā)布信息,有賣血意向的人與之聯(lián)系并約定見面時間和地點,然后見面或者直接前往賣血地點,辦理手續(xù),等待抽血,最后抽血并領(lǐng)取補貼等,其中應以哪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完成作為該罪的既遂標準,目前尚未形成共識。如刑法理論界有觀點認為,當被組織者沒有開始實際出賣血液,應屬于犯罪預備;若是正準備抽血時即被制止,則屬犯罪未遂;若已經(jīng)完成抽血過程,具備了損害賣血者健康的抽象危險,應成立犯罪既遂。①陳洪兵:《公共危險犯解釋論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頁。可見,該觀點認為非法組織賣血罪的既遂是以被組織賣血者的血液是否被成功抽出作為標準。也有觀點認為,只要為使他人出賣血液而實施了組織行為便構(gòu)成非法組織賣血罪的既遂,且不存在未遂②李少平、南英、張述元、劉學文、胡云騰:《刑法案典》,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2頁。。還有觀點主張,應該以被組織賣血者的全部環(huán)節(jié)都完成作為組織行為的完成,即從有了指標到被組織者“獻血”的全部環(huán)節(jié)完成。若只是引領(lǐng)、運送到地點或者在抽頭所得等環(huán)節(jié)時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能繼續(xù)下一環(huán)節(jié)即終止行為,就是犯罪的未遂③黃京平:《危害公共衛(wèi)生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頁。。試看以下幾種情形:
例一:被告人A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本市某獻血點出賣血液,在涉案人員抽血完畢,正在分贓的時候,被民警當場抓獲;
例二:被告人B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本市某獻血點出賣血液,在涉案人員正在分批接受抽血的時候,被民警當場抓獲;
例三:被告人C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本市某獻血點出賣血液,在涉案人員辦理好相關(guān)手續(xù)并在等待抽血的時候,被民警當場抓獲;
例四:被告人D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本市某獻血點出賣血液,在被告人D向涉案人員發(fā)放登記表格、排隊辦理相關(guān)抽血手續(xù)的時候,被民警當場抓獲;
例五:被告人E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本市某獻血點出賣血液,在被告人E和涉案人員剛到獻血點的時候,被民警當場抓獲;
例六:被告人F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本市某獻血點出賣血液,在被告人F帶領(lǐng)涉案人員從約定的集合地點前往獻血點的途中被民警當場抓獲;
例七:被告人G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本市某獻血點出賣血液,在約定的集合地點,當被告人G收取獻血者的手機、身份證后,欲前往獻血點進行賣血活動的時候,被民警當場抓獲。
以上七例情形均來自過去五年以來筆者所在地區(qū)司法實務中的真實案例①此外,還有一些案例如被告人帶領(lǐng)賣血者到了獻血點后發(fā)現(xiàn)此點被撤銷,換另一個地點,被告人聯(lián)系好后正準備去下一個點便被抓獲;如被告人帶領(lǐng)賣血者在獻血點附近徘徊等待時機進去時被抓獲等。但這些情形基本都可以視為尚未到達獻血點,可歸納進案例七情形之中。,并且是按照案件起訴至法院的時間順序編排。令筆者驚異的是,上述七種情形下,公訴機關(guān)對被告人均以非法組織賣血罪既遂向法院提起公訴。如果認為公訴機關(guān)指控的上述七種情形均為犯罪既遂是妥當?shù)模瑒t可以推導出的結(jié)論是,公訴機關(guān)認定該罪的既遂標準便是被告人的組織行為實施完畢②當然,反對者可以認為,公訴機關(guān)認定該罪的既遂就是以上述第七種案例情形是否出現(xiàn)為標準。由于實踐中尚未出現(xiàn)比上述第七種案例更早的情形而被抓獲歸案的非法組織賣血案,但如果真的出現(xiàn)了,說不定也會等到上述第七種案例情形出現(xiàn)再實施抓捕。。實踐中,被告人通常是在網(wǎng)絡上發(fā)布有償賣血的信息,然后通過手機短信、QQ、微信等方式進行聯(lián)系,當被告人聯(lián)系并確定好賣血者人數(shù)之時,其實質(zhì)上已經(jīng)完成了組織行為,按照上述公訴機關(guān)的標準,非法組織賣血行為為既遂。在這樣的前提下,后續(xù)的諸如是否至約定的地點集合,是否前往獻血點以及是否可能進行“獻血”等環(huán)節(jié)的有無均不影響該罪既遂的認定。
但事實上,當一個行為被作為犯罪處理,其嚴重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險理當通過該行為予以征表。在現(xiàn)實生活中,當行為人意欲非法組織他人賣血,在聯(lián)系并確定好賣血者人數(shù)之時,該行為是否就產(chǎn)生了嚴重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險呢?犯罪(既遂)的認定是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在認定犯罪,特別是犯罪既遂時,拋開行為人的主觀目的等因素也是不全面的。對于非法組織賣血罪而言,如果說行為人意欲非法組織他人賣血,在聯(lián)系并確定好賣血者人數(shù)之時,該行為就構(gòu)成既遂,則根據(jù)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犯罪構(gòu)成理論,行為人主觀上就在于或者說就是僅追求將賣血者組織起來?同時,筆者通過檢索北大法律信息網(wǎng)中“北大法寶”司法案例數(shù)據(jù)庫發(fā)現(xiàn),過去十年間,全國法院共審理非法組織賣血罪案件327起,其中一審267起,二審55起,再審5起,法院認定為未遂的僅一件,僅占0.31%。該案情大致為被告人G組織社會人員若干至某血液中心出賣血液,當被組織者根據(jù)被告人G的指示到達約定地點時,因被告人G已被公安人員抓獲而未能出賣血液,法院經(jīng)審理后認為被告人G已經(jīng)著手實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①案情詳見(2017)滬0106刑初某號上海市靜安區(qū)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這到底是源于非法組織賣血罪果真不存在犯罪未遂,還是其既遂標準尚未得到確定而所致?對此,筆者認為對非法組織賣血罪的既遂標準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
二、非法組織賣血罪的犯罪類別屬性
對于非法組織賣血罪在犯罪類別上的屬性,大多數(shù)觀點認為其屬于行為犯,如有觀點認為,本罪是行為犯,只要為使他人出賣血液而實施了組織行為,即使被組織者尚未出賣血液,也構(gòu)成非法組織賣血罪的既遂。因此,本罪不存在未遂問題。②周道鸞、張軍:《刑法罪名精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38至839頁。可見,認為行為人只要實施了組織行為就構(gòu)成非法組織賣血罪既遂的觀點,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認為該罪屬于行為犯所致,但問題是,即便如此認為,行為犯是否就不存在未遂?
在形式犯和實質(zhì)犯的概念分類下,有觀點認為,形式犯又稱為舉動犯、行為犯、實施犯。法律規(guī)定只要實施了一定的行為就構(gòu)成犯罪的是形式犯。形式犯與實質(zhì)犯的區(qū)分標準是以是否需要犯罪結(jié)果為構(gòu)成要件,因此形式犯不存在既遂、未遂之分③馬克昌、楊春洗、呂繼貴:《刑法學全書》,上海科學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頁。。在其看來,形式犯對應的便是行為犯,實質(zhì)犯對應的便是結(jié)果犯。對此,筆者認為,即便承認形式犯和實質(zhì)犯的概念分類,法律規(guī)定只要實施了一定的行為就構(gòu)成犯罪的是形式犯,也并不意味只要實施了法律規(guī)定的一定行為就構(gòu)成犯罪既遂。一方面,從文義表述來看,構(gòu)成犯罪與構(gòu)成犯罪既遂是兩個概念。只要實施了法律規(guī)定的一定行為者,便構(gòu)成相應的犯罪,從行為犯或者形式犯的角度來看沒有問題,但構(gòu)成犯罪并非就當然構(gòu)成犯罪既遂,這也應當沒有爭議。另一方面,實施了法律規(guī)定的一定行為就構(gòu)成犯罪,也并不意味該行為不需要任何犯罪結(jié)果。刑罰權(quán)的發(fā)動是基于一個犯罪行為嚴重侵害或者威脅法益這樣一個必要結(jié)果的出現(xiàn)。在結(jié)果無價值論下,行為是否危害社會,只能根據(jù)該行為所引起的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造成的實際侵害或者現(xiàn)實危險的結(jié)果為基礎(chǔ)加以判斷④黎宏:《結(jié)果本位刑法觀的展開》,法律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頁。。即任何犯罪都是由于行為導致的結(jié)果無價值而被科處刑罰,只不過這種結(jié)果可以是實害結(jié)果,也可以是危險結(jié)果,即對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者威脅。所以,當這種結(jié)果沒有出現(xiàn)的時候,即行為并未嚴重侵害或者威脅到法益,則該行為便不得被認定為犯罪,或者起碼不得被認定為犯罪既遂。
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凡是符合刑法分則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不論是實質(zhì)犯的行為還是形式犯的行為,都是對法益產(chǎn)生了嚴重的侵害或者威脅,否則便不值得刑罰權(quán)的發(fā)動。而所謂的行為犯便是“行為構(gòu)成的滿足于行為的最后活動共同發(fā)生,也就是說,不會出現(xiàn)一個可以與之分離的結(jié)果。這些行為的本身就具有了自身的無價值,它們的刑事可罰性不需要以其他別的什么結(jié)果為條件”⑤〔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一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216頁。。筆者認為,此處所指的“刑事可罰性不需要以其他別的什么結(jié)果為條件”應當是指不需要以其他的可以與行為本身相分離的結(jié)果為條件,即行為本身所附帶的結(jié)果,這一結(jié)果便是該行為對法益所造成的嚴重威脅或者危險,否則便只能是犯罪未遂。
此外,在我國刑法理論中,也有觀點認為“行為犯不同舉動犯,二者的區(qū)分在于行為犯有既遂和未遂之分,舉動犯無既遂與未遂之分”①葉高峰:《故意犯罪過程中的犯罪形態(tài)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頁。轉(zhuǎn)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73713.htm,2018-3-22最后點擊。,可能有人據(jù)此認為非法組織賣血罪是舉動犯,因而沒有既遂未遂之分,只要著手實施非法組織賣血行為便為既遂。筆者認為,一方面舉動犯是個不必存在的概念,“行為犯與舉動犯無異”②梁世偉:《刑法學教程》,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頁。轉(zhuǎn)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73713.htm,2018-3-16最后點擊。,即兩者系同一意義。因為行為犯概念系貝林提出,故其在被介紹到日本或我國臺灣地區(qū)時被翻譯為舉動犯或行為犯③林東茂:《刑法綜覽(修訂五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50頁;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頁。,因而有人誤認為舉動犯是不同于行為犯的一個概念,據(jù)此而引起了理論上一定程度的誤解。通過考察舉動犯產(chǎn)生之源頭可見其就是在翻譯中,一詞多譯的誤解結(jié)果。如日本學者大塚仁認為“構(gòu)成要件中,雖然存在像偽證罪那樣,僅以行為人的一定身體動靜為行為內(nèi)容的情況,但大部分都是像殺人罪、盜竊罪那樣,還以發(fā)生一定結(jié)果為必要,前者稱為舉動犯(單純的行為犯),后者為結(jié)果犯”④(日)大塚仁:《刑法該說(總論)》,有斐閣1992年改訂增補版,第121頁。轉(zhuǎn)引自:張明楷:《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修訂版,第346頁。。在日本學者木村龜二主編的《刑法學詞典》關(guān)于犯罪的種類中,也是從形式犯和實質(zhì)犯、侵害犯和危險犯、舉動犯(或譯行為犯”)和結(jié)果犯、即時犯和繼續(xù)犯與狀態(tài)犯等角度進行分類。⑤(日)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顧肖榮等譯,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3月第1版,第157頁。此為其無存在之必要理由之一。
另一方面,認為舉動犯就是行為人一著手實施犯罪行為就構(gòu)成犯罪既遂,主要在于“一是原本為預備性質(zhì)的犯罪構(gòu)成,如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罪等,本是預備性質(zhì)的行為,由于涉及犯罪性質(zhì)嚴重,一旦著手實際實行危害很大,便將其提升為實行行為,并規(guī)定為舉動犯;二是教唆煽動性質(zhì)的犯罪,如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由于其嚴重的危害性,因而也把它們規(guī)定為舉動犯。舉動犯是著手實行犯罪就構(gòu)成既遂,因而其不存在犯罪未遂問題,也就沒有既遂與未遂之分”⑥高銘暄、馬克昌、趙秉志:《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頁。。但上述觀點有待質(zhì)疑:首先,任何犯罪的實施行為都有一個過程,只不過這個過程的時間長短不同。而即便認可所謂的舉動犯概念,其實施行為也應當有一個過程,一個相對行為犯較短的過程。一個準備威脅或侵害法益的行為,剛啟動就意味著犯罪既遂,可以說是很難達到威脅或侵害法益而嚴重到被刑法所評價為既遂的程度,甚至難以被刑法評價。其適例不僅立法中,實踐中也是很難據(jù)此而認定。同時也不利于行為人積極中止犯罪①也有觀點認為舉動犯可包括在廣義的行為犯中,其不僅存在著犯罪的既遂、預備和中止形態(tài),而且也存在著犯罪的未遂形態(tài)。參見林亞剛:《刑法教義學(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頁。。其次,從實務角度看,如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規(guī)定的組織領(lǐng)導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罪,也并非行為人一著手“參加”就構(gòu)成既遂。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規(guī)定:“對于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的組織,沒有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或者受蒙蔽、脅迫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的組織,情節(jié)輕微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可見,即便“著手”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但行為人若沒有實施其他違法犯罪行為,就不構(gòu)成犯罪,當然也就不存在犯罪既遂②湯道剛、曾賽剛:《舉動犯芻議》載《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5期。。所以,舉動犯概念不僅在立法上不存在,其與我國的司法實踐也不相符。所以,舉動犯之概念無存在之必要。
可見,行為犯作為與結(jié)果犯對應的一種犯罪形式,盡管其無需以侵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為必備要件,但仍然需要至少發(fā)生危險結(jié)果。即行為犯依然需要一定侵害或者威脅法益的結(jié)果發(fā)生為必要,只不過行為犯“不以行為在外界產(chǎn)生一定變動或影響為必要”③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頁。。所以,“行為犯依然存在結(jié)果,只是這種結(jié)果與行為同時發(fā)生,不需要認定因果關(guān)系而已”④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第5版,第169頁。。因此,行為犯的處罰根據(jù)依然是與行為同時發(fā)生的結(jié)果。如果行為犯著手實施行為,但行為未完成或者完成時尚未達到法律要求的一定程度的危險結(jié)果,就應當以犯罪未遂論處。當然,行為人還可以有犯罪預備、中止形態(tài)。⑤林亞剛:《刑法教義學(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頁。
綜上,非法組織賣血罪屬于行為犯理當無太大爭議,只要非法組織賣血行為已經(jīng)完成,便滿足了該罪構(gòu)成要件中的行為本身對法益所造成的嚴重威脅或者危險,否則便可能是犯罪未遂。但如何理解非法組織賣血行為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三、非法組織賣血罪的客觀行為解讀
理論和實踐中之所以對非法組織賣血罪的既遂產(chǎn)生諸多爭議,除了在行為犯是否存在未遂這個問題之外,更多的則是集中在如何理解非法組織賣血罪的客觀行為上。
1.“非法”不具有實體意義
我國刑法分則條文大量使用了“非法”的概念與表述。其原因主要有:其一,立法者在沒有必要時也使用了“非法”概念;其二,我國的刑法典分則規(guī)定了大量的行政犯,而行政犯都以違反行政管理法規(guī)為前提,于是出現(xiàn)了大量的“非法”之類的表述;其三,我國的四要件犯罪論體系,沒有區(qū)分違法與責任,違法由四個要件綜合性決定,但四個要件只是對犯罪的描述,而缺乏評價概念。為了不致處罰合法行為,便不得不特別強調(diào)行為本身的非法性,從而導致“非法”概念的增加。可見,刑法分則中的“非法”概念,有些是必要的,也有些是多余的。經(jīng)過梳理后,對于“非法”的用法,大體而言有以下四類情形:(一)對違法阻卻事由的提示;(二)對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表示;(三)對行為非法性的強調(diào);(四)已有表達的同位語。①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頁。
對于非法組織賣血罪中的“非法”,筆者認為,其是對行為非法性的強調(diào)。即該罪中的“非法”僅具有語感上的意義,既不是構(gòu)成要件要素,也不是特別的違法性要素,僅僅只是對組織賣血行為非法性的一種強調(diào),強調(diào)該行為對行政管理法規(guī)和刑法的違反性。目前唯一一部對血液管理進行規(guī)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簡稱《獻血法》)第二條規(guī)定,國家實行無償獻血制度。第十一條規(guī)定,無償獻血的血液必須用于臨床,不得買賣。血站、醫(yī)療機構(gòu)不得將無償捐獻的血液出售給單采血漿站或者血液制品生產(chǎn)單位。該法第十八條進一步規(guī)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wèi)生行政部門予以取締,沒收違法所得,可以并處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非法采集血液的;(二)血站、醫(yī)療機構(gòu)出售無償獻血的血液的;(三)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的。可見,只要存在有償出售血液的行為均違反了《獻血法》的規(guī)定。一旦賣血,則必定是違法的,除了醫(yī)療機構(gòu)在診療過程中向病患輸入可以收取費用,以及根據(jù)《獻血法》第六條規(guī)定的國家機關(guān)、軍隊、社會團體、企業(yè)事業(yè)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動員和組織本單位或者本居住區(qū)的適齡公民參加獻血之外,不可能存在違法阻卻事由。但該條規(guī)定的是“組織參加獻血”,并非是“組織參加賣血”。因此,非法組織賣血罪中的“非法”,只是為了宣示組織賣血行為的非法性,不具有實體意義。
2.“組織賣血”應作行為整體理解
根據(jù)《獻血法》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的規(guī)定,無償獻血的血液必須用于臨床,不得買賣,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的應予以取締,沒收違法所得,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不應當有爭議的是,非法組織賣血罪,從其客觀構(gòu)成要件看,即違反法律規(guī)定,實施了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的行為。所謂組織,是指采用動員糾集、安排布置、發(fā)令調(diào)度等方法,使分散的個人有秩序地進行某種活動②周光權(quán):《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48頁。,非法組織賣血中的組織可以理解為行為人采取包含引誘、雇傭、招募、糾集、串聯(lián)、欺騙等手段,組織、指揮、領(lǐng)導并安排他人或者控制他人進行出賣血液的活動③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4頁。。由于組織行為的具體方式法律未作限制,所以也可以包含利用金錢誘惑、欺騙、慫恿等。值得研究的是,該罪中的組織賣血行為應理解為由“組織”行為+“賣血”行為構(gòu)成,還是將“組織賣血”行為做整體理解?
由于行為犯作為與結(jié)果犯對應的一種犯罪形式,盡管其無需以侵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為必備要件,但仍然需要至少發(fā)生危險結(jié)果,而行為犯的這種不以行為在外界產(chǎn)生一定變動或影響為必要的結(jié)果也是與行為同時發(fā)生的。因此,行為犯是因為其行為的實施對法益產(chǎn)生了嚴重的侵害危險,才需被刑法規(guī)制。所以,屬于行為犯的非法組織賣血罪中的構(gòu)成要件行為也應作此理解。如果將非法組織賣血罪中的客觀行為理解為“組織”行為+“賣血”行為的疊加,按照行為犯的特征,則當一個行為(“組織”)一經(jīng)實施完畢,就已產(chǎn)生了對非法組織賣血罪保護法益的侵害危險,便可以認為是構(gòu)成犯罪既遂。但事實上,當一個行為被作為犯罪,甚至是犯罪既遂來處理,其嚴重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險理當通過該行為予以征表。在現(xiàn)實生活中,當行為人意欲非法組織他人賣血,在其通過實施聯(lián)系并確定好賣血者人數(shù)等組織行為之時尚且不足以對非法組織賣血罪的保護法益產(chǎn)生嚴重的危險。同時,故意犯罪(既遂)的認定應當是主客觀相一致的。在認定犯罪,特別是犯罪既遂時,若客觀上行為已經(jīng)造成了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險,那么行為人在主觀上就應當認識到其行為已然造成的上述結(jié)果。同時,在故意犯罪中拋開行為人的主觀目的等因素的考量也是不全面的。“行為是否發(fā)生了行為人所追求的、行為性質(zhì)所決定的犯罪結(jié)果。這一標準適用于實害犯,也適用于危險犯”①周光權(quán):《危險犯的認定》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3月2日。。非法組織賣血罪屬于行為犯,同時也屬于抽象危險犯②陳洪兵:《公共危險犯解釋論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頁。,行為人主觀上所追求的應當是被組織者賣血成功并收取費用,如果這種結(jié)果發(fā)生的可能性程度很小或者尚不存在,便不應當認定為犯罪,起碼不應當是犯罪既遂。
因此,非法組織賣血罪中的組織賣血行為,不能理解為僅實施“組織”行為即可,但也無須等到“賣血”行為的完成,更不是“組織”行為和“賣血”行為的疊加,而應作行為整體理解,即領(lǐng)導、策劃、指揮、動員、拉攏、聯(lián)絡、引誘、招募、介紹并安排他人或者控制他人進行出賣血液的活動③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4頁。。
四、非法組織賣血罪既遂標準的認定
對于犯罪既遂的概念,世界各國大多沒有通過立法例對其予以規(guī)定,我國現(xiàn)行刑法也一樣,而是通過刑法理論予以解釋。綜觀中外刑法理論中關(guān)于犯罪既遂的解釋,大體上可分為以下主張:一是“結(jié)果說”④如我國國內(nèi)學者持此觀點,其認為犯罪既遂指行為人著手實行犯罪并造成了危害結(jié)果的情形。周光權(quán):《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頁;林亞剛:《刑法教義學(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頁。,二是“目的說”,三是“構(gòu)成要件說”。其中“構(gòu)成要件說”認為“當犯罪完全實現(xiàn)刑法分則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時,是為‘既遂’”⑤[意]杜里奧·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學原理》(評注版),陳忠林譯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頁。,這是中外刑法理論中關(guān)于犯罪既遂較為通行的觀點,即行為人著手實施犯罪行為具備了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該種犯罪構(gòu)成要件全部要素的情況⑥高銘暄、馬克昌、趙秉志《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頁;陳興良:《教義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89頁;劉憲權(quán):《刑法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頁。。如前所述,凡是符合刑法分則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不論是實質(zhì)犯的行為還是形式犯的行為,都是對法益產(chǎn)生了嚴重的侵害或者威脅這樣的一個結(jié)果。結(jié)果犯的犯罪既遂是發(fā)生了構(gòu)成要件結(jié)果的情形,而行為犯的犯罪既遂則是由于行為人著手實施的犯罪行為本身也具備了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該種犯罪行為對法益所造成的嚴重威脅或者危險結(jié)果的情形。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關(guān)于犯罪既遂的主張,結(jié)果說和構(gòu)成要件說是一致的。同時,構(gòu)成要件說認為的“當犯罪行為完全具備刑法分則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全部要素”情形較為抽象,其實質(zhì)依然需要通過構(gòu)成要件中的行為和結(jié)果兩個要素來具體解釋。因此,在將構(gòu)成要件結(jié)果解釋為實害結(jié)果和危險結(jié)果的情況下,筆者認為結(jié)果說更加便于實踐中的司法認定。在非法組織賣血罪犯罪既遂的司法認定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每個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均有刑法要保護的法益①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一切犯罪之構(gòu)成要件系針對一個或數(shù)個法益構(gòu)架而成。因此,在所有之構(gòu)成要件中,總可以找出其與某種法益的關(guān)系。因之,法益可謂所有客觀之構(gòu)成要件要素與主觀構(gòu)成要件要素所描述之中心概念,準此,法益也就成為刑法解釋之重要工具”②林山田:《刑法特論(上冊)》,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版,第6頁;轉(zhuǎn)引自:李立眾,吳學斌:《刑法新思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頁。。所以,法益具有作為犯罪構(gòu)成要件解釋目標的功能,在解釋具體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及既遂形態(tài)時,必須明確刑法規(guī)定該罪是為了保護何種法益并以此為指導。一般認為 ,非法組織賣血罪的保護法益為國家對血液采集、供應的管理秩序。但有觀點認為,非法組織賣血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國家血液采集、供應的管理秩序和公民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③高銘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 572頁。。由于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條第二款規(guī)定,有前款行為,對他人造成傷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的規(guī)定,即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因此,筆者認為公民的身體健康不在本罪的保護法益范圍之內(nèi)。作為行為犯的非法組織賣血罪的客觀構(gòu)成要件是行為人違反法律規(guī)定,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其犯罪行為導致了該罪所保護的法益出現(xiàn)了危險結(jié)果方可被認定為犯罪既遂。
其次,對于著手實施犯罪行為的判斷應堅持實質(zhì)的客觀說立場,參照行為人對犯罪進程的預設(shè),以一般人標準對行為加以定性,將主客觀要素一起作為認定行為越過預備階段進入實施階段的門檻,從而將不符合實質(zhì)危險標準的行為認定為犯罪預備可能性④吳昉昱:《論故意犯罪的實行行為著手》載《科學經(jīng)濟社會》,2015年第1期。。本罪的客觀行為是非法組織他人賣血,當行為人開始實施策劃、指揮、動員、拉攏、聯(lián)絡、引誘、招募、介紹等一系列組織行為,但未使被組織者產(chǎn)生賣血意愿及行動,可以認為行為人組織他人賣血行為尚未造成該罪所保護法益出現(xiàn)實質(zhì)危險,即行為尚未越過預備階段進入實施階段的門檻,只能認定為犯罪預備。只有當行為人實施的非法組織行為得到被組織者的積極回應,并具備了賣血的意愿及行動之際,方可認為行為人的非法組織賣血行為已然著手。
再次,盡管行為犯無需將危害結(jié)果作為犯罪構(gòu)成要件,也不必將實際完成實施行為作為犯罪既遂的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行為人一著手實施該罪行為,即成立犯罪既遂。行為犯的既遂形態(tài),也有一個從著手實施的程度較低行為向完成程度較高行為的發(fā)展過程。但也并不要求都必須達到實施行為完成的程度才可認定為既遂,而是要達到刑法規(guī)定的該罪所保護法益被侵害或者遭受危險的程度,即使行為人尚未完全實施完實施行為,也應以該罪的犯罪既遂論處⑤林亞剛:《刑法教義學(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頁。。因此,非法組織賣血罪不能以實施行為一著手就認定為犯罪既遂,但也無需等到被組織者的血液被抽取后才被認定為既遂,而應以行為人將被組織者從零散的狀態(tài),通過實施策劃、指揮、動員、拉攏、聯(lián)絡、引誘、招募、介紹等一系列組織行為,將被組織者統(tǒng)一到獻血點辦理完畢所有獻血手續(xù)為標準。即:行為人將屬于他的組織賣血行為全部實施完畢,為被組織者做好了只要等著被“抽血”即可的所有準備行為。因為,行為人的行為至此已經(jīng)全部結(jié)束,后續(xù)的行為就已經(jīng)不屬于行為人掌控的范疇。簡而言之,非法組織賣血罪應當以行為人將被組織者組織到能夠直接“卷起袖管被抽血”的狀態(tài),才可認定為犯罪既遂。
至此,從以上對于非法組織賣血罪的客觀構(gòu)成要件及其犯罪既遂的論述可見,本文開頭所引案例一、二、三情形均應被認定為犯罪既遂,例四、五、六和七應當以犯罪未遂論。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分則中有眾多的非法組織類犯罪,其中類似于非法組織賣血罪行為構(gòu)成的組織類犯罪諸如組織賣淫罪以及強迫賣血罪和強迫賣淫罪等,其犯罪既遂標準的認定也應參照非法組織賣血罪的既遂標準。如組織賣淫罪的既遂無需賣淫女實際和嫖客發(fā)生性關(guān)系,只要行為人通過招募、聯(lián)絡等組織行為,在賣淫女與嫖客之間建立了隨時發(fā)生性關(guān)系的現(xiàn)實可能性即為既遂。若行為人招聘、培訓好賣淫女,并讓賣淫女一切準備就緒,在尚未開始“營業(yè)”之前被人舉報而被抓的,應以犯罪未遂論。同樣道理,強迫賣淫罪的既遂也無需被強迫著實際和嫖客發(fā)生性關(guān)系,但也并不意味著行為人采取暴力、威脅等方式就屬于既遂,而是要看強迫行為是否達到了被強迫者主觀上已經(jīng)被迫同意去賣淫,且客觀上具有和嫖客發(fā)生性關(guān)系的現(xiàn)實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