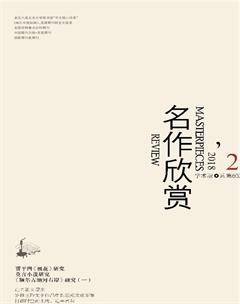傳統與困境
摘 要: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以女主角艾斯普蘭莎為代表的黑人女性身上具有典型的墨西哥傳統文化的身份特征。步入芒果街后,在西方“白人”文化的沖擊下,黑人女性們感受到了差異,并激發了她們身份意識的覺醒。雖然她們選擇了不同方式重塑身份,但她們的重塑都面臨同一個困境。
關鍵詞:女性 身份 傳統 重塑 困境
“女性”作為此研究的范疇,有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居住在芒果街上、跨越文化出身的同種性類的、擁有了身份意識且強烈需求身份重塑的墨西哥裔女性。具體而言,芒果街和墨西哥裔分別是區域性和類屬指稱,指生活在美國底層的缺乏“話語權”的被邊緣化的美國少數族裔的墨西哥人;而其中的女性又是“邊緣化”中被“邊緣化”的一個同質的團體。而此類“女性”又具備兩個重要特征:“跨文化”“身份覺醒及重塑”。跨文化促使了女性身份的覺醒,身份覺醒和重塑又基于本族文化和白人中心文化的碰撞。據此前提,那些身處傳統墨西哥文化,雖然認識到被邊緣的身份卻依然接受的老一代人(如艾斯普蘭莎的嬸嬸魯普)以及不愿脫離本族文化的人(如不學英語的瑪瑪西塔),不屬于此分析范疇。艾斯普蘭莎、莎莉(Sally)、阿里西婭(Alicia)等具有抗爭和反叛精神的女性隸屬此范疇,將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一、傳統身份特征
以艾斯普蘭莎為代表的女性身份意識的覺醒,首先體現在對墨西哥傳統文化中女性身份的清醒認識。這種認知既來自于親身經歷,也來自于對芒果街上女性現狀的觀察。
(一)女性作為男性暴力的犧牲品
在芒果街上,以男人為中心的傳統家長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不擇手段地確保女性的依賴和馴服。這些手段主要體現在對女性身體的暴力,如強奸、性攻擊及家庭暴力等方面。女主角艾斯普蘭莎在《紅色小丑》(Red Clowns)一章中講述了她被一群男孩性侵犯。她對好朋友莎莉說:“莎莉,我不喜歡他們碰我。”在《第一份工作》(The First Job)中遭遇老板的強吻,“他雙手扳著我的臉,強吻了我的嘴唇好長時間”。莎莉在《猴子花園》(The Monkey Garden)中也遭到一群男孩的性侵犯,與艾斯普蘭莎不同的是她“欣然”接受了,“其中一個小男孩說,莎莉要想拿回鑰匙必須把他們挨個親吻一遍,莎莉剛開始假裝很抗拒,但最后她欣然同意了”。在傳統文化中,芒果街上的女性被定義為男性控制——“性壓迫”的犧牲品。
(二)女性作為家庭體系的依附物
在家長制的墨西哥文化中,男人處于主導地位。這種地位的差異轉換成了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分化,通過依附關系女性被建構為攀附于男性的所有物,而男性隱含地要為這種關系負責,即家長。而女性并不是簡單地置于家庭里,相反,正是在作為親緣結構的一種結果的家庭里,女性之為女性在男人的主導之下才被定義,所以男性對女性擁有管理權和使用權。如《周二喝可可和木瓜汁的拉菲娜》(Rafaela Who Drinks Coconut & Papays Juice on Tuesday)中的拉菲娜,周二她丈夫出去打牌時會把她鎖在公寓里,因為她太漂亮怕她逃跑。在這里,拉菲娜已非獨立的個人,完全淪為丈夫的所有物,受其管教和支配。作為妻子的女性如此,為人女兒亦如此。在家長制的社會里,如果一個家庭失去了母親,往往不是由父親而是由最年長的女性去擔負起撫養弟妹的責任,如《看見老鼠的阿里西婭》(Alicia Who Sees Mice)中的阿里西婭,在母親去世后肩負起了撫養弟弟妹妹的重擔,“阿里西亞是家里最年長的,她的工作就是早點起床為弟弟妹妹烙玉米餅”,而父親僅扮演管理者和主導者的角色。
二、身份覺醒及重塑困境
(一)身份覺醒關鍵詞之語言
語言是人類重要的交流工具,是人們進行有效溝通的主要方式;芒果街上的女性不能用英語進行有效溝通或根本不與人交流,所以總是處于社會最底層。英語溝通能力的缺失以及所產生的困擾始終貫穿于整部小說。在《米飯三明治》(A Rice Sandwich)中,艾斯普蘭莎為了能夠在學校食堂吃午餐,哀求母親為她向老師寫一張便條說明情況:
親愛的修女教員:
請讓艾斯普蘭莎在學校餐廳吃午飯,因為她住得很遠,來回往返容易疲勞。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樣,她瘦骨嶙峋。上帝保佑,她不要暈厥過去。
感激你的, 科爾德羅夫人
但母親口語式的、孩子氣的表達毫無說服力。因此,修女看完信后立刻反駁道,她們家離學校僅有四個街區(或許只有三個),而且羞辱性地讓艾斯普蘭莎站在書盒子上指向她們家那丑陋的、連乞丐都不愿意進入的三層公寓樓。自己的親身經歷及周圍鄰居的境遇,使艾斯普蘭莎明白,不懂或是不能很好地掌握語言導致了弱勢的形成,如能駕馭英語將會使自己增添力量,改變身份。
(二)身份覺醒關鍵詞之差異
除了交流功能以外,語言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本族文化和思想的載體。而處于本族語(西班牙語)所構建的文化傳統中,墨西哥裔的女性們是沒有強烈的身份覺醒意識的,因為她們“身在此山中不識真面目”。進入美國白人文化后,隨著英語學習的深入,使得受本族文化所壓抑的女性體驗到了異質文化中紛繁復雜的多樣性。在白人文化中讓她們迷惑的身份問題,產生了一種持久的影響,使她們的視野不再那么狹隘了。差異讓她們了解了她們之前不知道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幾乎涵蓋了她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們要重塑自己的身份。
(三)身份重塑困境
艾斯普蘭莎一開始便意識到了語言的力量,她一心想通過寫作的方式重塑自己的身份。在《生辰不吉》(Born Bad)中,她去看望生病的嬸嬸魯普并讀了一首她自己寫的詩,魯普以一個疲憊的聲音說道:“艾斯普蘭莎,你一定要堅持寫作;寫作可以讓你獲得自由。”雖然當時她并沒有完全理解嬸嬸的意思,但通過身邊一系列的事件,讓她清醒地認識到,有效的語言溝通(英語,“白人的語言”)可以讓她脫離芒果街獲得自由,擁有自己的房子。與艾斯普蘭莎有著相似志向的阿里西婭則希望通過讀書、上大學(學習“白人”文化)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因為她不想像她母親那樣在小工廠和廚房中度過一生。富有叛逆精神的莎莉為了擺脫父親的家暴與管教,選擇了輟學結婚,依靠別人來逃離。
三位主要研究對象雖然以不同的方式(寫作、讀書、結婚)來重塑身份,但她們都面臨同一個困境:離開本族文化的傳統,受到白人“中心”文化的沖撞,原始身份的存在方式被白人文化擊得粉碎,她們需要建構新的存在方式;而這一新的身份是什么?文化特征是什么?她們并不清楚。在重塑中,她們是以白人文化的標準和本族男人的身份來定位自身的,即“他者”,她們并未跳出“中心——邊緣”“男性——女性”二元對立的身份困境。因此,在《三姐妹》(The Three Sisters)中,其中一個人預言式地告訴艾斯普蘭莎,“當你離開的時候,記住你要為他人而返回。這是一個‘圈,懂嗎?你將永遠是艾斯普蘭莎;你永遠屬于芒果街;你無法抹去你所知道的;你不能忘了你是誰?”以艾斯普蘭莎為代表的女性最終還是要回歸的,但是要以什么樣的身份回歸?回歸后還要幫助那些沒有出去的人,“他們不知道我的離去是為了回歸,為了那些不如我的人,為了那些出不去的人”。這又會是一種怎樣的“圈”(A circle)。文章在此留下了懸念,也是對身份重塑困境的一個再思考。
三、結語
身處傳統文化中,女性們雖有很多的無奈,卻擁有一套既定的體制、一個被定義的身份符號;白人文化的沖擊,使她們原有的身份出現了危機。語言的力量讓她們感受到了差異,差異喚醒了她們身份缺失的意識。然而,構建新的身份并不是一路坦途,游離于兩種文化之間——想要擺脫傳統文化卻無法被“中心”文化認可,又無法完全回歸固有文化,由此便產生了身份困境。
參考文獻:
[1] Sandra Cisnero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1st Vintage Contemporaries Ededition) [M]. The U.S.A: VintageVintage
Books, 1991.
[2] 羅鋼,劉象愚.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3] 桑德拉·希斯內羅絲.芒果街上的小屋(英漢對照)[M]. 蘇伶童譯.天津: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2010.
[4] 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7年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后殖民女性主義視野下美國奇卡納文學中的“他者”形象研究(編號:17jk0125)階段性成果
作 者:趙小慶,碩士,陜西理工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編 輯: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