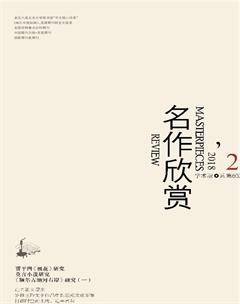城市底層的愛恨和掙扎
摘 要:《直立行走》是80后作家宋小詞發表于《當代》雜志2016年第6期的一部中篇小說,引起了文壇的關注。小說以武漢為城市背景,以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婚姻、家庭為線索,反映了城市底層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掙扎,直擊社會多重現實問題,揭示了人性的復雜性。
關鍵詞:宋小詞 《直立行走》 城市底層
《直立行走》是“80后”作家宋小詞發表于《當代》雜志2016年第6期的一部中篇小說,引起了文壇的關注和好評,該小說獲得《當代》文學拉力賽“中篇小說年度總冠軍”,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1期轉載,獲第六屆湖北文學獎,入圍2016年“《收獲》文學排行榜”。《直立行走》以武漢為城市背景,以一對青年男女周午馬、楊雙福的戀愛、婚姻、家庭為線索,直擊拆遷、城鄉差別、貧富不均等多重社會痛點,反映了城市底層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掙扎,但又沒有一味簡單地為某個階層、某個人群代言,而是能夠體諒到當下生活中每種人的艱辛和自尊。本文試從人物形象、人性、題目“直立行走”的內涵三方面入手,深層探究該小說的豐富內涵和藝術價值。
一、鮮明立體的人物形象
《直立行走》講述了出身于湖北農村的女青年楊雙福與武漢城市青年周午馬“靠吃飯和睡覺”維持了一年半的戀愛關系。為了使周家多拿到三十平方米的拆遷補貼面積,二人鬼使神差地結了婚,經歷了一系列變故后,婚姻破裂。男女主人公形象鮮明立體,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功力。
小說以內聚焦的敘述視角著重刻畫了女主人公楊雙福的人物形象。楊雙福從湖北農村來到武漢,勤勤懇懇地工作,對愛情和美好的生活有著熱烈的向往。她的內心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作為鄉下人的自卑感,在城市青年周午馬面前低聲下氣、唯唯諾諾,喪失了自己獨立的地位和尊嚴。她是一個善良淳樸的人,雖然深知同事所說的現實道理,但并不愛慕虛榮,即便得知了周午馬貧困的家境后也并未失落,而是十分同情,并堅信通過自己的努力,未來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這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物形象,敢愛敢恨,積極進取,但又有幾分可憐,特別是她的悲劇結局,令人同情。
小說的男主人公周午馬是一個可恨又可憐的人物形象。他雖也出身貧寒,但憑借著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和英俊的外貌,在楊雙福面前有著不可一世的優越感,將其玩弄于股掌中,沒有絲毫的真情實感。他放蕩不羈,不思進取,傲慢、虛偽、自私、冷酷無情,令人厭惡。然而,在小說結尾,隨著作者對楊雙福的心理描寫,讀者無不和楊雙福一樣,對周午馬產生了幾分同情——“他跟她在一起的生活和性生活他都要忍受郁悶和壓抑,這是多么的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他狗一樣蜷縮在狗房子里近三十年,受了幾十年的苦楚,總算要由狗變成人了……”{1}說到底,周午馬也不過是個窮苦的底層人民。
楊雙福和周午馬在出身、外貌、性格和人生態度等多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差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是他們婚姻破裂的一個重要原因。首先,在出身方面,楊雙福從湖北農村來到武漢工作,十分渴望在武漢站穩腳跟,但內心一直有一種鄉下人的自卑感,這從小說開篇的“說到底,她還是怕他瞧不起她。其實她心里也知道,無論她怎么努力,他都是瞧不起她的。城里人總是瞧不起鄉下人的”可以看出。而周午馬雖出身貧寒,但骨子里卻透露出作為城里人的優越感,一直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楊雙福。其次,在外貌方面,二人也有著巨大的差距,“周午馬武漢人,身高一米七五,眉眼間有幾分國民男神張國榮的樣兒,這樣的男人哪怕當眾擤個鼻涕吐口綠痰都是帥的”,而楊雙福是“一個農村姑娘,身高不足一米六,相貌平平,因為久坐,腰腹上趴著一圈贅肉,又不懂穿衣打扮”。最后,二人在性格和人生態度方面也有著鮮明的對比:楊雙福勤勤懇懇地工作,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現狀,擁有美好而光明的未來;而周午馬卻放蕩不羈,不思進取,對于生活沒有明確的目標和規劃,得過且過。此外,在對待愛情和婚姻的態度上,楊雙福對婚姻有著熱烈的向往,將婚姻視為莊嚴而神圣的大事,渴望從愛人身上獲得溫暖與關愛:“她想體會被人攙扶的滋味,想感受人與人相偎著的暖意。”而周午馬卻相反,將愛情和婚姻視為兒戲,將楊雙福當作自己的性工具,以一個花花公子的姿態游戲人生。
然而,兩人卻又有著相似之處——作為城市底層,他們出身貧寒,生活艱辛,有著難以言說的悲苦和掙扎,令人同情。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千千萬萬的城市底層,特別是底層青年與命運抗爭的酸甜苦辣。
二、對復雜人性的揭示
《直立行走》對于復雜人性的刻畫可謂是入木三分。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把人格分為三個層次:本我、自我、超我。小說中,關于主人公人格結構中的“本我”和“超我”展現得較多。
首先,本我遵循快樂原則,是人的原始的無意識本能,特別是性本能組成的能量系統,包括人的各種生理需要。小說中共有五處大膽而直露的性描寫,均帶有冷峻蒼涼的意味,絲毫沒有性愛應有的美感、莊嚴感和神圣感。這些性描寫表現出二人的情侶關系似乎只建立在肉欲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尤其是在最后一次性描寫中,二人連日來的苦悶和壓抑因為性愛而一掃而空,精神獲得了巨大的慰藉和放松,但楊雙福很快意識到“她只是他的性工具”,揭示出二人關系的實質。在楊雙福出獄后,周午馬不接她的電話,不想與她再有任何瓜葛,以至楊雙福感慨“他竟如此絕情”,這些描寫都將周午馬的獸性和冷酷自私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其次,超我遵循道德原則,由社會規范、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內化而來,是個體社會化的結果,起著抑制本我沖動,對自我進行監控以及追求完善境界的作用。小說中對于超我的表現主要在結尾,楊雙福出獄后,帶著強烈的恨意找到了周午馬的新家,打算報復周午馬。然而,當她看到周午馬寬敞明亮的新家時,想起了過往的種種,內心突然充斥著對周午馬的理解和同情,放下仇恨,原諒了他。楊雙福放棄了作惡的打算,一方面固然是源于她對周午馬的理解和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源于人格結構中,超我所遵循的道德原則,抑制了本我沖動。
小說中其他人物身上也展現出復雜的人性。比如周母為了多獲得三十平方米的拆遷補償面積,勸說楊雙福與周午馬結婚,為了一己私利利用楊雙福;在丈夫病逝后未及時將其安葬,因為“現在抬出去,半分錢的好也沒撈到”……這些都體現了周母唯利是圖、自私冷酷的特點。此外,樓下阿婆以及周父死后的圍觀群眾也是一種自私冷酷的看客形象。作者在對社會風氣的揭示方面,也獨具匠心。
三、“直立行走”的內涵
小說題目“直立行走”,構思精巧,與內容相契合,有著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可以說,“直立行走”四個字精準地概括了主人公周午馬和楊雙福精神的變化過程。
在《直立行走》中,作者多次將周午馬的生活與狗進行比較,如楊雙福第一次看到周午馬的房間時,“她才頓然明白這不是茅房也不是狗窩,而是周午馬的房”,周午馬“搖搖晃晃徑直去了自己的‘狗窩”,“月亮升起來了,照出了他們的影子,她覺得她跟他就像兩只狗”,以及小說結尾,當楊雙福看到周午馬的新家時,感慨“更重要的是他狗一樣蜷縮在狗房子里近三十年,受了幾十年的苦楚,總算要由狗變成人了”……作者將周午馬比作狗,將他簡陋狹小的房間比作狗窩,頗具諷刺意味。周午馬表面上放蕩不羈、尋歡作樂,其實內心是極度苦悶和壓抑的。這種苦悶和壓抑來源于底層生活的貧困、艱辛、沉重,以及對這種生活的憤慨和強烈的恨意。
在楊雙福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巨大轉變。此前,楊雙福內心一直有一種鄉下人的自卑感,在周午馬面前低聲下氣、唯唯諾諾,抬不起頭來,還討厭自己的生活,仇恨貧窮和自己的出身,自慚形穢,無法坦然地正視和接納自己。這些都使她無法昂首挺胸地做人和在世間行走。而到了結尾,當她出獄以后,她看清了周午馬的真面目,放下了仇恨,擺脫了鄉下人的自卑,以云淡風輕的態度來對待過去,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于是,她終于能夠在世間“直立行走”,這其實是一種自信、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是她思想的巨大轉變。然而,小說晦暗的結局又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懸念和期待。我們不知道楊雙福之后的人生會是什么樣子,但她思想的這一巨大轉變已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和飛躍,對她未來的人生有著重要影響,同時也給讀者以無限的啟迪。
正如作者宋小詞在《在城市的寒冬里蟄伏——〈直立行走〉創作談》中所說:“我要書寫他們,寫他們的艱辛,寫他們的疼痛,寫他們的淚水,寫他們的汗水,寫他們的渴望,寫他們的屈辱,寫他們的精明,寫他們的骨頭,寫他們的壓抑,寫他們的憤怒,寫他們的滄桑,也寫他們的精神,寫他們的被傷害,也寫他們的傷害人。”{2} 作者以冷峻的筆調和一波三折的敘述方式,塑造了鮮明立體的人物形象,對復雜人性進行了深刻的揭示,直面社會現實矛盾,反映了城市底層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掙扎,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和發人深省的思想價值。
{1} 宋小詞:《直立行走》,《當代》2016年第6期,第27頁。(文中相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2} 宋小詞:《在城市的寒冬里蟄伏——〈直立行走〉創作談》,《中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1期,第125頁。
作 者:魯靜,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